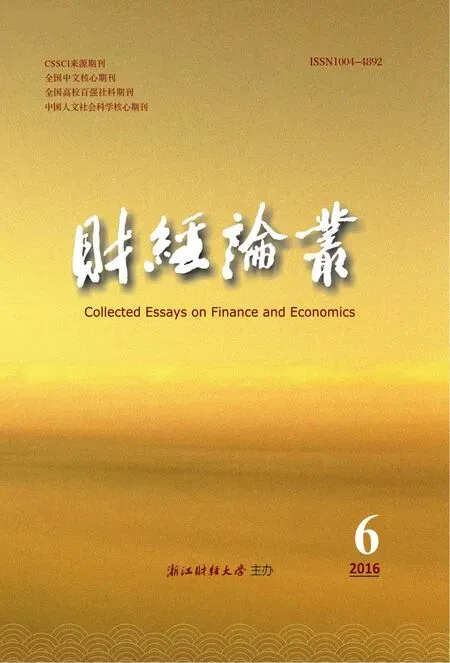信貸配給對農村地區貧困的門檻效應研究
劉艷華,鄭 平
(安徽工業大學商學院,安徽 馬鞍山 243032)
?
信貸配給對農村地區貧困的門檻效應研究
劉艷華,鄭 平
(安徽工業大學商學院,安徽 馬鞍山 243032)
基于信貸配給對農村貧困作用的內在邏輯,運用面板門檻模型剖析了信貸配給對農村地區貧困的非線性作用及其地區差異。研究發現:降低信貸配給程度是減緩農村地區貧困的有效途徑,且具有顯著的門檻特征;隨著農業信貸配給程度由高水平區間向低水平區間的轉換,農村地區貧困與信貸配給程度的關系呈“U”型變化;信貸配給對農村地區貧困的門檻效應具有明顯的區域特征,東部農村地區隨著信貸配給程度的降低,增加信貸有效供給的減貧效應逐漸變弱,中西部農村地區隨著農業信貸配給程度由高水平區間向低水平區間的轉換,農村貧困與信貸配給程度的關系呈倒“U”型變化。
信貸配給;農村貧困;地區差異;面板門檻
一、引 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世界矚目成績,同時,我國政府在農村扶貧脫困方面成績斐然。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由1979年的64%下降至2013年的37.7%。盡管如此,農村地區貧困仍然是“三農”發展所面臨的突出問題。一方面,我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量依然龐大。據統計,按照年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農村扶貧標準,2014年底我國還有8249萬農村貧困人口;而按世界銀行每天生活費1.25美元的計算標準,我國至少有2億貧困人口,且大多分布在農村(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4;中國反貧困發展報告,2014)。另一方面,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的地區分布也不平均。據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的信息顯示,2012-2014年全國592個國家貧困縣區中,東中西部地區分別占7.4%、29.2%和63.3%,其中,90%以上的貧困縣區分布在中西部地區,我國農村貧困分布的區域特征顯著。
農村正規金融對農村居民收入公平分配和減貧具有重要影響,這在孟加拉國的小額信貸項目實踐中得到了驗證。由此,諸多文獻開始關注農村金融與農村貧困之間的關系。這些研究具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研究發現,農村金融發展具有減貧效應。代表性的結論有:Burgess等(2003)發現印度農村金融機構的增量改革可以顯著降低貧困率[1];高遠東和溫濤等(2013)的空間計量分析表明,金融支農政策可以顯著促進本省農村地區的減貧,但這種減貧并不具有空間效應[2];唐青生等(2010)的研究結論暗示,填補農村金融服務空白能夠有效減緩貧困[3];Beck等(2004)研究發現,金融發展可以促進收入公平分配,惠及窮人[4];Remenyi(2000)等人的研究指出,創新微型金融服務項目能夠緩解貧困者的信貸約束,助其解脫貧困[5];胡宗義等(2014)則指出,農村正規金融僅具有當期減貧效應[6];呂勇斌、趙培培(2014)和田銀華、李晟(2014)研究表明,農村金融規模的擴大、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減緩農村貧困[7][8];此外,丁志國等(2011)、楊俊等(2008)、蘇基溶等(2009)均支持農村金融發展具有減貧效應[9][10][11]。另一類研究所得結論則與前述研究截然不同,認為農村金融的減貧效應并不明顯。諸如,呂勇斌、趙培培(2014)的研究結果顯示,農村金融效率的提高不利于降低農村貧困[7];胡衛東(2011)認為,從內生金融的視角看,農村正規金融緩解農村貧困的作用十分有限[12];王小華、王定祥和溫濤(2014)對比分析了貧困縣和非貧困縣農戶信貸的減貧增收效應,發現貧困縣的農戶信貸并未推動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且其影響系數呈倒“U”型分布[13];師榮蓉等(2013)通過金融減貧的門檻效應研究發現,在高收入水平地區,金融發展對貧困具有隱性增速效應[14]。
毫無疑問,已有研究為繼續探尋農村金融的減貧效應提供了有益的啟發,但尚有改進之處。其一,已有研究在探究農村金融與農村貧困的關系和作用規律時,多將農村金融作為整體要素進行考察,而忽視了農村金融對收入分配作用的關鍵傳導變量——信貸配給。實際上,利率管制、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交易成本、金融管制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信貸配給成為農村信貸市場的典型特征。信貸配給由于不能充分滿足貸款申請者的貸款需求,使其生產投資規模低于最優規模,進而對農民經營收入產生不利影響。其二,已有研究大多僅關注農村金融與農村貧困的整體關系,而忽略了二者關系表現在地區層面上的差異。實際上,在農村金融的地區異質條件下,信貸配給對農村地區貧困的作用也可能呈現出地區差異。其三,已有研究在探析農村金融對農村貧困的作用時,大多假設二者存在線性關系,然而二者的關系屬性仍需進一步檢驗。基于此,筆者以1994-2013年的省級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在闡釋信貸配給對貧困作用機制的基礎上,利用面板門檻模型估計信貸配給的農村減貧效應及其地區差異,為構建地區差別化的農村金融體系和制定信貸支農政策提供現實證據和理論依據。
二、信貸配給對農村貧困的作用機理分析
信貸配給是正規金融機構按照信貸標準將信貸資源進行配給的過程。由于抵押擔保機制的缺乏、傳統農業生產的低收益性和弱質性,農戶在申請貸款時經常會受到貸款配給,被配給掉的信貸資金投向了非農產業和城市地區。盡管如此,信貸配給仍然包括貸款供給和貸款約束兩層含義。前者意指,盡管貸款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滿足,貸款供給仍是客觀存在的;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隨著信貸標準的降低,貸款需求被滿足的程度提高,貸款供給規模相應增加。而后者是指,由于貸款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隨著信貸門檻的提高,信貸資金的可獲性減小,貸款供給規模隨之縮小。
信貸配給對農村貧困的作用可以從微觀機制和宏觀表現兩個層面加以闡釋,且兩個層面的作用效果取決于信貸配給程度。信貸配給對農村貧困的微觀作用機制為:在受到信貸配給的情況下,農村貧困者的有效貸款需求不能完全得到滿足,流動性資金受到約束,技術與文化投資及生產條件受到限制,醫療得不到有效保障,勞動生產率無法提高,農村貧困者的收入水平維持在較低水平。隨著信貸配給程度的提高,農村貧困者的生產性投資和生產效率會受到進一步的限制,獲取收入的能力可能降低,其貧困處境會進一步惡化。這種微觀作用機制在宏觀層面上的表現為:信貸配給的存在限制了農村總投資規模,會抑制農村經濟增長,使得農村失業率處在較高的水平,貧困者失業人數較多,收入來源與渠道較少,收入水平較低,貧困者無法擺脫貧困的境地;隨著信貸配給程度的增加,農村投資總量縮小,農村經濟增長放緩,致使農村貧困者的收入相對降低,陷入更大的貧困。因此,無論從微觀作用機制還是從其宏觀表現來看,隨著信貸配給程度的增加,農村貧困者會變得更加貧困。
在經濟和金融發展過程中,信貸配給程度會隨著經濟戰略、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的調整而發生變化,農村貧困程度也將隨之改變。因此,信貸配給程度和農村貧困程度具有階段性相對同步特征(如圖1)。
在農村金融發展的初期,信貸配給程度較高,農村貧困程度嚴重。在這一階段,國家為了實施工業化主導戰略,加速工業發展,農村金融通常會成為農村剩余資金的抽水機。在國家金融偏移政策和資金逐利本性的雙重驅動下,大量的農村剩余資金流向了城市地區和工業領域,嚴重縮小了農村信貸市場的貸款供給規模,加劇了農村信貸資金的稀缺性,提高了農村地區的信貸配給程度。一方面,農村金融機構在提供貸款時,通常會設置較高的信貸門檻,低于這一門檻的農戶,由于無法滿足抵押擔保、收入水平等貸款條件,其信貸需求被排斥在正規金融之外。另一方面,由農村信貸稀缺導致的貸款利率水平上升會導致信貸的價格配給,而將無力承擔高額貸款成本的農戶排除在信貸供給之外。因此,在農村金融發展的初級階段,農村信貸受到抑制,低收入農戶比高收入農戶更加難以獲得貸款服務,導致“馬太效應”,農村貧困以及城鄉收入差距難以得到緩解。

圖1 信貸配給程度與農村貧困程度的變化趨勢
在農村金融的中級階段,信貸配給程度下降,農村貧困得到緩解。在這一階段,一方面,工業化發展至一定規模后,工業自身資金積累能力有所增強,其對農村金融抽水機的功能需求減弱,農村資金外流規模相對減少。另一方面,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增長,農村剩余資金積累不斷增加,農戶在金融機構的儲蓄規模相應擴大;同時,農村金融機構融資業務的不斷創新,也有利于其拓寬融資渠道;相應地,在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利差不變的情況下,這為農村金融機構進行貸款擴張奠定了基礎。此時,農村金融機構降低信貸標準,直接提高了低收入群體的信貸可獲性,有助于改善農村低收入者的福利。
在農村金融的發達階段,信貸配給程度降至較低水平且基本保持穩定,農村貧困程度降至最低。在此階段,農村金融機構的風險甄別和客戶篩選的技術基本成熟,信貸標準維持在較低水平,貧困者與富裕者的信貸可獲性基本無差異,農村貧困維持在較低水平。
三、研究方法和指標選取
(一)研究方法
由第二部分的理論分析可知,隨著農村金融的發展,信貸配給對農村地區貧困的影響呈現階段性特征。在不同的經濟階段,信貸配給程度不同,其與農村貧困的關系表現可能不同。即信貸配給與農村地區貧困可能存在一種非線性關系。Hansen(1999,2000)[15][16]提出的面板門檻回歸方法為筆者探究兩者的非線性關系提供了一種解決途徑。結合前文的理論邏輯,筆者構建了信貸配給程度與農村地區貧困的面板多重門檻模型:

(1)



(二)指標選取與計算
1.農村地區貧困程度(Eng)。農村地區貧困程度是目標模型(1)中的被解釋變量,更是重點考察的變量之一。就已有的研究文獻來看,衡量貧困程度的指標主要包括貧困發生率[17]、貧困缺口、森指數[18]、恩格爾系數和FGT貧困指數[19]等指標。其中,貧困發生率描述的是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反映地區貧困的規模和密度而非貧困強度,其數據雖直觀易算且易獲得,卻未包含導致貧困產生的結構性因素信息。貧困缺口反映的是貧困者的收入與貧困線的差距,可以測度地區貧困的絕對程度和相對程度。該指標的局限性在于:其一,在貧困線和貧困者數量不變的情況下,貧困缺口指標僅與貧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有關,而對其內部的收入分布不敏感;其二,貧困人口的平均收入在統計上數據可獲性較差。森指數雖克服了貧困發生率和貧困缺口的不足,但其計算具有主觀性,且不能較好地滿足轉移性條件[20]。FGT貧困指數雖具有一系列良好的性質,但帶有一定的主觀性,且對數據的可得性要求較高。
而恩格爾系數體現了家庭食物消費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是國際上衡量居民生活水平和貧富程度的通用指標。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地區恩格爾系數越高,則該地區越貧困。與其他指標相比,恩格爾系數具有良好的屬性:其一,該指標屬于非構造性指標,對貧困程度的反映精確且直接;其二,恩格爾系數直觀地反映了家庭的消費效用和收入水平,通過收入水平這一中間指標可以與資本、技術等生產投入要素建立直接聯系,體現結構性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其三,該指標的數據可得性較強。基于此,與師榮蓉等(2013)[14]等的做法相同,筆者選擇恩格爾系數作為衡量農村地區貧困程度的指標。

在計算地區農業信貸配給程度時,筆者選用地區第一產業GDP和地區GDP的比值反映地區農業經濟的貢獻,利用農業貸款與各項貸款總額之比反映農業經濟被配給到的信貸資源。為了避免歧義,這里的信貸資金均為從正規金融機構所獲資金。由于農業貸款統計口徑截至2012年,2013年的信貸配給程度數據采用線性指數平滑法[21]預測而得,預測方法為設定阻尼系數分別為0.2、0.6和0.9,進行三次預測,選擇標準誤差最小時對應的預測值為缺失值的最優預測值。
3.地方財政支農力度(Czr)。該指標采用財政支農比重來衡量,具體等于地方農業財政支出額與地方財政支出總額的比值。由于我國財政預算科目于2007年開始調整,故2007-2013年的農業財政支出用農林水事務支出代替。
4.勞動力投入(Labor)。采用鄉村從業人口數量來衡量。
5.農業化學技術水平(Chemic)。農業化學要素的投入通過影響農業產出進而對貧困程度產生作用。筆者以單位面積施用的化肥和農藥量來表示,具體等于化肥和農藥施用量之和與農作物總播種面積之比。
6.城市化水平(Urb)。該變量為控制變量。城市化水平提升可以通過城鄉交通條件、醫療水平、消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多種影響機制作用于農村地區貧困。筆者以城鎮人口與地區總人口之比代表地區的城市化水平[22]。
因西藏地區的相關數據缺失太多,故未將其納入研究范圍。因此,樣本數據包括除西藏以外的30個省市區,樣本的時間區間為1994-2013年。相關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金融年鑒》、《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歷年《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各省市歷年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網站。
四、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
首先,對面板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以避免因面板數據存在單位根導致的偽回歸。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常用LLC檢驗、Breitung檢驗、IPS檢驗、ADF檢驗和PP檢驗等方法。這些檢驗的原假設均為面板數據存在單位根,但檢驗統計量和檢驗標準的設定互不相同。為避免采用單一方法而產生的缺陷,提高檢驗結論的可靠性,筆者采用上述五種方法來檢驗樣本數據的平穩性。檢驗均采用具有截距項和趨勢項,滯后期的選擇標準為AIC標準。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綜合來看,各變量的原始數據均不能統一拒絕單位根原假設,而其一階差分值在1%的水平下顯著拒絕單位根假設,這說明所有變量的一階差分值都是平穩的。

表1 樣本數據的單位根檢驗統計量及其顯著性
注:d(·)表示變量的一階差分;“*** ”、“** ”和“* ”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下同。LLC和Breitung檢驗結果為t統計量,IPS檢驗結果為W統計量,ADF和PP檢驗結果為Chi方統計量。
其次,為了判斷模型變量之間是否具有共同的隨機性趨勢,需要進一步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分別采用Pedroni檢驗、Kao檢驗和Fisher檢驗,以提高檢驗結果的可靠性。Pedroni檢驗結果顯示,除了維度內檢驗的V統計量不顯著外,其余統計量均顯著通過檢驗,這說明無論是同質面板數據,還是異質面板數據,變量之間均存在協整關系;Kao檢驗的結果也支持了上述結論;且Fisher檢驗結果顯示,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多個協整關系,這表明變量間的作用關系可能是非線性的。基于此,可以利用面板門檻模型進行進一步分析。

表2 Pedroni檢驗結果

表3 Kao檢驗結果

表4 Fisher檢驗結果
(二)面板門檻估計與結果分析
首先,采用Hansen(2000)[16]提出的門檻效應檢驗法確定門檻的個數。具體檢驗中,采用自抽樣法反復抽樣2000次進行仿真和格點搜索方式搜索門檻值,結果報告如表5。可以看出,單重門檻效應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而雙重和三重門檻效應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在95%的置信度下,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對農村貧困的作用具有顯著的門檻效應,其門檻值分別為-2.24、-3.55和-1.99,分別對應農業信貸配給程度10.65%、2.87%和13.67%。

表5 信貸配給對農村地區貧困影響的門檻效應檢驗
其次,采用普通固定效應線性模型和面板門檻模型對變量參數進行穩健回歸,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結果顯示,在固定效應模型中,農業信貸配給程度與農村恩格爾系數顯著正相關,說明信貸配給程度的提高會加劇農村地區的貧困。而其他變量中除財政支農系數不顯著外,勞動力投入、城市化水平和化學要素投入均對農村貧困有顯著的緩解作用。

表6 模型估計結果
在門檻效應模型中,總體上,農村恩格爾系數與農業信貸配給程度仍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與固定效應模型的結論一致。但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農業信貸配給程度處于不同區間,其與農村恩格爾系數的正相關程度有差異。這表明,信貸配給對農村貧困的正向作用更傾向于以農業信貸配給程度為門檻的分段函數關系。即當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小于2.87%時,農業信貸配給程度每增加1個百分點,恩格爾系數便增加0.031個百分點;而當農業信貸配給程度位于[2.87%,10.65%]區間時,其對農村貧困的促進作用相對減小,農業信貸配給程度每增加1個百分點,恩格爾系數增加0.0062個百分點;農業信貸配給程度介于[10.65%,13.63%]區間時,會加劇農村貧困程度,相關系數增加至0.017;而當農業信貸配給程度高于13.63%時,其對農村貧困程度的惡化效應進一步升高,相關系數增至0.031。
基于門檻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得到如下規律:降低農業信貸配給程度有利于緩解農村貧困,且隨著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在不同區間的轉換,農村貧困程度對農業信貸配給程度變化的正向敏感性呈“U”型變化。(1)當農業信貸配給程度處于最高水平區間時,農村貧困程度對農業信貸配給程度變化的敏感性最高。這說明,此時增加農業信貸有效供給,降低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可以最大程度地緩解農村貧困。其原因在于,當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很高時,增加農業信貸的有效供給,農村生產中信貸投入的邊際產出較高,從而加快了農村居民收入和農村經濟的增長速度,此時降低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可以更有效地減除農村貧困。(2)當農業信貸配給程度由高水平區間向低水平區間轉化時,農村貧困程度對農業信貸配給程度變化的敏感性逐級降低。隨著農村金融支農體系的不斷完善和國家對農村經濟建設的戰略反哺,農村信貸供給總量不斷增加,農業信貸配給程度逐步降低,不斷向低水平區間轉換。此時,農業信貸配給程度的降低對農村貧困的緩解程度開始下降。這主要源于邊際遞減規律,即農業信貸投入總量的不斷增加,農村生產活動中信貸投入的邊際產出開始遞減,農村居民收入和農村經濟的增長速度相對放緩,農村貧困的消減速度也逐步減慢。(3)當農業信貸配給程度處在最低水平區間時,農村貧困程度對農業信貸配給程度變化的敏感性又達到最高。隨著農村金融支農功能的不斷健全,農業信貸配給程度也會達到最低。此時,加強農業貸款的供給力度,會更有力地消除農村貧困。其原因主要是,農村金融系統功能的充分發揮,對農村經濟發展的支持比較充分,大幅縮小了農村居民收入的內部差距,貧困者和非貧困者的邊界變得比較模糊,此時增加農業信貸供給,使得相對貧困的農村居民進入了信貸門檻,有利于助其脫貧。
其他變量中,勞動力和化學要素投入的增加、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均對降低農村貧困具有顯著的積極作用,且其降低的程度與固定效應回歸結果大致一致。
(三)信貸配給對農村貧困作用的地區差異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由于農村金融改革的起點和進展不一,農村金融呈現出體系建構參差不齊、信貸市場區域分化明顯和信貸供求關系地區失衡等特征。通過計算1994-2013年農業信貸配給程度的變異系數(圖2)發現,農業信貸配給程度的地區差異呈擴大態勢,從1994年的0.2178增加至2013年的17.0592,尤其是自2002年以來,這種態勢尤為明顯。同樣,農村貧困也呈現出地區差異擴大的趨勢。圖3顯示,恩格爾系數的變異系數由1994年的0.4985升高至2013年的1.2735。與農業信貸配給程度的地區差異變化不同的是,恩格爾系數的波動更為頻繁和劇烈。可見,雖然信貸配給地區差異與農村貧困地區差異均在擴大,但從趨勢判斷,二者的非線性關系可能具有區域特征。
為了探索信貸配給與農村地區貧困關系的地區差異,采用前述方法和分析思路將樣本分為東中西部三個地區,并對每個地區的樣本分別進行了門檻效應估計。估計結果如表7和表8所示。
由表7可知,信貸配給對農村貧困的門檻效應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首先,東中西部三個地區的門檻值不同。東部地區的三個門檻值分別為-6.89、-1.74和-0.16,中部地區的門檻值分別為-2.05、-1.70和-0.18,西部地區則為-2.96、-0.72和-0.14。通過比較發現,三個地區的第一個門檻值存在較大差異,其中,東部地區門檻值最低,而中西部地區的門檻值較高。門檻值的地區差異決定了農村貧困與信貸配給在東中西部地區有不同的關系表現。

圖2 農業信貸配給程度的變異系數變化趨勢

圖3 恩格爾系數的變異系數變化趨勢

地區LnRaRa參數東部地區LnRa<-6.89(Ra<0.10%)0.025???-6.89

表8 其他變量的分地區估計結果
其次,東中西部的農村地區中,信貸配給對農村貧困的作用也顯著不同。東部農村地區,隨著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從高水平區間向低水平區間轉換,降低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對農村貧困的緩解力度逐級降低。在中西部地區,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在從高水平區間向低水平區間轉換過程中,恩格爾系數與農業信貸配給程度由負相關轉為正相關,且正相關系數逐漸變小。這表明,在中西部地區,降低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對農村貧困的緩解幅度呈倒“U”型變化特征。即當農業信貸配給程度位于最高水平區間時,降低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反而會加劇中西部的農村貧困。這說明,當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很高時,中西部農村地區的信貸減貧存在著低效率或無效率。原因可能是,當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很高時,中西部農村貧困者的數量較大,農村金融機構出于資產安全性考慮,會將貸款投放給富裕的農村居民,信貸相對于對緩解貧困的需求已杯水車薪。這說明,當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很高時,在中西部地區發揮財政扶貧的作用可能更有效。當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向低水平區間過渡時,降低農業信貸配給程度開始有效緩解農村貧困,緩解的程度逐步降低。
其余變量中,西部地區財政支農的減貧作用最為顯著,應進一步加大對西部地區的財政支農力度;東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投入對減緩農村貧困的作用依次增強,增加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投入,有利于縮小東中西部農村地區的貧富差距;農藥和化肥等化學要素的施用,對提高中西部地區的農業收入尤為顯著,有利于降低農村貧困;城鎮化對東部農村地區的貧困緩解最為明顯,其次是中部地區,再次為西部地區,應進一步推進各地區的城鎮化進程,尤其是中西部地區。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論文分析了信貸配給對農村貧困的作用機制,運用面板門檻模型分析了信貸配給對農村地區貧困的非線性作用,并進一步分析了這種作用關系的地區差異。
(一)研究結論
第一,總體看來,降低信貸配給程度有助于減緩農村地區貧困。
第二,信貸配給對農村貧困的作用路徑是非線性的,具有典型的門檻特征。隨著農業信貸配給程度由高水平區間向低水平區間的轉換,降低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對農村貧困的緩解程度呈“U”型變化。在農業信貸配給程度最高區間時,增加農業信貸供給,提高農村經濟主體的信貸可獲性,則減貧作用最大;隨著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向低水平區間的轉換,降低農業信貸配給程度的減貧作用逐級減小;當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到達最低區間時,增加農業信貸供給的減貧作用又會達到最大。
第三,增加財政支農以及勞動力和化學要素的投入力度,提高地區城市化水平,具有顯著的農村減貧效應。
第四,分地區來看,信貸配給對農村地區貧困的門檻效應具有區域特征。東中西部地區農業信貸程度的門檻值不同。隨著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從高水平區間向低水平區間轉換,降低東部地區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可以有效緩解該地區的農村貧困,且緩解作用逐級降低;降低中西部地區農業信貸配給程度,呈先惡化農村貧困后緩解農村貧困的倒“U”型態勢。增加西部地區財政支農的力度所產生的減貧效果最明顯;增加中西部農村地區勞動力投入,可以有效縮小與東部農村地區的貧富差距;農藥和化肥等化學要素的投入,可以更為顯著地改善中西部農村地區的農民福利,助其脫貧;城鎮化對東部農村地區起到的減貧效果最為顯著。
(二)政策建議
上述研究結論對我國政府開展支農扶貧具有重要的政策啟示。為了消除農村貧困,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第一,充分發揮農業政策性金融在扶貧開發中的主導作用,創新扶貧減貧的信貸產品,擴大對農村貧困者信貸支持的覆蓋面,大力發展普惠制金融;第二,鼓勵金融機構開展小額信貸業務,發展適合農村低收入群體的信貸業務,提高其信貸可獲性;第三,進一步深化農村金融增量改革,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充分發揮金融支農功能,展現金融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加速器效應,提高農村貧困者的收入;第四,針對信貸減貧效應的地區差異,金融扶貧還應因地制宜、因時制宜,按照不同地區的信貸減貧效應,實施地區差別化的貨幣政策工具和信貸政策;第五,優化農村貧困地區發展的外部環境,加大公共財政的扶貧力度,在積極增加要素投入的同時,降低農村經濟發展的成本,快速推進地區城鎮化發展,努力發揮地區城鎮化對減貧的外溢功能。
[1]Burgess R.,Pande R.. Do rural banks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Indian social banking experiment [J]. STICERD-Development Economics Papers-From 2008, This Series has been superseded by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Public Policy Discussion Papers,2003,95(3),pp.780-795.
[2]高遠東,溫濤,王小華. 中國財政金融支農政策減貧效應的空間計量研究[J].經濟科學,2013,(1):36-46.
[3]唐青生,陳愛華,袁天昂. 云南省貧困地區農村金融服務與網點覆蓋建設的財政金融扶持政策研究[J]. 經濟問題探索,2010,(8):179-184.
[4]Beck T., Demirguc Kunt A.,Levine R. Finance,Inequality,and Poverty: Cross-Country Evidence[M].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4.
[5]Remenyi Joe,Benjamin Quinones.Microfinanc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Case Studies from Asia and the Pacific[M].New York: Pinter Publishers,2000.
[6]胡宗義,唐李偉,蘇靜.農村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的減貧效應——基于PVAR模型的經驗分析[J].統計與信息論壇,2014,(11):52-58.
[7]呂勇斌,趙培培.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反貧困績效:基于2003-2010年的經驗證據[J].農業經濟問題,2014,(1):54-60,111.
[8]田銀華,李晟.金融發展減緩了農村貧困嗎?——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4,(5):22-29.
[9]丁志國,譚伶俐,趙晶.農村金融對減少貧困的作用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1,(11):72-77,112.
[10]楊俊,王燕,張宗益.中國金融發展與貧困減少的經驗分析[J].世界經濟,2008,(8):62-76.
[11]蘇基溶,廖進中.中國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貧困關系的經驗分析——基于動態面板數據的研究[J].財經科學,2009,(12):10-16.
[12]胡衛東.金融發展與農村反貧困:基于內生視角的分析框架[J].金融與經濟,2011,(9):60-64.
[13]王小華,王定祥,溫濤.中國農貸的減貧增收效應:貧困縣與非貧困縣的分層比較[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4,(9):40-55.
[14]師榮蓉,徐璋勇,趙彥嘉.金融減貧的門檻效應及其實證檢驗——基于中國西部省際面板數據的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3,(3):32-41.
[15]Hansen B. 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testing and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9,93(2) ,pp.345-368(24).
[16]Hansen B. E. 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Z]. Boston College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2000.
[17]Seebohm Rowntree,B. Poverty:A Study of Town Life[M]. London:Macmillion and Co. Press,1901.
[18]Sen, A.K. Poverty: 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J]. Econometrics,1976,44(5) ,pp.219-231.
[19]Foster J., Thorbecke E. A class of decomposable poverty measures[J]. Econometrica, 1984, 52(3) ,pp.761-66.
[20]Shorrocks A. F. Revisiting the sen poverty index[J]. Econometrica,1995,63(5) ,pp.1225-30.
[21]Thaler G. J.,Brown R. G. Analysis and Design of Feedback Control Systems: Formerly,Servomechanism Analysis [M]. Mc Graw-Hill,1960.
[22]宋元梁,肖衛東.中國城鎮化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關系的動態計量經濟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5,(9):31-40.
(責任編輯:原 蘊)
A Research on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Credit Rationing upon Poverty in Rural Areas
LIU Yan-hua, ZHENG Ping
(S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2, China)
Based on the internal log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effect of credit rationing on rural poverty,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to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nonlinear interac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credit rationing on poverty in rural area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Reducing the degree of credit ration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relieve poverty in rural areas, and has significant threshold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extent of agricultural credit rationing shifting from the high level interval to the low r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poverty and the degree of credit rationing exhibts a “U” shape change;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credit rationing on poverty in rural areas ha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s the credit rationing degree decreases in eastern rural areas,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increasing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credit gradually weaken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ural areas, with the extent of agricultural credit rationing shifting from the high level interval to the low r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poverty and the extent of credit rationing exhibits an inverted “U” shape change.
credit rationing;rural poverty;regional differences;panel threshold
2015-09-16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71203001);安徽工業大學研究生創新研究基金項目(2014128)
劉艷華(1979-),男,山東新泰人,安徽工業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博士;鄭平(1992-),男,安徽安慶人,安徽工業大學商學院碩士生。
F832.4
A
1004-4892(2016)06-004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