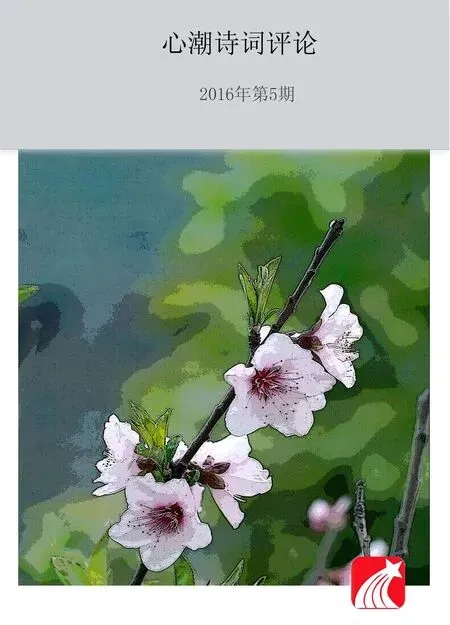淺探聶紺弩詩詞的雜文風格
王家英
淺探聶紺弩詩詞的雜文風格
王家英
聶紺弩晚年以大雜文家畢生的功夫來做舊體詩,所以他的詩,其實就是“詩體雜文”,或曰“雜文體詩”。所謂詩體雜文,就是雜文與詩的結合,用“雜文筆法”,或以“舊體詩詞寫雜文”。它具有詩性特征,詩體形式,但更多地兼備雜文品質,獨具雜文風格。即是說,聶詩是以議論和批評為主,以廣泛的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為主要內容,“革故鼎新,激濁揚清”,具備雜文品質,也就是雜文的那些基本要素、特質在雜文詩中都有反映。它表現為思想內容上的現實性、批判性、諷刺性以及“心靈歌哭”的情感性;寫作方法則是以曲筆、嘲笑、反諷、雙關、暗喻以及幽默詼諧等等藝術手法為主調。本文擬著重就聶詩的現實性、批判性、諷刺性、情感性四個方面作粗淺的探討。
一、現實性
聶翁的“雜文體詩”深深扎根于現實的土壤,將現實生活和從這些生活中產生出來的感受毫無顧忌地表達出來,且創作十分豐富,大約占其舊體詩詞的三分之一。這些詩詞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記錄了他本人以及與他相關的一些同志二十多年來真實的歷史。這段歷史是痛苦的,也是值得我們認真紀念的。”(胡喬木《散宜生詩·序》)有的“不僅反映出了中國整個社會主義時代中,一九五七年——粉碎‘四人幫’前‘左’傾路線統治下光怪陸離的面貌,而且寫出了被折騰的知識分子的掙扎和奮斗,這正是千秋詩史。”(王林書《當代舊體詩論·說“紺弩體”》)這些詩詞涵蓋面廣,遍涉了詩人對上世紀五十年代文藝界的反胡風運動,反右派運動,及以后發展到政界的反右傾運動,“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的觀察與思考。
以寫北大荒勞動生活的《北荒草》為例,53首勞動詩,詩人通過自己對勞動中的具體事情和感受的記錄,來濃縮一個時代的真實歷史。如《鋤草》,詩人借“每回鋤草總傷苗”的描寫,隱諱地傳達了詩人對“反右”斗爭擴大化殃及無辜,把“香花”當成“毒草”一齊鏟除的怨憤。寫出了“鋤草傷苗”、“物理難通”的千古絕唱!
對于“文革”初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亂象,聶翁在給朋友的唱酬應和詩中多有不屑情緒,如“雜花生樹群鶯亂,笑倒先春報信梅”(《贈老梅》),此詩以隱喻曲折的方式,顯示了“文革”對人才的摧殘。
對已故友人的懷念,“從今不買筒筒菜,免憶朝歌老比干”(《挽雪峰》)。詩人以沉痛的感情,對馮雪峰的逝世表示惋惜,同時又對馮一生忠誠革命的高風亮節作了公正的評價。
對自己無端蹲了十年監獄,在《贈周婆》之二中是這樣描述的:“探春千里情難表,萬里迎春難表情。”把探牢說成“探春”,把迎接出獄說成“迎春”。借用《紅樓夢》中的人名說夫人遠道而來探牢迎接,內心感到十分溫暖,而且激動,但更有無盡的苦澀,非語言所能形容。故以“情難表”、“難表情”的反復詠嘆表現自己當時的內心狀態。
對于借政治運動以整人幫兇為樂事的批判與揭露,詩人在《董超薛霸》中寫道:“佶京俅貫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董超薛霸》)董超、薛霸作為“佶京俅貫”的爪牙,以整人為能事,可惡、可恨亦可憐。詩人經歷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飽嘗過董、薛之類小人的苦頭。故借詠《水滸》人物,專為董薛搭上一筆。
以上舉例雖系聶詩現實性雜文詩的冰山一角,已足見聶翁其詩的真實性、針砭性。其筆調大膽潑辣,嬉笑怒罵,自成風格。
二、批判性
上述聶詩的現實性中已現針砭性,這里再次舉例說明之。
一是對封建倫理道德歧視女性的批判。如在《祥林嫂》中他寫道:“人果無魂抑有魂?女人何故屬男人?”“垂死愚氓苦思想,平生俚俗蝕精神”,這些詩句既是對舊中國最底層婦女的同情,同時也是對傳統痼疾的批判。聶翁對封建倫理道德的思考和批判是獨特的、深入的。他對《紅樓夢》悲劇主題和人物命運的評說,是建立在現代人道主義價值觀的基礎上的。“寒光閃處青鋒血,恨比晴顰似更深”(《尤三姐》)昭示的是尤三姐以死對封建社會進行的不屈抗爭。“三軍奪帥情何迫,匹女忘威事可歌”(《鴛鴦》),則是對鴛鴦的反抗精神給予最熱情的歌頌。“誰堪白璧青蠅玷,其奈紅顏薄命何”(《妙玉》),更是無情地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罪惡,充分反映了詩人對被壓迫婦女的同情。
二是對愚弱的國民性的批判。詩人在《題示眾》詩中寫道:“愚弱國民示眾材,圍觀不下百人來。何因示眾無人曉,嘲弄千言告示牌。”他認為作為示眾材料的人,是“愚弱國民”;作為圍觀者,同樣也是“愚弱國民”。因為被“示眾”者犯了什么罪,是什么原因示眾,沒有一個人明白。這說明了民眾的愚昧,也是對告示牌的嘲弄,更是對愚弱國民性的批判。
三是對奴性與皇權的批判。“何幸生逢奴樂島,縱談革命亦何加”(《孽海花》)是對奴性的批判;而“少女玩過又賜死,居然多情圣天子”(《華清池》)則是對封建皇權的批判。
聶詩中更有一些對現實社會丑惡現象的批判。如寫北大荒的詩中,有一首《懷張惟》:“《第一書記上馬記》,絕世文章惹大波。開會百回批掉了,發言一句可聽么?英雄巨像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北大荒人誰最健?張惟豪氣壯山河。”因為作家張惟寫的一篇小說《第一書記上馬記》,是反“大躍進”中的浮夸風和官僚主義,卻被召開大會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大毒草”。聶翁為張惟鳴不平,憤而作此詩。詩中頷聯是當時“批判會”的真實寫照,批判者執一面之辭,被批判者有口莫辯。頸聯更是直言不諱地以“英雄巨像”肯定被批判文章的價值,以“皇帝新衣”諷刺批判者言辭的虛假,堪稱警句。這是一首充滿現實主義批判精神的雜文體詩。
詩人他所處的時代,政治運動頻繁,“帽子”滿天飛,他在許多詩作中都有批判,只不過這種批判都夾雜在詩人沉郁復雜的情感之中。例如“誰知苦我天何補,說不贏君見豈非”(《六鹢》)、“十年已在人前矮,九日思知何處高”(《九日戲柬邇冬》)、“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心輕白虎堂”(《題壁》)等,都是他內心不平悲屈的寫照。所以他的詩里總是摻合了多種復雜情感在其中,表面上看似輕松俏皮,幽默詼諧,其實背后卻隱藏了作者深刻的沉痛,而在這沉痛之中,是一個雜文家面對時代變幻、個人苦難的哲理思辨和針砭批判。
聶翁還寫了一些寄人、悼人詩,批判了政治風云的變幻給社會和人造成的苦難。他以“于無聲處響驚雷,……痛徹乾坤此一悲”來哭總理;以“噩耗雷驚難掩耳,楚囚偷寫吊詩來”挽陳帥;以“君以一尸諫天下,世驚虎吼躍龍潭”挽老舍,詩人認為老舍“尸諫”是對“文革”的抗議;而“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挽雪峰》)則真實地反映了幾十年來歷次政治運動高壓下人們的心理,寄寓了對社會歷史的思考和批判。“文章名世無僥幸,血寫軻書《李慧娘》”(《挽孟超》),這是歷史的悲哀,也是對“文革”時期極“左”路線的批判與控訴!
三、諷刺性
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詩歸為閑適詩和諷諭詩兩大類。聶翁一生所處的時代風云變幻,世事不寧,而他一生又少有閑適,緣情為事之詩,諷諭見多。他將諷諭手法用于舊體詩詞的創作中,通過與夸張、反語、幽默等手段的巧妙結合,營造出一種嬉皮笑臉、指桑罵槐的針砭氣氛。在一種審美愉悅中完成對諷刺對象的批判指責,是文明的諷刺、溫和的嘲笑、幽默的蔑視,詩作就有了“雜文”的味道。更能使“教訓文字也富于詩的分子”,這比一般的譴責更富有感染力。如聶翁在《吊熊貓》一詩中寫道:“尤物人間何處尋,汶川四境柏森森。可憐弱土藏殊色,竟有強鄰慕好音。萬里和番天下計,一身報國女兒心。專機未發香先泯,頓使洋奴淚滿襟。”本詩的背景是這樣的:1946年10月,美國支持國民黨大打反共內戰。國民黨政府為博取美方歡心,在四川汶川境內搜捕國寶熊貓獻上。一只雌性熊貓身受彈傷,在運往美國途中不治而亡。《新民報》連刊《熊貓小姐,今日來渝》《熊貓昏睡上海,急壞移交先生》《熊貓玉殞香消,有人惋惜不已》等文章,聶翁因而作此詩。首聯、頷聯敘事,頸聯議論,把國寶熊貓奉獻美國比喻漢朝用“美女和番”,幽默詼諧的語言,已帶三分譏諷。尾聯更進一步“專機未發香先泯,頓使洋奴淚滿襟”,送往美國的專機還未起飛,熊貓小姐已香銷玉殞,那些崇洋媚外的奴才,如喪考妣,淚流滿面。特別在“洋奴淚滿襟”前冠以“頓使”二字,使諷刺意味增加七分。
如果說聶詩諷刺國民黨洋奴的詩如“投槍匕首”直刺對方要害,對于“四人幫”亦是如此。在“文革”初期,聶翁寫了一首《沒字碑》,以武則天暗射江青:“東施效顰人盡嗤,豈汝稱孤道寡時”,最后以“騎虎難下,有家不得歸”一語破題,直揭江青“女皇夢”。而對于自己在解放后所受的不公正待遇的諷刺卻以樸實率真、詼諧幽默、自我解嘲為主要色調。如詩人在《船屋》中寫道:“曾經滄海難為水,從此桃源便是家。”聶翁曾說,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關監獄,簡直等于進了陶淵明理想中的極樂世界——桃花源。樓適夷問聶:“坐在牢里是什么滋味?”聶回答:“比你們在外面好一些,沒有高帽子,沒有噴氣式,沒有大批判和紅衛兵!能安安靜靜地讀書!”可見《船屋》用的是十分幽默的諧語,也是十分辛辣的諷刺!
聶詩的樸實率真、詼諧幽默、自嘲自諷在他的“勞動詩”中俯拾皆是。如《放牛》之一云:“馬上戎衣天下士,牛旁稿薦牧夫家。”前莊后諧,蘊含更加深沉,今昔之比,感慨萬千,也更加耐人尋味。《放牛》之二又曰:“一鞭在手矜天下,萬眾歸心吻地皮。”昔時“天下士”,今當“放牛娃”,雖是“放牛娃”,但也可以“一鞭在手”,令“萬眾歸心”。在這個小小的天下,抖抖威風,貌似自嘲,實為諷刺。詩人讓讀者在《丁聰畫〈老頭上工圖〉》中看見“小伙軒然齊躍進”的英雄形象,“老夫耄矣啥能為”的我,詩人感到躬腰駝背能干啥?“美其名曰上工去”,恰被丁聰畫眼窺見。英雄狀變成滑稽樣,悲哀!在那個不能人盡其能的荒唐歲月,文人丟下了自己手中的筆,卻操起不會使用的農具,還要故作工農階級的英雄狀。一旦得到領導的一句表揚,“支書豎拇夸豪邁,連長拍肩慰苦辛”(《受表揚》),一個知識分子犯人能不誠惶誠恐,喜不自禁?竟有自我得意的滿足。詩人是在諷刺那個荒唐年代,還是諷刺詩人自己?他實則以諧趣寓不易說之情,使之成破涕之笑。在諧趣的深處,卻隱藏著沉郁。
正如施蟄存先生說:“一首詩,光有諧趣,還不易為高格,聶紺弩同志的諧趣,背后隱藏著另一種情緒:沉郁。”聶翁像這樣諧趣中又含沉郁的詩也表現閑適的題材。例如《即事用雷父韻》:“雖鄰柳巷豈花街,不為借書死不來。枯對半天無鳥事,湊齊四角且橋牌。江山間氣因詩見,今古才人帶酒杯。便是斯情何易說,偶因尊句一詼諧。”雖是用韻奉和詩,卻也寫得沉郁而格高。首、頷二聯是詼諧之語,頸聯是詼諧之后的莊重語,尾聯正以諧趣寓不易說之情,所以這諧趣便成為一種破涕之笑,創造了詩的高格。這種自嘲自諷詩,還經常出現于表達志同道合者的友情之中。如《中秋寄高旅》中一、二聯:“丹丹久盼過中秋,香港捎來兩罐頭。萬里友朋仁義重,一家大小圣賢愁。”其詩情來得輕松愉快,但這愉悅里卻隱含著“沉郁”。此意從作者自注中便可知曉:“圣賢愁,見《笑林廣記》,意謂白吃者圣賢亦無奈何。”第三聯“紅燒肉帶三分瘦,黃豆芽烹半碗油”,諧趣橫生,讓人未吃前已是饞涎欲滴。尾聯“此腹今宵方不負,剔牙正喜月當樓”,寫出了詩人的“窮酸”窘境,吃后更是捫腹大嘆,“我不負汝”!最后以景語作結,讓人想到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把自己的貧困落魄化作心理的滿足。全詩是在輕快中隱含沉郁,沉郁里折射出諷刺的味道。
四、情感性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聶詩所抒之情,首先是國家民族之情,人民之情。聶翁是在用“心靈”創作,將整個身心投入到題材中,感受筆下人與事的悲喜哀樂并與之共鳴,把自我熔鑄其中。“文章報國談何易,思想憂天老或曾”(《〈花城〉以“迎春”為題索詩》),他一生追求真理,對祖國人民有如赤子,充滿了真摯深沉的愛,就是身陷囹圄,身處“窮途罪室”,仍然“久想攜書,尋師海角,借證平生世界觀”。人雖“今老矣”,氣則融冰銷鐵,“迎春入沁園”,“魚躍于淵”(《沁園春·贈木工李四》)。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終關注著國家、社會。“天下人民無凍餒,吾儕手足任胼胝”(《麥垛》),這是一個智者的愛國情懷。“西風瘦馬追前夢,明月梅花憶故寒”(《六十》之二),表達了詩人對理想的追求,獻身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欲把相思栽北國”、“以此微紅獻國家”(《削土豆種傷手》),這是詩人報國情懷的表白,“大我”精神的寫照。
聶翁是個性情中人,“他重友誼,重信義,關心旁人遠遠勝于自己。”(夏衍《紺弩還活著》)
他與陳毅元帥在新四軍軍部相識相交,當年陳帥與張茜結婚就是聶翁當的“紅娘”,故有“東風暮雨周郎便,打打吹吹娶小喬”(《挽陳帥》),贊揚這位雄姿英發,文武雙全的儒將“酒酣抓筆當槍彈,一彈洞穿膏藥旗”(《挽陳帥》)。1972年陳帥逝世時,詩人還在山西獄中,聞訊后便用“噩耗雷驚難掩耳,楚囚偷寫吊詩來”挽陳帥。“噩耗雷驚”,可見陳帥逝世對詩人內心的震撼;“楚囚偷寫吊詩”則是歷史的悲哀,更見詩人對陳帥的感情之深厚。
聶翁重友情,講信義,說真話,不平則鳴的俠義情懷突出的表現在他與馮雪峰、胡風的贈答詩中。他與馮雪峰是世事風雨中的知音、知己。當馮雪峰為人所構陷,處境艱難時,聶翁敢于為朋友辯護,甚至以馮雪峰自況和自豪。如《雪峰六十》之三云:“荒原靄靄雪霜中,每與人談馮雪峰。天下寓言能幾手,酒邊危語亦孤忠。鬢臨秋水千波雪,詩擲空山萬壑風。言下挺胸復昂首,自家仿佛即馮翁。”要知道,當詩人挺胸昂首模仿馮雪峰的神情舉止之時,他正在北大荒勞動改造。又如《雪峰十年忌》中寫道:“相逢地下章夫子,知爾乾坤第幾頭。”雪峰之死,暴露了“文革”期間黨內派系斗爭延及社會自相殘殺,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峰。對革命忠貞不二的“馮雪峰未死于敵人的槍下,卻倒在各種同志的口誅筆伐中,怎不令人為之悲憤?”(姚錫佩語)這不僅是詩人情感的“心靈歌哭”,而且是社會的“心靈歌哭”!聶翁對以真言賈禍的胡風贈詩21首,反復為“三十萬言書”鳴不平。“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胡風八十》),通過兩個“無端”和兩個慘痛數字“三十”的重復,突出了“三十萬言”換來了“三十年”牢獄之災的奇禍奇冤,“不得其平劍尚鳴”!詩人又在《悼胡風》一詩中寫道:“精神界人非驕子,淪落坎坷以憂死。”哀其人已逝,念其志尚存。這是患難與共的良朋知音,同時也道出了這對“魯門弟子”真摯的革命情誼。
“南洋群島波翻筆,北大荒原雪壓詩”(《八十》),是聶翁一生經歷的濃縮。詩人經歷了“反胡風”、“反右”和“文革”,遍體鱗傷,他憂憤深廣的內心,積郁磅礴的情懷,不能直接縱筆揮灑于雜文,只有化為濃郁的詩情,噴薄而出。“壘塊須眉兩奈何,仙人島上借吟哦”,盡管他實在難以理解,自己一生追隨魯迅,扛起“左聯”大旗,與腐朽沒落勢力斗爭,以“韓康的藥店”揭露、諷刺、批判國民黨獨裁統治;在《血書》中,他是以新中國的代言人的姿態出現的,他在解放前夕和稍后在香港寫的那些文章,是對《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那些戰斗檄文的最有力的響應。他的詠橋詩《武漢大橋十首》,在瑰奇的意象中充滿了對時代的歌頌和對美好前程的憧憬。如此赤膽忠心,竟淪為“右派”、“反革命”。他的迷惘,他的郁結,現諸詩行:“他人飲酒李公醉,此地無銀阿二偷”(《自遣》),迷惘于不白之冤,無處申訴;他郁結那“地無裂縫天無路,你是何人我是誰?”(《反省時作》)的“同室操戈”。他面對“曾經滄海難為淚,便到長城豈是家”(《解晉途中與包于軌同銬,戲贈》)的茫茫哀傷;他只能接受“男兒臉刻黃金印”(《題壁》)的殘酷現實;“十年睽隔先生面,千里重逢異物驚”(《對鏡》),他無可奈何地經受了十年煉獄的磨難;他又承受了“膝下全虛空母愛,心中不痛豈人情”(《驚聞海燕之變后又贈》)的至悲至痛的家庭變故……這些磨難,在國家和人民至高至大的情感面前,自己個人和家庭只不過是屑小的瓶瓶罐罐。“方今世面多風雨,何止一家損罐瓶。稀古嫗翁相慰樂,非鰥未寡且偕行”(《驚聞海燕之變后又贈》),這是聶詩的真情真格,倒是引發了千萬讀者情感的“心靈歌哭”。
聶詩中表現出的現實性、批判性、諷刺性、情感性是真實的、深刻的。詩人以曠達樂觀的人生態度面對現實,以傳統愛國的憂患意識審視社會。他所創作的舊體詩彰顯出與眾不同的高超的雜文品質。詩人寓悲憤于曠達,寄憂傷于詼諧,在幽默中見嘲諷,在笑聲里聽歌哭。他的詩中那嬉笑怒罵、犀利爽快的社會諷刺批評和一針見血的現實主義雜文的戰斗精神,形成了聶體詩的獨特風格。
(作者系京山紺弩詩社原副社長)
責任編輯:劉 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