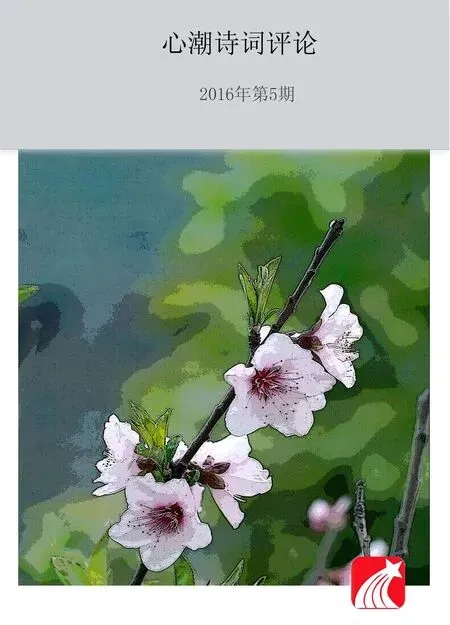“熱血和微笑”開出的奇花
姚泉名
“熱血和微笑”開出的奇花
姚泉名
聶紺弩的舊體詩從誕生起,就是引人注目的,向來不乏追慕者和研究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致力于聶紺弩詩的箋注考訂的,就有朱正、侯井天、郭雋杰、羅孚四家;專文論
述聶詩的,則燦若繁星,難以統計。在同時期,能享此殊榮的傳統詩詞作者,除毛澤東、魯迅等少數幾人之外,似再難有繼。
一、聶詩特色成因
關于聶詩的風格,很早就有公論,我以為主要的一點,就是“寓莊于諧”。“莊”是指莊重、嚴肅、正統;“諧”則是指滑稽、詼諧、逗趣,“莊”與“諧”本是事物的兩個極端,能將這二者調和一味,成為“調和油”,非有大匠功夫,豈能出彩!但聶紺弩卻做到了,而且,事實證明,效果還真不錯。
產生聶詩“寓莊于諧”“滑稽亦自偉”的藝術特色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為大體有三端:一是個性的造就,二是打油詩的影響,三是雜文的習慣。
首先說個性的造就。
清代畫家石濤在《畫語錄》中說:“我之為我,自有我在。”這是在強調“我”,也就是個體,主要是作者的個性在藝術創作中的重要地位。研究者認為,作品藝術風格是作者獨特的創作個性在作品的內容與形式中的和諧統一,是作者成熟的標志。簡單說,就是不同的個人稟性決定了不同的藝術風格。美術如此,音樂如此,文學也是如此。試想,沒有豪邁樂觀、豁達不羈、天真浪漫的個性,我們哪里去找李白?沒有仁善耿介、真誠狂狷、幽默剛毅的個性,我們哪里去找杜甫?沒有率真孤傲、豁達超脫的個性,我們哪里去找蘇東坡?那么,回到我們的問題上來,聶紺弩又具有什么個性呢?
很多聶紺弩同時代的人對他個性的評價是一個字:“怪”。
他的怪,主要是耿直剛烈、玩世不恭,是個天生的自由主義者。聶紺弩這個人經歷很復雜:老革命,早年進過黃埔軍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學,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主編過報紙副刊,他和國共兩黨的高層都有交往,在文化人中有很高的聲望。不過這些顯赫的經歷并沒給他帶來什么好處,相反,他一輩子是個倒霉蛋。先是坐國民黨的牢,解放后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沒有逍遙幾年,就被打為胡風分子,緊接著是右派,發配去北大荒,“文化大革命”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捉進秦城監獄。
這些坎坷的經歷,不能不說與他的耿直剛烈、玩世不恭的個性有關。早年的聶紺弩就已經具有這樣的個性,頗有魯迅的風范,他曾在一首詩里這樣形容自己:“二十歲人天不怕!新聞記者筆饒誰?”那時他是當記者的。到了晚年,性格也不見有所收斂。例如,他在北大荒當“右派”勞改的時候,一天,同案犯們正在食堂吃早餐,管教隊長不知在哪惹了閑氣,大概是想拿他們出氣,一進屋子,就打個鳴,吆喝一聲,叫站著吃飯的人坐下來吃飯。別人都驚愕地坐下,唯有聶紺弩,不知是沒有聽見還是故意不理睬,仍是站著吃,就算是隊長直呼其名,也依然如故。這下可就惹毛了這位威嚴的隊長了,他氣得大發雷霆,在食堂里跳上跳下。聶紺弩呢?是任其所為,如目無其人,如耳無其聲,還故意挺起干癟的胸,抬著高傲的頭,把臉沖著隊長,怒目而視,一面大口大口地咬著窩窩頭,一面一步步向隊長慢慢走去。就像一只不怒自威的老虎,走向一只狂吠的野狗。眼見淫威毫無用處,這位隊長也驚愕失措了,只好慢慢后退。人們忍不住了,開始哄堂大笑。在笑聲中,隊長落荒而逃。當時雖然震住了隊長,可事后聶紺弩還有好果子吃嗎?聶在北大荒勞改時期,一次國務會議上,有人提出,聶紺弩年紀大不適合在北大荒勞動,想讓他回北京。周恩來總理說:“聶紺弩自由散漫慣了,應當讓他多吃些苦,有好處。”這也間接說明了聶紺弩的個性剛烈,給自己添了不少麻煩。
他的怪,還體現在他的幽默風趣上。例如,聶紺弩喜歡下圍棋,在朋友圈子里極為出名。“文革”中,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身陷囹圄,卻念念不忘下棋。他將一件格子布襯衫撕成“棋盤”,將平素“打牙祭”才能吃到的米飯省下來,搓成“棋子”,又設法弄來墨水,染成藍白兩色。誰知這副“飯棋”瞞過了看守,卻沒能瞞過饑餓的老鼠。為此,聶紺弩懊喪許久。隨后,他和牢友又捏制了一副“土棋”。然而好景不長,在一次突擊搜查牢房中,“土棋”被搜查者踩得粉碎,聶紺弩本人還挨了一記重重的耳光。多年后,他談及此事,仍不失風趣,說:“數番挨打,唯此次不冤也!”
從這些小故事我們可以略見聶紺弩的個性中有著自由、剛烈、幽默的細胞,這樣一個復雜的人寫出“寓莊于諧”的復雜作品,是自然而然的。
其次說打油詩的影響。
打油詩,內容和詞句通俗詼諧﹑不拘于平仄韻律,創作起來較易,便于廣大人民群眾接受,還便于記憶,故而適合在民間流傳。清代翟灝在他的《通俗編·文學·打油詩》中曾引唐朝人張打油的《雪詩》云:“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后世則稱這類出語俚俗、詼諧幽默、小巧有趣的詩為“打油詩”。另外,有時詩人作詩自嘲,或出于自謙,也稱自己的詩為“打油詩”。聶紺弩就常稱自己的詩是打油詩,1961年3月15日他寫給詩友高旅的信中就說:“作詩有很大的娛樂性,吸力亦在于此。詩有打油與否之分,我以為只是舊說。截然界線殊難畫,且如完全不打油,作詩就是自討苦吃;而專門打油,又苦無多油可打。以爾我兩人論,我較怕打油,恐全滑也;君詩本澀,打油反好,故你認為打油者,我反認為標準。”意思是說自己的詩本來就是打油體,所以不能再打油,否則就會落入“油滑膚淺”一路。又如,1983年他在《散宜生詩·后記》中說:“詼諧、滑稽就是打油。秦似教授當面說我打油。都是內行話,不僅知詩,而且知人。”他評價自己的詩說:“何等阿Q氣,豈只詼諧、滑稽、打油而已哉!”聶紺弩稱自己的詩打油,固然有自謙的意思,但關于打油的原因說明,以及為打油正名、辯護的論述,卻是嚴肅而認真的。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李遇春教授認為,聶體或紺弩體,是一種現代打油詩。聶體打油詩的風骨,含有“三氣”:阿Q氣,離騷氣和江湖氣。其中,阿Q氣使聶詩詼諧,離騷氣使聶詩沉郁,江湖氣使聶詩狂放。阿Q氣是表,離騷氣和江湖氣是里,一邪氣(或曰逸氣),兩正氣,互為表里,亦正亦邪,恰構成了聶詩“盛氣凌人”的獨特魔力,也使現代舊體詩(打油詩)別開了新生面。阿Q式的自嘲、屈原式的憂患、江湖式的狂狷,正是聶紺弩直面人生苦難的三種方式。這是對聶詩手術刀似的解剖。
而對于聶詩打油特色產生的社會根源,著名學者錢理群也有深刻的剖析,他說:“被稱為聶體的打油詩是具有更鮮明的時代特征的。在那史無前例的黑暗而荒謬的年代,人的痛苦到了極致,看透了一切,就會反過來發現人世與自我的可笑,產生一種超越苦難的諷世與自嘲。這類通達、灑脫其外,憤激、沉重其內的情懷,是最適于用打油詩的形式來表達的。”總之,打油詩的影響,是聶詩“諧”的來源。
再次說雜文的習慣。
所謂憤思出雜家,激情出詩人。我們知道,聶紺弩是以寫雜文而著名的,他是繼魯迅之后的一流雜文家。在“反右”和“文革”中,他蒙受不白之冤,飽嘗逆境、厄運、磨難、痛苦,但他問心無愧,對前途對生活總是充滿信心。作為雜文家,在任何客觀情況下,他都不可能沉默。盡管他身陷囹圄,他的筆已經沒有機會寫雜文了,但是歷史老人卻給了他寫詩的意外機會。他在《散宜生詩·自序》中回憶說,1959年在北大荒住牛棚,一天夜里,正準備睡覺,指導員忽然來宣布,要每人都作詩,說是上級指示,全國一樣,無論什么人都得作詩。說是要使中國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魯迅、郭沫若。本來聶紺弩就對詩詞感興趣,勞改隊不讓寫還想偷偷寫一兩首,現在強迫寫,那不是正合我意嗎?于是他在厄難中激發出滿腔激情,以雜文家的思辨、敏銳的頭腦和犀利的思想,寫出了大量反映北大荒勞動和十年獄中切膚隱痛生活的史詩。
聶詩的雜文味,主要體現在詩的思想深度、高度、力度都特別強烈。他的詩不僅是詩人激烈情感的宣泄,更是詩人深沉思想火花的迸放。清人葉燮說:“文章千古事,茍無膽,何能千古乎?吾故曰:無膽則筆墨畏縮。膽既詘矣,才何由而得伸乎?”(《原詩·內篇下》)這是說,真正的藝術家必須具備藝術勇氣。對于優秀的雜文作家來說更是如此。這是由雜文直接干涉事實、參加政治、抨擊邪惡的特性所決定的。在這方面,聶紺弩的表現非同一般。聶紺弩的雜文,是最接近魯迅雜文風格的。著名作家夏衍在談自己的雜文時,曾說“最初是學魯迅,后來則學聶紺弩,因為紺弩的雜文幾乎可以亂真”。聶紺弩確實就像魯迅那樣,敢于用自己的筆對付反動當局的手槍,除了在作品中運用大量的隱喻、諷喻之外,被他指名道姓抨擊的國民黨要員就有汪精衛、潘公展、孫元良、張篤倫,甚至蔣介石,充分體現了聶紺弩的“文膽”,這也是聶詩“莊”的原因。
聶紺弩那些有思想深度,雜文味濃的詩詞,于詼諧風趣中包含著沉郁的情思,嚴肅的思考。“人或以為滑稽,自視則十分嚴肅”(《散宜生詩·自序》),這是我最為欣賞的。歷史上,以思想嚴肅,內涵深沉著稱的詩人很多,如屈原、杜甫、李商隱等,但他們要么眉頭緊鎖,要么淚流滿面,要么唉聲嘆氣,要么橫眉冷對,都沒有聶詩那種“熱血與微笑”的迷人風采。南宋楊萬里的“誠齋體”,風格活潑自然,饒有諧趣,在語言風格上與聶詩的詼諧接近,但他僅僅把自己的主觀情感投射在客觀事物上,很少以其詼諧之筆涉及南宋腐朽沒落的政治,因而打個不恰當的比方,“誠齋體”更像公子哥兒的貧嘴,在汪洋恣肆、嬉笑怒罵的“紺弩體”面前顯得手足無措,底氣不足。
人們在研究聶詩風格時,往往還會總結出“化丑為美”“與古為新”“信手拈來”等風格特點。但我認為,這些都已經涵蓋在聶詩的“寓莊于諧”之中,是促成聶詩“寓莊于諧”風格的創作技巧。也是我下面要重點講的一個問題,即我們該從聶詩中學習什么?
二、向聶詩學什么
對于向聶紺弩學什么的問題,答案其實很簡單——學創新。聶詩的創新是全方位的。有人會質疑我:既然如此,為什么剛才不將“與古為新”作為聶詩的風格呢?其實,答案也很簡單,創新是詩人的共性,不是個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創新是詩人的天職,是詩人存在的唯一理由。不會創新的詩人,肯定是不合格的詩人。所以,創新是詩人聶紺弩份內的事,而不是他的風格特色。
那么,聶紺弩是如何創新的呢?我以為,首先,是內容的創新。
聶詩拓寬了中華詩詞的題材內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勞動詩。描寫勞動的詩歌,在我國詩歌史上并不少見,但聶紺弩的勞動詩無論內容的拓展、形式的創新以及人文內涵的注重,都是獨樹一幟,散發出強烈的藝術魅力,達到了勞動詩創作很高的成就。
聶紺弩的勞動詩主要集中在他的《北荒草》之中,按題材進行歸納,主要有三類:一類是寫勞動生活本身的。諸如搓草繩、鋤草、挑水、推磨、削土豆、燒開水、放牛、拾穗、伐木等極其平常的勞動行為,都成為他吟詠的對象。即使象“掏廁所”這種與詩無緣的題材,手握奇筆的聶紺弩,竟以冷峻嘲謔而又寄意深微的手法,寫下了繞有韻致的詩篇,且看《清廁同枚子》:
君自舀來仆自挑,燕昭臺畔雨瀟瀟。
高低深淺兩雙手,香臭稠稀一把瓢。
白雪陽春同掩鼻,蒼蠅盛夏共彎腰。
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穢成坑便肯饒?
這是十年文革期間作者被投北大荒勞改時的作品。詩題中的“枚子”,是曾擔任國務院參事的資深報人萬枚子,我們的湖北老鄉,潛江人,與聶紺弩年紀相近。
詩的起句“君自舀來仆自挑”,以極其平實的語言直寫兩個人清廁時的分工勞動。一個用糞瓢舀,一個糞桶挑。“燕昭臺畔雨瀟瀟”。燕昭臺,又叫燕王臺、黃金臺或金臺,地址在河北省易縣東南。相傳戰國燕昭王筑臺于此,置千金于上,延請天下賢士。作者借顏色上的一點可比性,把堆積的糞便比作“黃金臺”,是詼諧與幽默;“雨瀟瀟”,可知他們是在冒雨清廁,影射管教者對右派分子的手段之毒辣。更深一層,“黃金臺”這個意象,本來彰顯的是對知識分子的尊重,而今,卻成為壓迫知識分子的舞臺和見證,不能不說是對當時社會的一個委婉諷刺。
頷聯,具體描寫清廁勞動。兩位老人兩雙手,時而高時而低,舀糞尿的茅勺,深一下淺一下,在粘稠惡臭的糞尿中起起落落。把那樣一種令人作嘔的活計寫得如此傳神而且不失典雅,真叫人拍案稱奇。
頸聯補寫時令和環境。用“陽春白雪”這樣一個大雅之詞來描寫與茅廁相關之事,形成雅與俗的強烈對比,堪稱絕妙。
尾聯總收全篇,是莊語也是諧語:清理世界上的污穢正是我們這些人的事情,怎么能放過這污穢成坑的茅廁呢?
聶紺弩勞動詩的第二類是謳歌勞動者的。代表作如《女乘務員》:“長身制服袖尤長,叫賣新刊北大荒。主席詩詞歌宛轉,人民日報誦鏗鏘。口中白字捎三二,頭上黃毛辮一雙。兩頰通紅愁凍破,廂中乘客浴春光。”她說話拿腔作調,不時帶出“白字”,活脫脫地勾畫出一個“黃毛”丫頭來,使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
第三類是對勞動成果和勞動物件的描寫。如《刨凍菜》:“白菜隆冬凍出奇,明珰翠羽碧琉璃。故宮盆景嵌珠寶,元夜花燈下隴畦。千朵鋤刨飛玉屑,一兜手捧吻冰姿。方思寄與旁人賞,墮地驚成破碗瓷。”一棵凍得結了冰的白菜,在詩人的筆下竟成了珠玉、琉璃、名瓷,真是美得出奇。
總結我國詩歌史上的勞動詩,從創作主體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勞動者自己寫勞動,由于文化層次低,無論內容或形式都很粗糙。二是知識分子寫勞動,由于身份的限制,大多缺乏對勞動的細致刻畫;有些雖然表達了對勞動人民的同情,但有一種置身事外的距離感。聶紺弩則別具一格,他既是知識分子,又是勞動者,無形之中避免了古代勞動詩那兩方面的尷尬,正如著名詩學家毛大鳳所說:“先生以深邃而活潑的思想,面對普通的勞動事物,諸如推磨、挑水、拾穗、清廁等都能構思新穎,寫人所未寫,大破作詩禁區,從而極大地開拓了格律詩的題材范圍,宣告‘無事不可入詩’,走出了一條格律詩的新蹊徑。”將勞動詩推向了一個嶄新的境界。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反過來,一定的社會意識都是一定社會存在的反映。聶紺弩生活的時代,特別是他大量進行舊體詩詞創作的時代,大約有近二十年時間,正是中國歷史上尤其是新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代,這個時代由極左思想、極左路線統治,是知識分子被打擊、被改造、被革命的年代,是一個我們現在稱為“浩劫”的年代。聶詩中的搓草繩、刨凍菜、挑水、削土豆、推磨、送飯、放牛、掏廁所等內容,記錄了那個年代知識分子被強迫勞動的歷史;而“社會主義春不老”“毛澤東思想都學”“贈君毛澤東思想,要從靈魂深處降”“投身階級斗爭里”“牛鬼蛇神第幾車”等詩句,則原汁原味地記錄了那個時代使用頻率最高的語言和被扭曲的時尚。這些,我們都可以看作是聶詩對中華詩詞內容的拓展。
其次,一些評論家認為,聶紺弩對中華詩詞的創新,還表現在形式上,也就是語言的創新。稍事歸納一下,我們發現,聶詩語言的創新主要有這樣一些表現,值得我們借鑒:
1.俗語入詩,不避雅言。
先看他詩里的俗語、口語、時語。“枯對半天無鳥事,湊齊四角且橋牌。”(《即事用雷父韻》)“無鳥事”,這是俗語入詩;“百歲只差三歲了,不曾寶貴卻壽考。”(《淦智老人九十七》)“百歲只差三歲了”,這是口語入詩;“贈君毛澤東思想,要從靈魂深處降。”(《贈小李》)“毛澤東思想”,這是時語入詩。因其反常,因其不雅,反覺其新而有趣。
再看他詩里的雅言,這些傳統詩詞的語言和意象,有的表現在聶詩的用典上。聶詩用典取材廣泛,如“哮天勢似來楊戩,搏虎威疑嗾卞莊。”(《遇狼》)前一句的典來自以前流行的小說《封神演義》,后一句的典來自傳統文化典籍《史記·張儀列傳》;“賽跑渾如兔與龜。”(《馬逸》)龜兔賽跑,則是古希臘的《伊索寓言》中的故事;“梁顥老登龍虎榜”(《受表揚》)用的是舊時兒童啟蒙教材《三字經》中“若梁顥,八十二,對大廷,魁多士”的典。
聶詩的雅言,有的還表現在襲用前人成句上,就是把人家的句子拿來我用,這也是允許的,但前提是用得貼切。“子曰學而時習之,至今七十幾年癡。”(《八十》)用《論語》的句子,將散文的成句放入詩歌,歷來少見;“一談龍虎風云會,頓覺乾坤日夜浮。”(《喜晤奚如》)用杜甫《登岳陽樓》的句子;“百年奇獄千夫指,一片孤城萬仞山。”(《有贈》)用王之渙《涼州詞》的成句。
“青眼高歌望吾子,紅心大干管他媽。”(《鐘三“四清”歸》)這一聯更是有趣,前一句用杜甫《短歌行贈王郎司直》的原句:“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頭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可謂雅到極致;后一句則大爆粗口,俗不可耐,這一雅一俗,一莊一諧,居然對仗工整,且對比鮮明,由此形成強烈的諷刺效果。類似的還有《雪峰以詩見勖依韻奉答》中的“在山憑定三分鼎,出水才看兩腿泥”。
聶詩的俗語入詩,不避雅言,目的就是追求“打油”詩的桀驁之氣,增加詩歌的表現力,達到“寓莊于諧”的創作目標。這種做法其實是很“討巧”,就是咱們常說的雅俗共賞,既將中華詩詞從高貴的象牙塔里請出來,推廣到廣大勞動人民之中去,又不失中華詩詞的典雅風度。聶詩流傳至今,愈見火爆,正是明證。但是,應當注意到,俗語、口語、時語入詩,最容易掉入枯燥無味、油腔滑調的大陷阱;典故、原句入詩,又容易落入晦澀難解、掉書袋子的大圈套,聶詩的腳很好地踩在這“大陷阱”和“大圈套”之間的鋼絲繩上,我們應該細心去揣摩,體味。
2.變化節奏,句法獨到。
七言律絕歷來慣用的句式節奏是“二二三”結構,聶紺弩詩中對此有許多突破,常用“一三三”,例如:“脫/紅綾襖/心真碎,補/雀金裘/力早拋。”(《晴雯》)還有“三一三”,如:“兩三點/血/紅誰見,六十歲/人/白自夸。”(《削土豆種傷手》)還有“二四一”,如:“但覺/三千世界/小,誰知/七十五年/非。”(《歲首自嘲》)還有“二三二”,如:“門對/珞珈山/不遠,人攜/辯證法/同居。”(《贈董冰如高啟夫婦武昌》)甚至有“五二”句式,如:“中國共產黨/同志,晚清小說史/殊名。”(《挽阿英前輩》)如此變化,增加了節奏的新穎感,使呆板的律詩句式變得活潑起來。
另外,他還常用倒裝句法,如“蘇武牧羊牛我放”(《放牛》其一)、“邊山客老幸牛騎”(《放牛》其二),兩句的后三字,其實是“我放牛”“幸騎牛”的倒裝。“棉衣棉褲三天跑,小兒小女一見才”(《贈浩子》)本來是“跑了三天”、“才得一見”,倒裝后不覺生硬,反有新奇感。“生事逼人何咄咄,牢騷發我但偷偷”(《六十》),本來是“咄咄逼人”“偷發牢騷”,倒裝之后,常用詞語的語序被打亂,產生一種認知上的陌生感。這種認知的陌生感是短暫的,稍稍一愣之后,就是恍然大悟,于是,在這一頓挫之中,覺得這詩就很有妙趣了。
句式變化一下,詞序倒裝一下,前人后人,都有人做,但像聶詩這么集中地使用,這么大膽地使用,還很少見。
3.對仗奇巧,挖空心思。
對仗(對偶)是中華詩詞很重要的一種修辭格式,在先秦的詩歌中就已存在了,如《易經》里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乾文言》)《詩經》里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對仗體現了中華詩詞的均衡美、整齊美的特色。對仗也是律詩區別于絕句的重要標志,人們常說,絕句功夫看意境,律詩功夫看對仗。具體到聶詩的對仗,研究者普遍認為,聶詩看似隨意,其實是苦心經營,尤其對于對仗,往往不僅追求“工”,還追求“巧”。
聶詩對仗的形式豐富。有掉字對,即一句中有相同的字來相對,同時上下句又要互對。說起來復雜,舉個例子就明白了,杜甫《曲江對酒》:“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出句“花”字相同且相對,對句“鳥”字相同且相對。這樣的對仗在聶詩中非常多,例如,“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胡風八十》)、“山中鳥語如人語,路上新苔掩舊苔”(《伐木贈尊祺》)、“一笑故人還故我,同傷多夢已多時”(《序詩》)、“昔時朋友今時帝,你占朝廷我占山”(《釣臺》),類似的例子在聶詩中很多,不勝枚舉。有流水對,即一句話的意思,分上下聯說。如“自讀馬恩列書后,漸知五十幾年非”(《三月十三》)、“不荷犁鋤到東北,誰知冰雪是山川”(《聞某詩人他調》)、“一曲高山流水后,千年長嘆永思中”(《琴臺》)。有當句對,就是一聯的一比之中,同類名詞自相對仗,又叫“就句對”,如“三萬六千日何少,鵝雞狗兔事偏忙”(《即事》),“三、萬、六、千”可以視為四個數字類的單字,“鵝、雞、狗、兔”是四個動物類的單字,上下句都是四字相連而成對仗。
聶詩對仗的技巧豐富。技巧,即表現手法。有虛實相生,如“春雷隱隱全中國(虛),玉雪霏霏一小樓(實);把壞心思磨粉碎(虛),到新天地作環游(實)。”有雅俗共賞,如“荒原百戰鹿誰手(雅)?大喝一聲豹子頭(俗)。”(《排水贈姚法規》)這是一聯之中有雅俗;“千詩舉火羊頭硬,六月飛霜狗臉皴。”(《答邇冬托向人乞蘭》)這是一句之中有雅俗。聶詩對仗的工、巧、妙、活、奇、絕,在當代中華詩詞創作中實在是“獨一無二”,已經引起眾多研究者的注意。
三、結語
中華詩詞是世界文學園林中的奇葩,無與倫比,無可替代。中華數千年的詩歌史上,群星璀璨,爛若星河。我們為擁有“逸響偉辭,卓絕一世”的屈原而驕傲;我們為擁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李白而自豪;我們為擁有“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的杜甫而慶幸,我們為擁有“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的蘇東坡而欣慰……縱觀歷史,我們的詩詞土壤多么厚實、多么肥沃!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上,中國歷朝歷代從來就不缺乏耀眼的詩人。由于歷史和個人的原因,中華詩詞在當代曾有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但,是金子總會閃光。改革開放以來,大開的國門迎納了世界各地的文明,既給我們中華文明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也帶來了生存的挑戰。然而,在這個大時代的文化沖擊中,中華詩詞非但沒有消亡,反而迎來了自己偉大復興的機遇,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吟詩寫詩的愛好者越來越多,品詩論詩的專家也越來越多,許多從前不為人所知,甚至處境艱難的詩人以及他們五彩斑斕的詩詞作品也趁著這春風破土而出,為大眾所認識,所景仰。我們也因此發現,哪怕是在中華詩詞最寂寞、最無助、最痛苦的時代,我們的詩人也依然堅守住了中華詩詞的陣地,維護了中華詩詞的高貴。聶紺弩無疑是這些“破土詩人”中的佼佼者。
讀聶紺弩的詩,就是在讀他的詩品和人品,就是在讀他們那個時代的痛苦和荒謬,就是在讀中國知識分子的“熱血和微笑”。在最后,我想借用胡喬木在《散宜生詩序》中對聶詩的那個著名評價來結束本文,他說:“熱烈希望一切舊體詩新體詩的愛好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熱血和微笑留給我們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許是過去、現在、將來的詩史上獨一無二的。”
(作者系《心潮詩詞評論》副主編)
責任編輯:方世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