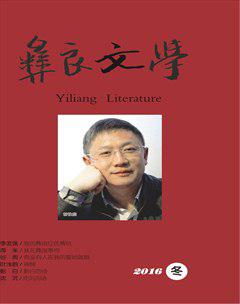有沒有人在我的墓地跳舞
谷雨
一把火
白水江邊的木噶鎮,我一閉上眼睛,就聽到了它的鳥鳴。村里的喜來寶,二十出頭,瘦得像只猴;他家爹喜老幺精瘦,你看他那下巴,長滿淺淺的花白齜須,雙頰微微癟下去,細細的眼睛說話時閃射著空茫的光,你萬萬想不到,在鐵路上頂喜來寶爺爺的班兒時,喜老幺煞是風光了一陣:有工作啦,偏分的兩片瓦頭型,牛仔喇叭褲緊裹出他瘦瘦的屁股,腳蹬锃亮黑皮靴,特別是那一到禮拜天就提回來的黑匣子錄音機,“蓬擦”“蓬擦”;可是,當他走在鄉間的小路上,蓬擦聲震動空氣也撩撥不了幾個婆娘的心思。啥?好吃懶做噻,出了名,誰稀罕?嫁漢嫁漢,穿衣吃飯!哈哈倒是成了鄉村搖滾,惹亮了不少放牛娃的歌喉。一眨眼,喜老幺快三十啰,而且聽說單位改制,喜老幺要文化沒文化要業績沒業績,文不得,武不行,聽說就是下崗的對象,這可急壞了麻臉的來寶奶奶。好在,有三河坡的遠房親戚,不知究里,帶了個姑娘來耍,叫銀花來著,你甭看那姑娘皮膚黃,但奶大腰圓,和喜老幺話沒說上幾句,就呵呵笑得滿臉緋紅。隔壁汪大嬸風聞,幾個兒女前堵后擁著湊到窗縫窺熱鬧,銀花呵呵呵,滾出一串笑聲,用蔭藍布圍腰一把捂住臉鉆進臥房;奶奶一發笑,臉蹙縮成干核桃,當機立斷,說: 成,保想能生個萌孫兒!
當銀花肚子頂得渾圓,臉養得像塊白里泛黃的饃饃,喜老幺企業轉軌改制,在“家里蹲”上班。曾在白水江邊拖船,一把花白胡子的老爺子有雷打不動的退休金!哎,眼巴巴兒的,兩代人巴望著的新生代呱呱臨盆了。老爺子說:這寶貝孫子總算給一家人帶來點喜氣,就叫喜來寶吧!奶奶一聽,干核桃樣皺縮的臉舒展開來,連聲叫好。
突 圍
一年后的夏天, 銀發如雪的爺爺,在竹躺椅里看來寶捉蟋蟀,含著笑,清風拂動他銀白的山羊胡子;銀花哭喪著臉,扯開嗓子鬼吼吶叫幾聲后,爺爺賦予這個家衣食無憂后的安靜與祥和也隨之結束。兩間瓦房,風大時直往下掉瓦;雨大時,墻頭灶壁簌簌漏雨,瓦縫里滲出的雨水滴答,滴答滴滴答,敲打得銀花的心一陣緊勝一陣,連她向鄰居大嬸學做的豆瓣醬,也時常被淋得濕漉漉,潮乎乎的;來寶看著檐下玉珠飛濺,水渦里漾開水花花,圓睜著清澈的雙眼,格格地笑;灶臺潮潤起來,蒼蠅在鍋瓢碗盞邊嚶嚶嗡嗡;喜老幺躺在木條凳子上,哼著信天游,瞇縫著眼;在這樣的梅雨季節,奶奶將尋常日子拄著的拐杖撂開,打著盹兒,也撒手西去。
接連料理完兩臺喪事,團轉四鄰的三三兩兩在檐下吃完飯,拾掇好家什。家里在悶熱和煩亂里一下陷入沉寂,只聽見知了躲在門前的玉米苞苞下,懨懨地叫得睡意襲來。一家仨好些天灰頭土臉,天晴了,銀花四處打聽,在趕集天里總算找來金鎦子。老小伙子姓金,腦瓜子靈活,手上活路勤勞肯干;可這人嘛,十馬九不全,全了不值錢。伙子到了成家的年齡,托媒人提了好幾次親,姑娘家都沒見他“彩禮”的影。用金家的話來說,沒得個樁樁,就掛不上個壺壺,姑娘只要看上地勢,想在這里坐家了,男方一分錢也不花,保管還能賺上“黃瓜二兩”,而且這金鎦子還上過趟省城,老爺子一封病危加急電報催回來了,實際是怕兒子在城市里伙壞。你沒聽說?不可能!木噶村你那位剛子老表,讀詩讀壞了腦子的,幼時又打了一針,半輩子就拖著條腿,后頭去城里頭發達了,手下好幾十條人配槍,還帶了卷發的俏姑娘回鄉成親;后頭咋樣?砰,的一聲腦殼敲開花,沒了,鴉片生意做得的嗎,哼!我回鄉這幾天,老爹習慣邊做家務,邊和我擺龍門陣。說完,將我撂在云里霧里,提起潲水嘩嘩地倒進巨大的潲鍋,弓著瘦骨嶙峋的脊背拌好了豬食。年輕時疾走如風的老爹,此時全白了頭,提著半桶潲,出灶房門時,踉蹌了半步,又沿著墻根,蹭進豬圈,豬圈里就飄蕩著豬草煮熟后的清香,三頭架子豬耷拉著耳朵,哼哼著,攢到槽子邊,仰著一雙雙瞇縫在腦袋褶皺里的眼,凝望老爹,老爹右手將潲桶升到一米左右,左手摳住桶底,豬潲瀑布狀“簌簌”落在豬頭上;眼前一灘濕漉漉的東西,慘白,變成剛子老表飛濺開來的腦漿,腦漿逐漸風干,化為一道青煙,那道騰起的青煙里,一個襲裹在白水江氤氳水汽里的聲音,繼續講述著故鄉的往事:還有件事愨得很,有位省城的大姑娘,帶著對二線城市厭倦后的抑郁,對鄉村田園生活的向往,跑到木嘎村來,在古木參天的隴氏墓群逡巡半天,看到了在松林里翻揀松果松枝的金鎦子。海子的詩句從姑娘腦海蹦出來:“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喂馬,劈柴,周游世界”,姑娘想:詩意人生就棲居在這里。于是,赤腳,緊身牛仔繃得前凸后翹的大姑娘,“蹬蹬蹬”跑下山崗,站在金鎦子身邊,搶過他的背簍說:“小哥:亭亭玉立的我,想請你當免費向導哦,還想嘗遍你家鄉的美食!”金鎦子看清了大姑娘湖水樣的眼睛,她的長睫毛下彈奏出秘密,又見大姑娘從包里拿出玫瑰紅內衣,念叨著“好漂亮啊,結婚時穿!”心里咯噔了一下,正想腳底下生油——開溜,姑娘挽起金鎦子的胳膊,小鎦子前世今生還沒享受過大姑娘臂彎的溫情,小子一下如墜入遙遠的云端,你呀你呀你,稀里嘩啦仿佛就要死在一個人的手心里!那天恰逢趕集天,省城大姑娘挽著金鎦子過大街時,趕街的鄉親們駐足而立,姑娘們捂住嘴笑;媳婦婆子們往他倆駐足的方向瞟一眼:嘖嘖!腦殼省事不?青天大白日的,大辮子姑娘上街拉伙子!男人們看著姑娘將金鎦子粗糙的手捺在臂彎里;金鎦子憋著紅臉膛,憨憨地嘿嘿直笑,男人們也嘿嘿地,傻傻直笑。山嫂埋著高原紅臉頰,用漏勺推刮豆綠的涼粉,瞬間豆綠的一鍋涼粉上凸起一團疏松;姑娘在山嫂的 “龍街涼粉”攤前站定,打心里因創造的愛而歡欣;山嫂乜了姑娘一眼,姑娘腦海里閃過路遙《人生》中的劉巧珍和高家林,斬截地松開了金鎦子的手;要了兩碗涼粉之后,金鎦子摸摸后腦勺,自覺地捏了捏褲袋,囁嚅道:“我們還是AA制!”當姑娘看清金鎦子掏出五毛錢遞給山嫂,才明白憨厚老實人的精打細算像美食里偶爾咬到的雜質;此時正好一輛開往市區的客車,在坑洼里喘了好一陣,帶著蹭上坦途的歡欣,“嗚嗚——”地催促旅客上路,姑娘幾步跨過去,上車;那客車翕動的門徐徐合攏,化為一縷煙塵,攙和著人們的哈哈哈,消失在木噶子村湛藍的天際。
金鎦子額上滲出油光透亮的汗珠,在陽光漫過檐下時,撿完了黧黑的瓦,吃著銀花遞過的熱茶歇腳。銀花瞅著眼前男人黑黝黝的胸膛,放眼望望房前春耕后的田地,在陽光下散發著泥土的氣息。她將余光灼熱地游離在小鎦子身上,小鎦子呷了口浮動著乳香的熱茶,扯著汗衫前襟擦把臉說:“這天兒熱得啊!”銀花滿眼小母獸的柔情,“鎦子,來啊,屋里涼快——”金鎦子蹭進屋時,銀花輕輕閂了門,一把拉著鎦子往里屋躥。床上潮潤凌亂,散發著銀花乳香的體味,眼前銀花的胴體活脫脫浸染在陽光里,無需繳械,已經投降;兩具活體的疊印,糾纏,燃燒,生命力在突奔,霍爾蒙氤氳在呼哧呼哧的喘息聲里,山陵仿佛崩催,決堤的河水沖出峽口,瓦解了那天大街上哈哈哈帶來的陰郁,繼而奏響歡歌,帶著一路上愛綠千山的繾綣,潺潺流淌。銀花肥乳豐臀,早已在滿足的呻吟中大汗淋漓;金鎦子帶著每個毛孔都舒展后的疲憊,開門出來,當一縷陽光撞進他的懷里時,來寶站在門前,一對烏溜溜的黑眼睛正望著他。這娃不知哪時候回來的,木板門那個罅隙里掩藏不了秘密!銀花看著那個透著亮光的門縫,面色一沉,撈開蔭藍布的衣襟,抱過孩子,將鼓囊囊面袋樣的奶子塞進孩子嘴里,來寶吐出蛇泡兒樣的乳頭,別過臉去;蒼蠅在檐前飛舞,金鎦子心里生起一陣嫌惡感,在東窗事發前匆匆離開。那天,喜老幺沒有了人影。
回 鄉
一年后,在暮靄沉重得罩住鄉村,坦露出死灰時, 喜老幺板著腰身回到故鄉木噶村。他逢人便說自己耍大城市來了, 大城市的姑娘屁股扭扭能濺落大黃蜂和蝴蝶;可是我的婆娘甩起面袋樣的奶濺落滿天云朵。銀花將沉得讓背系勒進肩膀的煤傾倒在破壁殘垣的耳房,聽見翻鍋弄灶的動靜,以為是隔壁養的阿黃翻找狗食,于是詐唬道:
“瘟器,你翻筋找死啊?”
“一個屋頭弄得烏煙瘴氣,給老子弄點吃的!”老幺公雞嗓亮堂著。在省城街頭翻撿垃圾一年了,天晴落雨的也餓不死,從沒想過回家。那天豆竹竿雨下得讓人睜不開眼,老幺俯身要去揀那件夾克衫時,一股子長飚的腥味噴在臉上,和惡心的甜混在空氣里,他怵在那里一動不動。你媽,為一個礦泉水瓶瓶,一部頭發亂蓬蓬的阿三,歇斯底里地將掉了手柄的尖刀刺進朱五瘦削的后背。警車嗚嗚地在弄堂里躥,簌簌地濺起他一身水花;來了幾個“大沿帽”,在讓目擊證人做完筆錄時,有人喊了起來。
“老幺,是你啊?” 原來是木噶村和自己同年的玉書,他一把拉起老幺就朝理發店走,老幺破天荒享受剪頭發時還有姑娘按摩的待遇,那時心里通透敞亮得像做了回皇帝。后來玉書拉他下館子,玉書直叫他慢慢吃,還說他們以前穿連襠褲上山放牛,下河洗澡,老幺家富,那時老幺還會塞給他一塊香酥餅干,或者一個潲水里偷煮的開裂雞蛋;老幺圓鼓著陷在眼眶的眼球,津津有味地抓啃著豬蹄,直“唔唔”點頭。臨了,玉書說大城市不好淘生活,回去吧,勤快點有飯吃,有衣穿,還可以摟著婆娘睡。昨天那場合嚇人毬得很!你想,持刀殺人該進監獄,可是家屬來了,說間歇性精神病,麻煩了嘛!老幺心里咯噔一下,猛抬起頭叫道:
“那朱武白毬拉拉了?”
“好在,人沒死,在醫院受洋罪啊。”玉書喟嘆道。
“這人在大城市呆久了,婆婆媽媽,自由慣了,哪想聽你瞎嘮嗑!”老幺想到,這時店里閃進來個精明的女人,高挑身材,瘦骨伶仃,飄飄衣裙拂過一陣濃香;老幺腦海里閃過銀花肥嘟嘟的胴體。女人進屋就說:
“你叫給老鄉買車票,我馬上托人買好了。還有路上吃的干糧。”女人說著,將車票和半食品袋鼓鼓囊囊的方便面放在桌子上。老幺心里一熱,眼眶里熱熱的,瞅著女人。
“老公,我上班去了,拜”說完,女人小鴉反哺地將一粒櫻桃,嘴對嘴塞進玉書口里。老幺渾身燥熱,惶恐地站起來,仿佛那粒櫻桃,塞進了自己一年沒刷牙的嘴巴里。這女人,不是十年前玉書帶回老家結婚那個嘛;難怪聽說后來離婚,重配了姻緣。
“你滴別鬧!”玉書說著,逐漸壓低了聲音;但老幺在寂靜里偏聽得分明。
“我這是在工作,遣散市區流竄人員,省得惹是非。你老公K市的公安局長,是辛苦滴!”,老幺一聽,一抹嘴,拿起車票,猶豫半秒,擰起食品袋,在春光里,匆匆朝火車站方向走去。
“你?……回來咋子?”銀花哽咽著,梗著脖子看著煙熏火燎后黑漆漆的樓巴竹。
“咋不在外面找死算毬!?我的媽,我造幾輩子孽啊”頓了頓,銀花鋒利地叫,接而歇斯底里地哭,淚流滿面。
“你媽嘴殼殼硬!×你媽!”老幺理屈,語塞,蹩進里屋。
銀花脫光了臟衣服,手里拿著件干凈衣服正要罩上身,一對面袋樣的奶子晃動起來;老幺高粱稈似的雙臂箍著銀花腰身,下體抵住銀花渾圓的臀,順勢將銀花摁倒在床。銀花索性張開身體,寫出“大”字。金鎦子冷冷的臉浮動在銀花眼前,她想水蓮有對畫眉眼咋個?老天報應讓她男人風光兩年后,在工地干活摔斷右手,截肢成“獨臂大俠”!金鎦子和這種騷婆娘纏在一起,銀花氣難平。那天早上賣菜回來,還看見他倆蹲在河邊洗衣服,眼角眉梢都齷齪!銀花過路沒招呼,彼此心照不宣。下午就聽說這對狗男女不見了,他們去的地方,銀花知道。金鎦子兩個月前,曾經找他談過,可是來寶兒咋辦?還是留下吧,苦是苦,還有命樣的土地。當銀花想著過往時,老幺蹭上來,氣喘吁吁地端著銀花的圓臉,就想啃咬,“啵兒一個,嗯?”銀花嗔道:“酸臭得很:要死了?!”
“馬上!”老幺說。
“馬下,包樣。”銀花推開老幺,他滑下床,蹲在床邊,雙手捂住了臉。可是一樣東西在頭頂輕彈一下,掉在地上,老幺定睛一看,一支春耕煙,家里從沒閑錢買煙。看銀花正忙不迭藏著啥;老幺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他操起床邊的木棍狠狠地敲在銀花雪花白的大腿上,頭上;銀花措手不及,“嗷——”叫了一聲,鉆到床下。腿上火辣辣的疼,鼻腔里一股腥氣直竄,熱熱的液體淌出來。心里憋屈得想掏心掏肺,于是她赤裸著胴體,趴在床下,顫抖著嚎啕大哭。
“欺負我媽!“來寶幼兒園小班,放晚飯學回來,將灰太狼書包甩在地上,順手要去抄一把鐵錘,但擰不動。
老幺看著嘟著小嘴,斜睨著自己的來寶,又好氣又好笑,將粗棍子扔到一邊。說道:
“幺兒,是我。我不敢打你媽了。”
“你是哪個?”來寶黑黑的眼珠轉動了一下,平時來家里的小鎦子叔叔,對他娘倆真好。
“他是你爸。回來帶你的。”銀花穿好衣服,擦干凈臉上的血跡,對著老幺冷冷地吐出一口帶血絲的唾沫,在暮色里頭也不回地離開。
上城
喜來寶前兩年幾乎沒了爹,后十八年等于沒有娘。在鄉村長大的孩子,帶著陽光和清新空氣的味道。二十歲的來寶長得膀圓腰壯,身板活脫脫隨了他娘,讓鄉親想起長得敦實的公牛。單眼皮,澄澈的眼睛,飛毛腿,哪家大盤小事,在喧鬧的人群里總閃現著他的身影,人們說:喜老幺有福;特別是來寶在何秀外出打工,杳無音信,他開始和小春歡天喜地,設想明天光景的時候。小春偎在來寶身邊,那時滿山坡桃花開得絢爛,硬著她的老爹拽回去,關在房里一頓打罵,不讓外出,嗚咽了一月,在抑郁中病得沒了人樣,“桃花謝了春紅,太匆匆”,她也匆匆一世輪回。現在就留下來寶一個人,守望明天:他在家里守著責任地里的橘子紅了又青,青了又紅;秋冬時節,小河溝里的水,嗚咽著奔向白水江;春夏復至,它帶著掙脫殘冬陰霾的欣喜,一路閃著锃亮的波光,奔騰向前。可希望呢?就是那灶孔里火星漸冷的灰燼,就是眼前老爹的末路。老爹傴僂著瘦小的身子,迎出來,對兒子說:
“來寶啊,你看你都沒人樣了。剛才家友兒來約你,你咋個想嘛?”
“約我干啥子?幾郎舅不唬就嚇,有啥子好事?”來寶悶聲道,他腦子里浮現出家友兒仨兄弟強買強賣的情形:在母校的香樟樹下,家友兒仨兄弟,一個抱,一個揍,一個拽,硬生生把一個二半山的鄉親唬住,將一背簍干筍子拖到手。
“你不曉得,人家都不做小生意,買挖挖機,走正路子找錢啦;說兄弟伙跟錢沒仇;還想推磨盤放響屁,弄大買賣,做火炮子要你搭把手!”老幺,仿佛看透來寶的心思,極力慫恿來寶卸下成見。但來寶和家華兒結上了梁子,那得從半年后得知鎮上何秀的景況說起。
當冰凌將南方的這座小鎮包裹得嚴實,黑瓦鎮像沉睡在冰窖里。山坳間,鳥語清脆,應和著公雞的啼叫;黑黢黢的山頭,頂著沉重的彤云,好容易吐出一道白,鎮上勤勞的人家,總在天麻麻亮的時候,窸窸窣窣地摸索著下床,在寒意直透脊背時,摁亮了電燈,其中一盞那一定是被山坳里,白水江邊的何秀掐亮的。
何秀的勤勞聰慧有口皆碑。上中學時,她騰出時間春種秋收,寒暑假跟父親走街串巷,倒賣山貨,或養豬喂牛,還在周末幫母親做石磨豆腐,蒸出可口的桐子葉粑粑。
黑瓦鎮就一所中學,何秀和來寶在同一個班,兩人都是好苗子,老師的愛徒。他倆同桌,來寶的記憶里存著一張何秀的黑白照片:一到夏天,何秀烏黑的劉海上,掛著晶晶亮的汗珠,盡管她不時捋秀發,但是,圓潤飽滿的額頭上還是掛著一綹濕潤的長發。來寶同何秀一起回家時,家鄉濕熱的天氣也澄亮有趣,一出校門,他倆在四散零落的嬉鬧聲里,走過雨天,來寶腳下生泥,滑到高坎子下面,又氣又惱,何秀格格地笑得彎腰捂肚子,來寶乘她恣意笑時,一把拉住她,她滑下來,跌到他懷里,羞紅了臉,不再笑鬧。一次恰好被同村同班的家華兒看到這一幕,他對著空氣啐一泡唾沫,頭也不回離去。中考那幾天怪事連連,何秀、來寶全班同學在飯后上吐下瀉,公安介入調查,水落石出,家華兒戴上锃亮的手銬蹲了半年班房,這潑皮在何秀后勤上任廚師的表兄,提著小炭錘將懸在駝背柳上的鐵塊敲得當當響的時候,他貓著腰鉆進食堂,將果導片摻進食堂的飯菜里;出于對少年犯的人性關懷,警局的人沒張揚,白天里人們說家友外出打工掙大錢;夜幕將黑瓦鎮罩住時,鄉親嘰嘰喳喳起來:媽逼,光光想著害人,活該造哈孽。但不管怎么說,何秀和來寶在此事里被買單,在歲月的淘洗中得學會討生活,何秀像一只風箏放飛在異地的天空。
一年后,當來寶將一把嶄新的落地式電扇扛回家的時候,何秀居然回鄉來請他喝自己和家友兒的喜酒。“幸福的子彈一定和速度與激情有關,可是現在我拿什么來留住你?你這像山間小鹿一樣可心的人兒!”來寶想著,將從同學那里賒的電扇放下,抹了一把在陽光下閃亮的汗珠,說:好嘞,沒得說,家友你們扣起手做點小買賣,可真行啊!其實是覺得家友兒真他媽行!而且家友兒上半年才在大年初一的時候,煤氣中毒死了剛討半年的老婆,那女人是他從發廊里帶來的“雞”,家友兒曾在江邊茶室“守塘子”,經常在日落時,瞥見從塑料簾子罅隙里灑落的粉紅色光暈,有長發的嬌俏剪影在簾子后面晃動,他蹩進去兩回,女人就跟他回了“家”,實際是奔赴在黃泉路上。仗著家底厚,又在挖鄉村公路時耍了些彎彎繞,新建的鄉村公路自然就盤繞在他家門前,家華放藥,家友揀浮財,硬生生在自己的路子越來越逼窄的時候,橫刀奪愛。他年輕的心,跳動著憤怒的火焰,卻細究不出其間原委。
雖是初夏,也覺一陣刺骨的冷,來寶病倒,在何秀的婚禮上缺席了,禮金都是老幺去送的。老幺晃悠著身子一進門兒就說:
“你媽×,做夢都念著送電扇給何秀姑,她稀罕得很!有本事你跟老子自己扛去啊——?”
“要活出人樣來,是不?!”老幺,俯下身,瞅來寶雖然有點蠟黃,卻不失剛毅的臉。來寶著紅背心,翻身一骨碌起床,端起滿木盆涼水,從頭頂嘩嘩直倒下來。他像輸了底氣的霸王,需要抖擻點精神,破釜沉舟,贏回百二秦關。
來寶不想看到何秀烏溜溜的那雙眼睛,自從她成了家友的女人,來寶不敢直視她忽閃的目光,只覺得她還和以前一樣,一看來寶,那眉睫像一對翩然飛舞的蝴蝶,惹得來寶渾身燥熱不安。當宏達礦業公司的煙囪開始“突突突”吐出滾滾濃煙的時候,黑瓦鎮的耕地已經被蠶食得七零八落,隔壁得福嬸子和馬大伯娘嫌賠得少,站在田邊地角不讓建筑隊施工,被防暴隊逮上車,押在看守所,馬大伯娘在看守所里,直著嗓子罵自己在北京軍分區的兒子,總算在晌午時見到了飯菜;而得福嬸子罵得唾沫橫飛,看見得福嬸子,吃了飯,抹抹嘴,響亮地打嗝,只得將一口唾沫從干澀的喉嚨咽下,怏怏地抱著膝蓋腦殼安靜下來。臨了,在賠償價錢上松了口,才放了回來。黃昏,來寶獨坐在山梁梁上,凝望難得寂寞的煙囪切割著的暮色,暮色里鴉雀忙著搬家,它們從甜棗樹的低枝椏搬到高一點點的枝椏,養育子女也就心安,此時來寶望著天邊淡退的晚霞,嘴角微微向上翹。
這時“蓬——”一聲沉悶的巨響,黑瓦鎮上空騰起一陣蘑菇云,那蘑菇云罩在家友兒家屋頂,像從天而降的磐石。來寶還是在中學課本里見過,我國原子彈點火實驗成功的彩圖,那騰起的也是這種炭黑的云朵。
“出事了,是何秀家!”來寶向走出門想看究竟的老爹撂下一句話,就爬去對面山坡何秀家。當他氣喘吁吁地站在彌漫著強烈刺鼻氣息的天井里時,家友兒正扶著他家老姐,蓬著頭,黑著臉走出來,她姐手臂熏得炭黑,炭黑中一塊皮肉不知去向,留下血淋淋的創面,手臂抖抖索索,呻吟得人心發怵;何秀在忙亂中找來包扎傷口的紗布。見何秀沒事,來寶舒了口氣。家友兒扶著工友猴星一瘸一拐走過來,上了三輪摩托,來寶急忙跳上開過來的另一輛三輪;在車里,家華兒扶著他不斷呻吟的老姐,眉頭擰成疙瘩,正不知所措。電三輪在鄉村路上趄趄趔趔,顛簸,顫抖,哼鳴著,一路向前奔向醫院,身邊一輛警車呼嘯而過。當來寶從醫院回來的時候,聽村里猴五說他去醫院看一趟,兒子猴星的耳朵炸懵了,聽不見;何秀被抓走了,嗚噓吶吼地上了警車,說他家違規生產煙花爆竹,營業執照上是她的名字;是啥子鬼找的噢!猴五說著,搖頭,擺手,留下一個傴僂的背影。一個月后,來寶打聽到何秀在本地Z市服刑,刑期一年,當他緊緊握住何秀的手,看到她淚流滿面,來寶咬咬牙,暗暗為何秀叫屈;他下了一個決定。
來寶伙同雄兒上了K城,找了堂兄,堂兄直嘆氣,說現在建筑行業不咋個行銷,他們正在修建的樓盤,如芝麻開花節節高,眼看就要喜封金頂,哪知說停工就停工,資金鏈斷毬嘍。臨走堂兄撂下一句:進不了建工集團礙毬不斗事,你懂行,水電安裝沒問題,可以混口飯吃,有活路會叫上你們。
老公的哲學
李曼兒偎依著老公壯碩的身體,老公環抱,接著右臂稍用力,一把拽上像面團樣癱軟的她,壯碩與嬌俏的疊加,竟如此和諧!迫切地追逐著生命的原點,找尋生命噴薄而出的巖漿。李曼兒呻吟著,貪婪地執著于原點,夢兮還是現實兮,恍然中不情愿地睜開眼。聽見老公如雷的鼾聲,震顫得人心發冷,她多想像剛才一樣墜入甜蜜的夢鄉,可那是過往或者曾經。現在,她看看自己日漸豐腴的胴體,心里一陣懊惱,自怨自艾地努力過濾春夢的殘渣。現在,老公盧瀚和自己形同陌路。自從他發現和自己的女人生活在一個屋檐下,仿佛兩個永遠無法咬合的齒輪,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棲身之所,打哈麻將,注冊四五個QQ,偶覓得有姿色的女人聊天約泡,當然好友里也有熟人,比如單位惹人眼饞心熱的琦君就是。最有趣的還是邀上三四個驢友四處觀光,人生嘛,走走看看也就過來了;當然,這些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正如 李曼兒不想要現在這個局面。現在他倆井水不犯河水,連半年前風貌改造,他也簽字付錢走人,懶得和李曼兒說起此事。 難得周末,加上琦君昨晚半夜不睡,總賴著不下線,他也大義凜然,一副不陪美女不是男人的樣子,你想:現在網聊有多水,即使聊得熱火朝天,愛也不容易;明知琦君剛離異,拿自己當備胎,他也愿意。昨兒傍晚,一條短信“瀚哥:來,想你!”就讓陸瀚加速度來到琦君離異后租住的蝸居。琦君雅致,人到中年,也難掩風韻,這女人的嫵媚張揚在骨子里。時至初夏,她一溜淺發攢在發髻下,掩映鵝黃的發帶,著一襲冷艷香凝,將胴體曲線勾勒得一覽無余的旗袍,眼前這女人妖媚性感而端莊;穿過長廊靠近她,盧瀚的呼吸急促而粗重;情不自禁攬她入懷,長廊漸漸掩藏在蒼茫的暮色里,一簇火苗在燃燒,琦君迎著他的唇,蘭香入懷。“瓦解了牡丹的抵抗,我們一起涅槃?”盧瀚攬著琦君,瞇縫了眼,突發詩意,有些狐疑地問;雖然琦君的小蠻腰有些僵硬,但眼睛里注滿期待,盧瀚有些茫然,琦君的雙臂卻柔柔地環在他的腰際。
“天啊,鬼才相信你冰清玉潔!我最討厭你那貌似高貴的靈魂,和眼前充滿頹蕩之氣的肉體!可是他們卻是你生命的孿生姐妹!”一位鼻梁高挺,器宇軒昂的男人從暮色里走過來,盧瀚相信眼前走來了“哈姆雷特”,否則哪來這排山倒海的氣勢?他后退兩步,距離立即被淺淺的暮色填埋。
“用你美麗的毒舌去哄騙你的情人,噢,不,現在應該是妻子!”琦君一字一頓,脊背卻在暮色里顫抖。
盧瀚終于明白眼前這人是琦君的丈夫,他們演的這是哪出呢?彼此還這樣在乎,看來自己英雄救美,反倒成人之美了。“呃,你們慢用。”盧瀚說完,頭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里,他的氣質就在:身處風口浪尖能全身而退還不失幽默。他親眼目睹的一幕至今想來還心有余悸。在挑水巷一同長大的強仔,那天在電話里死纏,說自己覓了半生,偷得半日閑,總算找對了另一半,要叫盧瀚到千嬌月看“弟媳”。盧瀚心里直打鼓,在挑水巷自家對面,他天天都碰到弟媳,接送孩子,弟媳清秀沉靜,打個招呼,莞爾一笑,那眉梢才舒展開來。捱到千嬌月,纏綿慵懶的音樂回蕩在曖昧的光暈里,盧瀚一看強仔心醉神迷地摟著一個女人,那黑裙勒出渾圓的臀,血紅色高跟鞋踩在綿軟的薩克斯曲子上,也踩在遙遠的云彩上。他忽然想出去透口氣。走到歌廳門口,忽聽人聲嘈雜,石級那邊幾道寒光在夜色中閃現,“轟啷——嘡——”鋼管碰撞了欄桿,或是摩挲著石級。盧瀚忽覺浸在一片寒意里,仿佛幾道寒光已經狠狠刺進后背,他踉蹌了一下,幾步躥進千嬌月,還未及向強仔喊出“跑!”只見十幾個身影已經杵在眼前,迷離的光暈中,那些影子越來越近地逼近強仔,強仔健步如飛,彈跳力突然爆發,他一躍而上,未及站穩,就飛身而下;盧瀚仿佛看到秋風起時,那片在風中不停地打卷飄零的落葉。
“沒便宜那狗雜種!閃人!”盧瀚嗅出白牙里咬出的腥氣,那女人被一瘦高個男人,擰著一把頭發,挾持而下,她黯啞著嗓音苦苦哀求;一團黑影罵罵咧咧一涌而下,消失得無影無蹤。在巡邏的防暴隊趕來時,盧瀚將肋骨摔斷十二根并刺穿肺部的強仔送進醫院,對昏迷中的強仔說:你真他媽現場直播,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著啊?”可是現在的自己,在腦海里過濾強仔的片段時,自己的生活也仿佛是在復制著自己說過的話,他有些老炮兒的抓狂,自己的江湖,自己怎么就沒能作主!他突然想回家了,打開門,妻子李曼兒沒有像想象中的那樣,坐在電視機面前,邊看韓劇邊翻渡邊的作品,而是不見蹤影!李曼兒外出經常不帶電話,這次同樣如此,每次都好像作好了外出就不再回來的打算。盧瀚坐在客廳里,家里井井有條,一塵不染,入戶花園里的山茶開得七零八落,恰似李曼兒呆在家里被自己忽視了的寂寥時光,想一想她在夜色里散步,順便遛狗,帶了丑丑,一前一后,就知道她有多孤獨;她的經脈隱約在白皙透明的肌膚里閃現,西瓜紅的夾克衫將瘦削的雙肩包裹,白色的貼身內衣,直瀉下來的披肩長發,將頸項襯得雪白,越發惹人愛憐。而他竟然忽視了一個事實,就是他想起自己的妻子,總是在戀愛季節的樣子,而她當下的模樣,他的意識仿佛習慣忘記。在黑暗里靜靜地坐了幾分鐘,究竟在等待什么他也不清楚,生命就這樣漫無目的地從出生駛向死亡,難免悲涼,但是有多少人就這樣寂寞地生死,就像天地間的江湖客不用問來路和去處。雖然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續,老母在兄弟家添了個胖乎乎的兒子后,就樂得抱孫子,不在自己的耳邊嘮叨,他也樂得自在,但有時虛空卻泰山壓頂般襲來。窗外,車聲漸行漸遠,對面人家的燈光漸漸暗淡成玫瑰的光暈,他在不急于剝裂開一個事實前酣然入睡。夢中,李曼兒還是自己初識時的模樣,自己整個高中稀里糊涂,神思總在下課時,到隔壁班門口偷看她那雙露出淺笑就特別明亮的眼睛上飄忽。后來從Z城上來,借居姨母家的李曼兒考上幼教班,盧瀚上了財校,在不同的省城上大學。寒暑假,都回到K城,在朔風漸起的黃昏,李曼兒外出散步的時候,總是將狗狗丑丑帶出家門,盧瀚看她瘦削的肩甲包裹在玫瑰紅的薄衫里,內襯一件雪白的內衣打底,頸項的肌膚晶瑩剔透,惹人愛憐。他準備好狗食,早早等在仡佬河邊,接近丑丑,漸漸地就親近了曼兒。想起這些,盧瀚在夢里咂著嘴,心里甜津津的。但男人們說,家中紅旗不倒,外面彩旗飄飄,同事們在祝賀盧瀚晉升為國稅局副局長時,他端起酒杯和大家觥籌交錯,酒酣之時說,醉眼迷離地瞟一眼琦君說:男人從來不能說自己不行!是不,君君?琦君嬌嗔道:你壞!盧瀚呵呵呵從胸腔滾出一陣驚雷般的笑聲,腆著肚子說:我快嗎?才九十碼,你曉得。哈哈哈——眾人爆發出一陣哄笑,哄笑聲里有某種他們想印證的東西,這恣意的哄笑里,發泄著他們多余的荷爾蒙。
白 光
半年前,李曼兒下班時,剛走到樓下,看見整棟樓用粗壯的鋼管搭起了腳手架,一些穿著白點子“迷彩服”的工人,站在架子上,有正在粉刷外墻的,其中一工人正在拆除她家的防盜籠。她穿過膩子粉刺鼻的樓道,匆忙回到家里,推開窗戶,站在窗口,拿著雞毛撣子,朝正在撬防盜籠螺絲的工人粗壯的手臂擊打,聲音因為不知所措而尖銳:“你干嘛?”只見一雙眼睛凝視著自己,似湖水般清透,卻隱藏著憂傷;一張臉英俊而不失堅毅,它們在眼前一晃而過;重心失衡,一雙粗壯的手掌在眼前揮舞了一下。看見眼前的工人“哎呦!”一聲,徐徐下滑,她驚呼:“抓緊!”同時狠狠地抓住了經滑輪簌簌下滑的安全繩,眼前的工人總算安全“軟著陸”;李曼兒輕拍凹凸有致的心口,長長舒了口氣。后來聽樓下果果說,市政府新政,得拆防盜籠。
習慣了盧瀚隔三差五的出差,即使他在家,早已習慣了彼此的漠視。李曼兒習慣在上班前沖個涼,不說步履生香,也通體清爽。改行后,李曼兒不喜歡老干局里的陰郁和壓抑,旁邊辦公室年近五十、瘦得風都吹得倒的副局老饒,你見他一對細長的眼睛總用余光瞄一眼你,仿佛老在揣摩你;特別是在李曼兒來了單位好幾年,肚子沒見動靜之后,老饒對自己越發近乎,李曼兒覺得這人真厭惡!辦公室人少,他會在身后輕敲你的臂膀;甚至有一次,李曼兒經過樓道口上樓,旁邊兩位同事攀談著已走下樓,老饒從后面走上來,忽地攬了一把李曼兒的腰,低語道:不好意思,太擠了!李曼兒憋紅了臉,明知故罵道:“你他媽的,哪個孫子?沒長眼!”老饒訕訕地躥到面前,回道:“是我,不好意思咯;嘻嘻,明兒見!”說完擺了擺手,溜之大吉。雖說沒有肌膚之親,看著老饒的側影,李曼兒還是覺得惡心!原本富有光澤的白皙肌膚就吸引著男人,而自己近年來日漸豐腴,她渾然不覺,疑惑自己略施粉黛的體味,特別是“大姨媽”光臨時,步履間的淡淡的甜腥,招惹了誰;從此李曼兒養成一個習慣,出門前都要沖個澡,而且素面朝天。
李曼兒趿著拖鞋走進衛生間,脫下薄如蟬翼的蠶絲鏤空睡衣,不知什么時候起,她開始喜歡精致生活,衣服講究款式、質地和顏色,也許是從偶爾看到圈子里的同齡女人,生養孩子后的疲沓開始;當然她也看到孩子跑在父母前面時,他們臉上洋溢的光芒,那時會從心底想起“家”,漾起一陣對生活的絕望,那是自己不敢觸碰的堅硬,也是盧瀚的阿喀琉斯之踵。瞬間,就可以讓心底的灰色植物瘋狂生長,繼而讓一切化為灰燼。她那散發著成熟女人氣息的胴體,罩在花灑里噴出的水柱中,朦朧中不失滋潤肌膚的光澤。隱約有尖銳的鉆墻聲傳來,李曼兒將兩手放在胸前,遲疑了一下,前兩天樓下王果果家在重新裝修房子,應該安全,她想。衛生間彌漫著清新的海飛絲味道,她將濕淋淋的秀發圈在干發帽里,繼續在“雨絲”的歡歌里享受清涼快感。水汽氤氳,乳房飽滿秀挺,臀部豐潤鼓實,小蠻腰像一塊由果林過渡到草原的豐饒土地,她們完美地閃現在氤氳的水汽里。她對自己身體的變化滿意,歲月是把雕刻刀,天然完成了對她豐胸提臀的雕刻。衛生間里,慢慢地透出一點點光,光暈漸漸洞開,在一點點鑿開的空穴里,一只眼睛閃亮著陽光下湖水的波光,那波光瞬間燃燒成一簇熾焰。李曼兒在臥室穿好衣服,走到衛生間拉開百葉窗,赫然看到衛生間外墻上洞開了枯葉蝶般大小的口子,那道白光從小孔中透過來,像一只枯葉蝶棲息在上身,她無處可逃,想弄清楚眼前的事實。
“砰砰砰——”一陣敲門聲,急促得像想說明什么。李曼兒惱怒地打開房門,看到眼前的工人,她愕然;他急切,滿頭大汗,昨天湖水樣清澈的眼睛不敢直視她,囁嚅道:改水管也是風貌改造,我……你丈夫留的號碼,主任挨戶通知,他沒接……
“滾!——”盧瀚的處變不驚和眼前這毛頭伙子的方寸大亂,讓李曼兒怒火直躥上來,她低吼道;喜來寶在她低吼的余韻里,轉身蹬蹬蹬下樓去了,身后帶起一張飄飛的紙屑。李曼兒疑惑地拾起來,只見用碳素筆寫得幾個圓潤的漢字映入眼簾:對不起,我看到了——你的身體!如果可以,我想面見你,表示歉意!電話:13578088594。李曼兒徐徐地癱軟在沙發上,惱怒,驚疑,羞赧,接著體內騰起燃燒的烈焰,臉上火辣辣地撲過一陣熱浪。“我這是怎么啦?難道自己是寂寞開落的梨花?”她自說自話,想理清已忙亂開始的清晨。李曼兒去了單位回來,忐忑不安地坐到黃昏。隔壁果果打電話叫茶室打麻將,她推說頭痛;她想起果果家裝修房子,是想給孩子裝一間嬰兒房。昨兒果果挺著大肚子和自己說:娃兒嘛,沒有的人想要;現在就在肚子里鬧騰,伸胳膊踢腿的,我想打麻將現在就有意見!李曼兒仿佛被螞蜂蜇了一下,她故作鎮定,輕笑一聲。早上下班去菜市場買菜,兩個女人在身邊攀談起來,一個是買菜的,另一個是賣菜的。賣菜的女人瘦小,黃頭發,她喋喋不休地說:真靈啦!人家給我算了一張,說我三十歲過后交好運,果真是。三十歲前自己剛離婚,帶著娃兒東跑西藏,像逃荒;三十歲后,重新找了一個,想,只要穩重,實誠的,后來真交了好運,日子好過啦!賣菜的女人將一把芥藍裝好,遞給瘦小的女人,說:哎,那先生說我的好運從四十五歲開始,不過我剛過四十這坎,慢慢時來運轉,好啦!準哈。李曼兒暗自發笑:人間萬象,女人們都學會了改變,難怪八字先生能忽悠人。
夜幕低垂,籠罩著K城,她站在拆除了防盜籠的窗前,想起那雙明澈的眼睛,遙望著天邊閃爍的星辰,忽覺得天高地遠,心境舒闊。盧瀚不是不想離,她知道他熬了多年副處,想要個美滿家庭的美譽,過渡到競選正處。這樣倒也相安無事,彼此不問來路和去處,李曼兒知道:這位在上財校時,開始迷戀自己的男人,讓自己開始迷戀他的時候,他已經慢慢走遠;那自己得找尋生命的出口。
她鼓足了勇氣,撥打了白天管道工留的那個電話。
“喂,請問你是?……”對方傳來的問詢聲,急切而有磁性。
“我是,呃……”李曼兒掛斷了電話。
“真的,我是誰呢?”她自說自話。
秋 涼
喜來寶拿著電話咂摸聽筒里繚繞的余韻,他仿佛嗅到一縷香軟的氣息,觸摸到家鄉小河水雞蛋清般的滑潤。來異鄉K城這半年,走了苦累的白天,就是酣眠的夜晚;阿雄忍受著這份累,待包工頭發了工資,裝在褲袋里鼓鼓囊囊的時候,接到一個女人的電話,他就心急火燎地出門。來K城一個月時,入秋天涼,菊花村一帶的城中村里,異鄉的人們勞累了一天,他們將平時在拆遷現場拾掇的柴禾聚攏來,燒起柴火;大家圍坐一圈,說著生活的苦樂。新寡后帶著兒子去K城討生活的小春,看到兒子福娃啃著饅頭,從隔壁浙江張姐家出來,她不無遺憾地對大伙說,下午拾荒時看到好一箍蒸鍋,都碼好綁上推車了,那老板偏說他要的。實際我家還是啥子都有,飯煲一個,電磁爐兩個,菜板好幾塊,還有臺舊電視看;剛抱回來的時候,放不出來呢,福娃對我說:你是憨包,插頭不是恁個插的!你見他蹲在地上,有模有樣地鼓搗一陣,就有雪花點點和人影了!這時張姐家靈兒一蹦一跳地跑出家門,拉起福娃圍著柴火唱啊,跳,火焰映紅了他們的臉,“泥娃娃泥娃娃,泥呀泥娃娃,也有那眉毛也有那眼睛,眼睛不會眨!”靈兒唱罷,“格格”的笑聲清脆得讓所有的人,都看到了生活的萬花筒。喜來寶眼前閃過何秀的臉,他們在上學路上摔得一身泥水的樣子,還有她那可以讓積雪融化的笑,一年半的光景,說短不短,說長不長;孩子們玩乏了,回家安睡。大人們守著柴火,守著一份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