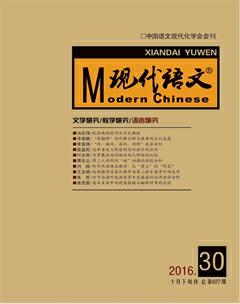《紅高粱》戰爭描寫的人性視角
○胥巖妍
?
《紅高粱》戰爭描寫的人性視角
○胥巖妍
摘 要:傳統戰爭小說注重揭示戰爭的殘酷和破壞性,從而表達人們對戰爭的厭惡之情,以及對安定與和平的渴望,對來之不易幸福生活的珍惜。而戰爭造成的流血和死亡被掛上英雄的勛章,榮譽成為了療傷的靈藥,崇高的光環掩飾了戰爭帶來的創傷。莫言的描寫直面血淋淋的戰爭場景,并從戰爭對人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的影響入手,通過人性的角度來解讀戰爭。
關鍵詞:《紅高粱》 戰爭 人性
傳統戰爭小說通常以慘烈的戰爭場景震撼人心,讓人的記憶停留在血肉橫飛的戰爭記錄中。戰爭中的英雄人物往往從國家安危、民族大義的高度出發,被塑造成一種高大英勇、不畏犧牲、勇當大任的光輝形象。榮譽的光環籠罩著戰場英雄,鮮血與死亡是忠誠與英勇最好的證據。模式化的英雄人物和戰爭描寫充斥著傳統的戰爭文學,莫言的《紅高粱》以一種新的視角,站在人性的角度去更好的解讀戰爭,讓我們以一種新的方式思考戰爭,以一種新的視角去觀察戰爭。
《紅高粱》講述了一個發生在高密東北鄉這片黑色土地上的紅色故事。在墨水河邊打死鬼子少將的著名戰斗,是這個故事發生的大背景。這個背景就像是盛著高粱酒的大酒壇,這片高粱地上的人和事仿如那千千萬萬的高粱,這人與事的交織仿如那釀成了的高粱酒,這個酒壇裝滿了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故事,這個酒壇承載了那一代人的生存狀態,“我奶奶”一生的傳奇沉淀在了這個酒壇中,“我爺爺”一生的豪氣被這個酒壇記錄著,“我”那羅漢大爺的悲慘終結沉入了酒壇深處,“我”家的大黑騾與羅漢大爺相伴著棲息在了酒壇中,“我”的那些鄉親們、同“我爺爺”戰斗的那些弟兄們,都一同地在這酒壇中實現了永遠的團聚。戰爭這個大酒壇,讓人們彼此的故事有了牽連,讓人們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釀造香醇來填充它。
莫言一改傳統戰爭描寫的宏大敘事模式,不重戰爭過程和戰爭結果,而是以戰爭作為背景和線索,將人的故事作為重點,填充戰爭的骨架,從“人性”視角入手,去觀察戰爭狀態下人的最本真的狀態,以及戰爭對人性的影響,從而引發人們對戰爭破壞性的深層次思考。就如莫言所說的“小說家寫戰爭,要表現的是戰爭對人的靈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戰爭中的變異”,我們就是要從戰爭所揭示的人的生存狀態、心理狀態和精神狀態入手,在戰爭所造成的生命財產安全破壞之外進行更深層次的解讀。
一、人性的赤誠狀態
羅漢大爺可以算作是“奶奶”家的忠仆,這樣一個忠厚老實的人,卻遭受了世上最殘酷的死亡方式。羅漢大爺為了保住“奶奶”家的騾子,惹惱了鬼子,頭皮被鋒利的刀刃開了口子。騾子被迫牽到工地后,羅漢大爺還不忘叮囑工人“你珍貴著使喚,這兩頭騾子,是俺東家的”,羅漢大爺滿心都是自己的東家,還有東家珍貴的騾子,一時間他忘了自己頭上的鈍痛,也不在乎自己的話是否會惹惱鬼子。羅漢大爺遇到了一個絕好的逃跑機會,本已經離開的他卻因為東家騾子的一聲嘶叫折了回去,就此錯過了唯一的一個機會。然而黑騾卻認不出遍體鱗傷的羅漢大爺,拒絕離開。本是要救騾子離開的羅漢大爺,不能容忍自家的騾子變成吃里扒外、忘恩負義的混賬東西,用鐵鍬向騾子發泄憤怒。因為騾子錯失離開良機的羅漢大爺,最終落得一個被生割活剝的結局。
羅漢大爺是這黑土地上的小老百姓,在“奶奶”家安安穩穩地做著長工。但是他忠于這個家的一切,必要的時候不惜付出血的代價。他為了東家的騾子,不惜再次身陷險境,這個樸實農民用自己的鮮血,在這片黑色的土地上書寫絢麗的忠誠。但是面對不識自己、里通外國的黑騾,劉羅漢發自內心深處的憤怒讓他忘記了處境,忘記了恐懼,哪怕丟了性命也要處置忘恩負義的叛徒。沒有人教導過劉羅漢家國大義,源自他靈魂深處的自覺讓他忠于自己的家自己的國。他不為留名千古,只為忠于內心的選擇。面對生與死的抉擇,人性方顯其真面目。戰爭以檢測者的角色,以最嚴格的標準,檢驗著生活在東北鄉這片土地上的百姓,讓他們以最為赤裸的狀態呈現自己。
二、人性的本真狀態
“我奶奶”為了給慘死的羅漢大爺報仇,邀請冷支隊長和余司令來商量。“奶奶”說道:“后日一起把鬼子汽車打了,然后你們就雞走雞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1]并毫不含糊地像男子一樣,咕咚咕咚地喝了摻著羅漢老爺血的高粱酒。將羅漢大爺視為親人的“奶奶”張羅報仇一事展現了她直爽、率性、英氣的一面。而奶奶自然樸實的語言,流露出她心中的大義:“買賣不成仁義在么,這不是動刀動槍的地方,有本事對著日本人使去。”[2]這是一種自覺的民族歸屬感和認同感,不需要刻意的灌輸和提醒,在遭受侵犯時這種意識會主動地覺醒,充斥著每一個普通人的靈魂,這就是在戰爭狀態下觀察到的深度靈魂狀態。它真實地反映了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的精神高度。這就是新式戰爭小說以戰爭視角解讀人性,從人性角度反思戰爭的意義所在。
膽小、遲鈍的王文義在余司令打鬼子的隊伍里就像一個笑話,但是王文義進入游擊隊的理由卻是嚴肅地直戳人的心窩。王文義的三個兒子被日本人的飛機炸成了碎塊,不分左右、膽小怕死的他被妻子送到游擊隊的隊伍里。喪子之痛、血海深仇——這就是王文義當游擊隊員的原因,縱使他害怕死亡,自己不是當兵的料,也要留在隊伍里,見證一個鬼子的死亡,便是對他死去兒子的一份祭奠,這是慰藉他們在天之靈的唯一方式。之后親眼目睹妻子慘死的王文義,跳出保護屏障,將自己暴露在鬼子的視線中,高喊著“孩子他娘”死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面對妻子的死亡,王文義的心也死了,他心中的愛與恨混雜交織,心痛、絕望與仇恨一齊涌上心頭,沖昏了他的理智。在戰爭與死亡面前,人的心靈與精神狀態被赤裸裸地披露,殘酷的現實襯托了人性的真實。
在這片高粱地里,殺人越貨的那一批人,同時也是精忠報國的那一批人。在戰爭面前,土匪和英雄的本色,在同一批人身上彰顯。“我爺爺”余占鰲司令殺過人搶過親,實在算不上什么正道人,被稱作土匪頭子一點兒都不為過,但是官職、地位、好名聲都收買不了他。“誰是土匪?誰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國的大英雄”[3],這便是橫在“我爺爺”心中的一把尺子。余占鰲強勁有力的話語,揭示了當時人們的一種心理狀態:人們不管自己處在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他們不需要任何人來賦予他們任何使命。他們為了自己心中的愛恨情仇在高粱地里穿梭,這樣的生命狀態,不禁讓現在的人汗顏。這種自發的斗志,無形中嘲笑著推脫的不肖子孫。歷史車輪的前進,并未必然地帶來物種的進化,這是戰爭揭露的事實為我們引發的又一思考。
三、人性的扭曲狀態
孫五在鬼子的威逼下用殺豬刀零割活剝了羅漢大爺,這段慘絕人寰的酷刑在作品中的刻畫讓人不忍卒讀,而孫五卻是親手行刑人。他將作為屠夫的一身本領施展在了自己的同胞身上,在此之后精神錯亂,再之后便口歪眼斜,鼻涕口水淋淋漓漓,話也說不清了。在生與死面前,善與惡的抉擇就變得分外艱難。我們無法評判孫五在面對死亡時做出的選擇,我們只能說他的結局是他得到的應有的報應,而孫五作為戰爭的犧牲品,也只是一個可憐人,這就是戰爭造成的人性的扭曲。戰爭以一種絕對的權威來施展自己的魔爪,因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直面死亡,所以難逃魔爪的人其內心在不同程度上都會留下無法抹去的陰影。就如高粱地里彌漫的濃烈的腥甜味,它不僅浸透了人的感官,更是浸透了人的靈魂,它在殘忍的歲月里伴隨了“我父親”一生——終其一生,他無法擺脫。
戰爭帶來的傷害從來不只限于肉體,心靈上的傷痕更為刻骨。人性有時便在戰爭的逼迫下走入歧途,被扭曲的面目全非。
四、人性的丑陋狀態
冷支隊長滿口答應幫羅漢老爺報仇,并向“我爺爺”放出了鬼子汽車路過的情報。“我爺爺”帶著那支連瘸帶拐、連傷帶病不到四十人的隊伍埋伏在河堤里。這樣的一支隊伍,兵力不足、裝備簡陋,然而士氣高亢,戰斗頑強。“爺爺”喊一聲打,響應者寥寥無幾,最后打到了這個地步,每一個死去的人都是鐵打的英雄,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是鋼筑的好漢,他們用生命守衛著腳下的土地,用鮮血染紅了摯愛的家園。這場仗打得異常慘烈,隊伍里的人死得不剩幾個,鬼子也元氣大傷,這時冷支隊長帶的兵才出來收拾殘局。冷支隊長大模大樣,假情假意,面對余司令慘死的兄弟作秀似地鞠了一躬。面對共同的敵人,冷支隊長將私心放到第一位,看兩方相斗,坐收漁利,而同胞的性命只是他謀權得利的籌碼。什么是英雄,什么是正義,冷支隊長打著保家救國的旗號,干著殘害同胞的行當。在戰爭中,有些人的本性發生了徹底的變異,人面對流血和死亡可以無動于衷麻木不仁,那些丑陋的真相被無情地揭露,沖擊著人的道德和良知。
五、人性的張揚狀態
整個故事是在戰爭的背景下發生的,但戰爭場景的刻畫描寫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奶奶”和“爺爺”相識相伴的傳奇故事穿插在緊張、血腥的情節中,他們為我們還原了一種人性的原始的張揚狀態,讓我們被這種人在殘酷的環境中對于自我、對于愛情、對于生命的意義的追求所震撼。“我奶奶”十六歲時被迫嫁給了麻風病人單扁郎,但“奶奶”盼著自己能有一個“識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熱”的好女婿,不愿自己的一生就這樣荒廢在這樣一個了無生氣、毫無希望的家,“奶奶”抱著一顆毋寧死,不茍活的心,“上馬金下馬銀”的日子也動搖不了“奶奶”的堅定決心。在“奶奶”看來,作為一個人活著的意義,就在于追隨自己的心,勇敢地愛,勇敢地活,舒適的生活完全撼動不了“奶奶”堅守的心。所以“奶奶”才能不懼世俗地同“爺爺”在高粱地里相親相愛,以高粱般火紅的熱情燃燒自己、釋放自己,尋求心靈真正的歸屬。就如奶奶瀕死的質詢:“天,什么叫貞節?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過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的十八層地獄。我該做的都做了,該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幾眼這個世界,我的天哪……”[4]這段是奶奶一生情感的釋放,奶奶熱愛生命,渴望幸福,在追求幸福的路上,她不怕采取離經叛道的方式,只要幸福肯來眷顧,罪與罰的代價也是值得的。在“奶奶”身上,閃耀著追求自我,渴望自由的光芒,在一個舊的時代,她身先士卒地樹立了典范,以超越的精神做出“新”的表率。莫言在一次講座中提到“我想,作為小說家筆下的歷史,首先是一部感情的歷史。人性很難用經濟和政治的方法來分析,只能用感情的方法分析……進行一種人性化的表述”[5]。紅高粱這段歷史,就是莫言筆下的一部感情的歷史,他以一種剝離的方式來寫戰爭中的人,通過人在戰爭中的表現,來進行對人性層面的深層次的解讀。
與“奶奶”相對的便是“我爺爺”,“爺爺”原本是個優秀的轎夫,但自從不小心看到“奶奶”玲瓏的小腳后,他心中的情感便泛濫的一發不可收拾,他靈魂深處的野性與狂放由此被喚醒,自此這片黑土地上便多了一個匪氣十足的英雄人物。“奶奶”激活了“爺爺”向往新生活的熱情,“爺爺”便從殺人越貨開始走向了通往新生的路,“爺爺”的命運是由“奶奶”改變的,“奶奶”喚醒了他沉睡著的種種本性,造就了一個出入在槍林彈雨、血雨腥風中的英雄人物,這個英雄在守護自己所愛的人的同時,也讓這片紅高粱的土地上又多了一個守護者。“爺爺”的感情自遇到“奶奶”才有釋放的機會,而他性情的真正面目才得以彰顯,并在艱苦的奮斗和艱難的掙扎中延續了下來。
“奶奶”是個知恩圖報、有情義的女子,她為了給羅漢大爺報仇犧牲在了戰爭上,她柔嫩肩膀上深深的紫印是她光榮抗爭的標志。“奶奶”生命走到盡頭之時,她只是遺憾自己的一生沒有活夠,但并未抱怨自己生命意外的終結。在不舍與豁達的情感相對比時,方顯“奶奶”本性中的純凈與美好,這便是人性最美的港灣。而“爺爺”只是一介草莽之人,不懂大義,但在情與理面前還是站在了理的一邊,因為他要為了自己的那支隊伍負責。血性之人本應更重情義,但是為了大局他要殺了養育自己的親叔。在恩情和法理的對決面前,方顯“爺爺”本性中的顧全大局和重情重義,這便是人性赤誠的所在。就像一些作家在創作中奉行的“第一是‘人’寫得好不好的問題,人寫好了一切大的問題都解決了。而我的創作目標,就是無限利用‘人’和‘人性’的分量,無限夸張‘人’和‘人性’力量,打開人生與心靈世界的皺折,輕輕拂去皺折上的灰塵,看清人性自身的面目,來營造一個小說世界”。[6]這便是戰爭小說中以“戰爭中的人”的視角切入的重要性,人性的狀態是對戰爭最有力的批判和控訴。
人性在戰爭面前的不同狀態被赤裸裸地揭示出來,真實的人性直擊我們的靈魂,它的沖擊力不亞于血淋淋的事實。莫言對于戰后場景的描寫是直接的,還原了戰后慘狀,他以圖景式的描寫,用最大的力量,沖擊著人的內心。“三百多個鄉親疊股枕頭臂,陳尸狼藉,流出的鮮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地浸泡成稀泥。”[7]越是這么直接地直面鮮血和死亡,越是能解釋那種迸發自內心深處的愛恨情仇。雷達說自己在讀《紅高粱》時,“我體驗著一種從未有過的震怵和驚異:震怵于流溢全篇的淋漓的鮮血,那一直滲瀝到筋骨里的感覺;驚異于作者莫言想象力的奇詭豐贍,在他筆下戰栗著、號叫著的半個世紀前的中華兒女,不僅是活脫脫的生靈,而且是不滅的魂靈”[8]。雷達從殘酷現實的描寫走進真實內心的描寫,從戰爭實況走向人性原貌,在雙重的震撼力下感受戰爭的別樣寫法。
“戰爭文學如果不單獨描寫戰爭過程,而能通過這一過程寫出其對人的命運、生存狀態、精神走向等的深刻影響,讓我們從中聽到人性的闡述,看到靈魂的歷險,它便可以成為一種重要的‘人的文學’。優秀的戰爭文學,應該具有這樣的特點。”[9]《紅高粱》借以高粱的形象揭示了人的生存狀態和命運走向:火紅的高粱地象征著蓬勃向上的生命。“一顆高粱頭顱落地”,便象征了生命的終結。這毫無準備的一幕,展現了生命的脆弱和命運的無常。王文義“司令——我沒有頭啦——”的慘叫,揭示了人們面對無常命運的恐懼。“鮮嫩的高粱在鐵蹄下斷裂、倒伏,倒伏斷裂的高粱又被帶棱槽的碌碡和不帶棱槽的石滾子反復傾軋。”[10]高粱被傾軋的慘狀象征了慘遭蹂躪的人們,戰爭讓人的肉體流血,讓人的心千瘡百孔。在戰爭面前,再絢爛的生命也感動不了無情的戰爭。生命的終結彷如高粱穗墜地那般隨意,越是看似不經意的描寫越能觸動人的內心。在戰爭的大背景下,人們在火紅的高粱地演繹著生命的傳奇故事,穿插的每個情節都在揭示人的狀態上獨具內涵,我們在聆聽人性的闡述中,體味著靈魂的歷險記。
注釋:
[1]莫言:《紅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25頁。
[2][3]莫言:《紅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24頁。
[4]莫言:《紅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64頁。
[5]莫言:《我的文學經驗:歷史與語言》,名作欣賞,2011年,第10期。
[6]周新民,蘇童:《打開人性的褶皺——蘇童訪談錄》,小說評論,2004,第2期。
[7]莫言:《紅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4頁。
[8]雷達:《游魂的復活——評紅高粱》,文藝學習,1986年,第1期。
[9]黃修己:《對“戰爭文學”的反思》,河北學刊,2005年,第5期。
[10]莫言:《紅高粱家族》,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15頁。
(胥巖妍 河南洛陽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 47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