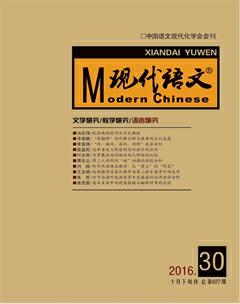新舊交替時(shí)代知識女性的艱難轉(zhuǎn)型
——《傷逝》中子君命運(yùn)的時(shí)代意蘊(yùn)解讀
○隋雪純
?
新舊交替時(shí)代知識女性的艱難轉(zhuǎn)型
——《傷逝》中子君命運(yùn)的時(shí)代意蘊(yùn)解讀
○隋雪純
摘 要:《傷逝》塑造的子君,既反映出知識女性在新舊交替時(shí)代背景下由于獨(dú)立觀念萌芽產(chǎn)生的新思想及突破意識,也揭示了在婦女覺醒局限性和社會(huì)舊規(guī)的雙重桎梏下知識女性體現(xiàn)出的順從和妥協(xié)。解讀作品中子君命運(yùn)的時(shí)代意蘊(yùn),有助于剖析新舊交替時(shí)代背景下知識女性處于艱難轉(zhuǎn)型期的生活狀態(tài)與心理特征。
關(guān)鍵詞:《傷逝》 子君 魯迅 知識女性 時(shí)代意蘊(yùn)
魯迅作為中國具有開創(chuàng)性與獨(dú)特見地的偉大文學(xué)家與思想家,其作品著眼于社會(huì)的各個(gè)階層,深度揭示社會(huì)病痛。女性作為社會(huì)的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自然成為魯迅筆下的一個(gè)重要敘寫群體。魯迅作品中塑造的祥林嫂、單四嫂子、華大媽等一系列女性人物形象,筆觸和立場均超越了性別層面,通過展現(xiàn)不同社會(huì)層面的女性形象,深入地體察和刻畫了所處時(shí)代女性的生活和內(nèi)心,深刻剖析了制約女性解放的桎梏和枷鎖。
正如魯迅所言:“凡中國人說一句話,做一件事,倘與傳來的積習(xí)有若干抵觸,……免不了標(biāo)新立異的罪名,不許說話;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為天地所不容。”(見魯迅《熱風(fēng)·隨感錄四十一》)。處于封建社會(huì)向近代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的女性,一方面“做了舊習(xí)慣的犧牲”(見魯迅《熱風(fēng)·隨感錄四十》),另一方面又體現(xiàn)出在時(shí)代大潮呼喚下的覺醒意識。《傷逝》是魯迅唯一的反映知識分子愛情悲劇的短篇小說。作品主題表明,身為啟蒙思想家的魯迅認(rèn)識到愛情婚姻問題對女性自身及社會(huì)的雙重意義,因此通過著力刻畫具有強(qiáng)烈時(shí)代反抗精神的子君這一人物形象,將當(dāng)時(shí)所處新舊時(shí)代交替的社會(huì)背景對知識女性命運(yùn)的影響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在魯迅女性主題研究中,大多根據(jù)女性群像展開對魯迅塑造的女性特征的綜合闡釋,但對單一形象的知識女性人物研究少有涉及。基于彌補(bǔ)罅漏的初衷,筆者將從《傷逝》的女主人公子君的命運(yùn)解讀這一視角,探究其在生命的不同時(shí)期表現(xiàn)出的兼具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思想覺悟與封建禮教意識的人物形象入手,通過闡釋分析其愛情婚姻命運(yùn)發(fā)展和性格的兩面性,分析魯迅作品中的知識女性形象所蘊(yùn)含的時(shí)代特質(zhì),探究新舊交替時(shí)代知識女性的艱難轉(zhuǎn)型。
一、新思想與突破意識——獨(dú)立觀念的萌芽
魯迅在《關(guān)于婦女解放》一文中言:“我只認(rèn)為(女性)不自茍安于目前暫時(shí)的位置,而不斷的為解放思想,經(jīng)濟(jì),等等而戰(zhàn)斗。”正是基于自身對新女性素質(zhì)的理解,魯迅在《傷逝》這部作品中著力刻畫子君作為新時(shí)代女性對舊傳統(tǒng)的抗?fàn)幣c完全自主的愛情觀,彰顯了子君在新舊時(shí)代交替背景下的新思想以及新思想影響所引發(fā)的積極抗?fàn)幮袨椤?/p>
在魯迅的筆下,主人公子君和涓生都是在五四新思潮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具有資產(chǎn)階民主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子君是受到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在“五四”運(yùn)動(dòng)及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的召喚下,她與涓生相識,用“稚氣的好奇的”求知欲與涓生“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xí)慣,談男女平等,談易卜生,談泰戈?duì)枺勓┤R……”,這些新事物、新理念、新精神開拓了這位少女的眼界,激蕩著她的心靈,滋潤著她心底抗?fàn)幣c獨(dú)立思想的幼芽。她思考著如何反抗封建父權(quán),如何沖破牢籠,如何爭取個(gè)性解放和婚姻自由。
緣于所接觸到的獨(dú)立觀念,子君不顧胞叔和父親反對與涓生同居:“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quán)利!”。作品中子君吶喊出 “我是我自己的”的心聲,除卻她對自由婚姻的堅(jiān)持外,更是對自我的發(fā)現(xiàn),是成為一個(gè)真正的“人”而非家庭附屬物的呼喚。同樣,在和涓生同行遭遇“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時(shí),“她卻是大無畏的,對于這些全不關(guān)心,只是鎮(zhèn)靜地緩緩前行,坦然如入無人之境”。這些描述無不浸透著子君在與舊秩序抗?fàn)幹械臎Q然之態(tài),同時(shí)也折射出是魯迅對子君所表現(xiàn)出的“新女性素質(zhì)”的欣賞。
正是受到所處時(shí)代新思想的影響,子君作為魯迅筆下唯一的新女性,表現(xiàn)出了強(qiáng)烈的突破意識,具體表現(xiàn)為她追求新生活的勇敢和無畏,這是魯迅筆下其它女性形象所不具備的新特征。子君所表現(xiàn)出的突破意識程度,甚至是同時(shí)代的男性所少有的。例如,子君強(qiáng)調(diào)自我,這種徹底的思想比文中的涓生還要“透澈,而且要堅(jiān)強(qiáng)得多”;再如,子君無畏面對譏諷和嘲笑,而涓生的全身卻“有些瑟縮”。魯迅采用手記的方式可謂別出心裁,它可以賦予人物更加直接的內(nèi)心剖白,從而更生動(dòng)地反映當(dāng)時(shí)境遇下雙方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在行文中,涓生以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將自己的行為一再和子君進(jìn)行對照,以子君的義無反顧反襯自己的怯懦,以子君的無私反襯自己的自私。人物對比充分表現(xiàn)了子君作為一個(gè)新女性所應(yīng)具備的魄力,也昭示了新社會(huì)家庭中男女雙方地位開始重新定位。
子君所追求的自主愛情是對于傳統(tǒng)包辦婚姻的突破與自立,她將新婚姻理解為雙方思想的一致性和關(guān)系的對等性。就關(guān)系的一致性來說,她認(rèn)為“愛情必須時(shí)時(shí)更新,生長,創(chuàng)造”。小說敘事者“我”和子君說起這一話題,“她也領(lǐng)會(huì)地點(diǎn)點(diǎn)頭”。可見,子君認(rèn)為,婚姻應(yīng)基于雙方愛情和未來生活的共識。就關(guān)系的對等性來說,從《傷逝》的第一人稱視角開篇即“寫下悔恨和悲哀”,即男性對男女關(guān)系中自我的批判和重新審視意識,都昭示了男女雙方的關(guān)系和地位在未來的正確發(fā)展方向,即平等,互敬,互愛,而這一點(diǎn)也可以在魯迅《南腔北調(diào)集·關(guān)于女性解放》的論述中得到佐證,即“必須地位同等之后,才會(huì)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會(huì)消失了嘆息和苦痛”。子君期盼迎來“雷峰塔的倒掉”(魯迅《墳·論雷峰塔的倒掉》)的欣喜,期盼自由婚姻,兩情相悅,自由結(jié)合。正是如此刻畫賦予子君這一人物形象鮮活的生命激情和無限的希望之光,也是該作品所代表的新時(shí)代女性之美,更是作品中對新生活的寄托與希望所在。
因此,無論是對自由自主新思想的接受,還是對舊時(shí)婚姻的突破,子君道出了新舊時(shí)代交替時(shí)期婦女群體中覺醒的心聲,彰顯了所處時(shí)代的女性由囿于封建大家庭框架下走向獨(dú)立自主、要求融入社會(huì)的積極生活態(tài)度,體現(xiàn)了“五四”時(shí)期一代婦女新的覺醒,成為知識女性思想發(fā)展過程中獨(dú)立意識的萌芽。
二、順從與妥協(xié)——婦女覺醒局限性與社會(huì)舊規(guī)的凸顯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魯迅《娜拉走后怎樣——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xué)校文藝會(huì)講》可視為對《傷逝》的極佳注腳。子君作為一個(gè)具有新式思想但又“大概還未脫盡舊思想的束縛”的婦女,在封建禮教“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yǎng)也,近之則不遜,遠(yuǎn)之則怨”的女性歧視觀猖獗而新式女性解放思想影響力尚未擴(kuò)張的社會(huì)中,只能順從與妥協(xié)。
社會(huì)大背景對人的影響力是極大的。子君深受社會(huì)舊規(guī)的束縛和重壓,使其即使具有一定的覺醒精神和追求,也只能“仿佛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社會(huì)對女性的歧視使子君沒有自食其力的出路,缺乏經(jīng)濟(jì)獨(dú)立能力的子君只得與現(xiàn)實(shí)妥協(xié),終日相伴柴米油鹽,擔(dān)憂失去生活來源的涓生拋棄她,從而逐漸“凄苦與無聊”,不再學(xué)習(xí)和探索,被困在庸俗和怯弱的牢獄內(nèi)。
處于新舊價(jià)值觀之間徘徊的新女性是痛苦的,子君基于初步新式教育以及對涓生的愛情之上的覺醒,帶有自身的局限性。“她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dá)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gè)空虛,而對于這空虛卻并未自覺。”子君新異的思想不被社會(huì)所容,幾千年來綱常倫理對人們靈魂的歪曲使子君最終對自己的信仰產(chǎn)生了懷疑。同時(shí),子君個(gè)體的覺醒能力局限使其不再繼續(xù)探索和學(xué)習(xí)簇新的思想,而是逐漸頹唐,從一個(gè)積極開放的新式女性成為受家務(wù)瑣事所累的庸婦,從立場堅(jiān)定趨于迷茫和彷徨。
同時(shí),作為“五四”時(shí)期被資產(chǎn)階級個(gè)性解放思潮喚醒的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青年,子君的思想是“淺薄”的,存在著單純追求自身幸福的思想弱點(diǎn),“她當(dāng)時(shí)的勇敢和無畏”不是因?yàn)樗哂袕氐椎慕夥藕酮?dú)立意識,而只是因?yàn)閷︿干M義的“愛”,這使子君的斗爭缺乏堅(jiān)實(shí)的理論根基:一旦與涓生男女之情擁有暫時(shí)的穩(wěn)定和自由,子君便失去解放自身的決心和動(dòng)力,故而逐漸從“目不斜視的驕傲”到“很頹唐……她的勇氣都失掉了”成為了必然。
基于此,涓生與思想逐漸發(fā)生質(zhì)變的子君在價(jià)值態(tài)度方面顯現(xiàn)出分歧乃至隔膜,失去心靈共識的雙方使得愛情的基石無從保障。而涓生的自私更加快了愛情悲劇的發(fā)生,在經(jīng)濟(jì)上具有巨大依附性的女性只能成為男性困境時(shí)的犧牲品,在涓生失去穩(wěn)定工作時(shí),為自保,涓生選擇拋棄子君:“我沒有負(fù)著虛偽的重?fù)?dān)的勇氣,卻將真實(shí)的重?fù)?dān)卸給她了。她愛我之后,就要負(fù)了這重?fù)?dān),在嚴(yán)威和冷眼中走著所謂人生的路。”在與涓生的愛情破滅以后,子君只得再次順從,重歸父兄身邊,“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親——兒女的債主——的烈日一般的嚴(yán)威”,再次在封建禮法與社會(huì)歧視的重壓之下茍延殘喘直至死亡。
子君的人生實(shí)際上形成了一個(gè)由突破舊規(guī)到走投無路重回舊規(guī)的輪回。由于教育與思想的影響,子君呈現(xiàn)出突破舊規(guī)的積極傾向,但迫于社會(huì)背景與自身思想?yún)T于更新以及經(jīng)濟(jì)上的無法獨(dú)立,子君最終未能完成與舊規(guī)的徹底決裂,如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一樣,仍舊只能回歸、順從、妥協(xié)。體現(xiàn)出“一切人都在矛盾中間,互相抱怨著過活”(魯迅《熱風(fēng)·五十四》)的社會(huì)總體特征,呈現(xiàn)了“悲劇將有價(jià)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魯迅《墳·再論雷峰塔的倒掉》)的濃厚悲劇色彩。
三、新女性何去何從
秋瑾言:“欲脫男子之范圍,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學(xué)藝不可。”(《秋瑾集》)魯迅通過子君在艱難轉(zhuǎn)型期的生活狀態(tài)描寫與心理活動(dòng)刻畫,正是對這一觀點(diǎn)的闡釋與證明,即知識女性“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經(jīng)濟(jì)權(quán),我以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話”。
子君作為“五四”時(shí)期的女性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反抗封建禮教、追求個(gè)性解放,到最后愛情破裂抑郁而終的過程,闡明了舊中國的“時(shí)代女性”獲得解放的唯一出路是“只有投身到革命風(fēng)暴中去,才能擺脫她們的動(dòng)搖性與妥協(xié)性,才能找到她們的出路,才能永遠(yuǎn)結(jié)束這悔恨與悲哀”。換句話說,女性的真正解放,只有在對整個(gè)社會(huì)封建勢力的徹底反抗、獲得經(jīng)濟(jì)獨(dú)立與社會(huì)活動(dòng)話語權(quán)的前提下才能夠?qū)崿F(xiàn)。否則,個(gè)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只能淪為空談,終究會(huì)遭到封建勢力的扼殺,并最終導(dǎo)致愛情悲劇。
事實(shí)上,對于新女性如何轉(zhuǎn)型問題,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獨(dú)特見地:第一,在家應(yīng)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huì)應(yīng)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項(xiàng)權(quán)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zhàn)斗;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quán)更要用劇烈的戰(zhàn)斗。”沒有經(jīng)濟(jì)地位而只能依附于涓生的子君缺少要求“平均分配”的話語權(quán),沒有經(jīng)濟(jì)收入的她更無法要求和丈夫獲得“相等的勢力”。因此,子君這一知識女性在新舊交替的激烈沖突時(shí)代轉(zhuǎn)型,其失敗并不具有偶然性。文學(xué)可視為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反映,“某些社會(huì)畫面可以從文學(xué)中抽取出來,這是毋庸置疑的”[1](勒內(nèi)、奧斯汀,2005:111)。子君代表了整個(gè)婦女群體在轉(zhuǎn)型過程中遇到的普遍問題,通過對子君這一人物的解讀可以透視作品中反映的時(shí)代的知識女性命運(yùn)的發(fā)展特點(diǎn)。這也是魯迅給予中國女性提出的極為深刻的命題:解放是經(jīng)濟(jì)的獨(dú)立,是地位的重塑,更是自我意識的蘇醒。
“在封建禮教依然控制一切的社會(huì),女性的抗?fàn)幒茈y看到希望。”[2](李徽昭、李繼凱,2014:140)小說中子君的奮斗、勝利、挫折、妥協(xié),以至棲牲,引伸出這樣一個(gè)道理:在強(qiáng)大的封建勢力面前,知識女性個(gè)人的反抗斗爭總是軟弱無力的。通過這一人物的塑造刻畫,魯迅將子君的愛情婚姻家庭故事鋪展在讀者面前,意在通過指出有了覺悟和一定的抗?fàn)幍⑽赐耆珨[脫社會(huì)思想桎梏的知識女性的命運(yùn)悲劇的根本原因。顯然,當(dāng)時(shí)“四千年來時(shí)時(shí)吃人”的封建社會(huì)制度正是造成子君個(gè)人悲劇的社會(huì)根源,而生活在這樣一個(gè)社會(huì)制度之下的子君無法擺脫社會(huì)環(huán)境對個(gè)人思想的影響,即使已經(jīng)受到新思想的啟迪,對自由的生活與愛情充滿向往,并勇敢付諸于行動(dòng),最終由于在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上的依賴性導(dǎo)致了其獨(dú)立性和自主性的喪失。同時(shí),封建女子的家庭觀念業(yè)已滲透進(jìn)子君的骨髓里,在沒有爭取得到社會(huì)分配權(quán)和經(jīng)濟(jì)的獨(dú)立權(quán)的情況下,子君漸漸地喪失了自身人格的獨(dú)立性,拋棄了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甘心情愿地成了丈夫的附屬品。魯迅對知識女性精神與命運(yùn)的著力刻畫與博大關(guān)懷,給予讀者以深刻思考,而這也是當(dāng)時(shí)所處歷史發(fā)展階段眾多知識女性向后人昭示的教訓(xùn)。
盡管魯迅已經(jīng)洞察到女性解放的道路還很漫長,但依然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正如他在《傷逝》一開始便提出:“中國女性,并不如厭世家所說的那樣無法可施,在不遠(yuǎn)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女性由封建愚昧向具備知識和新觀念轉(zhuǎn)變,是時(shí)代轉(zhuǎn)型的需要,也是社會(huì)歷史發(fā)展的必然。魯迅用獨(dú)到筆觸著眼女性轉(zhuǎn)型問題,以犀利的筆鋒揭露出了封建勢力的頑固與強(qiáng)大,深刻地反映出了子君這一代知識青年的思想局限性和性格上的軟弱性,生動(dòng)地揭示了知識女性命運(yùn)變革及文化發(fā)展存在的種種現(xiàn)實(shí)問題,有助于廣大女性群體的覺悟和解放,具有深刻的文學(xué)價(jià)值與時(shí)代意義,供后人思索、瞻仰。
注釋:
[1]劉象愚等譯,勒內(nèi)·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xué)理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1頁。
[2]李徽昭,李繼凱:《論魯迅與莫言小說中的女性命運(yùn)》,《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論叢》,2014年,第9期,第140頁。
參考文獻(xiàn):
[1]魯迅.墳·娜拉走后怎樣[A].魯迅雜文全集[C].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166-168.
[2]魯迅.關(guān)于婦女解放[A].南腔北調(diào)集[C].北京:譯林出版社,2014:163.
[3]魯迅.論雷峰塔的倒掉[A].墳[C].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77.
[4]魯迅.再論雷峰塔的倒掉[A].墳[C].北京:譯林出版社,2014:49.
[5]魯迅.熱風(fēng)·隨感錄四十一[A].魯迅雜文集[C].沈陽:北方聯(lián)合出版?zhèn)髅郊瘓F(tuán),2013:106.
[6]魯迅.熱風(fēng)·隨感錄四十二[A].魯迅雜文集[C].沈陽:北方聯(lián)合出版?zhèn)髅郊瘓F(tuán),2013:108.
[7]魯迅.熱風(fēng)·隨感錄五十四[A].魯迅雜文集[C].沈陽:北方聯(lián)合出版?zhèn)髅郊瘓F(tuán),2013:119.
[8]魯迅.傷逝[A].魯迅全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5:123.
[9]秋瑾.秋瑾集[M].北京:中華書局,1960:32.
(隋雪純 山東濟(jì)南 山東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