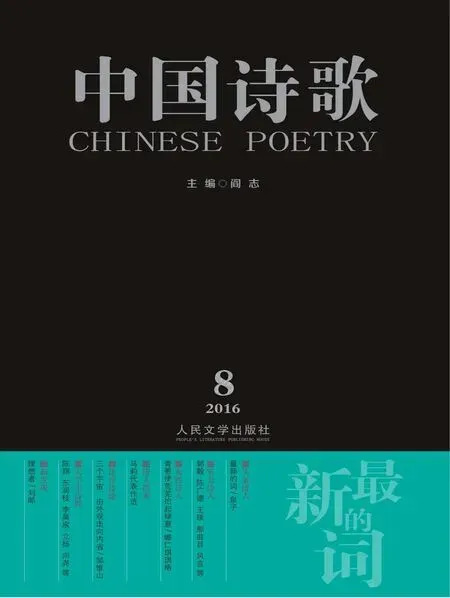我們還欠現代漢語一次辨認
□泉 子
我們還欠現代漢語一次辨認
□泉 子
古漢語,或者說,任何一種語言的輝煌,都是經過世世代代的人們,以這種語言為通道對千古不易之處的辨認來完成的。這辨認成為了一種雙向的成全,它在成全一種語言的同時,最終成全了那通過辨認,重新賦予語言以新的輝煌的人,以及以這樣的語言為標識的一個時代。從這個意義上,我們這一代詩人,或者說,迄今這近百年中的一代代新詩詩人們還欠著現代漢語這樣一次致命的辨認。
從另一層意義上,現代漢語并不始于1917年,并不始于這個所謂的偉大的白話文運動元年。波德萊爾所揭開的現代性,可能有現代漢語更為隱秘而確鑿的基因。或者說,現代漢語更是西方文明這個父,進入了東方柔軟的母體后,一個偉大的結晶。這無所謂幸與不幸,這是我們,是那之后世世代代的人們必須與之相認的命運。我們再也回不到那個單純意義上的,處女的東方了。而我們的父親是粗魯,甚至是暴力的。它剛剛完成一次對這個世界,也是對自己徹底的,粉碎性的破壞。而在今天,它正與那被它強暴后的東方,共同積攢著重回完整的力量。
我是想說,我們今天已不可能僅僅作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東方人在這里說話了;我們的立錐之地也不再是曾經的,所謂地理上的東方,而是西方文明摧枯拉朽般,全面而深入地占領這個小小的星球后,有待重新命名的一塊嶄新的土地。
在全球化急劇發展,地球變得越來越小的今天,或許,我們終將發明出一粒微塵那無分東西南北的特性。或許,只有這里,我們注視西方文明時,才能放下將我們割裂,甚至隔絕開來的分別心,而不再把西方文明作為一個他者。這樣的確認是重要的。這意味著我們已獲得了一個更為可靠而堅實的支點,這意味著西方已不再作為一座大山,一個所謂的龐然大物的陰影而得以顯現,而是我們腳下正勾勒出一個微微隆起的土丘的蜿蜒小徑。這還意味著,我們所面對的不再僅僅是一種語言的困境,也是一個時代,甚至是世世代代的共同困境。這困境曾經屬于過李白、杜甫,屬于過屈原,屬于過荷馬與但丁。但他們又通過各自如此艱難的開鑿,而為世世代代的人們奉獻了歷史的巖層上的一條縫隙。
而今天,這相同的困境再一次落在我們頭上。今天,那曾吞噬下世世代代人們的歷史的巖層正穿越著我們,我們是用一種新的喑啞來加深歷史深處的黑洞,還是以杜甫、屈原、但丁當年相同的決絕,為自己,為一個時代,為此后,甚至之前的世代開鑿出那被隔絕的藍天,那幽暗與寂靜的光芒涌入的一瞬。
這無疑是一次艱難的考驗,它同樣隱匿著巨大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