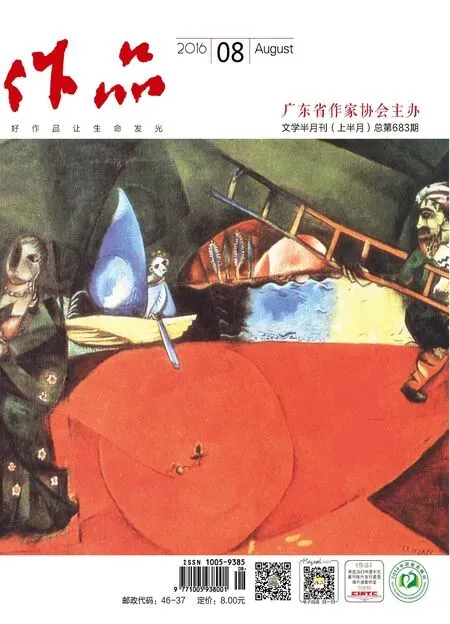環島旅行
文/馬 拉
環島旅行
文/馬 拉
馬 拉 1978年生。詩人,小說家,中國作協會員。畢業于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廣東文學院簽約作家。在《人民文學》、 《收獲》、《上海文學》等文學期刊發表大量作品,入選國內多種重要選本。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金芝》、《東柯三錄》、 《未完成的肖像》、 《果兒》,詩集《安靜的先生》。
我們這個地方離海不遠,開車的話,大約四十來分鐘。和你想象的不一樣,我們并不經常去海邊。海邊有什么好去的呢?到處飄蕩著難聞的海腥味,灰白色的泡沫黏乎乎地沾在巖石上,塑料瓶、海藻、死魚擠在堤岸的拐角處。偶爾有一片沙灘,到處都擠滿了人。每當退潮,孩子們手里拿著礦泉水瓶,小桶在巖石堆里抓小螃蟹,小魚,小蝦,亂糟糟的一群。
站在海邊,大海是黃色的,一眼望去,漫無邊際的黃上方有淡淡的山影和白云。能夠想象,海島上到處都是人,尤其是夏天。那里的海水會藍一些,有人游泳,到了傍晚,人會更多一些,穿著泳衣,試探著走進海里。在看不到的地方,還會有島嶼,那里的人少一些。杜若白常年駐守在其中的一個。
他是個警察,長得高大帥氣,略有點內向。杜若白不喜歡海,簡直深惡痛絕。他說,只有踩在大陸上,他的心才會放下來。在海島上,他總覺得像是在船上,似乎隨時有翻船的可能。離大陸那么遠,人都不精神。杜若白在的那個海島,真是一個非常小的海島,圍著它走一圈要不了一個小時。島上的常住人口很少,大約只有一百來人。到了捕魚的季節,島上會熱鬧起來,漁民習慣在島上停靠,一艘艘的漁船停在港口,看起來很壯觀。去島上的多是近海的漁民,遠海的漁民到了島上,往往會喝個爛醉,他們覺得快到大陸了。對在海上飄蕩大半個月的人來說,離岸不到十個小時基本算是到家了。
杜若白所在的派出所一共四個人,隔兩個月休息一個月,多半情況下,所里只有兩三個人,所長很少呆在島上。平時,島上太平,派出所無所事事,杜若白習慣早起圍著島跑一圈。到了傍晚,如果天氣好,他下海游泳。他的水性是在島上練出來的。即使他拼命鍛煉身體,他的時間依然多得沒地方打發。剛到島上那幾個月,還有一股新鮮勁兒,等新鮮勁兒過去,他覺得像是在坐牢。杜若白愛吃海鮮,初到島上,他每天盼著漁船回來,買螃蟹、蝦,還有他叫不出名字的魚。等和漁民混熟了,他給錢人家不要了。不就兩條魚嗎,不值錢,拿去拿去。他要是再客氣,給錢人家也不賣了。
幾個月下來,山上有幾塊石頭都摸清楚了,船和海水永遠一成不變,人還是那些人,日子變得難熬。有次,杜若白喝多了酒,半夜里下海游泳。他一直往前游,海面上只看得到星星和波光。等他感到有點累了,回頭一看,島上的燈光不見了,四周只有空闊的海水。他趕緊轉身往回游,等他扒在沙灘上躺了會兒,緩過勁兒,身體酸軟地站起來,胃里劇烈的抽搐讓他吐了出來。他的命丟了半個在海里了。回到所里,跟同事說起這事兒,同事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說,等你發過幾次瘋就好了。說完,同事嘆了口氣,這個雞巴地方,不瘋才真是奇怪了。后來,杜若白才知道,喝多了下海游泳這種事情,不止他一個人干過,幾乎每個來島上的警察都干過。
在島上呆了一年,杜若白對島上的情況都熟悉了。他不再去碼頭買海鮮,到了飯點兒,隨意找個地方坐下,總會有人請他喝酒的。隔上一段時間,他會做東,約大家一起喝酒。他買單,酒家象征性地收點錢。那么小的島,沒什么秘密可言。比如說,每到旅游旺季,島上的人會多起來,島民的家庭旅館生意火爆。到了傍晚,海灘上鋪滿了一頂頂的戶外帳篷,紅的、藍的、白的像一朵朵花開在海灘上。杜若白喜歡這個季節,可以看到不同的人,他喜歡看著年輕的情侶手拉手在海邊散步。作為一名警察,他多次在深夜去海邊巡查,帳篷里傳出來的聲音慵懶、性感,讓杜若白覺得親切。他會去海邊的礁石上抽根煙,海風把煙霧迅速地吹散。望著海邊的帳篷,他也想談戀愛了。
隨著游客來到島上的,還有年輕的姑娘。她們租下島民的房子,一般三四個月。到了晚上,她們換上性感的泳衣去海邊,看到單身的男人就主動貼過去,問要不要一起玩水,有些意猶未盡的客人會跟著她們一起去出租屋。等他們出來,多是帶著滿足的神情。派出所懶得管這些事,處理起來麻煩。所里不管,杜若白樂得輕松,他甚至會想,這也挺美好的,不是嗎?每到這個季節,島上的男人也隨之躁動起來。經常是在宵夜攤上,他和幾個島民正喝酒,看到姑娘過來,島民沖著姑娘喊,美女,來喝酒嘛!姑娘們笑嘻嘻地坐下,喝了點酒,一個沖另一個擠眉弄眼,過不了多久,姑娘站起來說,我上個廁所。心領神會的男人跟過去,消失個把小時,然后兩人重新回到酒桌上,像是什么都沒發生。剛開始,杜若白還覺得奇怪,見多了,也就習慣了。他還聽過一個故事,島上一個男的跟姑娘回去,正碰上他爸從另一個姑娘房間里出來,兩人擦肩而過,一聲不吭。島上的男人開玩笑,說誰和誰誰誰是連襟,這意思大家都懂的。如果全喝嗨了,姑娘們會逐一評點誰家伙大,誰活兒好,誰作風粗暴。桌上的男人和女人嘻嘻哈哈,又喝一杯。
大約三年前,也是夏天,游客最多的季節。杜若白和幾個島民坐在派出所邊上的燒烤檔烤生蠔,島上的蠔肉質細嫩,蠔體肥大,據說在全國能排進前五。他們喝了幾瓶啤酒,過了一會兒,其中一個打了個電話,過了十來分鐘,來了三個姑娘。她們應該剛剛洗過澡,臉上還沒有完全褪去的紅潤,穿的是短裙,露出年輕任性的大腿。杜若白掃了一眼,迅速地判斷出了她們的職業。路邊的燈光有些昏暗,她們的臉模糊而動人。杜若白主動舉起杯子和她們碰了下杯,心里想著,多好的姑娘。有人指著杜若白笑嘻嘻地說,這是杜警官,人民警察,趕緊敬杜警官兩杯,不然小心杜警官抓你們。姑娘“咯咯咯”笑了起來,像三只小母雞。杜若白擺了擺手說,不說這個,喝酒。說完又拿起了杯子,和周圍的人碰了下杯。在島上幾年,杜若白徹底變成了個酒鬼,一到晚上,不喝幾杯,他無法入睡。有人指著姑娘介紹,這是娜娜,邊上那個叫麗麗,對了,你叫什么?正在玩手機的姑娘抬起頭說,叫我小蘭。說完,看著杜若白說,你真是警察?杜若白點了點頭。小蘭似乎還不相信,她望著杜若白,若有所思的樣子。杜若白這下看清了小蘭,瘦、高,染了淡黃色的長頭發,她大概還不到二十歲。一幫人又喝了幾瓶酒,小蘭說,我想上廁所。杜若白站了起來說,我帶你去吧!其他幾個人似乎愣了一下,反應快的馬上說,對,對對,讓杜警官帶你去,喏,派出所就在邊兒上。
杜若白和小蘭并排走在街上,小蘭沒有說話,理了理頭發。走到派出所門口,杜若白拿鑰匙開門,小蘭問了句,你真是警察?杜若白一邊開門一邊說,你說呢?小蘭又問了句,里面有人沒?杜若白推開門說,都出去了,應該沒人。進了派出所,領小蘭去了洗手間,杜若白坐在外面抽了根煙。等小蘭出來,杜若白抬頭看了看小蘭,小蘭笑著對杜若白說,第一次進派出所,感覺好奇怪。接著又問,做警察好玩嗎?杜若白說,不好玩。和小蘭一起往外走時,他聞到了小蘭身上松木沐浴露的味道。回到燒烤檔,有人問,這么快?杜若白拿起酒杯說,你想多了,上個廁所能要多久。杜若白瞥了小蘭一眼,她的臉似乎紅了一下。
有幾天傍晚,杜若白在海灘碰到了娜娜和小蘭,她們在游泳。小蘭套著一個巨大的游泳圈,她應該還不會游泳,或者還不習慣在海里游泳。杜若白點了根煙,海灘上人很多,他一直盯著娜娜和小蘭,她們和別的姑娘一樣嬉戲玩鬧,像個孩子。杜若白心里動了一下,然后,又動了一下。抽完煙,杜若白走到下水的階梯邊坐下。大約過了大半個小時,杜若白看到娜娜和小蘭走過來了。和娜娜比,小蘭明顯瘦一點,她的頭發濕漉漉地搭在脖子上,肩上。等小蘭過來,杜若白打了聲招呼,游水啊?娜娜高興地說,到海邊可不就游水么?小蘭看了杜若白一眼,低了下頭。盡管曬黑了一些,小蘭皮膚還是很白,腿又長又直。
晚上宵夜,杜若白提了句,好幾天沒見娜娜了,怎么不見她來喝酒?有人笑著說,人家這會兒可能正忙著呢。杜若白“哦”了一聲說,也是。那天,杜若白喝得不多,慢條斯理的,像是在等人。喝到晚上十二點多,杜若白有些困了,他想回去睡覺。桌上幾個人喝得有點多了,又談起了女人。他們說,今年來的這批女人比去年的好。幾乎每年,都會有不同的女人來到島上,有些在島上呆個把月就走了,據說是去了別的海島,她們很少一直呆在一個島上。他們說到了娜娜和小蘭,都說娜娜活兒好,小蘭顯得有些生澀,還沒熟。杜若白聽了一會兒說,我先回去睡了。他夢到了小蘭,夢里的小蘭變成了一只海鷗,在暴風驟雨里飛。
在街上碰到小蘭,杜若白偶爾會打個招呼,她多半和娜娜在一起。娜娜活潑,見到杜若白,眼神活泛起來。杜若白身高一米八三,高大、挺拔,他穿著貼身的警服,臉上輪廓分明,再加上常年海風的吹拂,他的皮膚呈現出健康的小麥色。杜若白嗓音渾厚,如果你聽過他唱歌,你會被他深沉的男低音打動。和娜娜說話時,杜若白時不時看看小蘭,她挽著娜娜的手臂,看杜若白時帶著點羞澀,似乎他們發生過什么似的。有次在街上碰到娜娜,杜若白問了句,小蘭沒和你一起?娜娜笑了起來說,你不是看到了嗎?杜若白也笑了起來。兩人站在街上聊了幾句,娜娜說,杜警官,中午一起吃飯吧。杜若白想了想說,好啊。娜娜給杜若白留了電話說,我去買菜,快好了我電話你。杜若白說,麻煩你了。
去到娜娜的出租屋,讓杜若白意外的是沒有看到小蘭,他以為她們住在一起的。杜若白看了看房間,一室一廳,收拾得還算整潔。里面的房間里只有一張床,一個梳妝臺,還有一個小小的衣柜。外面的客廳里有一條舊沙發,一臺電視機,一個餐桌和幾把椅子。娜娜正在廚房里忙著,她扭頭沖杜若白喊,你要是無聊就看看電視。杜若白說,沒事。他站起來,走到客廳外的小陽臺,從陽臺可以看到大海,蔚藍色的一片。娜娜把菜擺上桌子,對杜若白說,兩個人,簡單吃點。杜若白坐在娜娜對面,娜娜彎下身子給杜若白盛湯,從娜娜的領口望下去,兩只蓬勃的乳房跳進杜若白的眼里,杜若白連忙把眼光收回來。它們豐滿,健康,白皙,杜若白已經好久沒有碰過它們了。杜若白有個女朋友,保持著不咸不淡的感情,一兩個月見一次面,雖然回到大陸他們可以一起呆上大半個月,剛剛升溫的感情隨著兩個月的分離又淡了下去,他們似乎是為了談戀愛而談戀愛,女友希望他早點調回去。
吃飯的時候,娜娜不停地和杜若白說話,講島上的見聞,講杜若白,說他高傲,和其他人不一樣。杜若白很想問問小蘭在哪兒,你們不是住在一起嗎?仔細想了想,又沒問,做她們那行,住在一起也不方便。杜若白吃得心不在焉,他能看懂娜娜眼里的意思。吃完飯,杜若白說,我先走了。娜娜說,這么快就走?再坐會嘛。說完,把杜若白拉進房間說,外面太熱了,坐里面吧。娜娜開了空調說,吃得一身汗,我去沖個澡。杜若白聽到“嘩嘩”的水聲,他能想象到里面的情景。坐在娜娜的床上,床很軟,杜若白的雞巴忍不住硬了。他想走,想站起來,打開門,走到外面的陽光里去。水聲讓他的心跳加速,身體發軟,他站不起來。娜娜出來時,身上披著一條浴巾,她一邊用毛巾擦頭發一邊說,我還以為你走了呢。擦完頭發,娜娜看了杜若白一眼說,你不熱嗎?杜若白把眼睛從娜娜身上挪開說,還好,開了冷氣。娜娜“咯咯”笑了起來說,我以為你會熱的。她沖杜若白做了個鬼臉,拉開浴巾。一個年輕熱力的裸體出現在杜若白面前,娜娜用浴巾擦了擦手臂,胸前,腿。杜若白看到娜娜小腹下蓬勃的陰毛,嗓子有點發干。娜娜把浴巾遞給杜若白說,你幫我擦擦背,我擦不到,還有水。杜若白接過浴巾,擦了擦娜娜背上的水珠,然后,丟下浴巾,從背后握住了娜娜的兩只乳房,接著,手伸到娜娜下面,他碰到了那片迷人的草地,山丘。娜娜發出一聲快活的呻吟,杜若白將娜娜扔到床上,壓了上去。
做完事,杜若白點了根煙,娜娜靠在他的懷里,撫摸著他的胸脯。太舒服了,真是太好了。杜若白有些感嘆,從來沒有這么好過。抽完煙,杜若白起身穿上衣服,掏出錢包,娜娜按住杜若白的手說,不用了,是我想要你。她光著身子抱住杜若白說,你很快會忘記我。杜若白沒說話,娜娜又說,我知道你喜歡小蘭。
杜若白在海灘上碰到過小蘭,她和陌生的男人玩水。甚至,他還遇到過和小蘭一起回出租屋的男人。這沒什么。他照常和小蘭打招呼,問個好。娜娜帶小蘭和杜若白一起吃過幾次宵夜,那天中午的事情,誰都沒有提。
很快到了八月底,島上最熱鬧的季節,到處都是游客。娜娜給杜若白打了個電話,約杜若白一起吃宵夜,說是小蘭要走了,給她送送行。杜若白答應了,還約了幾個人。杜若白說,晚上我請。等人到齊,已經十一點了。小蘭穿了條牛仔褲,上身套著一件T恤,臉上干干凈凈的。娜娜說,明天小蘭就要走了,今天大家喝個痛快,給小蘭送行。又對小蘭說,今天放開來,別老扭扭捏捏的。燒烤和啤酒很快上來了,娜娜喝得很猛,沒過一會兒,她已經有了醉態。她指著杜若白說,杜警官,你不喜歡我,你不喜歡我。杜若白笑了笑。娜娜指著小蘭說,我知道你喜歡她,你喜歡這個小婊子。桌上的人都笑了起來,小蘭拉了拉娜娜的手說,娜娜姐,你喝多了。娜娜摟過小蘭的腰說,我沒喝多。說完,指著杜若白說,他喜歡你。杜若白給娜娜倒了杯酒說,你喝多了。娜娜說,我才沒喝多呢,不信,我們連喝三杯。杜若白和娜娜喝了三杯,喝完,娜娜扒在桌子上。小蘭有些擔心地說,要不,我先送她回去?其他人說,沒事,休息會兒就好了,來,我們繼續喝酒。一圈人輪流和小蘭喝酒,小蘭一一應承。過了一會兒,杜若白突然對小蘭說,我們去海邊走走吧。小蘭愣了一下,有人叫了起來,哈哈,哈哈,到底還是忍不住啦!杜若白站起來,拉著小蘭說,走吧!
他們去了海邊,找了一塊礁石坐下。杜若白覺得有點撐,想吐,想尿尿。他對小蘭說,你先坐會兒,我去方便下。杜若白找了個偏僻的地方撒了泡尿,又拍了拍臉,意識似乎清醒了些。回到礁石上,杜若白點了根煙,小蘭說,給我一根。給小蘭點上煙,杜若白不知道說什么好,他到底想干什么呢?說不清楚。他想伸手把小蘭摟到懷里來,又覺得唐突,她還那么年輕。小蘭往杜若白身邊挪了挪,接著,靠在了杜若白身上。杜若白伸手搭在小蘭肩膀上,一下子自然了。他叫了聲,小蘭。小蘭吐了口煙說,其實我不叫小蘭。那叫什么?小蘭說,王哲詩,哲理的哲,詩歌的詩,是不是挺瓊瑤的?杜若白說,有點。小蘭說,我爸媽那代看瓊瑤談戀愛的,起個名字都瓊瑤了。王哲詩,杜若白念了一遍說,挺好的。他有點不習慣,叫了一個多月的小蘭,突然變成王哲詩,很奇怪。小蘭說,你還是叫我小蘭吧。杜若白問了句,干嘛這么早走,這才剛進入旺季呢。小蘭說,馬上要開學了,得回學校。杜若白“哦”了一聲。小蘭說,你不好奇我為什么來島上?杜若白說,其實,還是有點。小蘭吐出兩個字,好奇。接著,又補充了句,娜娜是我表姐。
在海邊坐了一會兒,杜若白對小蘭說,我們回去吧。小蘭說,回哪兒?杜若白愣了下,各自回去。小蘭往杜若白懷里擠了擠說,再坐會兒,你可能再也見不到我了。海風舒爽,杜若白用力地摟了下小蘭,轉個頭,親了下小蘭的頭發,又親了下小蘭的耳朵。小蘭轉個臉,把嘴唇壓在杜若白的嘴唇上。小蘭的舌頭靈巧地在杜若白口腔里跳動,杜若白的欲望升了上來,他把小蘭的手拉到他的下體,那里膨脹得厲害。小蘭的手縮了回去,放開杜若白說,不要。她對杜若白說,你加下我微信。
小蘭走后,娜娜還在島上。杜若白偶爾會去娜娜那里過夜,他們打開窗,讓海風吹進來。娜娜時不時會和杜若白講講小蘭,她說,搞不明白那小丫頭是怎么想的。她家里那么有錢,爸媽那么寵她。她的意思杜若白明白。我有些嫉妒她,娜娜說,都是爹媽生的,差別怎么就那么大,她要什么有什么,我呢?什么都得靠自己掙。不過,真不是我騙她過來的,她非要來。剛開始,我還怕我姨夫知道了打死我。小丫頭壞得很,說如果我不帶她來,她就把我的事情告訴我媽。娜娜摸了摸杜若白的臉說,你是不是有點恨我?杜若白搖了搖頭說,這也不是你的錯。娜娜說,其實,我也有點壞心思。我想,憑什么我就得過這種生活?你要來也好,以后,我們就一樣了,至少你怎么說都不見得比我干凈。杜若白的心疼了一下,他又想起了那張干凈的臉。
小蘭回學校后,杜若白沒有和她聯系,她的朋友圈杜若白每條都看了。她上課,她和同學一起出去宵夜,她買了新的包,她高數掛科了,她和室友自拍。和周圍的同學一樣,她看起來健康、活潑,有美好的未來。杜若白想起了她在島上的日子,他想,他不應該和她說話,過去的,就過去了。她還是個孩子。
小蘭給他發語音,他是意外的。他看了看微信,頭一下子大了,前天晚上,他給小蘭發了十幾條語音。重新聽了一遍,他才知道他說了些什么,他說他愛她,想她,想和她做愛。他喝醉了,失憶,做過的事情他都不記得了。小蘭回了三條,一條是“你怎么了”,一條是“你喝多了嗎?”最后一條隔了二十六分鐘,說的是“喂,你怎么了?醒了回我信息。”拿著手機,杜若白想了半天,回了幾個字,對不起,我喝多了。過了一會兒,小蘭回了條信息,沒事吧?杜若白說,沒事。放下手機,杜若白去了海邊,他望著看不見的大陸,他想,他要早點離開這個地方。
他和小蘭的聯系多了起來,多半是微信。幾乎是沒有痕跡的,他們進入了另一種狀態,每天不聊一會兒,似乎缺了點什么。有天,白天,杜若白坐在辦公室里,看著墻上的便民服務指南,杜若白想起了他的女朋友,他們已經大半個月沒有聯系了。杜若白拿出手機,給小蘭發了條微信,我想你。很快,小蘭回了一個笑臉,接著,杜若白又發了一條,我想我是喜歡你了。過了一會兒,小蘭回:真的嗎?杜若白說“嗯”。放下手機,杜若白心里輕松了很多,憋了那么久的話,說出來舒服多了。等杜若白再次拿起手機,他看到了幾個字“國慶節我來看你”。
晚上去娜娜那里,杜若白把事情告訴了娜娜。娜娜沉默了一會兒說,這小丫頭一直任性。杜若白說,不怪她,怪我。娜娜伸手抱住杜若白說,你不是有女朋友了嗎?杜若白說,估計快分了,很久沒聯系了,她受不了我整月整月呆在海島上。剛開始,她以為我很快能回去,這都三年了,等不住了。娜娜說,她還是個孩子。杜若白說,對不起。娜娜說,今晚別回去了,陪我。杜若白抱住娜娜說,對不起,我也不知道會這樣。娜娜親了杜若白一口說,這個島我呆不下去了。
娜娜什么時候走的,杜若白不知道,她沒有告訴他。杜若白買了菜,去娜娜的出租屋,開門的是另一個女孩子,杜若白問,娜娜呢?女孩子說,我剛搬進來兩天,你說的是以前的租客吧,大概是搬走了。杜若白打娜娜的電話,提示音說“對不起,你所撥打的號碼是空號,請查詢后再撥”。掛掉電話,杜若白去館子里喝了兩瓶啤酒,他覺得涼爽了些。
國慶節那天,島上的游客特別多,難得的長假,人們像潮水一樣涌向各個地方。杜若白站在碼頭,小蘭的船如果準點的話,大約六點靠岸,太陽還很大,光閃閃地照在海面上。等杜若白發現小蘭的身影時,已經七點多了,太陽沉到海里面去了。小蘭拖著行李箱,四處張望。杜若白走過去,接過小蘭的行李箱,朝小蘭笑了笑說,你白了。小蘭的手自然地挽在杜若白手臂上說,你還是那么黑。
安頓好小蘭,他們一起出去吃了個飯,沒有喝酒,兩個人安安靜靜的。吃完飯,小蘭說,你帶我去海邊走走吧。八九點鐘的海灘,到處都是人。杜若白牽著小蘭的手,沿著海岸一直走到山上,看著山腳的燈火和漫天的星星,小蘭說,真好。杜若白摟過小蘭,親吻,他的手在小蘭身上上下摸索。他抱得那么緊,小蘭說,我透不過氣來。小蘭捧起杜若白的臉說,你說你喜歡我。杜若白說,不,是愛你。
一個美好的假期。白天,杜若白上班,時不時回去看看小蘭。晚上,他們一起吃飯,做愛。小蘭瘦瘦的身體蘊含著爆炸般的能量,他們一次又一次,和杜若白夢到的一樣,小蘭像是一只海鷗,在暴風驟雨中飛翔,帶著他一起飛了起來。假期結束,杜若白到碼頭送小蘭,小蘭說,你要想我。杜若白說,嗯,肯定會的。船慢慢開了出去,從海平面消失,像是去了天國。
天漸漸冷了,島上的游客幾近絕跡,日子又回復到原來的狀態,單調,無聊。杜若白常常去海邊,望著天邊發呆。他不知道小蘭在干什么,她的喜怒哀樂遙不可及。小蘭回去后,他們經常打打電話,發發微信。在小蘭的朋友圈,他從未出現過,甚至從未提及,他像是一個隱形人,或者一個夢。也許就是一個夢,杜若白想,只要還在這個島上,外面的一切對他來說就是一個夢,不可實現的夢。
休假回到大陸,杜若白給女朋友打了個電話,約她一起吃飯。回來之前,杜若白委托小區物業幫他收拾了房間。兩個月沒有回家,里面布滿了厚厚的灰塵。一個房子,只要沒有人住,很快就破敗了。剛打開門,里面是干凈的,卻是生澀的,沒有一點人的氣息。每次回來,女朋友隔幾天會到他這里過夜。杜若白想過讓女朋友住在家里,她不愿意,她說一個人住在冰冷冷的房間,感覺特別凄涼,她還是更愿意和家人住在一起,互相有個照應。
吃飯的時候,女朋友明顯有些心不在焉,絮絮叨叨地講現在的形勢,說是什么事情都不好做,他又離得那么遠,根本沒有辦法照顧她,幫助她。這些,杜若白是知道的,從一開始,他就知道,他離大陸那么遠,即使有什么緊急的事情,也是趕不回來的。接著,女朋友開始講家里的事情,說她爸媽有點急了,覺得兩個人這么耗下去也不是個辦法,希望盡快能把問題解決。什么問題杜若白清楚,要么調回來結婚,要么分手。喝了口水,杜若白說,我想我應該沒那么快調回來。女朋友說,都三年了,還不能調回來,也不知道你平時都干些什么。我聽他們說,你們所里一般兩年就回來了,總不能一直把人放島上吧。吃完飯,杜若白對女朋友說,回家吧。女朋友看了看表說,我還有點事,就不過去了。杜若白說,好的,你忙。
在出租車上,杜若白給女朋友發了個短信,對不起,耽誤你這么久。過了一會兒,女朋友回了個信息,你也要保重,還是盡量早點調回來。你這個狀態,換哪個都受不了。杜若白說,明白,謝謝你。女朋友回,保重,有空常聯系。杜若白刪了女朋友的電話,臉上有熱熱的東西流了下來,他擦了擦,看了看窗外,城市的燈火輝煌燦爛,他愛這城市。
和家人呆了兩天,和朋友們聚過幾次,杜若白想見見小蘭。杜若白的日子空曠遼闊,他在市內沒多少朋友,再好的朋友見得少慢慢也就生疏了,他現在的朋友只剩下幾個同學以及一起長大的玩伴。他給小蘭打了電話,小蘭說,我想去看看紅樹林。
再次見到小蘭,她似乎胖了一些。紅樹林在城市的邊上,沿著海灘長長的一片。游客不多,似乎只有幾個人。潮水退了下去,水洼里還有滯留的小魚小蝦。小蘭牽著杜若白的手,沿著木質的棧道慢慢走,她看到紅色的小螃蟹,有兩只不對稱的螯,其中一只大得有些離譜。小蘭問,這是什么蟹?杜若白指著一個說,這個?招潮蟹。小蘭看了一眼說,長得真特別。杜若白說,嗯,是挺奇怪的。
小蘭逃學陪了杜若白大半個月,他們像所有熱戀的情侶一樣,看電影,去游樂場,吃喜歡吃的東西。晚上,回杜若白家里睡覺。杜若白想給小蘭買只手表,他看小蘭在朋友圈發過,說喜歡那款表,不過有點貴。他帶小蘭去了表店,找到那款表,問小蘭喜歡嗎?小蘭點頭,滿臉的歡喜。杜若白掏出卡說,喜歡就買了。小蘭說,不用,我以后自己買。杜若白說,沒關系,我送給你。小蘭說,不要。在杜若白家里,小蘭笨拙地幫杜若白收拾房間,撅起屁股擦地板,像一個戀愛中的小婦人。杜若白坐在沙發上,望望窗外,每一片樹葉都發出明亮的光。
假期結束,杜若白又回到了海島,繼續每天面對海浪、礁石和船帆的生活。他給小蘭發的信息再也沒有得到回應,每條信息后面都有一條“信息已發出,但被對方拒收了”。杜若白懶得再打電話,似乎沒有必要。他想起一個女孩的名字,王哲詩,哲理的哲,詩歌的詩,他們有過美好的過去。
(責編: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