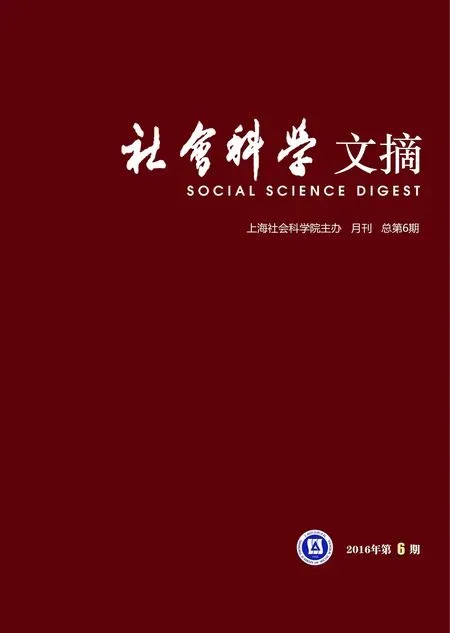“國民”的隱現
——淪陷后期周作人的反啟蒙姿態
文/袁一丹
“國民”的隱現
——淪陷后期周作人的反啟蒙姿態
文/袁一丹
在北平淪陷后期寫作的“正經文章”中,周作人最看重《中國的思想問題》這一篇。以往對這篇文章的解讀,主要依據寫定于1942年11月18日,發表在《中和月刊》,后收入《藥堂雜文》的版本,而忽略了與此相關的兩篇演講稿。其一是周作人在偽華北政委會教育總署主辦的第三屆中等學校教員暑期講習班上的講話,題為“中國的國民思想”,速記稿刊發在1941年9月《教育時報》第2期上;其二是在《中大周刊》上發現的,1942年5月13日周作人在南京偽中央大學的同題演講。這兩篇未入集的演講稿,不止于版本學上的意義,為《中國的思想問題》的再解讀提供了一些新線索。文本鏈的擴充,關鍵在處理新材料與常見書的關系。通過不同版本的對讀,從演說到文章的措辭調整中,可以發現其思想演變的中間環節,從而修正關于20世紀40年代周作人思想轉向的整體論述。
啟蒙姿態的調整
《中國的國民思想》作為《中國的思想問題》的雛形,本是1941年9月周作人以偽教育督辦的身份發表的一次講話。以“中國固有的國民思想”為題,看似脫離了淪陷區的特殊語境,周作人卻聲稱這個思想上的問題“好像一個人對于自己的身體一樣的重要”。“國民思想”之所以構成淪陷期間的“切身”問題,乃基于周作人一個相對悲觀的基本判斷:“中國的國民思想,現在已經到了病得很重的時期了,非請醫生檢查不可。”
然而到次年5月周作人作為“北方教育當局”的代表南下,受邀至偽“中央大學”發表演說時,完全推翻了此前的悲觀論調,稱這幾年來常有外國或中國朋友和他談起這個問題,以為中國國民的思想問題很嚴重,應該有對策,而他自己的態度倒頗樂觀,對此種疑慮的回應是“中國國民思想問題并不嚴重”,“中心雖然缺乏,卻不須另建”。
究竟戰時中國的國民思想是否構成問題,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如何,周作人這兩次演說的時間相隔不到一年,發言立場卻整個調換過來。要追究其突然改口的原因,一方面需對照當時的輿論環境,另一方面還得回到他個人的思想脈絡上去看。從作于1940年的《漢文學的傳統》開始,周作人便極力與“國民性”話語劃清界線,稱其為“賦得式”的理論,“說得好不過我田引水,否則是皂隸傳話,尤不堪聞”。周作人用來破解“國民性”話語的工具,一是衣食住,即生活方式上的細微差別;二是凌駕于民族特殊性之上的普遍人性。用“人性”消解“國民性”話語,明顯在偷換概念,實則是一種象征性的反抗策略。《中國的國民思想》這篇講話中周作人以對談引出“國民性”的問題:
有一位外國人問我:“中國的國民性怎樣?”我說:“中國人是人,是生物,他要生存,這是中國人的國民性,此外并無什么古怪異常的地方。”
提問者的身份特意設定為“外國人”,無異于暗示其對“國民性”的重新診斷乃是對外發言。將“國民性”等同于好生惡死的“人性”,進而等同于“生物性”,最后歸結到生存的基本要求上,這一長串等式必須置于淪陷的前提下才能得出“反抗”的結論:“因為中國人是人,是生物,要生存,所以你不讓他生存他是要反抗的。”
在淪陷后期民眾的生存需求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周作人以“人性”“生物性”為中介,將中國的“國民性”等同于生存的欲望。然而在五四時期批判“國民性”的啟蒙話語中,周氏以為中國人欠缺的正是對生存的執念。“國民性”批判本質上是一套啟蒙話語,放棄批判的立場,折射出淪陷下一度以醫師自居的啟蒙思想家所承受的內外壓力。“國民”的概念仍舊是40年代周作人談論中國思想問題的切入點,只是逐漸由對內批判的立場,轉向對外抗辯的姿態。
淪陷之下,何言“國民”?!
淪陷意味著“國”與“民”的分離。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滯留在華北的“國民”,一夜淪為中華民國的“棄民”,乃至于“亡國之民”。淪陷之下,何言“國民”?!若言“國民”,又是哪國的“國民”?現實世界中被分裂的“國—民”,在周作人文章中竟安然無恙,一方面歸因于“中華民國”在淪陷區的實亡名存;放到周氏個人的思想脈絡中,又可視為晚清經驗的復活。
周作人對“國民”一詞的特殊理解,在其留日時期雜湊而成的長篇論文中已顯出端倪。他對“文章”之意義及其使命的討論,便是以“國民”的概念為起點。與“臣民”相對的“國民”(こくみん),在近代日語中是nation的對譯詞。而nation在西方政治傳統中指涉的是一種理想化的“人民全體”或“公民全體”。從這個意義上說,nation與state的區別在于,前者是理想化的人民群體,而后者是這一群體自我實現的工具。所以nation-state在日語中通常被譯為“國民國家”而非“民族國家”。nation與state之間的這個連詞符,表明二者的關系尚未穩固,其實是被歷史地建構出來的。40年代周作人口說或文章中隱現的“國民”,其實是民族國家的代替物。
在晚清“亡國滅種”的陰影下,周作人經由日語轉借來的“國民”(nation)一詞,包含“質體”與“精神”兩個要素。“質體”即民族國家的軀殼:“同胤之民,一言文,合禮俗,居有土地,賡世守之。”“精神”作為構成“國民”的另一要素,所起的作用“猶如眾生之有魂氣”。清末周氏兄弟標舉的“國民精神”,又謂之“立國精神”,換用當時言論界流行的說法,相當于“國魂”或“民族魂”。在“質體”與“精神”之間,周作人更看重后者:
質體為用,雖要與精神并尊,顧吾聞質雖就亡,神能再造,或質已滅而神不死者矣,未有精神萎死而質體尚能孤存者也。
尊“精神”而輕“質體”,是因為“質雖就亡,神能再造”。周氏相信“亡國滅種之大故,要非強暴之力所能獨至也”。探討一國一文明之盛衰興廢,但視“精神”何如而已,不必以“執兵之數”即捍衛“質體”的軍事實力為根據。周作人以埃及、希臘等文明古國為例,試圖證明在“質雖就亡”的情境下,憑借舊澤與新潮激蕩而成的“國民精神”仍能實現“邦國再造”的理想。由此可知周作人對“亡國”的理解,不在乎國家形態之存亡,更看重“國民精神”的再造力。
基于周作人對“亡國”的特殊理解及“質體”與“精神”的二分法,才能明白他淪陷后期為何反復強調漢字、漢文學的政治作用。周作人將文學視為一種象征性的政治工作,前提是“國將不國”,或國家已淪為一種非現實的但又必須信奉的虛體。在被占領的特殊語境下,漢字、漢文學(即國文、國文學)被賦予前所未有的政治功能,甚至取代了政治生活的所有職能,這些職能在國土淪喪時已被剝奪殆盡。
問題的曖昧性更在于“國民”“國家”這些詞在淪陷區并未成為政治禁忌,無論是汪精衛為首的南京偽“國民政府”,還是始終保持特殊化的偽“華北政務委員會”都不諱言帶“國”的字眼。而日本在中國大陸分而治之的統制策略,與經營臺灣、偽滿洲國不同,亦無力將民國之“棄民”統統改造為“皇民”。故周作人演說或文章中出現的“國民”,就他個人的思想脈絡而言,可視為晚清經驗的復活;從淪陷區的政治生態與輿論環境來看,其實也毋庸避諱。
“國民”“國家”之所以毋庸避忌,關鍵在于“中華民國”在淪陷區實亡而名猶存。從七七事變后日偽在北平扶植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到以汪精衛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都頂著“中華民國”這塊招牌與重慶方面爭奪法統。對滯留在淪陷區,熟悉春秋筆法的文人學者而言,正朔雖在西南,能繼續使用“民國”紀年,未嘗不是種心理補償。據竹內好日記,七七事變后與周作人過從甚密的尤炳圻向他講述新文化人的動向,透露周作人決意在“中華民國”這一名號被取消時南下。傳聞的真偽無從驗證,但至少反映出北平淪陷后周作人在去留問題上給自己劃了條底線。其信守的“中華民國”,與具體政權無關,只是一個虛名及其象征的“邦國再造”的理想。
如果說周作人“落水”前對“中華民國”抱有某種遺民情懷,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國家與政府的分離,而這點對于周作人由清末種族革命及無政府主義培養起來的政治自我而言,正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1907年周作人針對立憲風潮而作的一篇雜感中,試圖將滿清政府——種族革命者眼里的異族政府——從中國人之愛國觀中剔除出來。他所認可的“愛國”,更接近于詩人對故土,即“生于斯,歌哭于斯,兒時釣游之地”的眷顧之情,而非晚清“志士”所鼓吹的“盲從野愛,以血劍之數,為祖國光榮”,后者被其視為“獸性之愛國”。周作人繼而從語源學上厘清“愛國”(patriotism)與政府的關系:
吾聞西方“愛國”一言,義本于“父”;而“國民”云者,意根于“生”,此言“地著”,亦曰“民族”。凡是“愛國”、“國民”之云,以正義言,不關政府。
滿清政府在受種族主義熏陶的知識人眼里,不僅是與“國家”相分離的,甚至處于“國家”的敵對面。在異族主政的背景下,愛國即意味著與政府為敵。
“勝國之民,何言政事,何云國民?”國家與政府尤其是異族政府相分離,作為從晚清種族革命經驗中形成的思想前提,并不適用于40年代北平淪陷的特殊語境,但對于選擇“苦住”的周作人而言,這或許是他賴以維持“遺民”幻覺的救命稻草。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摘自《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