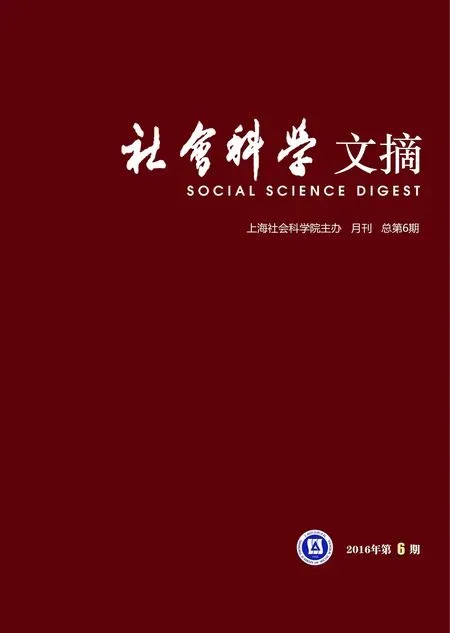我國憲法解釋的范圍
——兼與《憲法解釋程序法(專家建議稿)》第6條商榷
文/馬嶺
我國憲法解釋的范圍
——兼與《憲法解釋程序法(專家建議稿)》第6條商榷
文/馬嶺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這是推動我國憲法解釋體制的啟動、進而推動我國憲政建設的重要一步。我國目前采用的是立法機關解釋憲法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憲法解釋的空間有多大?由于其他國家基本采用司法機關解釋或專門機關解釋制,而蘇聯等采用立法機關解釋體制的國家并沒有多少解釋實踐,因此,我們沒有什么經驗可以借鑒。我們首先要弄明白的是憲法解釋應當解決、能夠解決什么問題,在立法機關解釋的體制內憲法解釋在什么情況下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在韓大元教授等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解釋程序法(專家建議稿)》中(以下簡稱《專家建議稿》),其第6條〔解釋的事由〕規定:“有下列情況之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解釋憲法:(一)憲法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的;(二)憲法實施中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憲法依據的;(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等規范性文件可能與憲法相抵觸的。” 筆者認為該條款方向大體正確,但不夠細致,其中第(一)款和第(二)款試圖構建出一種脫離違憲審查的獨立的憲法解釋機制(與我國目前的法律解釋類似),其必要性和可能性需要進一步說明;而第(三)款主要涉及的可能是合法性審查而不是合憲性審查,其中更多地可能涉及法律解釋而不是憲法解釋。
憲法解釋在我國憲法實施“主”渠道中的作用
憲法需要實施,實施憲法的“主”渠道是立法機關的立法,即把原則的憲法條文具體化、把實體的憲法條文程序化;除此之外,實施憲法還有“次”渠道,即對立法機關的立法是否符合憲法進行監督、審查,以保障立法的合憲性(其中可能涉及憲法解釋)。許多國家認為,既然立法機關已經占據了實施憲法的“主”渠道,那么實施憲法的“次”渠道就應該是立法機關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如普通法院或憲法法院),而我們的體制是把實施憲法的“主”渠道和“次”渠道都交給了立法機關,這樣就產生了自己監督自己的問題。
雖然憲法解釋與監督憲法實施密切相關,但憲法解釋畢竟不能完全等同于憲法實施,因此,在享有立法權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時享有監督憲法實施權的體制下,是否完全沒有解釋憲法的空間呢?如果在法律實踐中發現憲法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或者法律實施中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憲法依據時,立法機關一般會采取制定新的法律、修改原有法律、對法律進行解釋等方式,其中憲法解釋的空間是比較小的。法律很難對全國人大常委會采取何種方式(制定還是修改法律、法律解釋還是憲法解釋)作出嚴格的規定。這一方面是因為常委會自己就是立法機關,即使是全國人大為常委會立法,它們在體制上的一體性也很難產生真正的制衡;另一方面也因為立法機關行使其權力時應該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它畢竟不是執行機關或司法機關,如果對立法機關的約束過于刻板恐怕有違其權力屬性。
1.立法機關實施憲法的主要途徑是制定或修改法律,而不是解釋憲法。憲法的原則性規定要得到實施通常須先將其具體化,即使憲法作出了具體規定,也還需要將其程序化,這通常由議會通過立法來實現。
2.有關國家機關在“制定規范性文件”時可能有解釋憲法的需求。立法機關解釋體制可能導致我們的憲法解釋主要在“立法中”(而不是在立法后)發揮其作用。《專家建議稿》的第8條規定了〔預防性解釋的請求主體〕:“國家機關在制定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等規范性文件時,認為需要對憲法進行解釋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解釋憲法的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當受理。”這種國家機關在“制定”規范性法律文件時提出的憲法解釋,反映了其在確定規則的過程中對憲法規范含義的解釋需求,基本屬于國家機關內部的溝通,社會意義并不十分突出,但對于統一國家機關內部對憲法和法律的理解,還是有一定價值的。然而這里有兩個層次需要加以區別。
首先,立法機關在制定“法律”時不太可能提出憲法解釋。《專家建議稿》中第8條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即應當排除國家機關在制定“法律”時提出解釋憲法的可能性。因為在我國,制定法律的國家機關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全國人大制定法律時,如果需要解釋憲法,它自己就可以在法律條文中進行解釋,無須向地位在自己之下的常委會提出解釋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法律時,如果需要解釋憲法,它自己也可以在法律條文中進行解釋,無須向自己提出解釋請求。 其次,有關機關在制定法規、規章及條例時可能提出憲法解釋。當有關國家機關“在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等規范性文件時”,也就是說,國務院在制定行政法規、國務院各部委在制定行政規章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制定地方性法規時,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務會在制定地方性法規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政府在制定地方規章時,較大市的政府在制定地方規章時,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在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時,“認為需要對憲法進行解釋的”,它們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憲法解釋請求才具有合理性,在這種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也才有必要性和可能性。這些立法尤其是地方立法在數量上是很龐大的,其中有的法規可能會涉及憲法解釋的問題。但這些國家機關在制定這些規范性法律文件時,更需要的可能是常委會作法律解釋而非憲法解釋。
憲法解釋在我國憲法實施“次”渠道中的作用
當憲法條文在具體化為法律后出現某些問題,如“憲法的規定需要進一步明確具體含義”(《專家建議稿》)第6條第一項),或憲法跟不上形勢變化的需要、不能完全適應復雜多變的現實生活,即“憲法實施中出現新的情況、需要明確適用憲法依據”(《專家建議稿》第6條第二項),大多數國家是由司法機關或專門機關來處理這一問題的(即合憲性審查及憲法解釋)。如果由立法機關來處理,它一般會采取制定新法律或修改舊法律的方式,而一般不會采取憲法解釋的方式。
1.在立法機關解釋的體制下,當立法出現空白或不當時,立法機關一般會修改補充法律,而不會解釋憲法。
細化憲法原本是立法的任務,如果立法有疏漏或失誤,立法機關一般會采取修改法律或解釋法律的方式來對社會發展需要作出回應,一般不會采取憲法解釋的方式。在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實踐中,立法機關經常對法律進行廢立改,以達到貫徹實施憲法的目的。
2.在立法機關解釋的體制下,立法機關行使的法律解釋權遠多于憲法解釋權。
如果憲法條文在具體化為法律后,在實踐中仍然發現有空白或出現爭議,在我國目前的體制下,立法機關除了修改有關法律外,還可以通過對原有法律作出解釋的方式回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如1984年廣西壯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曾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對《地方組織法》的有關規定作出解釋:“地方組織法第28條規定的‘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人大常委會可以決定本級政府副職的個別任免,是指兩次大會之間,還是整個一屆大會之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的回復是:“地方組織法規定的‘在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是指兩次人大會議之間。”
即使在法律解釋的過程中對于該如何解釋某條文才更符合憲法,立法機關內部出現爭議,也不太可能提出解釋憲法的請求,因為解釋憲法的機關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自己。如果在法律解釋作出后,對該解釋出現爭議,其爭議可能也主要涉及該法律解釋是否符合其法律而不是是否符合憲法的問題,這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違法審查,即常委會對自己作出的法律解釋是否符合自己制定的法律(數量較多)以及是否符合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數量較少)作出審查。
從實踐來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法律遭遇實踐挑戰后,較多地啟動的是法律修改權,較少行使法律解釋權,從未行使過憲法解釋權。在1996-2014年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僅作了16個法律解釋,而同一時期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有230多部。全國人大常委會至今從未行使過憲法解釋權,這固然與常委會的工作力度不夠有關,但也與其制度設計有關,當常委會同時擁有法律的制定權和修改權、法律解釋權、憲法解釋權時,它很自然地會傾向于行使立法權(包括制定和修改法律),因為這比行使法律解釋權效果更好。
3.我國規范性文件審查主要涉及的是法律解釋而不是憲法解釋。
《專家建議稿》中第6條〔解釋的事由〕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解釋憲法的第三種情況是“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等規范性文件可能與憲法相抵觸的”,這看上去很像與違憲審查相結合的憲法解釋,具有憲法實施的意義,但實際不完全是。
根據《專家建議稿》中第6條的規定,我國可能涉及憲法解釋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審查有兩個層次。首先,對法律的審查是一種自我審查。在審查法律是否與憲法相抵觸時,在我們現行體制下不太可能存在憲法解釋。法律對憲法的有關內容已經有了(或應該有)具體而詳盡的規定,如果有關主體認為這些法律對憲法的具體化不符合憲法的本意,憲法的本意不是這樣而是那樣,進而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憲法究竟是何意作出解釋,這實際上是法律的合憲性審查。由于我國采用立法機關解釋體制,這種審查基本上屬于自我審查,因此其中憲法解釋的必要性也往往不復存在。按常理推論,行使憲法解釋權的常委會不太可能認定自己在行使立法權時違反了憲法,也不太可能認為產生自己并有權監督罷免自己的全國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違反憲法。其次,對法規、規章的審查主要是合法性審查而非合憲性審查,涉及的主要是法律解釋而非憲法解釋。在審查法規、規章時,如果需要動用解釋權,一般啟動法律解釋權(而不是憲法解釋權)即可。因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等規范性文件”大多數應該是直接根據法律(甚至是根據法規、規章)而不是直接根據憲法制定的,它們不太可能直接“與憲法相抵觸”,而是更可能直接“與法律、法規相抵觸”,在這種合法性(非合憲性)審查中可能更需要的是進行法律解釋,而非憲法解釋。
以上論述說明,在我國,當憲法條文在具體化為法律后,如果出現了空白或有爭議,立法機關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彌補,憲法解釋只是其中的一種方式。由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時擁有法律制定權、法律修改權、法律解釋權、憲法解釋權這四項權力,而行使何種權力常委會自己可以選擇,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常委會對自己各種權力的權衡,在此立法機關對憲法解釋權的運用也可能存在著“窮盡所有的法律途徑”之后才宜啟動的問題,立法機關解釋憲法的體制固然給憲法解釋以崇高的地位,但同時也極大地壓縮了憲法解釋的空間。
我國現行體制下憲法解釋的空間
盡管目前我國憲法解釋的空間不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
1.立法或修憲時機不成熟時,憲法解釋有一定空間。有些憲法規范自身需要細化,可以用立法將其細化,也可以用修憲的方式進一步明確,而立法或修憲的時機尚不成熟時,可以先進行憲法解釋。如憲法第67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其中“部分”補充和修改的具體標準是什么?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很難通過制定法律的途徑來彌補,因為它不太可能專門為此制定一部新法律;也不太可能通過修改或補充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的方式來改進,《議事規則》只能規定常委會會議的召開、議案的提出和審議、聽取和審議工作報告、詢問和質詢、發言和表決等程序性問題,而不宜對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律的“幅度”這樣實質性的權力作出規定。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憲法解釋對“部分補充和修改”基本法律的范圍作出限定,是目前體制下較為可行的方案。此時的憲法解釋雖不是唯一的方案,甚至不是最佳方案(屬于自我限權),但至少是方案之一,它可能是修憲或修法前的一個鋪墊。
2.行政機關、地方機關在制定規范性法律文件時可能有憲法解釋的需求。當有關國家機關“在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等規范性文件時”,“認為需要對憲法進行解釋的”,可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憲法解釋。雖然其中法律解釋可能有更大的需求,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憲法解釋的可能性。如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其中“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具體包括哪些?它和2004年第22條憲法修正案規定的“公共利益”是什么關系?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不一定專門立法作出規定,散見在各法律文本中的相關條文也不一定能回應現實中的諸多問題,因此有關國家機關在“制定”規范性法律文件時,可能提出憲法解釋的請求。
3.在立法有空白或不完善的情況下,憲法解釋也可能有一定空間。在我國有關領域雖然有立法、但立法還不夠完善的情況下,憲法解釋作為立法的補充可能有其一定的存在意義。如《憲法》規定了通信自由,《刑法》將“通信”的“信”解釋為“信件”“郵件、電報”,在今天這個信息高度發達的社會,“信件”顯然還應包括電子郵件、短信、微信等,在此立法機關可以對現有法律作出補充修正,使憲法規定的“通信自由”的“信”有較為明確的范圍(修改法律);也可以通過解釋《刑法》的方式予以說明(解釋法律);同時也不排除有關組織或個人依法提出解釋憲法“通信自由”的“通信”之請求后,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憲法解釋以回應社會的需要。對此類問題,應優先考慮采用修改或解釋法律的途徑,在窮盡這些途徑后才宜啟動憲法解釋機制。
不過這些憲法解釋似乎都只是緩兵之計,最終還是要靠立法機關盡快制定相關法律、使法律體系得以完善來加以解決。如果通過個別的、零星的憲法解釋來逐步完善憲法的有關規定,憲法解釋實際上將起到類似判例法的作用,這固然沒有什么不好,但可行性較小。對后發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沒有時間慢慢積累,沒有必要親自一一實踐摸索,可以并應該借他山之石,成文法顯然是更有效、更便捷的途徑。
在當下中國,啟動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法解釋權并非完全沒有意義,只有啟動了才能接受實踐檢驗,只有經過實踐檢驗才能知道是否符合中國國情,也才可能加以改進和完善。在此過程中我們可能最終尋找到某個適合我們的他國模式,也可能組合幾種模式而形成一種新的模式,也不排除創造出一種嶄新模式的可能性——采取什么模式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能夠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
(作者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學院教授;摘自《法學評論》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