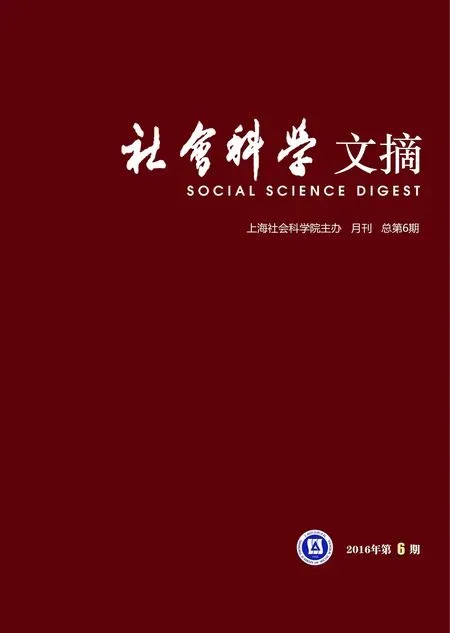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需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文/朱鋒
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需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文/朱鋒
中國(guó)國(guó)際關(guān)系類智庫(kù)的興起,反應(yīng)了中國(guó)與世界關(guān)系發(fā)生歷史性變革的時(shí)代特征,客觀上順應(yīng)了中國(guó)必須更加全面、準(zhǔn)確和深入地了解、把握以及影響世界的內(nèi)在需求。尤其是在對(duì)外政策與戰(zhàn)略的認(rèn)識(shí)、思考和決策層面,國(guó)際研究智庫(kù)的興起標(biāo)志著不斷提升與活躍的“智力支持”需求,是中國(guó)國(guó)家治理體制進(jìn)步的標(biāo)志。
國(guó)際問題智庫(kù)建設(shè)面臨著諸多的問題
然而,國(guó)際問題研究領(lǐng)域內(nèi)的智庫(kù)建設(shè)面臨著諸多的問題。思考、澄清和解決這些問題,對(duì)于中國(guó)智庫(kù)建設(shè)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一,中國(guó)的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要有清晰而又科學(xué)的“自我定位”,換句話說,要從戰(zhàn)略高度解決“智庫(kù)”到底是“干什么”的問題。智庫(kù)必須明確定位為是一種相對(duì)獨(dú)立的“社會(huì)性的力量”,能夠?yàn)楦鞣N國(guó)際問題與外交對(duì)策提供“不同聲音”和“不同選擇”。因此,智庫(kù)的作用不是簡(jiǎn)單地與政府捆綁,而是要強(qiáng)調(diào)有自身研究的相對(duì)獨(dú)立性,能夠不僅為政府更好地認(rèn)識(shí)國(guó)際問題提供深入的分析,而且隨時(shí)圍繞政府政策的執(zhí)行去及時(shí)和靈活地尋找和提供更好的、更有效的政策選擇。
當(dāng)然,中國(guó)的智庫(kù)定位必須為“政府發(fā)聲”,宣傳、講解和傳遞政府的聲音,幫助國(guó)內(nèi)民眾和國(guó)際社會(huì)了解中國(guó)的主張和立場(chǎng)。但僅僅局限在這一點(diǎn)是不夠的,智庫(kù)研究能力的提升和為政府提供的智力支持的發(fā)展,都需要智庫(kù)有深厚、客觀而又相對(duì)獨(dú)立的研究趨向和研究成果,智庫(kù)要發(fā)出“社會(huì)性”的聲音,而不是單純的“政治性”看法。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在“自我定位”上越明確,就越有能力為政府和政策提供真正有參考價(jià)值的政策咨詢。我們太多智庫(kù)都以拿領(lǐng)導(dǎo)人的批示和解釋政策作為自己的工作,謀求怎樣與體制更緊密地結(jié)合。這些確實(shí)是智庫(kù)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智庫(kù)的真正價(jià)值是要為應(yīng)對(duì)今天嚴(yán)峻復(fù)雜的國(guó)際問題提供多樣化的選擇和可操作的方案。智庫(kù)怎么“往前走”,要有長(zhǎng)遠(yuǎn)規(guī)劃,就必須以對(duì)自身研究工作的準(zhǔn)確和科學(xué)的定位為基礎(chǔ)。
第二,中國(guó)的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需要良好的“制度設(shè)計(jì)”。美國(guó)的智庫(kù)很成功是因?yàn)樗闹贫群苋妫诎ㄈ瞬耪心肌⒊晒a(chǎn)出、資金籌集以及智庫(kù)的影響力建設(shè)等方面,都有系統(tǒng)的、可資借鑒的制度,因而美國(guó)的智庫(kù)發(fā)展也是全世界最成功的。智庫(kù)制度建設(shè)的核心在于影響力建設(shè),即在重大國(guó)際問題上能夠隨時(shí)推出高端知識(shí)產(chǎn)品,既服務(wù)于政府,又能滿足社會(huì)的需求,得到社會(huì)的支持、理解,而非只是建設(shè)一個(gè)政府機(jī)構(gòu)類型的學(xué)術(shù)單位。例如,每年美國(guó)的布魯金斯、戰(zhàn)略與國(guó)際研究中心等代表性智庫(kù)都有大量的面對(duì)社會(huì)的活動(dòng),讓百姓和國(guó)際社會(huì)知道它的存在。在研究團(tuán)隊(duì)的建設(shè)上,智庫(kù)更是不同于一般的院校和科研機(jī)構(gòu),與大學(xué)有本質(zhì)的不同。智庫(kù)不是培養(yǎng)人才的地方,而是展示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資源的地方。比如一個(gè)研究項(xiàng)目,智庫(kù)需要什么樣的相對(duì)成熟和有專長(zhǎng)的人才,就需要去選擇、招聘和組合。新畢業(yè)的博士生可以在大學(xué)爭(zhēng)取“科研崗”,但在西方智庫(kù)一般只是研究輔助人員。
第三,中國(guó)的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需要有可持續(xù)的“經(jīng)費(fèi)來源”。現(xiàn)在中國(guó)是智庫(kù)熱,但我相信過幾年一大批智庫(kù)會(huì)死掉,因?yàn)闆]有經(jīng)費(fèi),不能保證可持續(xù)的經(jīng)費(fèi)來源。布魯金斯學(xué)會(huì)一年至少有一億美金的經(jīng)費(fèi),而且80%是社會(huì)募集的,有很強(qiáng)大的資金募集團(tuán)隊(duì),通過各種形式籌集經(jīng)費(fèi)。除此之外,布魯金斯的很多研究項(xiàng)目就是以經(jīng)費(fèi)為導(dǎo)向的,有什么樣的經(jīng)費(fèi)才做什么樣的項(xiàng)目。而我們的智庫(kù)有很多需要靠國(guó)家撥款、企業(yè)籌集,這固然很好,但要想長(zhǎng)期發(fā)展仍需一整套嚴(yán)密的、規(guī)范的募款制度和財(cái)務(wù)制度,讓智庫(kù)從社會(huì)上獲得基本的經(jīng)費(fèi)來源。蘭德公司70%的經(jīng)費(fèi)來自政府的研究合同,但布魯金斯等一批智庫(kù)的政府經(jīng)費(fèi)只占很少一部分,所以要把增強(qiáng)經(jīng)費(fèi)的籌集能力當(dāng)作智庫(kù)戰(zhàn)略性的議題。
智庫(kù)是“智力工廠”,不光靠現(xiàn)有的經(jīng)費(fèi),而是應(yīng)將知識(shí)產(chǎn)品的社會(huì)影響轉(zhuǎn)化為可持續(xù)的金融能力。此外,整個(gè)國(guó)家的科研管理、財(cái)務(wù)審計(jì)體制與智庫(kù)經(jīng)費(fèi)制度的設(shè)計(jì)是息息相關(guān)的。目前的制度對(duì)智庫(kù)的發(fā)展極其不利:國(guó)家投入大量的經(jīng)費(fèi)在做高端智庫(kù),但卻在財(cái)務(wù)和金融體制上沒有給智庫(kù)在社會(huì)上更好發(fā)展的政策空間。這個(gè)問題非常值得深思。
第四,中國(guó)的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應(yīng)該有多層次、多面向的“成果管道”。目前管道太單一,就是“拿批示”。實(shí)際上這種管道應(yīng)該有3個(gè)層次。一是政府管道。不光包括拿批示,也包括各政府部門下達(dá)的研究課題和定期提供咨詢報(bào)告。二是“社會(huì)管道”。如美國(guó)的各個(gè)智庫(kù)都在政治光譜的左、中、右當(dāng)中有自己的定位,它代表了社會(huì)力量和有代表性的社會(huì)聲音。三是“國(guó)際管道”。特別是國(guó)際性的智庫(kù),要交流,要發(fā)聲。我目前工作的南京大學(xué)中國(guó)南海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就要求有“三發(fā)聲”原則:“社會(huì)發(fā)聲”“政策發(fā)聲”和“國(guó)際發(fā)聲”。這可以多元化地展示和發(fā)揮智庫(kù)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這符合中國(guó)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的“服務(wù)功能”。
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建設(shè)亟須解決的問題
一是如何在智庫(kù)競(jìng)爭(zhēng)中形成合理的“社會(huì)分工”。中國(guó)的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不可能都建成像中國(guó)現(xiàn)代國(guó)際關(guān)系研究院和中國(guó)國(guó)際問題研究院那樣的“大而全”的智庫(kù)。這兩個(gè)智庫(kù)的規(guī)模優(yōu)勢(shì)是傳統(tǒng)、現(xiàn)實(shí)和體制的多重產(chǎn)物。中國(guó)的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要更多地有自己的特色、專長(zhǎng)和側(cè)重。現(xiàn)在很多智庫(kù)起個(gè)好聽的名字,但缺乏獨(dú)特的研究領(lǐng)域和代表性的研究方向,這不符合智庫(kù)建設(shè)的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規(guī)律和學(xué)科發(fā)展規(guī)律。智庫(kù)的功能要明確,研究領(lǐng)域要聚焦,并應(yīng)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和充實(shí)智庫(kù)研究專長(zhǎng)的社會(huì)化分工和智庫(kù)產(chǎn)品的市場(chǎng)化分工。
二是如何在不斷提高智庫(kù)能力建設(shè)的同時(shí),讓中國(guó)的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有充分的“國(guó)際面向”。中國(guó)多數(shù)的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都存在研究人員外語(yǔ)能力薄弱、國(guó)際溝通經(jīng)驗(yàn)不足以及國(guó)際問題研究的數(shù)據(jù)運(yùn)用欠缺等問題,其團(tuán)隊(duì)的外語(yǔ)能力、國(guó)際交往與溝通的能力都有待于進(jìn)一步提高。國(guó)際問題研究的智庫(kù)如果外交能力不夠,或者研究人員只會(huì)“看”、不會(huì)“說”,或者只會(huì)運(yùn)用有限的外文資料、而無法全面地掌握和使用外文數(shù)據(jù)庫(kù),就不可能有對(duì)國(guó)際問題及時(shí)、深入與準(zhǔn)確的認(rèn)識(shí)和分析,其研究成果必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的能力建設(shè),必須重外語(yǔ)能力、重國(guó)際區(qū)域和國(guó)別研究的經(jīng)歷,重國(guó)際數(shù)據(jù)庫(kù)的開發(fā)和運(yùn)用。
三是如何讓中國(guó)的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發(fā)展出靈活而又有效的“網(wǎng)絡(luò)體系”。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還需要國(guó)際關(guān)系中的“區(qū)域研究”與“問題研究”相融合。目前國(guó)內(nèi)的研究更側(cè)重區(qū)域和國(guó)別研究,缺乏問題領(lǐng)域的研究。如南海研究,不是簡(jiǎn)單的中國(guó)與東盟關(guān)系、中美關(guān)系,它涉及南海的能源、資源、生態(tài)、法律等多個(gè)方面。但是,任何一家國(guó)內(nèi)的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都不可能“大而全”。因此,如何促成國(guó)內(nèi)不同智庫(kù)之間就相關(guān)研究領(lǐng)域、研究項(xiàng)目和研究日程上的合作、圍繞著課題導(dǎo)向和經(jīng)費(fèi)分配上能夠在國(guó)內(nèi)智庫(kù)網(wǎng)絡(luò)中快速配置資源,建立智庫(kù)間優(yōu)勢(shì)互補(bǔ)、合作共生的“智庫(kù)網(wǎng)絡(luò)”,盡可能地共享資源、共同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這是對(duì)中國(guó)智庫(kù)的重大考驗(yàn)。
(作者系南京大學(xué)中國(guó)南海協(xié)同創(chuàng)新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教授;摘自《現(xiàn)代國(guó)際關(guān)系》2016年第4期;原題為《國(guó)際問題研究智庫(kù)發(fā)展中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