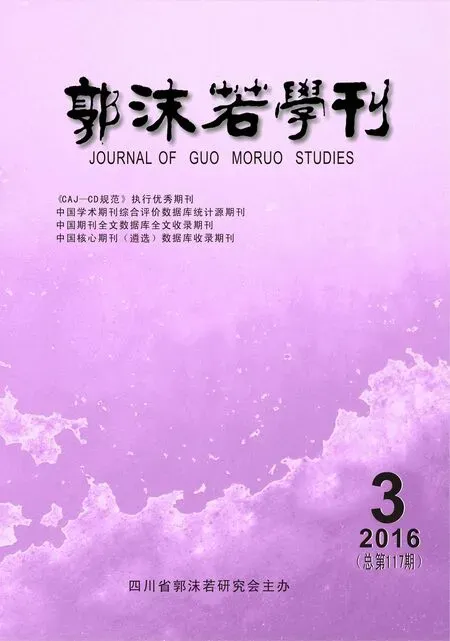一部哀悼“天才”“毀滅”的人物傳記——讀《敬隱漁傳奇》
王錦厚
一部哀悼“天才”“毀滅”的人物傳記——讀《敬隱漁傳奇》
王錦厚
敬隱漁的名字,我是從讀魯迅和郭沫若的著作中知道的。知道他翻譯了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魯迅的《阿Q正傳》,溝通了羅曼·羅蘭和魯迅的心靈;知道因為他一封信引起文壇的軒然大波,加深了魯迅和郭沫若的恩恩怨怨……僅此而已。
1979年11月,學校和樂山地委市委在凌云山上的大佛寺舉辦郭沫若逝世一周年紀念暨郭沫若研究學術討論會。我參加籌備工作,期間,與參會的戈寶權、段可情等老人交談中,幾次提及敬隱漁。戈寶權還囑咐我想法了解敬隱漁的身世。根據戈寶權的吩咐,我先后托了相關人士向遂寧方面打聽。其中,正在我校干部進修班學習的四川省政協干部趙勇同志費力頗多,了解不少情況,搜集到許多信息和材料,遂整理成一篇題為《敬隱漁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的文章,刊發在四川大學學報叢刊《郭沫若研究專刊》(第六輯),文章雖然不完善,但總算提供若干可供參考的線索。
1983年7月,我率隊去北京參加郭沫若全集雜文注釋討論會。戈寶權作為顧問也參加了,再次談到敬隱漁。7月29日,戈夫人打電話稱,戈老約我31日去他家一談。31日,吃罷晚飯,我便和注釋組的幾個同志一道去到戈家,談了不少問題,臨行時,戈老當場提筆在新作《“阿Q正傳”在國外》簽名,贈我。此后,我多方留意敬隱漁材料的尋找、搜集,特別是他與羅曼·羅蘭交往的資料,但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始終不能如愿,無可奈何?!
今年4月下旬的一天,無意接到張英倫先生從巴黎打來的長途電話,交談了關于敬隱漁的研究,他告知我,經過五年的努力,撰寫一部《敬隱漁傳奇》。將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不久,將該書序言和目錄寄我,看后,給人一種新的感覺,征得他同意,將其中《一封信水落石出》一節率先在我主編的《郭沫若學刊》(2015年2期)刊發。6月中旬,快遞送來了由責編寄給我的七本《敬隱漁傳奇》,我以先睹為快的心情閱讀了,給我極大的震撼,同時,也給我許多驚喜。一個才華橫溢的天才作家、翻譯家、中法文化和友誼的使者敬隱漁鮮活地出現在我腦海。張英倫先生為這個幾乎使人遺忘的敬隱漁立傳,真可謂慧眼識珠。
敬隱漁像流星一樣的在中國文壇閃亮而過。但他的名字始終聯結著文豪羅曼·羅蘭,魯迅、郭沫若,其生平、事跡,卻一直被“隱蔽”,被“遺忘”。張先生沿著敬隱漁走過的足跡:遂寧、成都、上海、維爾納夫、巴黎,尋訪知情者,閱讀檔案文獻,搜集材料,哪怕一點蛛絲馬跡也不放過,從而獲得大量稀有、珍貴的資料,特別是敬隱漁與曼羅·羅蘭來往的材料,盡數發掘。在此基礎,按傳主生活、學習、工作的地域精心結構了《出生之謎》,澄清世間流傳的敬“是一位棄兒”“無名無姓”,“上海垃圾桶旁的棄嬰”,“北京大學肆業”諸多無稽之談;《奇特的才華》,詳述了在上海與創造社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相識和交往,參加創造社,從事寫作,介紹并分析了他所寫作的詩歌、評論、小說、翻譯,頌揚了他的橫溢才華;《奇特的貢獻》,生動描繪了他和羅曼·羅蘭在奧爾加別墅的相見,傾心交談,成功將羅曼·羅蘭的巨著引進中國,又成功將魯迅的《阿Q正傳》推向了世界,從而溝通了兩位巨人的心靈,聯結了兩個民族的奇特貢獻,更澄清了因為“一封信”而引起的文壇軒然大波;《奇特的病》,真實地敘說了他的病狀,并探究得病的原因,羅曼·羅蘭如何無微不致的關懷,千方百計的救治;《奇特的結局》,述說了他的神秘消失,真可謂匠心獨具,全書充滿了新意:
略舉數例,可見一斑。
關于翻譯的評論,無疑是五四時期一個最薄弱的環節。那時,翻譯成為時尚,外國作品像潮水一樣涌向中國,良莠不齊,沙石俱下,如何提高翻譯質量,好的評論顯得格外重要。張先生注意到這點,因此,特別介紹了敬隱漁對《“小物件”譯文的商榷》。該文是敬隱漁唯一的一篇評論翻譯的文字,刊發在1924年3月9日《創造周報》第43號上,對李劼人翻譯的小說提出準確的批評。張先生怎樣評論這篇文章的呢?開頭引用了敬文的話:
未加批評以前我先當求得者劼人君原諒。劼人君我本不認識;但他的兩位兄弟卻與我相識很久。希望他不要怪我不去批評別人,偏只批評他譯的書;須知道在我所見的法文文學譯本中,此書譯筆是很有希望的。
幾句引文足以證明敬隱漁奉行的“不偏、不黨、不盲從別人,不拾人牙慧”的批評態度。接下來分析了敬隱漁指出的李劼人譯作的七處硬傷的正確,最后結論道:
《“小物件”譯文的商榷》開篇伊始的一翻話,既顯示了敬隱漁只講學問不虞私情的耿直性格,也表達了他對譯者的尊重。……不但顯示了敬隱漁法文知識的深廣,更表現了他性格的坦蕩和心地的和善。
敬隱漁這個后生評論李劼人譯的《小物件》卻提供了一個與人為善,以理服人的生動事例,與這些大師的意氣用事形成截然對照。
張先生把敬的評論放在當時創造社與文學研究為翻譯相互指責的背景中分析,其結論更顯得十分正確。也許因為如此,才得到李劼人的積極回應。李劼人當時雖沒有公開著文,但卻一直銘刻在心。二十年后終于將《小物件》重新翻譯,且以《“小東西”改譯后細說由來》文中詳細說明當時翻譯該書的動機及出版的情況、對敬隱漁批評的態度。恕我多引用李劼人的原話,如下:
及至《新青年》雜志興起,提倡自然主義的文學,介紹左拉、莫泊桑等人。胡適之先生所譯的《最后一課》,更成為人眾皆知的作品,而后,也才知道亞爾風士·都德之為如何人;不久,更知道了幾年前所縈回于腦際,而為主編者不甚重視的《知縣下鄉》《獵帽記》兩篇,原來也是都德的作品。從此,在未能直接閱讀法文之前,都德的文章,已是為我所愛好。及至數年后,能夠讀法文了,故在中華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作第二部翻譯時,(第一部譯的是莫泊桑的《人心》,曾于民國二十年改譯過。)便選中了《小東西》這部書。當時本應譯為《小東西》的,卻偶然懷疑東西這一名詞,好像不甚偕俗,因而改譯成《小物件》。出版之后,許多朋友說及,認為《小東西》一詞較妥,可是業已印出了,不好改變。這也和在民國十一年春,匆匆將其譯畢,未能仔細校正,便任其印行,及至自己發現了不少可以改易之處,寫信去與出版的中華書局編輯部朋友商量時,朋友第一便不贊成修改;其次,不得已時,僅能在每一行改若干字,而不能多一字,也不能少一字,說是如此方好移動版子。倘改多了,而字數與原版不合,則須花錢另排。堂堂書局不能為區區一本小書,費錢費事,乃至費神,這于天理人情,自是應該的。所以自《小物件》出版以來便內疚起,不但名詞之須得改正而已也。
也因為這原故,不惟自己不再重看,一如初譯本的《人心》一樣,甚至在十三年時,敬隱漁先生(真可惜此公竟死去了!)給我指摘出的一處絕大錯誤,也只好任之,一直到今日才得更正。
敬先生所指摘的,為第二部第八章,一個藍蝴蝶的奇遇中,藍蝴蝶所唱的一句:“我的腰肢很健康,我呵!雖沒有那樣的翅子,蔥皮似的一如那般蜻蜓。”當年譯至這句Comme Les demoiselles,只知道demoiselle一字,義為姑娘閨秀,便不再去翻翻字典,而竟意會之為“蔥皮似的嫩得象那般姑娘”,本已不通了,卻因《紅樓夢》上,有這么一句贊頌美人的造語,謂為水蔥似的嬌嫩,倒也強免通得下去;不料我原稿上的“嫩”字,稍為寫得潦草,排字先生和校對先生遂一再誤為“懶”字,這一下:“蔥皮似的懶得象那般姑娘”,真就太不成話了。所以敬先生一連來了三個不可解,而校正曰:“譯者乃不知demoiselle一字,尚解為蜻蜓。”這真指教得萬分對。同時早一點,還有一位先生,在什么雜志上作了一篇書評,也將《小物件》的譯錯之處,指出了二十幾處。……敬先生的指數,某先生的批評,都只好擺在心里,在內疚上更加幾層內疚!
但是,也曾發過洪誓大愿,愿將所曾譯過、自以為極不對的東西,得有機會,必不惜痛痛快快改它一番,以贖前愆,以求睡得著覺。(李劼人:《“小東西”改譯后細說由來》《小東西》1943年11月作家書屋版)
李劼人虛心接受批評,重新翻譯了這本小說,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翻譯家和批評家密切合作的范例,值得點贊。
五四時期,人們更多地注意引進外國作品,卻很少注意翻譯質量,更很少注意將中國的新文藝推向世界。敬隱漁在這兩方都很留心,他絲毫沒有滿足把魯迅的《阿Q正傳》推向了世界,還決心繼續努力將更多的新文藝推向世界。當時陳西瀅在他的《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長文中說:“新文藝的作品,算短篇小說的出產頂多,也要算它的成績頂好了。我要舉的代表作品是郁達夫先生的《沉論》和魯迅先生的《吶喊》”,還有冰心的《超人》(《西瀅間話》新月書店1928年6月初版)《黃昏后》,《幻滅》《麗辛小姐》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敬隱漁便根據魯迅先生寄給他的三十三種小說,在羅曼·羅蘭的指導下,從中挑選了陳煒謨、落花生、冰心、茅盾、郁達夫等人的代表作品各一篇,進行實譯、縮譯和改譯,連自己已譯出的魯迅的《孔乙己》、《故鄉》、《阿Q正傳》和自己創作的《離婚》,計7人,9篇,編輯成《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寫了“引言”,由羅蘭介紹巴黎厄戴爾出版社1928年3月30日出版,不久,英國、美國、巴西等國的出版商又以英文、葡萄牙文相繼出版了這本小說。對此,張先生在書中列了專章詳加論述,從選材到翻譯,從出版到反響一一給予了介紹。明確指出:這是“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推向世界”,值得肯定,值得贊揚。這,的確是敬隱漁將新文藝作品推向世界所作的又一次努力。然而,國內卻有雜音,1929年9月15日由水沫書店出版的《新文藝》卻刊載了署名伯子的《敬隱漁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作家作品選〉》,大加指責,肆意攻擊。
把本國的作品這樣不負責任地介紹到別一國去,思之真令人痛心,要出風頭或是弄錢,別的方法正多著,我不解敬先生為什么取了這種不顧羞恥,抹煞良心的辦法。(伯子:《敬隱漁的〈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1929年9月15日《新文藝》第一卷第一期)
多么狠毒的攻擊啊!
伯子何許人?了解一下《新文藝》的編輯人就不難知道了。該刊的編者是施蟄存、劉吶鳴、戴望舒等人,以施和戴為主。據他們自己說:所刊文章,多是自己撰寫。如此說來,攻擊敬隱漁的文章正是出自正在從事法國文學作品譯介的戴望舒無疑。這種看法,當然不只施、戴,自然還包括了他們的好友沈從文等人。難怪這位自稱“為整個文學運動短篇小說部門作尖兵,打前站”,其作品可以與莫泊桑、契訶夫“比肩”的“多產作家”要急急忙忙向在美國的友人王際真報告。1931年6月2日,他在給王際真的信里寫道:
聽人說有一本從法文譯成英文的《中國短篇小說選》,被人罵過了一陣,很不好,這文章由敬隱漁選譯的,這人是不夠做這個工作的。(沈從文:《致王際真》,《沈從文全集》18卷144頁)
“被人罵了一陣子,很不好”,“這人是不夠做這個工作的”,包含著比伯子評論更多的貶意,流露了更陰暗的心理。敬隱漁沒作回答,也許不知道此文。張先生替敬隱漁作了回答、辯析,以事實駁斥了伯子們的胡言亂語,認定伯子“將它一筆抹煞。‘見不來人’的毋寧說是伯子的陰暗心理。”這種辯駁是很有意義的。
“一封信”的軒然大波持續半個多世紀,經過戈寶權等幾代學者不懈的努力探討,可以說已經“水落石出”:羅曼·羅蘭沒有直接寫信給魯迅,而是在給敬隱漁的信中談到《阿Q正傳》。
張先生從魯迅對敬隱漁的態度微妙變化切入,抓住三個問題:一、“一封信”是什么?二、一封信的內容是什么?三、一封信的下落如何?展開論述。以敬隱漁當年和羅曼·羅蘭的通信為據:“一封信”是“羅蘭寫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敬隱漁一月二十四日收到”的信,其內容:有“羅蘭對《阿Q正傳》的贊語”,主要是“對敬隱漁翻譯的夸獎和評論”,“信”到上海后,由于創造社的變化、搬遷,“投遞過程中遺失了。”這是一個有根有據的合理的推論,難得的是張先生還考證出:叫敬隱漁勃然大怒,火冒三丈,大發雷霆,所著《讀了“羅曼·羅蘭評魯迅”》文中批駁《京報副刊》刊發的《羅曼·羅蘭評魯迅》一文的作者柏生不是孫伏園,文中所說“全飛”也不是孫伏園的弟弟孫伏熙。這就為“原文”所引起的軒然大波的“水露石出”提供了又一個強有力的證據。
戈寶權先生在其權威著作《“阿Q正傳”在國外》一書中曾經這樣說過。他說:
據了解,寫文章的柏生就是副刊的編者孫伏園,“全飛”先生是他的兄弟孫伏熙,當時在法國里昂留學,經常用全飛名字給《京報副刊》撰寫有關法國文學的文章。
寶權先生說得十分肯定。然而張先生卻從孫伏熙的留學經歷發現,敬隱漁得知羅曼·羅蘭對《阿Q正傳》的贊語時,孫早已離開法國,根本不可能聽到敬隱漁談及此事;《京報副刊》從頭到尾并無用“全飛”的名字發表的文章,更談不上“常用‘全飛’的名字給《京報副刊》撰稿”。看來,寶權先生的“了解”確實是不可靠的。到是孫伏熙在該刊1926年1月27日397號上發表的《介紹韓敖君》一文中透露了“全飛”是韓敖的筆名。孫文說:
韓敖君的名字諸位沒有聽到過吧,然而你們早已屢談他的文學了。他就是做《十九世紀法蘭西文學》的全飛。譯波特萊爾詩的伏睡以及胡然等許多名字都是他。
這一發現與考證相當重要。難怪張先生用了整整一章:《詭秘的雜音》予以詳論。它從另一個方面有力的證明了敬隱漁所謂的“原文”不是羅曼·羅蘭直接給魯迅的信件,而是給敬隱漁的一封信,為“原文”是否就是“一封信”的“水落石出”提供了強有說服力的新的旁證,讓一封信的風波可以徹底平息了。
敬隱漁的結局是研究者所關心的問題。
郭沫若說:
他到歐洲后,深受羅蘭的誘掖,但不久便因神精失常,被送回了中國……有人說他因失戀而踏海。我也不知道他的詳細情形。(郭沫若:《偉大的戰士,安息吧!——悼羅曼·羅蘭》,《文藝雜志》1945年5月25日)
親近過羅蘭的梁宗岱也有過一次回憶。說他訪問羅蘭時,羅蘭曾關心的向他打聽敬隱漁回國后的情況時說:
最近敬隱漁給他寫了不少的信,一封比一封令人焦慮,羅蘭焦慮而氣憤地說:“這完全是巴黎毀了他。完全是巴黎毀了他。”(梁宗岱:《憶羅曼·羅蘭》《宗岱的世界》,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敬隱漁到歐洲到底干了些什么事?為什么“神精失常”?得了什么病?寫了一些什么令羅蘭“焦慮”的信?這是人們很想知道的事情,張先生一一作了披露,讓人們清楚地看到羅曼·羅蘭,對“天才”敬隱漁父親般的關愛呵護,如何為他的譯作發表、出版作細致而穩妥的安排;如何千方百計為他的奇怪的病尋醫問藥;以致中法大學將他強行遣返回國的憤怒……這種關懷不僅是對敬隱漁個人,而對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關愛。難怪他后來一直譴責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全力支持中國的抗戰。
綜觀全書,充分占有材料是它的最大優點、最大優勢。但作者并沒有滿足這種優勢,而是充分利用這優勢,對基本材料和史實也進行了一番認真的研究,縝密的思考,再結合時代,結合環境及人物特點,進行了揣摩,想象,從而勾畫出了敬隱漁的奇特經歷,奇特貢獻,奇特命運,較為準確地寫出了敬隱漁這個才華橫溢的“天才”如何從輝煌走向了“毀滅”,天才雖然從肉體上毀滅了,但他的著作,他的業績,他的精神,還存留在人間,郭沫若就曾在《〈偉大的戰士,安息吧〉——悼念羅曼·羅蘭》文中對敬隱漁的“毀滅”表示了由衷地哀悼,他沉痛地寫道:
就這樣,當我默禱羅蘭先生安息之余,我卻由衷地哀悼著我們這位多才的青年作家敬隱漁先生的毀滅。(郭沫若:《偉大的戰士,安息吧》1945年2月《文藝雜志》新1卷1期)
敬隱漁的“毀滅”!實在令人深思,更令人警惕!《敬隱漁傳奇》的出版發行,有歷史意義,也有現代意義,特別是對當今的留學青年,還有那些不重史實,胡編亂造,取悅低俗,追名逐利的作者也都是一劑良藥。
二○一五年八月酷暑中
于成都川大花園寓所
(責任編輯:陳俐)
2016-07-27
王錦厚,男,四川大學出版社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