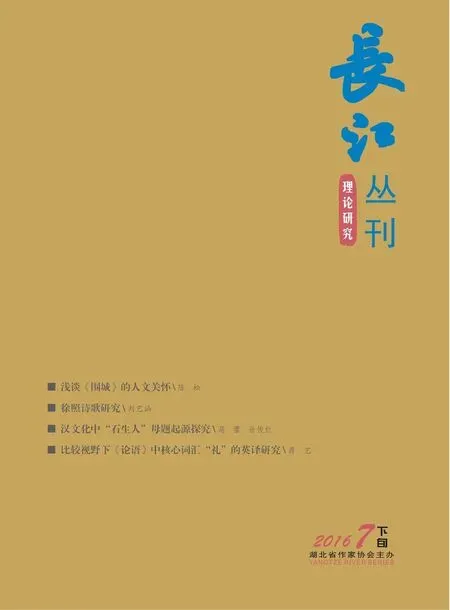民族音樂對古代中國文學教育的影響
羅世琴
民族音樂對古代中國文學教育的影響
羅世琴
上古詩、樂、舞三位一體,古代民族音樂接受、傳承中歌辭是極其重要的內(nèi)容。文人對宮廷樂辭不斷創(chuàng)新、教授、研習,形成具有文學教育因素的樂辭教育。清商樂受到漢末魏晉時期文人雅士的普遍喜愛,影響著文學的教育與傳承。在民族音樂形式的影響下,文人通過潛移默化的自我接收方式、與人交游的探討方式以及正式的教習,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教育的一種重要途徑。
民族音樂 文學教育 影響
音樂對文學的影響已是學界不爭的事實,上古詩、樂、舞合而為一,互為補充,構(gòu)成藝術表現(xiàn)的重要形式,因此在文學的各類體裁,不但樂府、曲詞、歌舞辭,而且辭賦節(jié)奏、詩歌抑揚頓挫的韻律、散文的長短句式安排等,都無不體現(xiàn)出音樂的影子。
少數(shù)民族音樂與中原音樂的互動與交流也是中國古代文化交流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呂氏春秋·古樂》載:“昔黃帝令伶?zhèn)愖鳛槁伞A鎮(zhèn)愖源笙闹鳎酥铌溨帲≈裼趲O溪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jié)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吹曰‘舍少’。”①雖這一記載屬歷史傳說,但民族之間音樂文化的交流由此可窺一斑。音樂教育方面,周代就設有專門的對少數(shù)民族音樂進行管理的官職,《周禮·大司樂》:“鞮鞻氏掌四夷之舞與其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宋代朱申《周禮句解》注鞮鞻氏的人員設置情況:“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②可見,當時有專門的執(zhí)掌官員進行少數(shù)民族音樂教育活動。至于這些歌辭究竟是使用少數(shù)民族語言進行還是經(jīng)過一定語言翻譯后再進行教授,可由《巴渝舞》的傳承過程為例進行探討。
據(jù)《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載:
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shù)陷陣,其俗喜歌舞。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③
這是史載少數(shù)民族《巴渝舞》的起源。《巴渝舞》雖屬俗樂,但在漢代宮廷音樂中有較高地位,這種民族舞樂歌樂辭的教育與學習也是漢代官方音樂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晉書·樂志》還專門對其文學成分——樂辭進行了記載:“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④此處的“古”,一方面是語言隔閡,另一方面是接受背景隔閡:這些歌辭很有可能因保留初創(chuàng)時期的民族語言而未經(jīng)翻譯,或僅僅對民族語言進行了部分翻譯進而形成語言障礙;歌辭中的場景、表達的意境等,與傳習者所處的背景也有可能形成較大落差。唐《蠻書·云南界內(nèi)途程》“嶺東有暴蠻部落,嶺西有盧鹿蠻部落,又有生蠻磨彌殿部落,此等部落皆東爨烏蠻也。男則發(fā)髻,女則散發(fā),見人無禮節(jié)拜跪,三譯四譯乃與華通。”⑤樂辭傳習教育的過程中出現(xiàn)辭義理解的困難并未影響民族樂舞歌辭在宮廷音樂中的特殊地位,據(jù)載漢哀帝曾對樂府進行裁減,仍然對“巴渝鼓員三十六人”予以保留,其歌辭的傳承也依然保留宮廷專門教授的方式。《晉書·樂志》載到魏晉時期,《巴渝舞》成為雅樂的一部分,或因語言不通問題進行了歌辭的漢化改造。王粲修改樂辭“以述魏德”,黃初三年“改《巴渝舞》曰《昭武舞》”,晉“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直到荀勖等人創(chuàng)制新曲,“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才不再使用。
文人的參與,歌辭的重新創(chuàng)制,宮廷樂府的不斷教授、研習、更新,構(gòu)成了民族樂舞歌辭傳習中文學教育的重要內(nèi)容,這在古代歷朝的宮廷音樂和文學創(chuàng)作中都極為普遍。
魏晉南北朝是音樂與文學逐步游離的時期,各民族之間文學的交流與互動及其頻繁,少數(shù)民族詩歌在中原地區(qū)廣為傳頌,當時流行中原的少數(shù)民族音樂形式也很多,較為典型的有鼓吹與橫吹。《藝文類聚》卷六十八載:
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阜。”嘆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七也有相近記載。對于這種音樂的民族特點,陸機《鼓吹賦》載:“騁逸氣而憤壯,繞煩手乎曲折。舒飄搖以遐洞,卷徘徊其如結(jié)。” 其效果 “節(jié)應氣以舒卷,響隨風而浮沉。馬頓跡而增鳴,士嚬蹙而沾襟”。從音樂形式到文學創(chuàng)作,一方面是因為音樂感染而引發(fā)文學創(chuàng)作靈感,另一方面也暗含著當時對少數(shù)民族音樂在審美視角方面的接受與認同,正是因為得到美感與共鳴,才能引發(fā)創(chuàng)作靈感。正因如此,鼓吹可以引發(fā)經(jīng)典之作,《世說新語·文學》載孫綽所言:“《三都》,《二京》,《五經(jīng)》鼓吹。”劉孝標注:“言此五賦是經(jīng)典之羽翼。”⑥魏晉時期文學與音樂之間的關系極為密切,文士多集文學創(chuàng)作與音樂修養(yǎng)于一身,接受少數(shù)民族音樂,必然引發(fā)以文學為主題的交游活動和生活中對民族內(nèi)容相關的文學創(chuàng)作。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一:“有簫茄者為鼓吹”,“有鼓角者為橫吹”,又卷十六:“鼓吹曲, 一曰短簫饒歌。”崔豹《古今注·音樂》:“橫吹, 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 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⑦在流傳、接受、進行教授與學習等方面,流入中原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具有共性。考今存樂府歌辭,有很多都是南朝文人依據(jù)橫吹曲進行的創(chuàng)作,是在當時流行的民族音樂基礎上進行的。古代文人所寫的賦作中,有關少數(shù)民族音樂的就有《鼓吹賦》《琵琶賦》《笙賦》《箜篌賦》等,其所折射出的基于少數(shù)民族音樂而引發(fā)的對文士文學創(chuàng)作觀念的潛移默化不容忽視。杜甫有《夜聞觱篥》,觱篥就是龜茲國的樂器。
除了雅樂,中國古代民間流行的音樂還有清商樂與燕樂。其中清商樂是漢代的相和歌曲與“荊楚之聲”相融合的而生成,漢代相和歌本身就具有少數(shù)民族音樂的特點,《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楚、汝南歌詩等,大都屬于相和歌。《晉書·樂志》言:“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并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也。”所列民間樂歌中有一部分就是來自少數(shù)民族,這些歌曲再與荊楚之地的民族歌曲進一步結(jié)合而成為清商樂,受到漢末魏晉時期文人雅士的普遍喜愛。南朝有艷曲新聲背景下宮體詩歌的盛行,《梁書·簡文帝本紀》載:“帝(蕭綱)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于輕艷,當時號曰宮體。”⑧蕭綱、蕭繹以及聚集在他們周圍的文士在文學交游與民間新聲的影響下,形成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的特有風格,其后又引發(fā)一個民間學習并創(chuàng)作的“后生好事,遞相縱習”的高潮(《隋書·經(jīng)籍志》),正是對由民間音樂形式而引發(fā)的文學創(chuàng)作形式自上而下的模仿過程。與之相應,隋唐時期流行的燕樂是對少數(shù)民族音樂的進一步融合,在流行的民間音樂的基礎上確定的十部伎樂,基本上都是少數(shù)民族音樂。唐代著名的文學創(chuàng)作者,無不受到這種民間流行風的影響。唐詩中多出現(xiàn)描寫少數(shù)民族音樂、舞者的作品,元稹《法曲》詩“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擅滿成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描寫的就是當時少數(shù)民族音樂廣為傳播的情形。至于元代雜居和散曲的產(chǎn)生,毋庸多言,更是與少數(shù)民族的音樂形式的影響極為密切了。
無論音樂與文學形式是否各自獨立,少數(shù)民族的音樂形式對中原民族音樂形式的影響一直就未曾間斷。在這種音樂形式的影響下,文人通過潛移默化的自我接收、與人交游的探討以及正式的教習,對其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的學習接受,都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些影響,正是構(gòu)成中國古代文學教育的一種重要途徑。
注釋:
①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M].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154.
②十三經(jīng)注疏周禮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720.
③[南宋]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2842.
④[唐]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693.
⑤[唐]樊綽.蠻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⑥[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60.
⑦[西晉]崔豹.古今注(重影《四部叢刊》三編影宋本)[M]上海:上海書店,1986:5.
⑧[唐]姚思廉.梁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
本文系全國教育科學規(guī)劃教育部重點課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國古代文學教育——中國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教育互動研究的視角”(DMA140214)階段性成果。
羅世琴(1976—),女,漢族,甘肅白銀人,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師,博士,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