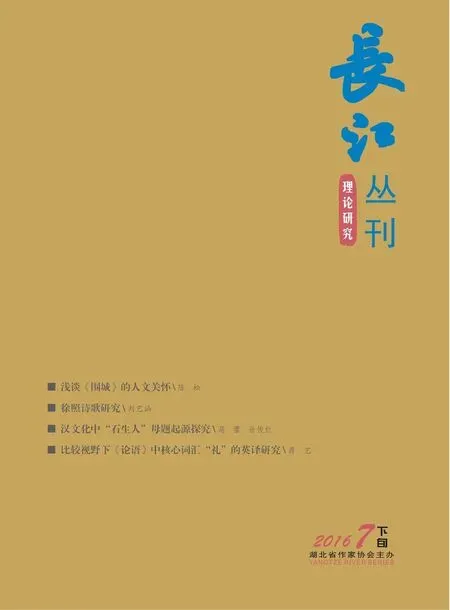“十六字心傳”與宋儒《書》疑芻議
張志杰
“十六字心傳”與宋儒《書》疑芻議
張志杰
“十六字心傳”被稱為儒家傳心法要,并依此確立起完整的儒家道統體系。處在“經學變古時代”的宋儒一方面對此體系的建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普遍的疑古思潮又對其所據經典多有疑慮,二者表面的矛盾中實則正體現出宋儒思想的內核。
十六字心傳 《尚書》 疑經 宋儒
《朱子語類》卷八十三的一段對話對于理解《尚書》有重要啟示:“(伯豐)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朱熹)曰:‘如《大禹謨》又卻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于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1]此段問答頗似禪宗公案,僧問師曰,似乎答非所問。細讀之后發現,其說至少包含三個方面的信息:一是對《尚書》今古文問題的疑惑;二是特別提及《大禹謨》,認為其既明白條暢又有不可曉處;三是特別強調推索義理。本文由此段語錄啟發,擬從《大禹謨》篇入手,對所謂“十六字心傳”與宋儒疑《書》思潮及二者關系做一淺窺。
一、“十六字心傳”的內涵
“十六字心傳”乃“人心謂危,道心謂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四句十六字,語出《尚書·大禹謨》,經宋儒發揮后地位日顯,至朱熹闡發為堯舜禹“三圣相傳秘旨”,并依此確立起完整的儒家道統體系。《大禹謨》其文云: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偽孔傳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孔穎達疏云:“(帝)因戒以為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惟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云:“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為萬慮之主,道心為眾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危則難明。欲將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后可得明道而安民也。”[2]偽孔傳與孔疏的闡釋無疑對此說在后世的弘揚與發明有重要影響。偽孔傳主要側重“危”“微”二字的含義,解釋為何要戒以“精一”“執中”。孔疏則更進一步將用力點集中在“心”字上,其“人心”“道心”之論,對宋儒尤其朱熹從心性之學闡述此四句十六字有重要意義。
二、宋儒關于“十六字心傳”的注疏
朱熹的闡發對此十六字地位的奠定至關重要。《朱子全書》卷三六《答陳同甫》云:“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于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3]又《朱子語類》卷七十八云:“或問人心道心之別,曰:只是這一個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個物事,但所知覺不同。惟精、惟一,是兩截工夫;精,是辨別得這個物事;一,是辨別了,又須固守他。若不辨別得時,更固守個甚么?若辨別得了又不固守,則不長遠。惟能如此,所以能合于中道。”[1]朱熹拋開漢唐諸儒,直以《中庸》《孟子》說《書》,此四句十六字最終形成“堯舜禹相傳密旨”之說。
以究其實,朱熹“三圣相傳密旨”當然不是一家之說,而是在宋代諸儒基礎上的結語性陳述。且擇其要者略述之。
朱熹之學來自二程,此說也不例外。程頤《伊川先生語十》針對人心、道心曰:“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自明。”“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則忘天理也。”又云:“看《書》,要需知二帝三王之道。”[4]此論對朱熹影響甚巨。朱熹云:“《書》曰:‘人心謂危,道心謂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圣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欲。”又“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代之變。’曰:‘不若求圣人之心。’”[1]朱子對人心、道心及求二帝三王之心的觀點很明顯本于二程。
二程之外,再如蘇軾《書傳》卷三云:“人心,眾人之心也,喜怒哀樂之類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樂者也。安危生于喜怒,治亂寄于哀樂,是心之發,有動天地傷陰陽之和者,亦可謂危矣。至于本心,果安在哉?為有耶?為無耶?有,則生喜怒哀樂者非本心矣;無,則孰生喜怒哀樂者故夫本心。學者不可以力求而達者,可以自得也,可不謂微乎?”[5]蘇軾認為人心就是《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等各種情感,道心是能生出人各種情感的本心。又說“放之則二,精之則一。桀、紂非無道心,放之而已。堯舜非無人心,精之而已”則又來自孟子“求其放心”之說。“桀、紂非無道心也,堯、舜非無人心也”之說似乎也與孟子“四心”之說有關。孟子認為人皆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蘇軾結合《中庸》與《孟子》解此十六字,大大擴展了其闡釋空間,對后之學者影響巨大。
此后再如林之奇(1112—1176)《尚書全解》援韓愈《原道》闡發此十六字云:“此堯、舜、禹三圣人相授受之際,發明其道學之要以相畀付者。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歷代圣賢所以相傳者,不得盡見,然以堯舜禹之所以相授受者而視之,則知湯與文武而下,其所以相傳者蓋不出諸此矣。”[6]與蘇軾相似,林之奇也以“此(十六字)蓋與《中庸》之言相為表里”,且闡述了詳細的道統傳接,一個漸趨完備的儒家心性體系至此顯現。
“虞廷十六字”地位的最終確立與儒家道統體系的完整建構在朱熹手中,上文已有論述。《四書章句集注》中朱子也有詳細闡述:“《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7]下文又以大段筆墨記述了湯、文、武,皋陶、伊、傅、周、召,孔子、顏、曾,子思、孟子以至二程“圣圣相承”的道統譜系。朱熹在前人的基礎上最終將這十六字發揮為“孔門傳授心法”,最終以“三圣傳心”構筑起儒家道統學說。
三、宋代《書》疑與“十六字心傳”
皮希瑞《經學歷史》以宋代為“經學的變古時代”[8]。主張發揚主體意識和理性精神的宋儒并不滿足前人之說,從疑一、二經者如歐陽修、劉敞、王安石等,至遍疑群經者如胡宏、張栻、朱熹、蔡沈、王柏等,疑經風潮彌漫持續有宋一代。有學者考得宋代疑經文人達165人,其中北宋53人,南宋113人[9]。宋人疑經風潮由此可見一斑。
于諸經之中,《書》疑尤為典型。早期疑《書》者如蘇軾、程頤等人主要集中在脫簡錯簡以及文本的完缺、文字的正誤層面,且懸置不論。最早對《古文尚書》提出懷疑的是吳棫(1100--1154)。清人閻若璩稱數百年來至吳棫“始以此書為疑,真可謂天啟其衷矣。”[10]吳棫《書裨傳》已軼,但從明人梅鷟《尚書考異》的引述中尚可一窺:“伏生傳于既耄之后,而安國為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后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佶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二體乎?其亦難言矣。”吳棫從文字的難易開始懷疑確實獨具只眼,認為伏生、孔安國的傳授與批注的訛誤也造成了“作書之本意”的不可把握。吳棫發前人之未發,為后代從整體上重新審視《尚書》有重要啟發意義。其后,王柏(1197--1274)《書疑》認為造成《書》疑問題的原因在于“秦火一也,傳言之訛二也,以意屬讀三也。”[11]又認為《大禹謨》當為《禹謨》,已觸及《大禹謨》的真偽,但并無明確有關“十六字”的論述,觸及最深者還在朱熹。
朱熹對《尚書》的疑惑與“虞廷十六字”有重要聯系。《朱子語類》卷七十八云:“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同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于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又云:“《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1]朱熹的懷疑在情在理且直中要害。此疑最終在后世如明人梅鷟尤其清人閻若璩、惠棟、丁晏諸儒的考證中被證實。
針對上述疑經風潮與《書》疑之議,值得思考的問題在于,既然宋代已疑《大禹謨》存在作偽的可能性,則建立在其基礎上的“十六字心傳”與道統體系是否仍然具有合理性?另外,宋儒疑經的實質如何理解。
首先,“十六字心傳”與道統體系建立的合理性顯然是不可否認的。三圣相告的傳承是一種普遍認同的價值和事實,并非由《大禹謨》中此十六字所任意發揮,所以,《古文尚書》的文本即使確存偽作可能,“虞廷十六字”所本的歷史來源則不可否認是真實的,如上文所述,《論語·堯曰》中即有堯、舜、禹三圣以“允執其中”相傳的記載,又有《中庸》《荀子》等書的論述。即使此十六字的文字乃偽造,其所論之事實則不偽已為其他文獻所證明。儒家道統體系的確立是構建在儒家的傳承精神之上,而不在此十六字的表述。其二,對于宋人疑經的實質問題,可以從朱熹的態度做一說明。朱熹一方面對《尚書》充滿疑惑,一方面有極力又維護。朱熹自身的一句話最能說明問題本身:“《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宋儒疑經其實并不是為疑經而疑經,不以疑經為目的。相反,其疑經的實質乃是尊經,維護先秦經典的本源面貌,以糾“圣人有郢書,后世多燕說”之弊,目的在于剝落諸經流轉之偏頗而正本清源,罷黜訓詁,直尋義理,求“二帝三王之心”以經世致用。其所疑所尊,可以說始終不離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感與自我期許,這正是宋儒思想的內核所在。
[1]黎靖德編.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局,1985.
[2]尚書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M].北京:中華書局,1980.
[3]朱熹.朱子全書(第20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程顥,程頤.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
[5]蘇軾.書傳[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6]林之奇.尚書全解[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7]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8]皮希瑞.經學歷史[M].上海:上海書店,1996.
[9]楊新勛.宋代疑經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07.
[10]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王柏.書疑[M].樸社出版,1930.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張志杰,男,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宋代文學與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