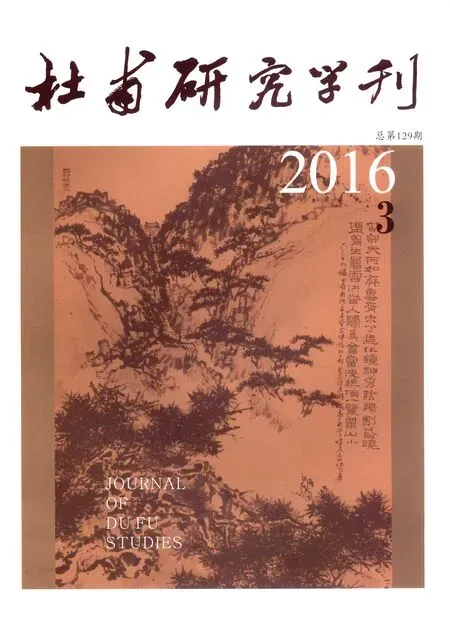宇文所安杜詩英文全譯本“The Poetry of Du Fu”書后
曾祥波
宇文所安杜詩英文全譯本“The Poetry of Du Fu”書后
曾祥波
2016年出版的哈佛大學宇文所安教授 (Stephen Owen)譯“The Poetry of Du Fu”,是首部學術性的杜詩英文全譯本。就譯本所用底本,譯本對杜甫研究現狀及相關文獻的掌握,對杜集早期編纂與流傳狀況的分析,對杜甫形象、杜詩詩歌“真實性”、杜甫的性格及能力等問題的理解,以及對翻譯的技術性操作的說明等方面來看,該譯本體現了目前西方漢學界杜甫研究的前沿水平。
杜詩 英譯 杜集版本 翻譯技巧
杜詩的首部西文全譯本,是1932—1938年間出版的厄溫·馮·薩克 (Erwin von Zach)德文全譯本。2008—2009年,美國人James R.Murphy自助出版的“Murphy’s Du Fu”四卷是首部杜詩英文全譯本,然出自民間愛好者之手,未為學術界所重視。哈佛大學宇文所安教授 (Stephen Owen)譯“The Poetry of Du Fu”則是首部學術性的杜詩英文全譯本,2016年出版后即引起學術界的關注。
譯本采取了比較新穎的出版方式,一方面有皇皇六大冊的紙質書刊印行世,另一方面讀者也可以通過網絡 (www.degruyter.com)獲得公開免費、長達3000頁的電子版PDF文本。關于此點,譯本 《致謝》解釋說:“杜詩六冊全譯本是獲得梅隆基金資助的 ‘中華人文 (經典譯本)文庫’(Library of Chinese Humanities)收錄的第一種典籍譯本,此后的系列典籍譯本都將以普通紙本與網絡免費獲取的電子文本兩種形態面世。”(“The Poetry of Du Fu”,Acknowledgments, vii)①即使在這個時代,快捷獲得最新的異國出版物也并非容易之事,譯本采取的這種出版形式確實體現了學術為天下公器的精神,讀者很方便通過網絡獲得電子版,第一時間來品味譯本對杜詩的理解傳達。
就我的初步閱讀體會,譯本確實體現了目前西方漢學界杜甫研究的前沿水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譯本對底本的選擇。
譯本的文字底本主要依靠 《宋本杜工部集》(Song edition)、郭知達 《九家集注杜詩》,以及宋人編 《文苑英華》及 《唐文粹》中的杜詩文本 (“The Poetry of Du Fu”,Introduction,lxxxiv)。這四種版本的選擇可謂當行有識。對宋人編類書、總集中杜詩文本的利用,很有眼光。就杜集系統而言,直接源出王洙、王琪編,裴煜補遺祖本的 《宋本杜工部集》自不待言。郭知達《九家集注》本是宋代集注本中公認選擇有法的善本,洪業 《杜詩引得》即以此本為工作底本,而不取所謂以南宋初紹興三年建康府學“吳若本”為底本的 《錢注杜詩》,并在 《杜詩引得序》中對所謂“《錢注杜詩》用吳若本為底本”的說法提出十條懷疑。195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 《宋本杜工部集》,張元濟作跋考其書為王洙本十五卷與吳若本五卷的衲配本,洪業因此承認了吳若本的存在。但今天的最新研究已經說明 《錢注杜詩》任意篡改吳若本編次,并對其改動刻意隱瞞,已非可堪引據的善本,洪業的“十條懷疑”大部分仍是正確的。②譯本選擇《九家集注杜詩》而非 《錢注杜詩》(吳若本)作為底本,正說明了對這一學術公案的了解與判斷。
另外,杜集與一般古代典籍還有一點不同,即在文字文本之外,同樣重要的還有詩篇之間的編次,因為編次意味著對杜詩的系年,而系年是杜詩作為“詩史”的核心因素之一。杜集版本有三種基本形態:即分體本、編年本與分類本(分韻本亦可歸入分類本)。除去分類本,前兩種形態的編次都帶有系年意圖。因此,杜集底本除了文字因素之外,必須考慮到編次因素。譯本在這一點上做得極好,文字上以上述四種杜集或宋人編類書、總集的宋本為底本,編次上則選用仇兆鰲 《杜詩詳注》作為底本。 《凡例》(Conventions of Presentation)交代說:“譯本按照仇兆鰲 《杜詩詳注》(1703年)的順序將詩篇依次編號,第一個數字代表卷數……仇兆鰲本將體裁(古體、近體)打亂后對詩篇加以系年編次。盡管現代杜詩選本將某些詩篇系于不同年代,學者們對某些詩篇的系年也有相當激烈的爭論。大體來說,仇兆鰲本做得很好了,有明顯系年依據的詩篇作了準確的系年編次,有待爭議者仍保持可爭議性,無法準確系年定位者一仍其舊。” (Introduction,lxxxiii)選擇仇兆鰲 《杜詩詳注》作為英譯編次的底本,對西方漢學讀者還有兩個好處:首先,仇兆鰲 《杜詩詳注》號稱清人杜注的集大成者,從資料搜集的廣泛性來說,對讀者很有幫助,漢學讀者如果對譯本還不夠饜足,可以根據譯本詩篇的編號,很方便地找到仇本文本進行延伸研究。其次,目前漢語世界中最為全面詳盡的杜甫行實研究與杜詩闡釋之作,是陳貽焮先生的 《杜甫評傳》。該書以現代漢語撰寫,在杜甫行實梳理、詩篇順序與詩義理解上,大致以仇兆鰲本為底本,漢學讀者如果對仇兆鰲注時有疑惑,那么根據譯本的編次數目,對應到 《杜甫評傳》的相關部分,一定會獲得更好的閱讀體驗。
第二,譯本對杜甫最新研究現狀的把握。
從譯本對杜甫研究的最新進展比較熟悉。其中對西方杜甫研究學術狀況的熟稔是題中應有之義,如洪業 《杜甫》一書,譯本 《前言》主要從杜詩翻譯的角度加以評價,認為:“洪煨蓮的杜詩翻譯主要是從杜甫傳記敘述的角度進行了散文式翻譯。” (Introduction,lviii)另外,“劍橋中華文史叢刊” (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literature,and institutions)收錄的周杉(Eva Shan Chou) 《重識杜甫:文學巨匠及其文化語 境》 (“Reconsidering Du Fu:Literary Greatness and Cultural Context”,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95)各個章節多以洪業《杜甫》作為出發點展開論述,是近些年關于杜詩接受史比較重要的漢學著述。譯本 《前言》一開篇談到“杜甫在十一世紀就被加以推崇,不僅被作為唐詩的杰出代表,也被視為儒家價值觀的充分人格體現,這些意義在宋代又不斷被加強”(Introduction,liii),就特別提到對此問題的更全面闡述可以參見周杉 《重識杜甫》一書。
譯本對中文世界里杜甫研究較為顯著的進展也有關注。如譯本提及陳貽焮 《杜甫評傳》三大冊,指出如果細讀此書,會得到極為明顯的印象,即作為文學文本的杜詩中,“歷史”的因素占據了多么大的分量 (how deeply Du Fu’s poems are embedded in history,Introduction,lviii)。應該說,這個評價對 《杜甫評傳》一書的撰述著力點的認識比較到位。2014年出版,蕭滌非主編、張忠綱終審統稿 《杜甫全集校注》是近年來國內杜集整理最重要的成果。譯本對此也有關注,一方面提及 《全集校注》耗費35年心血而成,同時自道甘苦,承認翻譯杜甫是一個“耗費時間精力的黑洞 (a black hole)”,喜見漢語 《全集校注》之成,自言有“吾道不孤”之感 (I felt that I was not alone,Acknowledgments,liii);并給予較高評價,指出 《全集校注》有取代仇兆鰲本成為最新標準本的趨勢 (likely to supersede Qiu as the standard edition,Conventions of Presentation,lxxxiii),在某種意義上,就其杜注資料集成性 (a large compendium of premodern scholarship)而言,已經是仇兆鰲本的有益的替代者了(a useful replacement for Qiu Zhao'ao,Conventions of Presentation,lxxxiii)。另一方面也不無遺憾地嘆惋,指出譯本對杜集早期版本的異文校勘(collating 1400 poems in the early editions),在早于譯本出版兩年的 《全集校注》的同類工作面前,不免顯得重復了 (Acknowledgments,liii)。這種校勘對英語讀者來說,還是很有意義的。有必要指出,因為 《杜甫全集校注》共有皇皇十二大冊,而且出版不久,所以英譯本對它的利用不夠是很自然的。盡管如此,英譯本已經迅速在詩篇中添補了 《全集校注》的相關頁碼,有利于讀者按圖索驥以資利用了。
第三,譯本對早期杜集編纂與流傳狀況的推測。
英譯本最見學術鋒芒的靈光一現,是對早期杜集編纂與流傳狀況的推測,頗具啟發性。譯者以杜甫晚年漂泊湖湘期間 《入衡州》“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兩句為例,譯作“My soul melted,escaping the flying arrows,I crept fearfully through those wolves and jackals”,然后發揮說:“我們不得不設想,這個旅途中的戲劇性場面里,總得有人隨身攜帶著至少一千四百首詩稿,不是以書冊形態,而是以六十卷帙的抄本形態。③累足,如果逐字翻譯,即一只腳踩在另一只腳之上,代表著極其恐懼的形象。即使我們允許詩歌有著某種隨意描寫的特權,但在這種情況下,也總得給六十卷帙的詩稿騰出個地兒,再算上杜甫的隨身攜帶用品,例如烏皮幾,④以及毫無疑問的,杜甫還要隨身攜帶其他自用藏書。如果我們相信杜甫自己在公元八世紀五十年代早期所說的,‘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到那時已經寫下了千首詩篇。而杜甫的早期詩作大多已經亡佚,考慮到他曾經歷了長安陷落于安史叛軍之手的那段危急歲月,這一點都不令人奇怪。我們所讀到的杜甫早期詩作很可能是后來根據回憶追記的。換言之,沉重的六十卷帙詩集,乃是出自一位完全成熟的詩人之手。”(Introduction,lvi-lvii)中國學者對杜集早期編纂與流傳狀況也有過相關研究,但像英譯本這樣推測到“場景還原”的細膩、可信程度,似乎還不多見。
再如譯本論及杜集的編年編纂方式,說到:“我們能看到的最早宋本,以古體和近體兩種類別編纂,兩部分中的詩篇皆按系年編次。我們并不太了解唐代集子的編纂形態,只能根據某些跡象來推測。從某些證據來看,杜集可能是最早以系年編次的詩集之一,盡管在系年之上還存在著一個 ‘分體’ (古體、近體)的層級。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杜甫用詩歌循次記錄了自己的一生。”(Introduction,lvii)對杜集二王祖本表面為“分體本”,實則“分體”之下為“編年本”這一性質特點的點明,頗具慧眼。筆者曾撰文談及杜詩系年的版本依據,也指出此一問題至為關鍵,這使得杜詩研究的核心因素之一“系年”研究,因為存在祖本的“編年”性質,從而獲得了編次上的源頭性版本基礎。⑤故讀至英譯本此處文字,不覺有會心之怡也。
在以上三種顯著優點之外,譯本中的某些觀點,也許未必能取得一致認同,但也有相當的啟發性。如對杜甫詩歌“真實性”的質疑,譯本將這個質疑命名為“應酬之詩”(The Business of Poetry)。譯本選取 《送重表侄王砅評事使南海》中的兩句“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 (My greatgrandfather's sister,was your great-grandfather's mother),指出:“沒有其他杜詩以這么令人難忘的平庸方式開頭,然而這正是詩歌的社會應酬功能之一,用來建立與受贈者的某種關系——就這首詩而言,家族關系被追溯到唐代開國之初——詩歌藉此往下發揮。” (Introduction,lix)關于此詩,仇兆鰲考辨說:“自高祖起兵,至代宗大歷五年,共一百六十余年。公祖審言仕武后、中宗之世,其曾祖姑應生于太宗季年,不應生于隋文之代。以年數世次考之,則杜為珪妻,尚疑太早。此條記事,斷屬差誤。”⑥因此,仇注結論是:“今按此詩所載事跡,明與 《唐書》紀傳不合……大抵人情好為夸大,每有子孫而自誣其祖宗者,此詩亦據王氏傳聞之說,一時沿訛,失考耳。”⑦但是,試想年邁的老杜在國亂家破之后,與重表侄王砅相逢于湖湘,追憶親舊,撫嘆開元,或者是王砅挑起話頭,或者是老杜緬懷家風,亦或還有旁人在座,一座相與煽噓烘托,共同緬懷大唐開國之初的輝煌功業、奇人異事,是完全可能的,具有“通性之真實”;即使老人記憶上有所偏差,后輩作善意的應和,就“現場的真實”而言也是很有意義的。所以,趙次公注說得好:“洪龜父云:老杜 《送表侄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從欵如此,敘說都無遺。其后忽云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再論其事,他人更不敢如此道也,其說是。然上言虬髯,則王殊母所見之辭。此言秦王,則公講之辭,蓋秦王,太宗也,所以引下句尚書踐臺斗之事。龜父不省也。”⑧鐘惺更從讀者的角度表達了對此詩的激賞:“前段不過敘中表戚耳,忽具一部開國大掌故。自往者以下,只是亂離相依,飲食仆馬細故,卻無端委轉折可尋。胸中潦倒,筆下淋漓。”⑨鐘說確有性靈體悟!總之,此詩完全超出一般應酬之作的園囿,以致于使得見多識廣如胡震亨略表懷疑:“此詩轉韻后,事辭俱不屬,疑本是二首,前首缺其后,后首缺其前也。”⑩撇開“真實性”角度,從詩歌體制來看,子美以老手斫輪,批郤導窾,真可謂提筆四顧而躊躇滿志。胡震亨疑為兩篇之牉合,恐怕對老杜晚年臻入化境、竹頭木屑順手拈來皆足成篇的手段皆認識不足。換句話說,譯本提出“應酬之詩”概念與真實性的關系問題,確實值得重視,然而這個例證沒有注意到 《送重表侄王砅評事使南海》一詩既帶有寫作情境中的現場感,又在史實上具備“通性之真實”,還忽略了老杜晚年在詩歌體制上的開闔妙用。這或許是譯本考慮到英語讀者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社會性 (business)不夠熟悉,從而作出的一種帶有協調性的闡釋。
與“真實性”問題相關的,是譯本對杜詩作為杜甫“生活史”記錄的可靠性的反思。譯本認為:“詩歌似乎常常代表了杜甫對生活中偶然事件的一種文學回應,我們也知道杜甫總是在修改他的詩作——因此我們完全無法確定,如今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詩歌文本,在多大程度上是杜甫當下即時性的回應,亦或是杜甫根據近來的回憶寫成,甚至是他根據更遙遠的記憶追溯所得。我們發現自己 (閱讀杜詩時)處于日記與自傳兩種體裁之間,記錄者對當下事件迅速反應、形成文字,文學家卻會建構自己的生平 (constructing his life),說那些按他們的身份應該說的話(things he should have said)。”(Introduction,lvii)這個觀點很有見地。按照一般的理解,現存最早的杜詩已經是杜甫省親兗州時期所作,即使按照洪業的觀點,《夜宴左氏莊》是今存最早的杜詩,作于杜甫漫游吳越期間,?那也已經是杜甫青年時期了。其實很多所謂杜甫幼年的生活經歷,例如四歲觀公孫大娘舞劍器 (錢謙益認為應該是六歲)、七歲詠鳳凰等,都是他晚年如夔州時期的詩作,這些信息有沒有必要作為信史看待,并生發出相關的微言大義,確實需要慎重。
其二是對杜甫政治能力的定位。譯本認為:“除卻作詩,杜甫沒有其他技能——然而作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這就足夠了。而且杜甫對普通民眾的同情也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替他加分。不過,杜甫的政治判斷力常常有誤,他總是天真,為了支持朋友而帶有片面之見。在那樣一個動蕩時代,人們或需要政治上的敏銳性,或者應具有采取行動的能力,杜甫恰缺乏這兩點。他不懂得維持這個搖搖欲墜的帝國需要政治平衡手段。短暫擔任華州司功參軍的經歷,似乎可以體現杜甫行政能力的大致水準,而他極度地厭惡這個工作……他經常承認自己的懶散,承認自己不善處理事務——這都應該屬實。”(Introduction,lxii-lxiii)老杜作為中國人的“詩圣”,作為中國文化中士人精神生活與文學創作的一種標準,理所當然得到推崇。加上他一生遭遇的種種不幸,使得推崇之上附帶了值得憐憫的成分,更顯得容易親近。低姿態而為人親近的善良之輩,常常獲得好評,而一切缺陷都容易被忽略、寬恕。然而在注重事務、講求實際的眼光里,詩人杜甫的行為能力確實沒有在現實世界里得到他在詩歌中自詡的那種效果。當然,譯者所說“支持朋友而帶有片面之見”,應該是指杜甫陷入房琯之黨的麻煩。目前學界已經漸成共識,即房琯被罷免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陳濤斜以車戰而潰敗,而在于他最早為玄宗提出“諸王分領諸道節制”的“強干弱枝”之法,在肅宗即位之后,已經變成諸王威脅肅宗地位的一種隱患,而杜甫從始至終都堅定支持房琯的這一主張,指出“由來強干地,未有不臣朝” (廣德元年 《有感五首》其五)、“必以親王委之節鉞”(廣德元年 《為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等等。 “支持朋友而帶有片面之見”的說法,還可以再作進一步討論。另外,我記得洪業在 《我怎樣寫杜甫》一文中曾經指出:“再說他在華州那一段罷。司功參軍的位置約當于今日教育廳長。唐時每年秋中須舉行鄉試,好選送諸生來年在京應禮部之試。杜甫的文集里有五道策問,是很有意義的文字。記得十一年前我以譯寫華州那一段的初稿,交與一位現在已去世的老太太,請她替我在打字機上打出清稿。她半夜打電話告訴我說:‘我真沒想到在中國的詩人中,居然有一個像這樣的腳踏實地關切國計民生的大政治家。’”?洪業的杜甫研究譽滿漢學界,譯本的議論似乎為此而發。杜甫的文字與行為在中、西方視野里得到不同的理解,這對于了解杜甫接受史,了解在不同文化世界的價值觀念中對同一事物的評判差異,也是很有意義的。
譯本談到杜甫排律問題,指出:“杜詩翻譯中,譯者遇到問題最多者無過于排律。杜甫的大多數排律 (也有個別著名的篇章例外?)是寫給社交圈的朋友們。這些朋友是誰,常常可以通過詩題小注標明的排行 (the number of footnotes)辨識,而詩題往往也會標明全詩共多少聯 (韻)。有時,杜甫的排律是同時寫給兩位朋友的,A和B,詩中的聯語,不露聲色地指向A,然后指向B,或者倒過來。即使是最簡略的注家也不得不說明具體的詩句是指向哪一位。” (Introduction,lxiii)宋注也指出過與此類似的杜甫慣用的藝術手法。宋人趙次公著有 《句法義例》(今佚,散見于 《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校》),其中提到所謂“雙紀格”,如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光”,次公注:“尋常兩句,或皆用美一人之身,或一句說彼,一句說此,詳見 《句法義例》。”又如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峣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趙次公皆注為“雙紀格”。結合“雙紀格”,就更能理解譯本所指出的排律中分述A、B的手法了。另外,譯本對2014年出版的 《杜甫全集校注》評價很高,也引用 《杜集敘錄》,但文中涉及二書主要編著者之一張忠綱先生時,皆誤寫作“張忠網 (Zhang Zhongwang)”,應是排版之誤。?
就具體詩歌譯文而言,譯本采用中英文并行對舉的方式,便于覆核,應該成為一種通例。筆者初讀之下,覺得辭義平正,堪與譯者自己提出的翻譯期待相符合。譯事艱難,且工程浩大,欲通覽尋繹,尚須來日。西方漢學界對中國唐前典籍的翻譯,令人矚目的有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倪豪士教授 (William H.Nienhauser,Jr)的《史記》英譯 (尚未最終完成)、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康達維教授 (David Knechtges)的《文選》賦英譯等,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教授的杜詩全譯本以其嚴謹的學術性,也將進入這一令人矚目的中國文學典籍譯本的行列中。
注釋:
①按,以下引用皆出自宇文所安教授杜詩英文全譯本“The Poetry of Du Fu”,由筆者徑譯為中文,不再贅注書名,僅標注英譯本的章節標題及頁碼。
②參見曾祥波:《〈錢注杜詩〉成書淵源考——從編次角度論 〈錢注杜詩〉與吳若本之關系》,《中國典籍與文化》2015年3期。
③按,關于六十卷的信息,如五代劉昫 《舊唐書·杜甫傳》載:“甫有文集六十卷。”北宋王洙 《杜工部集記》:“甫集初六十卷。”
④⑥⑦⑨仇兆鰲 《杜詩詳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109頁、第2043頁、第2048頁、第2048頁。
⑤參見曾祥波:《論杜詩系年的版本依據與標準》,《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1期。
⑧趙彥材撰,林繼中輯校:《杜詩趙次公先后解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93頁。
⑩蕭滌非主編,張忠綱終審統稿:《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3頁。
?洪業撰,曾祥波譯:《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427頁。
?洪業撰,曾祥波譯:《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附錄三 《我怎樣寫杜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頁。
?按,譯者所指應該是如 《偶題》等詩篇。
?散見于頁lxxii注?、頁lxxiii注?、頁lxxiv注?、頁394《縮寫表》第4行等處。
責任編輯 張月
作者:曾祥波,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