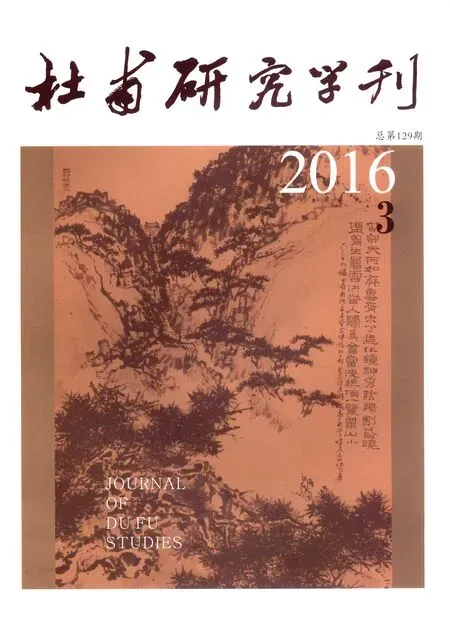李杜賦及詩賦地位的變遷
劉偉生
李杜賦及詩賦地位的變遷
劉偉生
李白 《明堂賦》《大獵賦》,杜甫“三大禮賦”及 《封西岳賦》,均屬光贊盛美之作。真正能表現李杜個人性情的是詠物自喻、寫景抒懷之作。李白 《大鵬賦》、杜甫 《雕賦》,既完成了個體生命的宏觀寫照,也切合著國家形象的時代建構,并以其高遠的境界與卓異的品質感染著歷代讀者。李杜賦作的體制風貌同而又異。“同”在:假賦試才以求仕進,以散馭駢以為新變。“異”在:李白與心徘徊,以文馭詩、化詩入賦,以至詩賦難分,由此可見賦體新進的承繼與預告;杜甫隨物宛轉,刻意錘煉、化賦入詩,乃至以賦為詩,留給賦史的是超越傳統的失敗與警示。自李杜始詩取代賦而成為文壇主流。詩賦地位的消長主要由詩賦本身的體式特征所決定,也與外部環境有關。
李白 杜甫 詩 賦
作為中國古代頂尖的詩人,李白和杜甫在詩歌上的成就一向不欠關注,也不乏清晰公允的論斷。可當詩賦兩大韻文文體,詩史、賦史兩大文學脈絡交織于這兩位雙峰并峙的大詩人身上時,會激發我們怎樣的思考與期待?可不可以參照詩歌史的研究比較他們的辭賦在題材內容與體制風貌上的異同?可不可以籍此特殊個案探究詩賦不同的文體特質及其相融互化的過程,探究詩賦不同的發展脈絡及其相對地位的變更,甚至作家性情稟賦與賦體特質之間的隱微關聯?本文即嘗試做這些方面的努力。
一、李杜賦的題材內容與性情稟賦
今存李白賦八篇:《明堂賦》《大獵賦》《擬恨賦》《大鵬賦》《惜余春賦》《愁陽春賦》《劍閣賦》《悲清秋賦》;杜甫賦七篇:《朝獻太清宮賦》《朝享太廟賦》《有事于南郊賦》《封西岳賦》《雕賦》《天狗賦》《越人獻馴象賦》①。李杜賦題材相對集中,一半光贊盛美,一半詠物抒懷。
(一)盛世之禮贊、致仕之捷途
李白 《明堂賦》《大獵賦》,一寫宮殿、一寫田獵,杜甫“三大禮賦”及 《封西岳賦》鋪述典禮,均屬“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京殿苑獵”之作。
《明堂賦》序文及首段回顧皇唐“革天創元”的偉績與明堂“累圣纂就”的經歷。然后極陳明堂之宏大壯麗:
觀夫明堂之宏壯也,……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豁龍門以開關。……勢拔五岳,形張四維;……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其左右也,則丹陛崿崿,彤庭煌煌,……其閫域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筵列位,南七西九。……其深沉奧密也,……②
上合天文,下得地理,遠則勢拔五岳,形張四維,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左右丹陛彤庭,室內戶牖密布。這一大段文字由大至小、由遠及近,由外而內地鋪陳了明堂在天地、日月、山川間的雄偉氣象,明堂左右建筑的布局與室內結構面積、神位圖畫等情況。接下來寫圣主祭祀神靈、宴請群臣。最后申明理國若夢的理念與目標:“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群云從龍,眾水奔海”。
《大獵賦》與《明堂賦》結構略同。開篇即頌揚玄宗“總六圣之光熙”“括眾妙而為師”的開元之治,并交待按古制校獵于冬日農閑之時。然后極力鋪陳天子田獵的規模聲勢。再往下集中筆力專寫勇士搏擊猛獸、君王親臨指揮,說這場面連秦皇、漢武也不足爭雄。然后突然一轉,寫君王“茫然改容,愀若有失;居安思危,防險戒逸”,命撤網釋禽獸以示君主之仁。最后以狩獵為喻,諷諫天子收羅賢俊以輔佐朝廷,天子接受諷勸,回心向道,結束田獵。
杜甫“三大禮賦”為同期作品,分別為唐玄宗太清宮、太廟、南郊三大祭祀典禮而作。太清宮祭享“圣祖玄元皇帝”老子,《朝獻太清宮賦》前半鋪陳朝獻的由來、路次、儀衛、過程、場面與氛圍,極寫廟宇軒昂、陳設輝煌、儀衛繁盛、執事虔備,圣主颙望神靈,有洋洋如在之意。后半設為問答,先代玄宗陳意,言自三國以來世運紛擾、天下瘡痍、生靈顛躓,唐興致治,順天應民,所以禎符畢集、靈異昭應。然后假天師答頌之辭,嘉美唐王朝厘正祀典之盛德。結尾筆鋒突轉,說當此太平之世,莫不優游自得,何況開創繼起之人。暗喻天下太平,實人主自致,非關神降。太廟為皇家祖廟,《朝享太廟賦》開篇即敘寫祖功宗德,并強調漢唐正統,以為朝享張本。然后從鑾輿初出,虔宿齋宮開始,鋪陳朝享的過程、儀式及場面氛圍,大抵也是殿宇森嚴、執事誠恪、從官肅恭、音循舞亂。中間插入功臣配享之事。最后假丞相陳詞,極言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其“勤恤匪懈”與“恢廓緒業”非前代可比。③南郊合祭天地,是三大祭禮的最后一項。與前兩賦一樣,《有事于南郊賦》也對先期準備、主祭場面及祭畢推恩的整個過程詳加鋪述。賦末則假孤卿侯伯、群儒三老上推歷數,追原圣祖,歸功玄宗。
《封西岳賦》的結構程式也類同于三大禮賦,首敘封岳之意,次敘儀衛之盛,然后寫登岳封禪、祭畢作樂,最后歸美帝德。
宮殿、田獵、祀典的表層描繪與陳述所承載的是赤裸的頌贊與隱微的諷喻,這頌贊與諷喻表彰著相同的時代意趣。
除了歌功頌德、娛樂人主的通常特性外,李杜這些潤色鴻業的賦作,還有著身國合一的自我張揚。無論國家還是個人,山河一統與國勢強盛都是最值得驕傲與自豪的資本。與漢人相比,歷經大分裂、大動亂后的唐人更能感受到山河一統的寶貴,上舉五賦都用了不少筆墨盛贊大唐帝國的開創過程,杜甫三賦更能以社會發展的眼光,陳述古今歷史的變遷,強調國家正統的延繼,表達對唐王朝一統天下、長治久安的謳歌。卒章諷喻的傳統在李杜這里也有承繼,不過一個更直接地陳述理想、描寫仙國,一個更含蓄地規避怪誕、遵奉禮制。
不管是赤裸的頌贊,還是隱微的諷喻,上述賦的意涵,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的獻奉本質。這類獻奉之作,固然不乏對大唐帝國由衷的贊美,也因賦需大才足以讓人獲取終生自豪的資本,但最根本的目的還在于媚主求仕。這樣的寫作目的與體制遵從便決定這些獻奉賦難脫古人窠臼,難得后人好評。當然它承續了漢代以來的獻賦傳統,展示了盛唐的社會環境與獻賦風氣,也反映了人性的多面與辭賦尚存的地位。李白、杜甫兩位詩歌泰斗的介入,便一方面反映了時代風尚,另一方面也說明在當日的仕途上,詩歌并未完全取代辭賦。
(二)個我之形塑、愁情之散發
真正能表現李杜個人性情,代表李杜辭賦成就的還是那些詠物自喻、寫景抒懷之作,如李白的 《大鵬賦》《擬恨賦》《惜余春賦》《愁陽春賦》《劍閣賦》《悲清秋賦》,杜甫的 《雕賦》《天狗賦》。
詠物而有寄寓,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真正以物自況、以物自喻的賦先唐時期并不多見,自李世民 《威鳳賦》開始驟然增多,如楊譽 《紙鳶賦》、盧照鄰 《窮魚賦》、王勃 《澗底寒松賦》、駱賓王 《螢火賦》、崔融 《瓦松賦》、楊炯 《幽蘭賦》、宋之問 《秋蓮賦》、馬吉甫 《蝸牛賦》、鄭惟忠 《泥賦》、東方虬 《尺蠖賦》等等。但這些賦往往還只是比況賦家一時的處境或某一方面的習性,不足以表征整個活脫的生命,所選物象也多瑣細、幽冷、窮困、卑微。唯李白 《大鵬賦》、杜甫 《雕賦》,既完成了個體生命的宏觀寫照,也切合著國家形象的時代建構,并以其卓異高遠的境界與品質感染著世世代代的人們。
《大鵬賦》由莊子《逍遙游》開端敷衍而來,細述大鵬初化、升騰、翱翔、息落的過程。說其初化時:
脫鬐鬣于海島,張羽毛于天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憑陵乎昆侖。一鼓一舞,煙蒙沙昏;五岳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④
海島、天門、渤澥、扶桑、宇宙、昆侖、五岳、百川,用的都是極宏大的地名,為大鵬的出世提供了無垠的空間。言其起飛時:“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迅征;……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突顯的是大鵬升騰時非凡的氣勢。至其騰空飛翔時:
足縈虹蜺,目耀日月,……噴氣則六合生云,灑毛則千里飛雪。……塊視三山,杯觀五湖。……任公見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爾其雄姿壯觀,坱軋河漢,上摩蒼蒼,下覆漫漫。……繽紛乎八荒之間,掩映乎四海之半。……忽騰覆以回旋,則霞廓而霧散。⑤
塊視三山,杯觀五湖,任公罷釣,有窮棄弧,上摩蒼天,下覆九州,遨游八荒,掩映四海,渲染的都是鵬翔高天時的雄姿。便是息落,也讓水伯海神為之驚恐,巨鰲長鯨躲匿不出。總歸起來,賦中的大鵬鳥是神異、奇絕、壯偉、迅疾而又逍遙自在的。作為自譬自喻之作,《大鵬賦》所塑造的大鵬形象寄寓的是李白個我意向高遠、氣概豪邁、適性自由、鄙薄塵俗、藐視庸常的心志情懷。
再看杜甫筆下的勁雕形象:
當九秋之凄清,見一鶚之直上。以雄才為己任,橫殺氣而獨往。梢梢勁翮,肅肅逸響。杳不可追,俊無留賞。彼何鄉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鷙鳥之累百,敢同年而爭長。此雕之大略也。⑥
賦的開篇,即以直上之鶚引寫大雕的志趣、形貌、效用,并比對鷙鳥,算是總起以明大略。雖是大略,卻足以勾畫出大雕雄俊勇決、所向無敵的形象。以下分別寫虞人捕雕之艱苦、閩隸馴雕之嚴酷、大雕捕獵之神勇、比諸凡鳥之卓異,最后寫不被見用之寂寞與不失其志之品格。其中關于大雕形象刻畫最為精粹者莫過于以下兩段:
觀其夾翠華而上下,卷毛血之崩奔。隨意氣而電落,引塵沙而晝昏。⑦
夫其降精于金,立骨如鐵,目通于腦,筋入于節。架軒楹之上,純漆光芒;掣梁棟之間,寒風凜冽。⑧
一寫動,一寫靜;動如電落,迅猛雄俊;靜同鐵骨、凜然難犯。活畫出了大雕的才具、魄力、狀貌、神采。
作為自喻賦,《雕賦》終歸是在寫作者自己,寫自己的希企效用與貞剛正直。仇兆鰲 《杜詩詳注》說:“公三上賦而朝廷不用,故復托雕鳥以寄意。其一種慷慨激昂之氣,雖百折而不回。”又:“全篇俱屬比喻,有悲壯之音,無乞憐之態,三復遺文,亦當橫秋氣而厲風霜矣。”⑨杜甫自己在 《進雕賦表》中則說:“臣以為雕者,摯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于旌門,發狂于原隰。引以為類,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賦。”⑩
總之,李白筆下的大鵬神異、奇絕、壯偉、迅疾、逍遙,它寄寓的是作者志高意遠、適性隨意、奔放自由的主體追求與自得意滿、雄豪狂傲的心性氣格;杜甫筆下的雕勇悍絕倫、迅猛雄俊,寄寓著作者擔當效用、正色立朝的意旨與失意、悲壯、剛烈、正直、謇諤的性情品質。
《大鵬賦》與《雕賦》都作于天寶前期,適值大唐王朝繁榮昌盛之時,“愿為輔弼”(《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李白與“致君堯舜”(《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杜甫不約而同地以神異雄健的猛禽為鋪陳對象,既寄托了李杜個人建功立業的理想抱負,也煥發著大唐蓬勃向上的時代精神。
杜甫 《天狗賦》也是托物寄慨之作。賦從天狗所處環境寫起,接連刻畫其神氣品貌、出獵雄姿、承用經歷與見疑心緒,莫不為自愿效用、自負才雄、自命清剛的杜甫待制集賢院,始蒙賞識而終不見用,混非同類,群材不接的情景心境之寫照。
平心而論,李杜詠物自喻之賦,在整個賦史中,也算是絕構了。
詠物而外,李白的寫景抒懷之作,多寫愁苦情緒,清新別致。如 《惜余春賦》,寫北斗東指,天下皆春,作者登高望遠,但見楚地瀟湘芳草萋萋,頓生時光消逝、佳人難遇、行人遠別等種種無所不在而又莫可名狀、難于確解的愁緒。如 《劍閣賦》,前半寫劍閣橫斷、松風蕭颯、巴猿長嘯、飛湍灑石,后半以“佳人”“夫君”比友人,發抒眼前的離愁、懸想別后的牽掛。而這表層的情景背后,其實也暗含賦家本人對世路艱險、光陰虛度的感喟。與 《大鵬賦》相比,李白的這些小賦在情感的抒發上真有天壤之別,一邊高昂豪邁,一邊感傷愁苦,大概他將那些壯志未酬、人生遲暮的愁思都發諸在魏晉以來就擅長抒懷的小賦里了。又或如李長之所言:“李白的價值是在給人以解放,這是因為他所愛、所憎,所求,所棄,所喜,所愁,皆趨于極端故。”?
二、李杜賦的體制風貌與詩賦的互化
李杜賦的題材內容與體制風貌同而又異。這“同”,體現在:文才之展示 (假賦試才)與傳統之復歸 (以散馭駢)。這“異”,在李白是:與心徘徊,以文馭詩、化詩入賦,以至詩賦難分,由此可見賦體新進的承繼與預告;在杜甫是:隨物宛轉,刻意錘煉、化賦入詩,乃至以賦為詩,留給賦史的是超越傳統的失敗與警示。
(一)傳統之復歸與文才之展示
獻賦而能致仕,是因為“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的傳統觀念與創作實踐,李杜以大詩人而作賦,多半也是因循舊例、展示文才,以獲取仕進的機會,因循而又想突脫,必得取法乎上。所以他們不約而同以前代大賦家的大手筆為典則。
李白在其詩文中曾幾次以揚雄自況,夸耀因獻賦而獲得優寵的往事。博學而任俠的相如更為性情相類的李白所景慕:“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從侄耑游廬山序》);“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贈張相鎬》)。杜甫也曾自擬揚馬,或被人比為揚馬:“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贈》); “視我揚馬間,白首不相棄”(《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李杜對揚馬的推崇,無疑是兩個輝煌時代四位文學巨星的呼應,其意義早已超越李杜比超前賢、假賦致仕的原初動因。
題材制約手法,范式影響后繼。李杜對揚馬的推崇落實到賦體創作便表現為題材的因襲與體格的師范。以題材言,京殿苑獵都是漢賦的重中之重,也是漢賦之所以為漢賦,揚馬之所以為揚馬的關鍵因素,李杜要想比擬前賢,便先得選取這些可以“窮壯極麗”、足以“光贊盛美”的題材,所以李杜于獻賦中最傾心的都是有明堂、大獵、四大祭典這些足以體現國家規模、象征國家意志的建筑與活動。題材本身影響體格,京殿苑獵之作因為要“體國經野,義尚光大”,便須配以“鴻裁”與“雅文”,而非“奇巧” “小制”(《文心雕龍·詮賦》),所以李杜的獻賦,在首尾布敘與文辭氣勢方面都會自覺向揚馬看齊。祝堯 《古賦辨體》說:太白 《明堂賦》“實從司馬、揚、班諸人之賦來”; 《大獵賦》“與 《子虛》《上林》《羽獵》等賦首尾布敘,用事遣詞,多相出入。”?杜甫的 《三大禮賦》與《封西岳賦》更極力模擬漢賦。揚馬賦中汪洋恣肆的鋪陳、精雕細琢的描摹、不遺余力的夸飾,在杜賦中比比皆是。因為師法揚馬“宏衍巨麗”之文章體格,在駢體方興的盛唐時代,李杜也能于駢體中貫注散文意氣,從而以散馭駢。如李白 《大鵬賦》,賦中散句恰可構成全篇的敘事框架。 《明堂賦》《大獵賦》更多參差之句、勁健之氣。祝堯在肯定太白 《明堂賦》“從司馬、揚、班諸人之賦來”后,又曾說:“若論體格,則不及遠甚。蓋漢賦體未甚俳,而此篇與后篇 《大獵》等賦則悅于時而俳甚矣。”?受時代影響,李杜賦中的駢對之句肯定比漢賦多得多,但反過來看,因為效仿漢賦,李杜賦又比時文質樸得多。所以馬積高先生針對祝堯的這一觀點說:“實際上這兩篇賦的缺點不在于什么 ‘俳甚’,而在于作者有意學班、馬諸賦,以糾正當時的 ‘俳甚’,但在類似的題材、主題的范圍內,要與前代的大匠爭雄是不容易的,即使象李白這樣的天才也難以辦到。”?祝堯以古賦的標準來衡裁,李杜也難稱合格,其實從賦史演變的實際來看,李杜在由駢而散的復古革新歷程中也是不可忽略的環節。仇兆鰲 《杜詩詳注》為《朝享太廟賦》所加引文與按語頗合此意:“張潛曰:此賦駢麗繁復中有樸茂之致,勝宋人多矣。”?“少陵作賦,隊伍整嚴,詞華典贍,不待言矣。……殆兼子安、退之之所長矣。”?前勝宋人,后啟韓愈,便是駢句,也能參以長句逸語,可見他在六朝文風的糾偏方面所做的努力。
(二)與心徘徊與隨物宛轉
李杜賦作體制風貌之“同”已如上述,其“異”也是顯而易見的。它源出于兩人不同的思維氣質,影響及于賦體創作時不同的藝術構思、體物方式、取材好尚,形成為各具特色的總體風貌,在詩賦互滲互化的過程中也表現出不同的傾向。
清人賀貽孫曾以“英”“雄”分論李杜:
詩亦有英分雄分之別。英分常輕,輕者不在骨而在腕,腕輕故宕,宕故逸,逸故靈,靈故變,變故化,至于化而英之分始全,太白是也。雄分常重,重者不在肉而在骨,骨重故沉,沉故渾,渾故老,老故變,變故化,至于化而雄之分始全,少陵是也。?
這種以才性喻詩的論說,自有其歷史淵源與現實依據,不過沒有交待才性與詩貌的必然聯系。楊義先生也曾以“醉態詩學思維”與“詩史思維”來比較李杜。?立論新穎,但也玄惑。其本意無非說李白擅玄想,杜甫重實錄,用袁宏道簡潔而現成的話說,就是:“青蓮能虛,工部能實。”(袁宏道《答梅客生開府》)?
可這些論斷都是針對詩歌創作而言的,詩賦有別,雖然詩賦都可以體物寫志,但相對來說,詩更重于寫志,賦更善于體物。與此相應,在創作構思上,詩更傾向于“憑心而構象”,賦更傾向于“感物而造端”。?其實即便在體物、感物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心、物關系,或由物及心,或由心及物。《文心雕龍·物色》篇說:“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隨物宛轉” “與心徘徊”,既是感物的具體過程,也是構思的不同方式。二者既相互發生,也各有側重,或心隨物轉,或物由心生。
這“與心徘徊”和“隨物宛轉”,正好可以用來區分李杜賦作藝術構思上的不同特征。以《大鵬賦》與《雕賦》為例,大鵬源出于莊子鯤鵬變化的寓言,本屬虛無之物,李白受此啟發,馳騁想象,敷衍出大鵬由初化到升騰、到翱翔、到息落的全部過程,從不同角度刻畫神異、奇絕而又曠蕩縱適、不為物役的大鵬形象。這樣的運思確實“發想超曠,落筆天縱”?,全出想象,是與心徘徊的結果。大雕是生活中實存的猛禽,杜甫的構思便要顧及這實存的物象,從大雕的形貌、習性寫起,鋪陳虞人捕雕、閩隸馴雕、大雕捕獵等種種情事,以刻畫大雕勇猛神俊、忠于職守的形象。這樣的運思即非親見耳聞,也須合乎邏輯,“隨物宛轉”。
影響及于寫作,在形象的塑造上與心徘徊者略貌取神,隨物宛轉者精雕細刻,在事典的運用上與心徘徊者偏重神話傳說,隨物宛轉者多取史書典籍。所以李白大鵬的用功之處在其氣勢神韻,杜甫大雕的著力之點還詳及形貌舉止。所以在大鵬的生存環境里,有燭龍、列缺、盤古、羲和、任公、有窮等神幻人物為背景,而在大雕的活動空間里,與之關聯的多為閩隸、烏攫等人間形象。
至于兩人賦體創作總體風貌之別,與詩類同,一者雄奇豪放,一者沉郁頓挫。
(三)以詩為賦與以賦為詩
“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文心雕龍·詮賦》)?,因此詩賦分流,詩緣情而賦體物。但這種壁壘分明的狀況并不顯著,也難持久,因為漢代文人詩賦的成就嚴重失衡,魏晉以后,隨著體情之作的增多,詩賦開始相融互化,賦重抒情而且講求駢對與聲律,詩尚巧似而且講求鋪陳與用典。初唐的律賦與歌行,更是詩賦交融互滲的產物。可見詩賦互滲互化是六朝以來的久遠傳統,初唐已然劇烈。盛唐的李杜,應該說是詩賦互化歷程中的高潮與轉折,大體而言,李白承上而化詩入賦,杜甫啟下而以賦為詩。
李白是詩賦相融的高峰,一面是詩的賦化,一面是賦的詩化。詩的賦化主要在于歌行這一體式被李白發展到了極至,并成為李白詩歌中最有特色的門類;當然,賦體體物入神、樂于夸飾、氣勢宏闊的特點也常為李白詩歌所共有。賦的詩化,在李白這里可從兩個角度切入:大賦的“義歸博遠”與小賦的情景交融。
“義歸博遠”(《大獵賦序》)是指賦作的意旨要廣大深遠。但這廣大深遠的內涵本身是有彈性的,一面如 《大獵賦序》中所言,要“光贊盛美”“以大道匡君”,一面如 《大鵬賦序》所言,要“窮宏達之旨”。前者是賦體頌贊與諷喻的體式要求與社會期待,后者是個人理想與抱負的張揚與申說。所以在李白的賦作中處處貫注著主體的志愿與意識,而非簡單的夸張與鋪排。主體意識影響藝術構思、表現技巧和作品風格。可知與心徘徊的詩性思維與言志緣情的詩歌功用,是李白賦體詩化的重要推手。
這種主體意識在李白的寫景抒情小賦中表現得更為突出,相較而言,其小賦更具詩性,也更多革新的意味。李白小賦的抒情性在題稱上便有表現。他的五篇小賦除 《擬恨賦》《劍閣賦》一為擬作,一為送別外,其余三篇的標題用詞都是情懷加物色的模式:“愁陽春賦”“惜余春賦”“悲清秋賦”,一開始就給人以物我相融的詩性感覺。以體式而言,這五篇小賦也都不同程度地運用騷體句式,騷體情緒的悲苦與聲調的搖曳無疑也使這些作品更富聲情之美。與巧構形似者或情景分立者不同,李白小賦“事類”與“情義”兼顧,?寫景與抒情均衡而互錯。
在詩賦交融方面,杜甫對律賦的形成曾做過有益的探索?,但其主要貢獻與影響還是以賦為詩。杜甫之前,以賦為詩已有成功范例,四杰和李白的七言歌行,多用賦的鋪敘手法,表現重大題材,展開廣闊場面,既開拓了視野,也提升了情調。杜甫以賦為詩的突出貢獻在于長篇古詩和排律的創作,以及沉郁頓挫的思慮與形制,當然也在于紀事詠物題材的擴張與鋪陳排比手法的運用。
賦體體物的特點有利于題材的開拓,杜甫以賦為詩首先便表現為詩歌取材范圍的擴大,紀行、寫景、詠物等傳統賦體題材被杜甫移入詩中,增強了杜詩的寫實性。
杜甫一生漂泊,大部分時間在流離失所中度過,所以他的詩歌中有不少紀行之作。如逐地紀名的組詩“發秦州” “發同谷縣”,以及以紀行為主的名作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等。杜甫的這些作品極盡敘事體物之能事,在自己的征行經歷中融入自然山水,以賦為詩,隨物肖形,為紀行詩的寫作開辟了新的路程。更有將時事納入詩歌的行旅之作,如 《兵車行》《洗兵馬》《哀江頭》《悲陳陶》《悲青坂》等,在鋪陳其事中廣泛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的社會矛盾。杜甫是詠物大師,杜集中詠物詩很多,范圍也非常廣泛,涉及天象、江河、草木、蟲魚、禽獸、器具等方方面面。所詠之物,無不精微巧妙,寓意深遠。明胡應麟曾說:“詠物起自六朝,唐人沿襲。雖風華競爽,而獨造未聞。唯杜諸作自開堂奧,盡削前規。……皆精深奇邃,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應該說,杜詩對賦體題材的吸納與革新,擴大了詠物詩的容量,也為后來以賦為詩者積累了經驗。
在藝術手法上,杜甫也吸取了賦體擅長鋪述描寫,講求辭藻豐富與氣勢恢宏的特點,拓寬了詩歌的表現力。因為參照賦體文學的常用手法,按空間方位和時序推移對事件與場面進行多層次的鋪陳,杜甫的紀事述行詩常能以巨大的景、事容量展現廣闊的社會背景。較之初唐詩對人物和具體物象的鋪寫,杜甫的“以賦為詩”顯然是一大進步。他如對語言的錘煉,也是杜甫詩賦共有的特點。后人常以“沉郁頓挫”概稱杜詩的總體風貌,其實“沉郁頓挫”本出杜甫 《進雕賦表》,是杜甫對自己“述作”的一個評價。它包括深沉的思慮與曲折的形制。杜甫以長篇古詩、排律乃至組詩的創作,開拓了以賦為詩的新境界。元稹曾極力標舉杜甫“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說連李白也“不能歷其藩翰”,?主要是就律詩特別是鋪陳排比、屬對律切的長律而言的。
李杜都是能同時駕馭詩賦兩種文體并將其融會貫通的大家,不過從賦史演變的角度而言,李白以詩為賦,情感真摯、語言平易、風格清新,“反映了唐賦發展的一般趨向”?,杜甫極力摹擬,刻意錘煉,然終不能比超漢賦,在唐賦中也“終是別格”?,但他的以賦為詩,卻可延續賦體生命,也使其在詩史上別立一宗。
三、李杜賦的成就與詩賦地位的變遷
(一)李杜賦名不如詩名
李杜雙星,并峙盛唐,考察李杜詩賦的成就與地位有助于理解中國古代詩賦地位的變遷。
揚馬以賦著稱,李杜因詩聞名,李杜的身份與徽號首先是詩人而非賦家。千百年來,人們就李杜展開的論議絕大多數都集中在他們的詩歌上面。嚴羽說:“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太白 《夢游天姥吟》《遠離別》等,子美不能道;子美 《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胡應麟說:“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匯。李唯超出一代,故高華莫并,色相難求。杜唯兼綜一代,故利鈍雜陳,巨細咸蓄。” “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大思精而格渾。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李杜優劣,眾說紛紜,但總的趨勢是:李杜各有優長,李杜都是詩中天子。
李杜在賦史上也算大家,但他們的賦名卻遠沒有詩名那樣崇高。朱熹說:“白天才絕出,尤長于詩,而賦不能及魏晉”,?祝堯說:“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律之根固在,雖下筆有光焰,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爾。”?仇兆鰲說:“按歷代賦體,如班馬之《兩都》《子虛》,乃古賦也。若賈揚之 《吊屈》《甘泉》,乃騷賦也。唐帶駢偶之句,變為律賦。宋參議論成章,又變為文賦。少陵廓清漢人之堆垛,開辟宋世之空靈,蓋詞意兼優,而虛實并運,是以超前軼后也。陳氏稱其詞氣雄偉,非唐初余子所及,尚恐未盡耳。”?張道 《蘇亭詩話》云:“太白之 《希有鳥賦》《惜余春賦》,子美之《三大禮賦》,實可仰揖班張,俯提徐庾。”?
因為立場與視角不同,后世論家對李杜賦藝的評價存有差異,但無論褒貶,都不會認為李杜賦藝強于詩藝,賦名重于詩名。
(二)詩賦文體之別
揚馬以賦著稱,李杜因詩聞名,其中原由,既有作家才性與時代氛圍的因素,也與詩賦文體本身的區別及衍替有關。清人吳喬曾有詩酒文飯之說:
問曰:“詩文之界如何?”答曰:“意豈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詩文體制有異耳。文之詞達,詩之詞婉。書以道政事,故宜詞達;詩以道性情,故宜詞婉。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文之措辭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啖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文為人事之實,詔敕、書疏、案牘、記載、辯解,皆實用也。實則安可措詞不達,如飯之實用以養生盡年,不可矯揉而為糟也。詩為人事之虛用,永言、播樂,皆虛用也。”?
這一段話涉及詩文不同的表現對象與社會功用:一以“道政事”,一以“道性情”;一“實用”,一“虛用”。更重要的是它用貼切的比喻闡釋了詩文形體與本質的區別:一變形,一不變。用現代的眼光來看,這形質之變既包括傳統表現手法之異,也體現在感知與語義的不同。賦介乎詩文之間,就其本質而言則更近文。詩賦之別也可類比詩文之別。在表現對象上,詩緣情而賦體物;在表現手法上,詩多用興,而賦尚鋪陳。因為用興,詩便要從廣闊的生活中選取最有特征,最能反映本質的事物來形象地表現詩人的情感。因為鋪陳,賦可以窮盡一切物態,“斯于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暢,暢無或竭”?,簡言之,詩緣情而簡約,賦體物而繁博。?
自漢末至初唐,詩賦在互滲互化中伴隨有體質的變革與地位的消長,詩為窮情而寫物,賦為體物而寫志,詩賦各有勝場,但詩更善于吸取賦的經驗,所以總的趨勢是詩吸取了賦的體物之長并開創出簡約、含蓄、空靈的近體詩歌,因而逐漸取代賦體成為文壇主流。
詩賦的優長可以通過相同題材的作品進行比較,這些作品可以出于不同作家,如江淹的《別賦》與李白的《送友人》,也可成于同一作家,如李白的 《劍閣賦》與《蜀道難》等,詩因為簡約空靈而比繁復冗長的賦更有生命力。
有趣的是,不同文體有時也會承載不同的性情品格與社會功能。比如詩歌中的李白,常常超凡脫俗,藐視權貴,而書信中的李白,卻不免阿諛奉承,摧眉折腰。與此相似,杜賦與杜詩也有互為矛盾的時候,杜詩揭露權貴、批判社會,而杜賦歌功頌德、粉飾太平。
(三)詩賦地位之變
1.詩賦在盛唐時代的影響
詩賦地位的消長主要由詩賦本身的體式特征所決定,也與它們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外部環境有關,其中科考取士的用人制度與唱誦題寫的傳播方式影響較為顯著。
科舉制度為社會各階層的流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加快了整個社會的生活節奏,包括詩賦創作與傳播的速度。六朝世族因為壟斷了一切入仕的門徑,生活安定,地位優越,因而也容易養成優游閑散的風氣。到了門蔭制度被不斷削弱的初盛唐時代,世族卻不得不加入到通過詩賦競技以為進身的行列中來。當大部分讀書人的功名欲望被調動起來以后,創作、投贈、傳唱詩賦的節奏大大加快,而在新一輪生產與傳播的競爭中詩歌又顯然優于辭賦。普通的詩歌尤其絕句常常可以即席而成,賦體的創作卻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桓譚 《新論》自述其作賦經歷及揚雄作賦佚事時說:“余少時見揚子云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瘳。子云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詔令作賦,為之卒,暴思精苦,始成,遂閑倦小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而內之。及覺,病喘悸,大少氣。病一歲。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用思太劇以致于傷神發病,可見作賦其實是很痛苦的事情。不僅如此,作賦的過程也是很漫長的。“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于苦思,王充氣竭于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象張衡、左思那樣花上十年時間寫一篇賦,在唐代是不太可能了,因為高才如李白、杜甫為了生存也得遍干諸侯,歷抵卿相。所以詩賦作品的速成很重要,干謁如此,正式的科考更有時間的限制。唐以詩賦取士,表面看來是詩賦并重,詩賦具有同等的發展機會,實則不然。因為詩賦文體的不同本質已然決定它們的創作速度,新體律賦雖然可以提升賦體創作的速度與產量,但它本身是科考的產物,缺乏社會生活基礎,即便就生產節奏而言也無法與詩歌抗衡。
詩歌的生命力更體現在社會生活的層面,聞一多先生曾以“詩唐”二字標舉詩歌在唐代的影響,因為各個階層的人都參與到詩歌的創作與傳誦中來了。我們想說的是,廣泛而快速的傳播,更需要簡約通俗而又能抒情寫志的文體,所以詩,甚至只是詩中的“秀句”成了時代的寵兒。在這樣的世風里,詩名比賦名顯然更重要了,寫詩比作賦也更容易出名。宋人葛立方《韻語陽秋》就記載了唐人以詩成名,更準確地說是以秀句成名的情況: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眾。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公先達為之游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錢起以是得名;……“華裾織翠青如蔥,入門下馬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
在聲聞影響科考的唐代,佳句、秀句于科考也是有益的,韓愈 《寄崔二十六立之》詩云:“佳句喧眾口,考官敢瑕疵?”賈島 《酬胡遇》詩云:“麗句傳人口,科名立可圖”,雖屬友朋間戲言,也可看作詩中秀句影響科考之佐證。其實李杜本人的詩家意識與秀句意識也是很強烈的。杜甫說“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李白自稱“興酣筆落搖五岳,詩成嘯傲凌滄洲”(《江上吟》)。 《全唐詩》中,李杜用“秀句”最多:“秀句滿江國,高才掞天庭” (李白 《獻從叔當涂宰陽冰》)、“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杜甫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杜甫 《解悶十二首》其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杜甫 《哭李尚書芳》)。另有“佳句” “麗句”之稱:“何日睹清光,相歡詠佳句”(《早過漆林渡寄萬巨》)、“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杜甫 《戲為六絕句》其五)。當然在賦序中李杜對自己的辭賦也很自負,但這既是上文所說的尊題法,也是賦家一貫的作風。李白的自信更是無所不在,“文不加點”(《贈黃山胡公求白鷴》)、“賦凌相如”(《贈張相鎬》),不過從杜甫對他的稱頌來看,主要還是在詩歌方面:“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春日憶李白》)、“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飲中八仙歌》)。
2.盛唐詩賦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對李杜最恰當的評價,應該是韓愈的“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愈 《調張籍》)。事實上,李杜既是大詩人,又是大賦家。對李杜的詩藝賦藝與詩名賦名進行比較,是想借以說明初盛唐之際,詩賦的地位正悄然發生變化,詩正取代賦而成為傳統文學的主流。
古代有不少關于詩賦代興的說法,如何景明說:“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何景明《雜言》)?,程廷祚認為:“蓋自雅頌息而賦興,盛于西京。東漢以后,始有今五言之詩。五言之詩,大行于魏、晉而賦亡。此又其與詩相代謝之故也。唐以后無賦,其所謂賦者,非賦也。”?。章太炎說得更具體:“賦之亡蓋先于詩。繼隋而后,李白賦 《明堂》,杜甫賦 《三大禮》,誠欲為揚雄臺隸,猶幾弗及,世無作者,二家亦足以殿。自是賦遂泯絕。”?說李杜以后賦絕或唐以后無賦,可能有點過,單就賦史而言,唐代賦作內容的豐富與體式的多樣并不遜于前此后此的朝代,王芑孫甚至說“詩莫盛于唐,賦亦莫盛于唐”?。但無可爭辯的是,到了李杜的時代,詩歌經過反復的檢驗后,已經正式坐上了文壇的第一把交椅,而辭賦則開始從整體上走向衰落。此中原因,除了上文提及的文體自身的特質與時代氛圍外,也與整個中國古代文化尚簡約含蓄的風習有關。賦的鋪張繁復與這種文化習性格格不入,只好不斷變化著自身的體格,并伺機滲入到其它的文學體式中去。所以古賦后有駢賦,駢賦后有律賦,律賦后又有新文賦,但它的文體特質也因此變得更加模糊。對它種文體的浸入倒使善于鋪陳的敘事體詩和傳奇小說逐漸興盛起來。
注釋:
①《越人獻馴象賦》不載于仇兆鰲 《杜詩詳注》,《文苑英華》卷131、《歷代賦匯》卷134錄入此賦,并署“闕名”,《全唐文》卷359、汪森 《粵西文載》卷1則列名為杜甫所作。本文姑且存目。
②④⑤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2-45頁、第3頁、第5-7頁。
③⑥⑦⑧⑨⑩??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133頁、第2173頁、第2176頁、第2180頁、第 2182-2183頁、第 2173頁、第 2136頁、第2136頁。
?李長之: 《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
???(元)祝堯:《古賦辯體》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66冊,第806-808頁、第806頁、第802頁。
???馬積高:《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8頁、第292頁、第292頁。
?(清)賀貽孫:《詩筏》,《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頁。
?楊義:《李杜詩學》,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479頁。
?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34頁。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神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頁。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693頁、第136頁、第494頁。
?(清)方東樹著,汪紹楹校點:《昭昧詹言》卷一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249頁。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云:“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905頁。
?“從句式看,作為律賦獨特面貌呈現的四六隔句對偶格式,《三大禮賦》是不少的……不妨說 《三大禮賦》的體式有很重的律賦成分;或者更準確地說具有律賦發展初期的面貌。”鄺健行 《從唐代試賦角度論杜甫〈三大禮賦〉體貌》,《杜甫研究學刊》,2005年第4期。
?? (明)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頁、第70頁。
?《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冀勤點校:《元稹集》卷五六,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601頁。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評》,(宋)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166、168頁。
?(宋)朱熹:《楚辭后語》卷四 《鳴皋歌》,(宋)朱熹撰,蔣立甫校點:《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頁。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2157頁。陳氏指陳子龍。
?詹锳主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第七冊,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3頁。
?(清)吳喬: 《圍爐詩話》卷一,商務印書館 《叢書集成初編本》,第8頁。
??(清)劉熙載:《藝概·賦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頁、第86頁。
?(漢)桓譚:《新論·祛蔽》,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30頁。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16-517頁。
?(清)王芑孫:《雜言》,李叔毅等點校:《何大復集》,中州古籍出版1989年版,第666頁。
?(清)程廷祚:《青溪集》卷三 《騷賦論中》,《金陵叢書本》。
?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頁。
?(清)王芑孫:《讀賦卮言》,何沛雄編:《賦話六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5頁。
責任編輯 張宏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 (13YJAZH055)、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2YBA116)
作者:劉偉生,湖南工業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41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