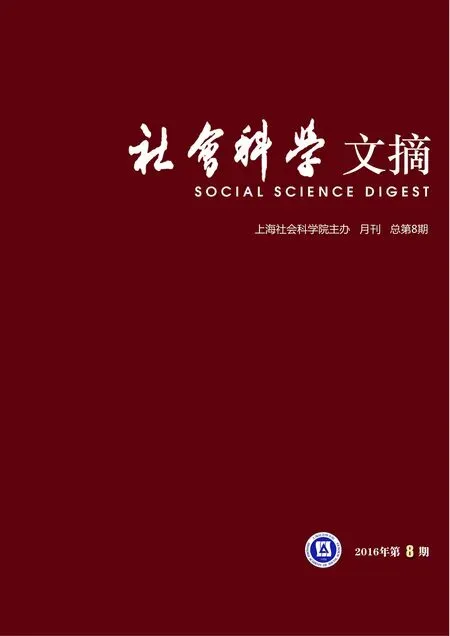現代政治的形而上學基礎
——對《君主論》“命運”章的哲學闡釋
文/聶敏里
現代政治的形而上學基礎
——對《君主論》“命運”章的哲學闡釋
文/聶敏里
問題的提出:為何設“命運”章?
《君主論》全書討論政治問題,但只有一章例外,這一章就是第25章。單從這一章的標題“命運在人世事務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樣對抗”上就可以看出,它與政治的主題相去甚遠,更像是一個形而上學的主題。從而,一個很容易產生的問題就是,為什么要有第25章?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這部著作的倒數第二章寫這一主題是為何?
施特勞斯顯然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在他的《關于馬基雅維里的思考》中,第25章是被歸入他對《君主論》全書結構劃分的第四個部分,即第24-26章,他將這部分的主題概括為討論“審慎與偶然機遇”,并且更重視的是第26章,而不是第25章。
第26章作為針對新君主的一個吁請,是馬基雅維里寫作《君主論》這本書的實踐目的和實用目的的雙重的結合,他以此寄托了他對意大利的現實政治形勢的最深切的關懷,表明了他長時間的辛勤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此而言,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把第26章看成一個獨立的部分,它實際上正構成了《君主論》一書的結語。至于第24章,和施特勞斯的觀點不同,我們倒是認為它更應當被歸入前一個部分,亦即第15-23章的那個序列中去,因為,它是第三個部分對君主應該具有的品質的討論的一個自然的延續,表明恰恰是由于不具有已經討論過的那些德行才干,意大利的君主們才喪失了他們的國家。但是,一旦我們這樣來處理第24章和第26章,第25章的獨立地位就顯露出來了。它實際上既不能夠被歸入第15-24章的序列中去,也不能夠被歸入第26章的結語部分中去,而是自身構成了一個獨立的部分。它的出現在字面上僅僅是由于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即,在第24章的結尾,馬基雅維里告訴那些喪失國家的意大利君主不應該為此而去咒罵命運,而應當很好地檢查自己是否不具有之前討論的那些君主所應當具有的德行才干,顯然,正是由于話題到此,他才專門辟出一章的篇幅就命運這一主題進行討論。但是,由此一來,這也就需要我們深思馬基雅維里這一做法的深意。他為什么在全書行將結束之際專門就這一看似與全書的政治議題無關的形而上學主題進行討論?在全書即將結束的部分進行這樣一種討論具有怎樣的理論深意?它作為獨立的一個部分在全書中具有怎樣的一種理論地位?
直面命運:現代政治學的第一層形而上學內涵
現代政治學和古代政治學的一個根本的不同就在于,現代政治學通過直面命運這一主題,將政治的考量奠立在了一個特殊困難的處境當中。就這一特殊困難的處境不僅是現實意義上的,而且還是理論意義上的而言,現代政治學的這一思考因此就具有了形而上學的內涵,它實際上是對現代政治的形而上學的奠基。通過將對現代政治的種種行為設計奠定在一個自始就不理想的境遇中,現代政治學也就等于是更換了政治思考的基礎,并且因此也就更換了政治思考的基本模式。現在,人們必須面對一種并不理想的境遇來思考自己的行為的意義、價值及其方式、方法,他并不能夠直接訴諸環境的友好,例如自然的和諧與美好、人性的高貴與善良以及社會的公正而有序等等,也就是說,他不能從理想出發來設想自己的行為,而必須針對現實的種種可能的不利的處境,來尋求自己有效的行為對策。在這個意義上,他不僅是現實主義的,而且是實用主義的;他不以某種脫離實際的理想為目的,而是以生命的保存及生命在環境中的進一步發展與豐富為目的;他不對自己的生命生活進行任何先驗設計和構想,而是始終關注于針對現實處境的具體而富有實效的行為策略設計和謀劃。從而,他立足于分析現實,而且是冷靜地、客觀地分析現實,在這里找到自己行動的實際的依據和準則。
顯然,現代政治學的這樣一種思想模式與古代政治學存在著根本的差別。在《理想國》第五卷中,柏拉圖曾經向我們展現了一種典型的古代政治學的思想模式。當時,蘇格拉底已經完成了對他的理想國的基本的設計,而這時,格老孔針對這一理想設計的現實可能性提出了質疑。這在對話中被蘇格拉底稱作“最大最厲害”的“第三個浪頭”,而蘇格拉底的應對策略也是眾所周知的。他辯解說,他前面對理想政治制度的勾勒,只是想要為一切現實的政治制度提供一個模板,使得人們可以參照它來“判斷我們的幸福或不幸,以及我們的幸福或不幸的程度。我們的目的并不是要表明這些樣板能成為在現實上存在的東西”。
這里所展示的就是古代政治學的最基本的思想模式,即,基于對政治生活的一種先驗構想——而這也就是柏拉圖的理念——來對現實政治活動進行價值裁判。它是理想主義的,而且正因為它的理想性,它似乎就天然地占據了道德的制高點,仿佛可以抵擋一切對它的詆毀和攻擊。但是,現代思想對古人的這樣一種理想主義的思想模式所可能提出的一個挑戰是柏拉圖不曾想到的。由于為懷疑主義所“敗壞”,現代思想不曾像格老孔那樣詢問這種理想的現實性,而是恰恰針對它的理想性發出質疑,并且最終將思想從理想的高峰拉回到了現實的平地上。因為,在現代思想看來,問題的重點不在于一個理想是否能夠實現和如何能夠實現,而在于如何判定它夠不夠理想和由誰來判定。顯然,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理想被表明超出了一切現實知識的領域,并且因此就是一個人人都可以對它有所談論而不會受到任何批評和指責的領域。但是,正因為它是人人都可以在其中大言不慚的領域,因而,它就不是如人們在想到理想時所以為的那樣一個純潔神圣的國度,相反,卻是一個充斥著混亂和愚昧的幽暗之所。因此,針對種種信仰與啟示在其中擾攘不休的理想國度,現代思想給出的富有啟示的答案就是,正因為它超出我們的知識能力,我們應當對它保持沉默,而將思想的主要精力放在我們能夠知道的東西上面,這也就是人們的經驗現實世界。
馬基雅維里實際上早已清楚地表達了這一現代知識原理和實踐原理。在《君主論》的第15章中,他表明他的目的是寫一些“對于那些通曉它的人是有用的東西”,“論述一下事物在實際上的真實情況,而不是論述事物的想象方面”。這樣,從人們的現實處境出發,而不是從對人們生活的理想虛構出發,這就是現代政治學的基礎。《君主論》就是做這一嘗試的第一部現代政治學著作。在自始至終的論述中,它沒有絲毫訴諸于某種理想的政治模型,訴諸于理想的人性、人心,訴諸于全知全能的人或神,相反,它是從人性、人心乃至現實政治環境的種種不理想出發。馬基雅維里告訴我們,正是在這里,才是政治學的思考和有意義的政治行動開始的地方,因為,正是在這里,才是考察人們實際能夠做些什么和能夠怎樣做、亦即考察人們的現實的政治活動的地方。
積極行動:現代政治學發生的形而上學基礎
現在,我們就挑明了命運對于現代政治學的第一層形而上學的內涵,也就是說,通過直面命運,現代政治學第一次將對政治問題的思考建立在了現實的基礎上。但這不是命運這一主題在現代政治學中的最重要的形而上學內涵。因為,如果所謂“直面命運”僅僅是指與命運相遭遇、面對命運,也就是說,發現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并且深刻認識到它在人類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那么,古代進入成熟期的各大文明實際上都曾經“直面命運”。文明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人類面對命運、對抗命運的產物。因此,現代政治學在這一點上并不能自夸優越于古代政治學。
但是,在命運面前,古人所采取的最典型的做法就是無所作為,而這要么是通過對命運的坦然接受達到的,要么則是通過對命運的基于先驗目的論的理想化達到的。關于前者,我們只要想一想索福克勒斯關于俄狄浦斯的系列悲劇就明白了。而關于后者,我們只要想一想柏拉圖的宏大的被善和正義所主宰的宇宙和諧圖景,想一想亞里士多德的具有同樣的自然目的論色彩的形而上學體系,就可以明白了。
而現代思想與古代思想在出發點上的一個根本的不同就是,它認識到,面對暴烈的命運,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上一點兒什么,來多少改變一下我們本來已經極端不幸的處境。雖然,由于我們自身各方面能力的不完善——這也是我們的命運給我們設置的格外不利的處境——我們能夠改變的并不多,但是,這卻總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一點兒。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中,一種積極的公民生活的理想發生了,這就是,我們在命運面前能夠有所作為,我們能夠去爭取一種更為美好的生活,這不是通過對生活的理想的虛構達到的,而是通過現實的行動在不理想的處境中所盡可能多地爭取到的。它并不訴諸一種關于生活的理想的標準,而只是尋求我們實際能夠做些什么和能夠爭取到什么。這就是現代政治發生的形而上學的基礎。
就此而言,《君主論》的第25章恰恰是全書的形而上學的理論基礎,它為全書的政治討論以及所討論的種種實際的政治行動及其策略,從形而上學的高度提供了一個理論的說明和總結,點明了它們根本的形而上學的意義。它不僅是全書所討論的政治學理論的形而上的升華,而且是其形而上的奠基。從某種意義上說,它闡明了人類政治活動或者《君主論》中那種得到特殊論證的積極的人類現實政治活動的形而上學的基礎,即,這樣一種現實的積極有為的政治活動在根本上起源于人同自身命運的對抗,在仿佛不可抗拒的巨大命運面前人并不是無所作為的,而是可以實際地做些什么,并且可以由此使自己的不甚理想的境況實際上有所改善。
命運主題貫穿《君主論》全書
如果我們已經從理論上說明了這一點,那么,現在,從文本上來證實這一點就是十分必要的。我們首先要表明的是,命運主題實際上是貫穿《君主論》全書的一條主要的思想線索,它構成了一個無處不在的思想背景和平臺,為《君主論》其他各章那些主題明確的政治學的討論提供基本的前提和出發點。
在這方面,一個最為顯著的證據就是《君主論》一書的獻辭部分。在《君主論》的開篇部分,命運之神便已經隆重地登場了。它被描述為使一些人上升,使一些人下降,使一些人達到偉大,使一些人飽受折磨。這樣,命運就仿佛構成了一個基本的背景,和接下來一切討論的前提。而且,我們可以注意到,馬基雅維里顯然并不認為人面對命運是無所作為的,因為,與“命運之神”相并列,他沒有忘記提及“其他條件”,從而,他的“這個小小的禮品”所討論的不過就是命運和人在命運面前可以做些什么,而這篇獻辭乃至整個《君主論》本身都可以被看成是馬基雅維里在其個人悲苦的命運面前的一個積極的行動。
因此,正是在這篇獻辭中,命運已經被明確為一條主線隱伏于全書的所有討論之中,為全書各章的政治議題提供它們開始和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從而,在第1章中,在以二分法對各類政體形式進行了劃分,而將論述重點放到了新君主國上后,馬基雅維里便明確提出了這類國家的得國方式:“或者是依靠他人的武力或君主自己的武力,否則就是由于幸運或者由于能力。”在這里被譯為“幸運”的fortuna,也就是在其他地方被翻譯為“命運”的同一個詞,而馬基雅維里同時提到了與之相并列的另一個重要概念,這就是或者被翻譯成“能力”或者被翻譯成“才干”或者被翻譯成“美德”或“德行”的virtù。這樣,《君主論》的基本主題可以被概括為,人能夠做些什么以戰勝命運。在這里,同“人能夠做些什么”相關的就是人的virtù,而《君主論》、乃至整個現代政治學就是對人在命運面前能夠做些什么的探討與謀劃、設計與建構。
而當我們觀察《君主論》的其余各章,一個鮮明的印象就是,馬基雅維里總是首先將他的討論置于各種現實的困難的處境之中,而不是像古代政治學那樣,首先論述一種理想環境下的政治制度。此外,又有誰能夠否認,在具體的各類政治評論中,“命運”被馬基雅維里一再地用來作為觀察他所評論的那些政治家的一個主要的視角,從而成為一個最為頻繁地出現的關鍵詞?
顯然,只是由于命運這一主題從一開始就隱含在《君主論》的各章之中,成為其中各種明確的政治議題討論的自然前提和出發點,在一個適當的地方對這一分散在各處的主題加以概括、凝煉和集中、明確地探討,以點明命運對于政治考慮的形而上學基礎的意義,無疑就是十分必要的。而這就是第25章,在這里,馬基雅維里以“命運在人世事務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樣對抗”為題,為他的《君主論》一書進行了形而上學的奠基。
作為《君主論》隱秘主角的“命運”章
現在,我們可以具體考察第25章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盡管馬基雅維里承認命運至少部分地主宰了我們,但是,他仍舊延續了前期文藝復興思想家那種積極的觀點,認為命運并不能消滅掉我們的自由意志,我們的行動至少有一半是由我們自己來支配的。這樣,有為而非無為就是馬基雅維里面對命運所給出的基本的政治策略。在此基礎上,他便給出了他所認為正確的面對命運的因應之道,這就是,一個人必須保證他的行動能夠符合時代的特性。由此,他就將人面對命運的正確方式的討論帶入到了更為具體的針對時代特性的現實主義的分析之中,表明正是在對時代特性做理性的分析、然后采取合理的行動的基礎上,才造就了一個人事業的成功。這樣,馬基雅維里就創造性地將文藝復興思想家關于人類命運的特殊思想同他自己的關于人類政治事務的現實主義的考察結合在了一起,表明正是通過對時勢的正確合理地分析,采取正確合理的行動步驟,才實際地造成了在一般人看來似乎完全為變幻莫測的命運所支配的那種政治上的勝利。
因此,命運對于馬基雅維里不是決定性的因素,相反,是人的行動的背景性的因素。這就是說,正是由于命運的存在,人才不得不直面命運,并且選擇通過積極的行動戰勝命運。從而,行動而且是積極、現實的行動,恰恰是《君主論》第25章的真正的主角。這樣,在表明了命運只是我們的“半個行動”的主宰,而其余的一半則由我們支配,而我們完全可以針對命運有所提前準備和適時應對之后,在具體的討論中,我們看到,不僅行動應當符合時代特性的原則被提了出來,作為一個基本的政治原則,而且它在更為具體的討論中實際上還被凝煉為一個異常重要的概念,這就是“迅猛的行動”。對于馬基雅維里來說,“迅猛的行動”實際上代表著一切積極的行動,而不只是某一種特殊的行動方式。而正是這種積極的行動,是一個人能夠面對命運并且戰勝命運的根本保證。而就它同時也是一切成功的政治人物的政治行為的根本特征而言,顯然,政治就奠定在這種積極的行動之中。
這樣,命運,以及面對命運的符合時代特性的積極的行動,這就是現代政治的形而上學的基礎,而就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的真正隱秘的主角不外乎是這二者而言,它們也就構成了對現代政治的形而上學的奠基。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摘自《哲學動態》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