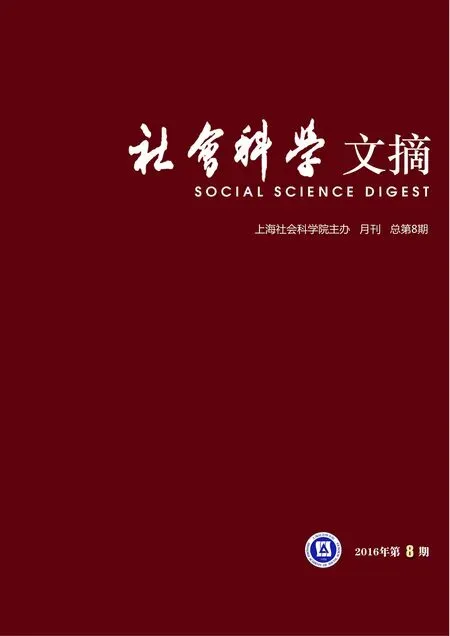馬克思晚年學術轉向的思想史意義
文/諶中和
馬克思晚年學術轉向的思想史意義
文/諶中和
學術界通常把馬克思晚年“人類學轉向”的精神實質解讀為“從普遍史觀到特殊史觀”的轉變。這種研究雖然意識到馬克思晚年的東方社會論斷已經蘊含著某種對世界歷史發展道路的新理解,但缺乏對馬克思晚年思想轉變精神實質的深刻洞察。如果把馬克思的所有思考置于人類思想史之“中”而不是之“終”,把馬克思思想看作是人類文明從農業時代的“民族歷史意識”向工業時代的“世界歷史意識”邁進的一個節點,就有可能把馬克思晚年思想轉變視為“世界歷史意識”覺醒過程中一次通過馬克思自身而實現的理論升華與超越,即從具有深刻西方“民族歷史意識”烙印的歐洲史觀向真正的“世界歷史意識”轉變的一次偉大嘗試。馬克思晚年的世界歷史思考不僅對當下中國道路實踐探索的進一步展開,而且對世界歷史未來發展方向的理論思考指明了方向。
馬克思晚年思想轉變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認為,所有前工業時代的人類文明都依次經過三種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意識到資本將按照自己的本性開創世界歷史。“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而人類最后的共同歸宿是他所預期的共產主義社會。
基于這種對世界歷史道路的理解,從19世紀50年代開始,馬克思開啟其對東方社會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研究。他認為,農村公社是東方社會的基本單位,個人是這一實體的純粹天然的組成部分。農村公社的經濟特征是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生活自給自足。國家是土地的更高或唯一的所有者。東方社會的這種經濟結構不僅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基礎,還導致了東方社會的停滯。他說,中國像一個“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里的木乃伊”,而“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因而馬克思雖然對東方所遭受的侵略表達了道義上的同情,卻歡呼西方資本主義力量對東方傳統社會的沖擊。他堅信東方社會的唯一出路是步西方資本主義后塵。
但是,在馬克思生命的晚期,他對東方社會的歷史與未來的理論判斷發生了重大變化。在1877年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他拒絕將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上升為“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的作法,并且指出,不是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資本主義這條道路。在1881年給查蘇利奇的回信中,馬克思認為,俄國農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及其與資本主義生產同時存在的特殊歷史環境,使“它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馬克思晚年把農村公社比喻為“下金蛋的母雞”,認為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俄國社會新生的支點。他晚年譴責英國在印度對農村公社的破壞,呼吁俄國革命者挽救農村公社。
從普遍史觀到特殊史觀?
魏特夫在《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中,率先把馬克思上述思想轉變認定為從“普遍主義的歷史概念”或“單線的社會發展概念”到譴責普遍主義歷史概念的轉變。魏特夫認為,馬克思倡導的“特殊的亞細亞形態”理論“暗示了一種新的世界-歷史概念”,因而是“無與倫比的科學成就”。但他批評馬克思“在關鍵時刻沒有道出他按照他的認識和信仰應該道出的思想”——那些由他在《東方專制主義》中才予以揭露的治水社會理論。“馬克思后來既決心把亞細亞社會看成是一種特殊的制度形態,又不愿意討論東方專制主義的管理方面”,這就是“從真理面前退卻”。魏特夫對馬克思前后期思想轉變的這種認定(即從“普遍主義”或“單線”社會發展概念到譴責普遍主義的歷史觀念),產生了深遠的理論影響。從普遍史觀到特殊史觀、從單線發展到雙線發展,成為現在中國學術界進行相關討論的首要范式。
用“普遍主義歷史觀”概括馬克思早期的社會歷史思想無疑是合乎實際的。但是,把馬克思晚年思想概括為基于俄國經驗的“特殊史觀”,就缺乏堅實的證據。首先,“特殊史觀”這個概念本身就存在問題。任何一種歷史觀,都應該理解為對某種歷史普遍性的揭示。實際上,馬克思的早期思想——在承認歷史規律內在發生的意義上——固然表現為“普遍主義”歷史觀,但是這絲毫不意味著馬克思認為世界各民族歷史的具體展開可以是無差別的,而是必然包含著對歷史發生的具體性與差別性理解。而馬克思晚年對具體“歷史環境”的強調與對“超歷史”的“一般歷史哲學”的批判,也完全不意味著他放棄了對歷史普遍性的信念。當馬克思晚年多次明確肯定,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雖然其具體歷史道路可能不同,但都要趨向某個共同的世界歷史結局時,就明確表明了他對普遍主義歷史觀念的執著信念。這就不僅使魏特夫對馬克思晚年思想轉變的認定只具有表象的意義,同時使國內學術界由此生發的關于馬克思從普遍史觀到特殊史觀的種種議論成為無的放矢。因而對馬克思晚年思想轉變的精神實質,應該重新進行理論思考。
馬克思晚年思想轉變的實質
馬克思很早就有一個對人類歷史發展的洞見,即明確意識到“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這種歷史轉變的實質,是從農業時代的各主要文明區域之間缺乏大規模、經常性緊密聯系的“民族歷史時代”轉變到各文明區域之間日益地建立起大規模、經常性緊密聯系的“世界歷史時代”。與這種歷史發展狀況相一致,人類的自我認識也必然相應地從民族歷史時代的“民族歷史意識”轉變為世界歷史時代的“世界歷史意識”。包括馬克思及其思想前輩與后輩在內的工業時代思想家們的主要努力,都可以歸結為試圖從某個側面直接或間接地實現對世界歷史意識的某種自覺或揭露。馬克思及工業時代的很多思想家都認定,世界歷史將以某種可以預期的確定的方式終結,世界歷史意識也將隨之獲得最后的穩定的表現形式。這種樂觀主義除了基于對人類理性的高度自信,還基于這樣確定的歷史經驗:在民族歷史時代,各主要古典文明曾經普遍達到過某種各有特色、各自穩定的民族歷史意識。最先提示這一點的是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學說,軸心時代的思想則標志著“民族歷史意識”的形成。
根據筆者在《中國的誕生》中對農業文明發展道路的研究,從技術化時代(即解決在特定地理條件下與大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核心技術問題)到倫理化時代(即在既定的技術或財富狀況下,發明維持特定社會的穩定存續所需要的各種制度與思想)是民族歷史過程展開的主要情節,因而民族歷史意識(即軸心時代的思想)的呈現,只是在民族歷史已經充分展開或即將走向“終結”之際(也就是軸心時代)才能實現。同樣,工業時代的“世界歷史”必然也有一個逐步展開的過程,當世界歷史本身還處于不斷展開之際,真正的世界歷史意識是不可能呈現的。按照筆者的觀察,當下的世界歷史時代仍然處于工業文明的技術化時代,如何實現技術進步與財富增長,是迄今工業時代社會生活的主題,因而也是當下在實際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的各種制度設計與思想發明(資本邏輯)的主旨。只有在資本邏輯運行的盡頭即工業時代的技術進步與財富增長趨于穩定,從而使工業時代的人類文明既獲得了一種具有充分穩定性與可持續性的生產、生活方式,也達成了一種與這種生產、生活方式相適應的具有最大普遍性的倫理與價值信念時,真正的世界歷史意識才能最終呈現出來。那將意味著工業時代世界歷史的終結。
在馬克思早期最偉大的思想發明即唯物史觀中,他不僅率先對工業資本主義展開了深刻的歷史與道德批判,明確宣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命運,并且很肯定地把共產主義視為世界歷史的終結,甚至非常明確地指出達至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與方法——雖然在具體細節上有所變化。由于世界歷史時代所有的思想家都不可能憑空開啟對世界歷史的思考,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注定要以生活于其中的民族歷史觀念作為其思想的基本資源與起點,這就使其對世界歷史的思考不可避免打上民族歷史觀念的烙印。馬克思早期思想主要基于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理解世界“歷史必然性”,并把它作為一切民族都必然要承受的“鐵的自然規律”,他的思想被批評為具有歐洲中心論傾向的歐洲史觀就在所難免。馬克思晚年的思想轉變,主要并不是基于對他生活于其中的歐洲社會的新觀察,而是基于對東方社會歷史的新理解,這決不是偶然的。這意味著馬克思在努力掙脫西方民族歷史意識即西方中心論的束縛,自覺地站在整個人類發展史的新高度來重新把握世界歷史,因而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一次偉大自我超越。
因此,馬克思晚年思想轉變的實質,應該理解為從歐洲“民族歷史意識”視野下的世界歷史觀念——因而本質上還是工業時代的西方“民族歷史意識”——向人類歷史視野下的“世界歷史意識”的轉變。這一判斷主要基于這樣一個思想史的基本事實:直到馬克思晚年之前,馬克思一直沒有看到東方社會成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主動或積極因素的可能性與現實性,東方被當作世界歷史的必然附屬物或“獵獲物”。世界歷史不僅是由西方文明開創的,而且也將在西方文明的主導下進入未來社會——共產主義。在馬克思早期的共產主義設想中,人們完全看不出東方社會的元素或貢獻。但馬克思晚年的社會歷史思想,不僅意識到東方在工業時代有可能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文明發展道路,而且明確肯定東方歷史傳統對于人類共同未來的積極意義,因而是一種具有嶄新內容的世界歷史思想。
馬克思雖然沒有來得及充分展開他的思想就與世長辭了,但他晚年的思想至少有這樣兩方面的重大啟示。一方面,馬克思既充分意識到東西方文明的歷史差異會導致不同的達致人類共同未來的道路,也提示了這兩種不同道路的內在關聯。馬克思認為東方社會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主要依據,是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同時存在,所以它能夠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積極成果”。這就非常明確地提示我們,新的生產技術和與生產有關的機構創設,對于工業時代的物質生產具有普遍意義。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技術化是工業時代的必經之路。馬克思當時沒有充分考慮到的一個歷史境況是,在他生活的時代,工業文明的技術進步與財富狀況還遠沒有達到工業時代的極限。在資本邏輯的全部積極成果還沒有充分呈現前,資本邏輯不可能真正被超越的。另一方面,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的歷史與性質作出了很多迥異于前期甚至與之前相反的價值判斷——他作這些價值判斷的時候態度非常肯定,而且對世界歷史終結或人類具有共同未來的信念絲毫沒有動搖,尤其是,他認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新制度”將是“古代類型社會在一種高級形式下的復活”。這就意味著,馬克思不僅認為東方社會的歷史傳統對于東方社會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具有明確的積極意義,而且啟示了工業時代的未來發展方向。不過,從馬克思晚年兩個重要文本的具體內容來看,由于考古學當時還沒有發展起來,而人類學對古代文明的揭示又具有相當的局限性,馬克思當時既不具備充分把握“古代類型社會”發展過程與實質的歷史條件,也不可能深入地展開關于“古代類型社會”如何“在一種高級形式下復活”的各種想象。按照筆者的研究,主要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和集體生產是農業文明技術化時代普遍實行的制度安排,其目標是實現社會的技術進步與財富增長。到農業文明的倫理化時代,基本生產資料的家庭支配與小生產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生產形式,其目標是維護基本的社會公正與自由。因而當代的社會化大生產(無論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大生產),主要應該視為工業文明在技術化時代為實現技術進步與財富增長而采取的制度措施——雖然公有制經常還被過多地賦予實現社會公正的責任,而工業文明的未來即工業文明的倫理化時代,應該是農業文明的倫理化時代在一種更高形式下的復活。因此,馬克思所說的未來社會向古代類型社會的復活與復歸可能不是他所預期的趨向古代類型社會早期的公有制與集體生產,而是趨向古代類型社會的成熟時期。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被不由自主地投置于世界歷史之中,而且長期扮演世界歷史的配角,但經過一個多世紀的努力,我們的狀況正在或已經發生重大改變。可以肯定的是,世界歷史決不可能僅僅是西方文明的歷史,世界歷史也不會單獨終結于西方世界,東方文明的歷史經驗必將成為世界歷史意識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馬克思晚年的教導啟示我們,仍然活著的中國文化傳統必將對之作出重大歷史貢獻。筆者深信,中國文明在農業時代創造的偉大倫理傳統,不僅是中華民族開創中國道路的重要思想資源,而且將成為世界歷史時代人類文明共同的偉大精神財富。以馬克思晚年思想為起點,經由中華民族在21世紀對中國道路的創造性開辟,呈現或復活中國文明倫理化時代的歷史經驗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既是中國思想的歷史使命,也是中國思想的無上光榮。
(作者系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摘自《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