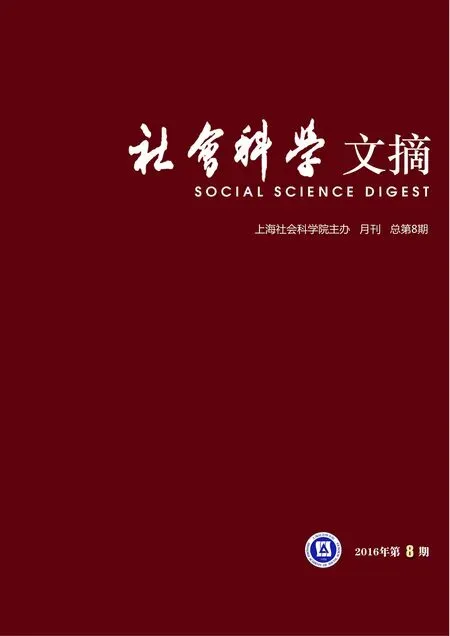中國地方領導任期與政府行為模式
——官員任期的政治經濟學
文/耿曙 龐保慶 鐘靈娜
中國地方領導任期與政府行為模式
——官員任期的政治經濟學
文/耿曙 龐保慶 鐘靈娜
根據迄今相關研究發現,中國經濟的關鍵在地方政府。由于政府決策主要是官員所為,針對政府行為的解釋,自然離不開官員的偏好,特別是那些掌握決策的地方領導。而地方領導官員如何決策與施政,受到各種制度的激勵與約束,有關任期的規定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由于他們只能在任期內有所表現(所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因此,“任期”成為官員表現的機會集合,他們將合理規劃任內作為,藉此實現其職務晉升的目標。
就任期而言,政府人事體制可分兩類:固定任期和彈性任期。固定任期規則下官員的任職時間固定,考核調職節點明確,官員的“表現機會”受到制度保護;而彈性任期規則下,官員的任職時間不固定,考核隨時進行,調職也無所謂預警,官員“表現機會”缺乏制度保護。
倘若處于“固定任期”制度下,官員對剩余時間的“貼現率”較低,不必急于收割政績,可以安排最佳的“表現組合”。這便引發了機會主義式的“政治經濟周期”:官員確知換屆時間,會將考核節點,發展為政績高點,擴大續任/升任的機會。換言之,政經周期的前提在任期固定。倘若任期不甚明確,考核隨時可能進行,調職也無法預知。此時當然無法規劃政績,也不至形成經濟周期。換言之,不同的官員任期制度,不同的政府日程,自然造成不同的經濟波動。
綜合上述,“任期明確與否”問題,邏輯上先于“任內如何規劃”問題。唯有任期明確,官員才能設定行動,才會出現規律周期。西方有關政經周期的研究,迄今已歷30余年,卻始終未形成一般理論,問題便在缺乏不同體制的比較。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是否存在政經周期”問題,具有相當的理論意義。
任期規則與官員行為模式
在固定任期制度下,由于官員的任職時間確定,通常不會被提前調離,對官員的考核節點也是明確的。官員會根據時間節點來安排行為,往往形成“政經周期”,關于固定任期條件下的官員表現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這里無需贅述。而在“彈性任期”制度下,官員的任職時間不確定,官員考核節點也不明確,上級隨時可能進行考核,他們可能隨時會被調任。因此無法形成明確預期與施政規劃,官員行為會呈現逐步增加的特點。彈性任期規則之下的官員為何并非上任之初,旋即拿出最大投入,而是逐步加碼、層層升高,原因有以下三種可能。
第一個可能是上級官員的“近因效應”。此乃基于上級記憶往往有限,“近期政績”具有放大效果。這類傾向經常出現在“政經周期”文獻中,但此類研究中的“考核方”是一般選民,對官員政績的關心程度與識別能力均有局限。倘若“考核方”換做上級官員,在下管一級的格局下,他們對下級政績的關心與識別,都不存在明顯局限。因此,在“由上而下”甄拔的體制下,前述“短視傾向”未必成立。有鑒于此,本文并不以此作為分析的預設。那為何官員的資源投入還會節節攀高?關鍵在于兩個層面“棘輪效應”,前者緣于時間層面的不可逆性,后者來自政績層面的不可墜性。
先說“時間層面的不可逆性”。這屬于信息滯后問題,其癥結在官員“信息更新”與“投入行為”間的時間落差。由于無法預知任期節點,官員只有到點才能確定尚未晉升(時間點為t),此時往者已不再可追,只能下期加碼投入(時間點為t+1),藉此提升其晉升概率。這個情況就像隨時間前滾的棘輪,一輪輪驅迫官員們賈其余勇、奮力投入。
其次為“政績層面的不可墜性”。這涉及政績如何歸因:究竟歸功于官員或運氣(其他各種不可控因素的綜合)?如果從任期展開來看,就任之初的政績,或能歸咎于其他因素(如地方稟賦或前任影響),越后期的表現,越聯系官員個人因素(無論能力或努力),越適合作為考核依據。此外,官員政績不但得拔高,還要求水平穩定。否則即便平均績效不錯,但表現卻時起時落,其績效易被視為其他因素所致。因此,對官員而言,其政績表現只能逐步攀爬,盡量避免下墜或波動。但事實上施政存在各種變故,未必能盡如人意,為了逃避政績下墜,當事官員最好:(1)任期之初,不求馬上登頂;(2)政績走勢,維持上升勢頭;(3)任期后段,絕不容許閃失。將此三個原則加以結合,便形成基于“前一年表現”上的政績棘輪,一輪輪驅迫官員們逐步拔高,奮力投入。
基于上述,我們可以得出兩大類迥異的行為模式:在“固定任期”下存在中后期高點,而在“彈性任期”下則呈現節節攀升趨勢。
中國地方政府官員任期
中國地方政府官員任期為何?多數學者根據相關法規認為中國是五年一屆的固定任期規則(比如黨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黨政領導干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2006)》),但相關報道卻顯示官員調任又比較頻繁,那么中國實際中運行的任期規則是何種形式呢?針對此,我們詳細統計了我國地方政府(省、地市和縣)主要官員(行政首長和黨委首長)的實際任期情況。
首先,來看省級官員的任期情況:1994-2010年31個省份的省委書記任期從1年到15年不等,任期3年的人數最多,為19人,占比為17%,省委書記的平均任期為4.77年,省長任期從1年到12年不等,任期4年的最多,為25人,占比為21%,省長的平均任期為4.32年。其次,地級市的官員任期情況:2000-2010年全國333個地級行政區的市委書記任期從1到11年不等,任期3年的人數最多,為284人,占比為29%,市委書記的平均任期為3.6年,市長任期1到11年不等,任期為3年的人數最多,為317人,占比為30%,市長的平均任期為3.21年。最后,縣級官員任期情況:1998-2010年江蘇省各縣縣委書記任期1到11年不等,任期為3年的人數最多,為44人,占比為19%,縣委書記的平均任期為3.53年,江蘇各縣縣長的任期1到10年不等,任期為3年的人數最多,為55人,占比為23%,縣長的平均任期為3.34年。
從官員任期的實際情況統計可知,即便法有原則規定,具體實踐卻有相當落差。首先,官員調動十分頻繁,多數并未做滿法定任期。其次,官員任期長短不一,彼此相去甚遠。因此,我們可以說我國地方政府官員的職務任期并非固定任期,而是彈性任期。在此種任期規則下,官員的行為表現會呈現出節節攀升的趨勢。
實證發現及討論
針對前述研究假說,接續的部分我們將采用定量模型來實證檢測。其中因變量為“創造政績的投入”,通過基建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加以度量。自變量為官員任期。控制變量為:人均GDP;人均財政支出、財政自主比例;官員年齡;國企比例;西部大開發。我們采用1994-2006年省級面板數據來進行實證檢驗,采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
模型顯示:隨著官員任期每增加一年,基建支出比重將增加0.3個百分點,可以確認官員基建支出隨其任期增長而逐步上升的趨勢。但這是任期塑造的官員壓力,還是“職務交接”所致?還是任期增加,官員“熟悉情況”所致?為此,我們通過剔除任期首年樣本排除了“職務交接”的影響,通過63歲官員有無晉升激勵排除了“熟悉情況”的影響。
此外我們還進行了如下穩健檢測:(1)是否存在模型誤設?(2)是否存在異常值?(3)排除干擾:剔除非完整任期的案例。(4)改進控制:控制官員個體效應。最后我們還利用2000-2006年地級市數據、江蘇縣級數據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同樣支持本文發現。
通過上述檢測可以發現:無論在省級、地級或縣級,地方政府的基建投入,均一致隨領導任期推移而逐年加碼。現有官員信貸投放、環境污染的研究也從不同角度支持作者的發現和解釋。但上述研究對其背后原因討論過于簡略,作者直指此均乃“彈性任期”的制度后果。
結論
通過基于美國經驗的“政經周期”理論,我們了解到官員任期如何塑造官員激勵,同時切割出政府施政的時間節點,進而引發規律的政治經濟周期。本文則針對中國地方政府行為,發現比“任期如何產生影響”更重要的是“是否存在(制度化的)任期制度”。本文從這個角度考察了中國省、市、縣三級政府的財政投入,發現實踐于中國的任期制度,屬于“任期彈性,隨時遷調”的性質。這一方面有助解讀中國發展的特征,另一方面或能啟發更通則的任期政治經濟研究。
接續的問題是:既然法規規定了明確的任期制度,實踐過程中為何出現權變?根據作者看法,關鍵在固定任期無法滿足中央與上級控制官員的需要。從委托-代理角度來看,宏觀層次的控制存在于“中央-地方”間:中央為提振合法性,必須驅使地方官員配合;微觀層次的控制發生于“上級-下級”間:上級為創造依附,往往藉此掌控下級。換言之,為了在兩個層面上分別完成“強效控制”,委托方必須限縮代理人的制度保護,削弱本來明確的任期,最終形成“彈性任期”。
(耿曙單位: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龐保慶單位:上海大學社會學院,鐘靈娜單位: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美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摘自《經濟學(季刊)》2016年第3期;原題為《中國地方領導任期與政府行為模式:官員任期的政治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