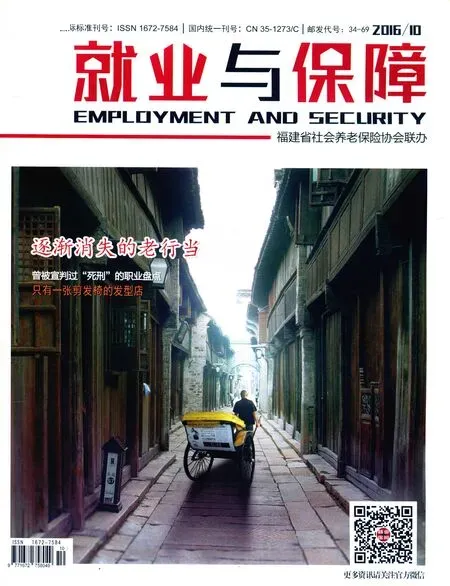探究嚴歌苓作品深受導演青睞的原因
吳星華
探究嚴歌苓作品深受導演青睞的原因
吳星華

據《中國電影報》的粗略估算,目前嚴歌苓的中、長篇小說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的已有二十余部之多。從臺灣電影界1995年《少女小漁》(改編自同名小說),到近來深受關注的《金陵十三釵》和《陸犯焉識》,此外她的小說《白蛇》《灰舞鞋》《第九個寡婦》《寄居者》等作品的電影版權已被知名導演購買,更多小說將被改編成電視劇和電影,影視界已形成嚴歌苓小說的改編風潮。
為什么中國導演對嚴歌苓的文學作品有如此大的興趣?因為大部分嚴歌苓的作品都頗具“電影色彩”,其作品中吸引人的畫面故事,獨特鮮活的生命力主題,精準的描寫方式和冷靜筆調,引起讀者和導演的關注。嚴歌苓是一個有獨創個性和藝術才能的藝術家,她的才能和創作個性從其一系列影片場作思想內容和影像風格的電影化表現中顯露得十分明顯。除此之外,嚴歌苓成功的雙語創作以及好萊塢編劇身份,也使她成功涉足電影行業。她寫的小說由于包含諸多影視元素而深受內地導演歡迎。
一、東西方元素在作品中的體現
不同尋常的人生經歷,東西方文化融合與沖擊,造就了嚴歌苓與眾不同的視角和觀念。“有了外國的生活經驗,不自覺的新角度,我的思考有了新拓展。移民生活的確給作品增添了深度與廣度,顯然與完全生活在國內的作家是不一樣的。”
嚴歌苓小說中的人物,不論男人女人都有豐富的人文內涵。她的主體虛實概念符合人們的正常想象,她對中國人文環境的營造具有大氣的整體感和真實的置入感,教堂、塞外、都市、民間,人物在其間自如穿行,自然流暢。對人物的塑造上,用一種古舊的感覺表達平實的、樸素的、內斂的民間做派,還有思想禁錮年代的壓抑感和保守氛圍。她的電影,經得起歲月的磨礪和不同時段的品味,慢慢地讓更多的中國人發現她創作的獨特性。正如嚴歌苓自己所說:“我的小說無意間就照顧到了商業的需求。”
嚴歌苓小說中多處充斥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對于文化身份問題的探索,這也是國內導演和觀眾想要通過她的小說看到的外面的世界。人們對華人在國外的生活充滿好奇,他們好奇的不僅僅是不一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包括移民后所帶來的文化的沖突以及身份的構建過程。嚴歌苓以大陸新移民的異域生活為題材,用大量的筆墨敘述懷揣夢想的移民們在西方世界的艱難,中西方文化觀念沖突所造成的苦悶、失落、恐慌等也在嚴歌苓的筆下深刻地揭示出來。
例如,嚴歌苓借助《失眠人的艷遇》表達自己在異國的感受:“床的一步開外是窗子,打開來,捂在我臉上濃稠的冷中有異國的陌生,還有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敏感。”嚴歌苓也在其他新移民小說《海那邊》《扶桑》《茉莉的最后一日》和《少女小漁》表現華人在異域中居留權、話語權、生存權等方面的壓力與痛苦。書中人物的“舞臺背景”,不但表現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生活的傳奇故事,還將筆觸深入人物內心的深處,挖掘復雜的情感和內心的共鳴。這樣對人物內心關注的敘事,是嚴歌苓小說改變傳統寫作的一種全新的嘗試,是西方現代主義敘事在其創作中影響的體現。也因為這樣的主題,滿足國內觀眾獵奇的心理,從而為小說改編電影打開又一新的通道。
大部分接受過西方教育的華人作家都避免不了受殖民主義的潛在影響。他們的作品里總是迎合西方話語的東方主義式的描寫,關注西方讀者怎樣看待故事的規則。強大的西方霸權令華人作家把對中國的想象不約而同地暗合在作品中。中國的導演也喜歡表現中國農村的陰暗落后以博得西方人的審美和閱讀心態。張藝謀的電影就因為這樣屢屢獲獎,但卻遭到中國觀眾強烈抵觸。也有一些華裔作家在寫作中有意維護東方主義的描寫,試圖擺脫西方話語的束縛,掙扎的結果是敘述者身份不同,體現不同的情感,體現了作家的文化認同與文化選擇。
嚴歌苓的小說到處體現中國文化元素,這也是中國導演喜歡改編她的作品原因之一。例如《扶桑》里克里斯一見面就被身著腥紅大鍛的扶桑和神奇的畫面驚嘆不已;《紅羅裙》中,代表嬌艷的血色青春和強烈生命欲望的紅羅裙;《雌性的草地》里為了革命理想的一抹紅等等。紅色是被西方人確認的中國式象征符號。所有的莊嚴與神圣,都在對紅色的膜拜中完成,也在大徹大悟中完成對壓制人性的批判。作家與導演都愛把這種紅色代表符號體現在他們的視覺作品與非視覺作品里。這和追求畫面美感及視覺沖擊力的張藝謀不謀而合。注重畫面色彩的鋪張和感染力也使張藝謀對紅色過分鋪排,用心構筑意象中國。大部分旅居美國的華人所創作的作品都逃離不了投射強烈文化和政治意味在里面,認同美國人的性別隱喻規則:女性就是中國,男性就是西方列強。
與《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女人》自我維護民族自豪感不同的是,嚴歌苓并沒有維護中華文化或妖魔西方文化,嚴歌苓把重點放在華人日常瑣碎生活中,真正體驗華人在異國他鄉的真實故事。她清醒地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自由精神,因此她能抽離對自己對中國文化感情的肆意偏淡,以自己的生存體驗、異國經驗客觀審視中國文化。正如嚴歌苓自己所說的那樣:“僥幸我有這樣遠離故土的機會,像一個生命的移植——將自己連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移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這個生命的全部根須是裸露的,像是裸露著的全部神經,因此我自然是驚人地敏感。”正因為嚴歌苓對生活如此獨特的敏感,她所創造的作品才有其與眾不同的地方,才有導演爭先恐后等待購買她的新作品。
基于嚴歌苓在西方受大學教育并生活工作的經驗,她在創作中對中國歷史和文化人格有超乎一般中國人的反思能力;她熟悉西方的文化語境,表層用的是傳統的中國元素,內涵卻還是“自由”和“愛情”這兩大西方電影的主題,不僅有對人類終極價值的追求,還不含而露地融入“性與原欲”等西方現代藝術的觀念,從而讓西方人在驚嘆中國傳統文化等東方想象中,重溫他們熟悉而認同的價值理念。嚴歌苓也“在對邊緣人物的刻畫中,在對移民美國的命運的轉達中,完成了對祖國文化的深刻反省和對西方文化的敏銳剖析。”目前華語電影編劇中,只有嚴歌苓能游刃有余地穿行在東西方文化之間書寫電影詩作,并贏得如此巨大的國際聲譽。嚴歌苓改編的電影,是東方的,也是西方的;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二、主人公與主題的獨特性
嚴歌苓小說對人性在異族語境下迷失和掙扎的刻畫,表現出其對新移民“失語”狀態和“文化邊緣人”身份的憂慮和關切。就是這樣的一種獨特性,嚴歌苓寫出來的小說所體現的主題讓中國導演愛不釋手,她作品中思想內容和藝術情趣都是相當中國式的,但那是屬于雅文化范疇的,與“影戲”中常見的市井平民的思維方法很不同。
例如在《金陵十三釵》中,嚴歌苓沒有被時代所限制,不像大家談到抗日就慷慨激昂,她看透了這個東西,她從來沒有被狹隘的家、國、民族等大概念的迷障所引誘,她關注的是原始的人性,在障礙重重穿行的男人女人的命運和抉擇。
在電影《小漁》里,嚴歌苓也是通過這樣一個平淡且并不曲折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移民后中國人的苦悶心情。盡管作者毫不吝嗇表達對中國母親的愛,但小漁最后拋棄中國文化,以母性般的慈愛與人道主義精神,選擇留在美國,選擇嫁給美國文化,盡管內心無法割舍中國情感。
與此相反,在《扶桑》中,盡管扶桑對克里斯有什么愛慕之意的話,最后她沒有游離在美國文化與中國的東方文化之間,她宣布自己是是大勇的妻子,就是選擇中國文化。嚴歌苓在小說里以開闊的胸懷融合中西文化,這是她不同于20世紀60年代旅美留學生反映出來固守文化的不同之處。
三、電影敘事的運用
在小說情節的設置上,嚴歌苓基本摒棄了外在的強烈的戲劇沖突,但又不全靠寫實性的細膩描寫。她把沖突和情節的進展集中建立在人物的內心活動上,扣住人物間的情感沖突來展開情節。這種主客觀的融合所創造的特殊的意境美,通過一系列優美的視聽語言表現出來。
在敘事層面上,嚴歌苓刻意讓視聽形象直接參與故事意境美的營造。如帳篷、湖面等許多場景段落中人與景物的融合,直接創造了情景交融的境界。這樣的寫作手法容易讓導演通過鏡頭的運動和組接等電影化的手段也參加到意境營造中來,給了電影情境特殊的美感,便產生了更強大的藝術沖擊力。如《天浴》中無人物定性的全知型旁白體系,絕不僅作用于虛實層面,它在與畫面的結合中,一方面揭示了文秀復雜的心理矛盾,一方面又賦予整個影片一種朦朧的情調。
作為資深編劇,嚴歌苓清楚地知道,如今的電影觀眾厭惡抽象地、深奧莫測地來使用電影敘事手段。觀眾尋求的是一種對現實的表現,不論是外在的、內在的或是幻想的,只要它不是堆滿了暗示、字謎和莫名其妙的符號組成。嚴歌苓認為,電影作為一種表現手段有其局限性,必須了解它的優點和缺點。沖突和運動更接近其實質,而平靜、希望和偉大的真理,全部具有一種靜態的性質,電影手段便無法很好地表現出來:思維和概念,特別是抽象的概念,在電影中便不能像文字表達得那樣清楚。這些必須通過人物、動物或事件的行動由攝影機紀錄下來。
深諳此道的嚴歌苓,也在小心翼翼地將電影敘事運用到小說里。她認為,高明的電影創作者堅持他們的視覺形象,但把視覺形象從創作者的腦海中轉移到一條膠片上,二者之間還有復雜的工藝過程,而這個復雜的過程不應使創作者看不見那個激發他要用電影作為交流手段來表達的主題,不應使他脫離自己對主題的富有個性的獨特的想法。
所以,要想成為效率高的故事講述者,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對故事有一個清晰的視覺構思,同時反映出自己獨有的特點。嚴歌苓正是對電影敘事研究的透徹,成功地將電影敘事融入到小說創作里,才使得她的作品不但易于改編成電影,也成為各路導演手里的香餑餑。
嚴歌苓嘗試將電影語言融入她的小說藝術創作,她非常注重人物表現的含蓄性,成功地采用迂回的寫作手法,給觀眾帶來了豐富的藝術想象和審美體驗。例如,她根據電影語言的特色,將說話的韻律、正確的字詞選擇、句子的長度、怪癖的字眼、俚語等巧妙地將電影語言融入到文本寫作中。她讓人物用言語粗俗的角色滔滔不絕地說了一串臟話,就好像把人物生命中的暴力以語言表現出來一般。嚴歌苓認為好的電影對白總能造成好的“聽覺”效果。這使得導演或編劇不用費勁心思改編她的文本語言,特別是在處理代表低下層人物方言時,嚴歌苓文本中的人物對話,都接著一股鮮活的地氣,讓人“隨意拎出一段對話,都可以直接放上銀幕成為臺詞”。
例如,在《第九個寡婦》里的河南方言,《小姨多鶴》里的東北方言,以南京話為主調的《金陵十三釵》中,主要人物和情節都有刪減,但很少改動對白。特別是《金陵十三釵》小說中,妓女以南京方言嬉笑怒罵,將臟話、性事揉進笑話里,將秦淮妓女的粗俗且鮮活的形象復蘇在紙上。另外,《陸犯焉識》也是成功運用電影語言的作品,它以敘緩的節奏、富于變化的長鏡頭和空間表現,直接傳達出大量敘事難以表達的思想信息,在舒緩的敘事流程中,運用豐富的電影語言,深入細致地描繪了人物的心理和情感波動,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這樣的寫作效果,正如嚴歌苓所說,“要寫電影,首先要懂戲劇。有時候把戲突出了,就通俗了,不夠嚴肅了,跟我的原則是相背的。我喜歡電影,但從來不看電視。文字之外的東西,可以通過電影語言表達。”
嚴歌苓用獨特的方式強有力地表達自己的敘事角度。她用拍攝者的角度講故事,這是一種極度令人興奮和高度個人化的探索過程,這使得她觀察事物的角度與眾不同,她能用與世間其他作家不同的方式——拍攝者的角度(條理清晰的場景、視角和吸引人的配樂)——來講述在視覺上引人入勝的故事。
例如在《金陵十三釵》中,嚴歌苓用較多的筆墨集中在畫面上,來表達戰爭所帶來的恐懼,徹底刪除聲音。嚴歌苓懂得掌握圖像與聲音之間的互動給讀者帶來視頻般的效果是她創作的核心技巧,這是為什么她寫的書容易被改編成電影的原因之一。
因為做編劇得來的豐富經驗,嚴歌苓在描寫場景時,總能對背景元素作縝密的控制。因為那些背景通常比前景或是主題本身能傳達更多的東西給讀者。這是因為讀者天生愛懷疑,總是在不停地掃視畫面的邊邊角角,尋找故事中的線索。背景能講述真實的故事。例如,《天裕》里,對文秀為了進城,讓各種各樣的男人到她的帳篷里跟她睡覺,嚴歌苓這時候把故事背景嚴格控制在對帳篷外“兩只底朝天的男人鞋”的描述上:
“每天老金回來,總看見帆布簾下有雙男人的大鞋。有次一只鞋被甩在了簾子外,險些就到帳篷中央的火塘邊了。老金掂起火鉗子,夾住那鞋,丟在火里面。鞋面的皮革被燒得吱溜溜的,立刻泌出星點的油珠子。然后它扭動著,冒上來粘稠的煙子,漸漸發了灰白。一帳篷都是它的瘟臭。老金認識這鞋,場里能穿這鞋燒包的沒幾個。”
嚴歌苓用放大鏡,通過讀者的閱讀,將精力集中在描寫“兩只底朝天的男人鞋”的描述上。我們通過上面的敘述,可以知道大量的信息,文秀和別人睡了,不同的男人來了,這鞋透露男人的地位,文秀變成了破鞋,老金內心的痛苦,當時社會的“瘟臭”風氣,暗示故事結局是“發了灰白”。
通過上述對嚴歌苓電影文學作品的解讀,我們從中梳理出嚴歌苓海外生活經歷與編劇身份對她后期的創作有著巨大的影響,從東西方元素在作品中的使用,到主題選取的獨特性,再到電影敘事寫作手法游刃有余地融匯到文學創作中,最后好萊塢影視元素的完美結合,使得嚴歌苓成為各位導演心目中的熱門搶手作家。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
[1]萬佳歡.嚴歌苓:“寄居”在文學深處[J].中國新聞周刊,2009(12).
[2]江少川.走近大洋彼岸的繆斯——嚴歌苓訪談錄[J].華文文學,2006(3).
[3]張愛華.善良與偏見——論嚴歌苓小說中的邊緣人物及西方人對中國的想象[J].開封大學學報,2008(9).
[4]嚴歌苓.天浴[M].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