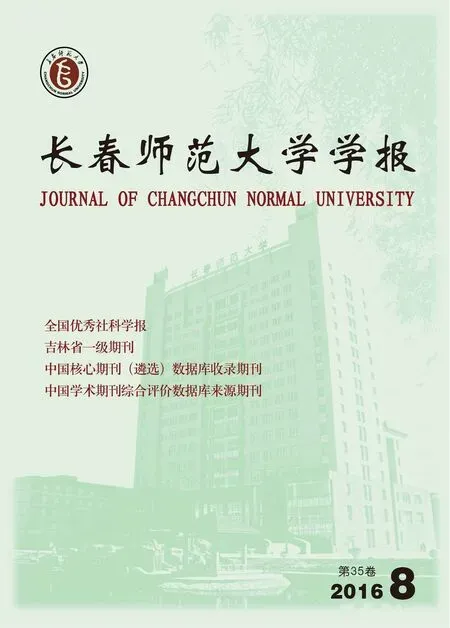淺談音樂劇《巴黎圣母院》中音樂、舞蹈、舞美對人物形象的塑造
姚 穎
(濱州學院音樂系,山東濱州 256600)
?
淺談音樂劇《巴黎圣母院》中音樂、舞蹈、舞美對人物形象的塑造
姚 穎
(濱州學院音樂系,山東濱州 256600)
本文從音樂、舞蹈和舞美入手,對音樂劇《巴黎圣母院》中人物塑造展開剖析。該劇采用歌手、舞者的方式,將音樂、舞蹈和抽象的寫意性舞美在戲劇框架下進行有機結合,共同完成了人物角色塑造。劇作者采用史詩劇的創(chuàng)作模式,通過間離與移情的手法,將發(fā)生在距今幾百年前的歷史畫面活生生、立體化地呈現(xiàn)在舞臺上,以史為鑒,引發(fā)人們對現(xiàn)實生活的深刻思考。
音樂劇;巴黎圣母院;人物塑造
音樂劇《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又譯為《鐘樓怪人》),改編自法國文學家雨果的同名長篇浪漫派小說,呂克·普拉蒙登作詞,理查德·科奇安特作曲,1998年6月首演于巴黎國會大廳。劇中成功塑造的陽光下跳舞的率真少女艾絲美拉達、飽受愛欲煎熬的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弗羅洛、英俊多情的衛(wèi)隊長腓比斯和內心善良卻樣貌天生丑陋的敲鐘人加西莫多這些鮮活人物形象,讓萬千觀眾沉溺其中嗟嘆不已。其主演卡胡(Garou,原名PierreGarand)因飾演卡西莫多而成為法國巨星,艾絲美拉達的扮演者伊蓮娜·西嘉賀(Hélène Ségara)因此劇躋身最受歡迎法國女歌手行列,被譽為法國溫婉天后。本文以人物塑造為切入點,以期管窺法語音樂劇在人物塑造上的獨到之處(以下將音樂劇《巴黎圣母院》簡稱《巴》)。
1 音樂對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音樂是音樂劇的重要表達手段。音樂有助于推進戲劇動作展開、揭示矛盾沖突,是塑造鮮明的人物形象所不可或缺的。音樂劇《巴》沒有一句對白,由52首音樂組成,主要涉及搖滾、吉普賽(西班牙弗拉明戈)、法國香頌和中世紀宗教圣詠四種風格。這些音樂風格的使用并非隨意為之,而是與劇中人物的身份、性格特征緊密相連。
音樂劇《巴》中的女主角艾絲美拉達(Esmeralda)是一位來自吉普賽的異國少女。為了表明她的異族身份,在第一幕首次出現(xiàn)時她便唱出極具吉普賽風格的歌曲《波西米亞女郎》(Bohémienne)(譜例1、譜例2、譜例3)。
這首歌曲采用二部曲式,a自然小調,音域不寬,情調憂傷,在一個八度之內,由歌者采用流行音樂唱法真聲演唱。旋律線條(譜例1的紅色線條)盤旋下行,帶有凄涼和憂傷的基調。每句的結尾處(橢圓圈所示部分)采用大二度上行或下行級進,并伴有即興的裝飾音和滑音等。在節(jié)拍上都采用4/4拍,但在節(jié)奏上,先是在譜例2采用平穩(wěn)的××××××××節(jié)奏型,像是艾絲美拉達以敘述的口吻正在平靜地訴說。旋律中三連音的使用與伴奏采用的分解和弦的平穩(wěn)節(jié)奏形成了節(jié)拍交錯,加強了音樂的對比,突出了音樂的層次感。

譜例1

譜例3
色彩性樂器吉他和印度西塔爾琴的使用更突出了音樂中的異域風情。音樂與劇詩相結合,由艾絲美拉達用低沉略帶神秘感的聲音反復吟唱著“我是吉普賽女郎,沒人知道我來自何方”,一個謎一樣的吉普賽少女形象立體地展現(xiàn)在觀眾面前。而緊接著(譜例3)音樂不斷變化發(fā)展,轉為使用××0×0×0×︱0×0×××××︱帶有跳躍性的節(jié)奏型,既與前面節(jié)奏形成對比,又加強了音樂的律動感。隨著節(jié)奏律動性加強,艾絲美拉達自然地邊唱、邊舞,并興奮地擊掌,表現(xiàn)出吉普賽民族與生俱來的熱情、開朗的性格特征。這時,劇詩以簡明扼要的語言介紹了艾絲美拉達的成長背景:“聽母親說西班牙的安達盧西亞是我的故鄉(xiāng),而父母早已離我而去,只有我一個人在這世界上孤獨的流浪。在普羅旺斯度過童年,現(xiàn)在巴黎已經(jīng)成為我新的家鄉(xiāng)……”在講述童年的經(jīng)歷時,艾絲美拉達沒有表現(xiàn)出一絲憂傷的情緒,反而嘴角略帶微笑,既表達出身為吉普賽人的自豪感,也仿佛充滿著對過去美好的遐想與懷念。音樂在接近尾聲時又回到開始時的舒緩吟唱:“不知道明天將會去什么地方,命中注定我將一生流浪。”表現(xiàn)出艾絲美拉達早已習慣了流浪的生活,并坦然把它當成命運的安排。一個對生活充滿美好向往、熱情、開朗的吉普賽女郎呈現(xiàn)在觀眾面前。
在艾絲美拉達的人物塑造中,帶有中世紀宗教圣詠風格的歌曲《異教徒的圣母頌》(Ave Maria paien)(見譜例4)使角色脫離了天真、單純的性格特征而被賦予了為種族、為人類呼吁消除隔閡的神圣光環(huán),角色的豐滿度得到了提升。

譜例4
這首歌曲全曲在f小調進行,曲式結構為:引子(2)+A(4+2)+B(2+2)+C(2+3+3)+B+C+B+C。曲調舒緩、典雅,多采用級進進行,帶有宗教圣詠寧靜的氣質。整個主題樂句“圣母瑪利亞”在屬音上持續(xù)進行,如教堂里的圣歌純潔無暇,表達了對圣母的無限崇敬之心。第二樂句降低二度,音符加密,聲音愈加低沉。但低音伴奏織體有較大的上下旋律的起伏,色彩和弦造成不停的離調潛滋暗長。B樂段開始引申了主題樂句,但旋律升高了六度。第三樂段在主題旋律的基礎上升高四度。此三段為樂曲的主體,從小節(jié)數(shù)來看分別是6+4+8的小節(jié)長度,這種不均衡的比例在第二樂段開始就用縮減的方式打破,為樂曲的進一步發(fā)展蓄積了力量。這首作品帶有雙重意義:一是為整個在社會夾縫中生存的族群而唱。艾絲美拉達雙膝跪地,張開雙臂做受難狀的動作,虔誠地請求圣母“拆除人與人之間的藩籬,我們都是姐妹兄弟”,對不分國家、不分種族的人以憐憫與庇護,她悲天憫人的情懷賦予她神性的光輝;二是這首圣樂充滿了艾絲美拉達對自身痛苦人生的哀怨與迷惘。B和C樂段的兩次重復,尤其在樂曲結束時用一個綿長的嘆息之音,不僅請求圣母保佑未來,更帶有獲得愛情的美好愿望,以致曲終時已不能自持。
通過不同風格音樂的使用,刻畫出一個充滿了浪漫、神秘色彩的十七八歲吉普賽少女艾絲美拉達,其性格熱情率真、豁達開朗。也通過其內心情感的表達,展現(xiàn)出她心系族群的形象。
2 舞蹈對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音樂劇《巴》的舞蹈設計是整個音樂劇的一大亮點,專業(yè)舞者將現(xiàn)代舞、即興舞蹈等采用群舞、三人舞等舞蹈形式,用肢體語言表達出角色演唱中描繪的情境或情感狀態(tài)。有的舞者用原始的肢體力量表達角色內心的強烈情緒。各種翻滾、倒立、跳躍不僅帶給觀眾前所未有的視覺沖擊,也為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鐘》(Les Cloches)作為表現(xiàn)加西莫多(Quasimodo)內心情感的重要唱段,在鐘聲與吉他輕柔的伴奏中,用嘶啞而低垂的聲音訴說著每天陪伴他的伙伴——“我所敲的鐘,是我的愛,我的情人……”此時的舞臺中央懸掛著三座大鐘,每座鐘的下面都有一個舞者,他們穿著與加西莫多相同的衣服,如同他的分身,伴隨著歌聲翻轉、卷身、擺蕩,描繪出加西莫多日復一日與圣母院的三座大鐘相依相伴、形影不離。接著,音樂進入d小調,在伴奏賦予跳躍的O×××O×××節(jié)奏中,旋律配以與之一致的32分音符,快速跑動,盤旋級進下行。隨著d—f—ba—b—d—f頻繁轉調,音區(qū)不斷上升。此時的舞蹈也由三人擺鐘開始加入更多的群舞演員,他們步調一致,夸張地跑跳、踢腿、搖擺、旋轉、翻滾……表現(xiàn)出莫名與不知所措的傷感,而這傷感正是加西莫多內心的寫照。正如他此時所唱:“它為出生而鳴,它為死亡而鳴……日日夜夜,時時刻刻”。加西莫多的情緒在講述中越來越激動,到達情感的頂點。鐘下方的舞者此時已攀爬到鐘的上端,他們有的拽著繩子將鐘置于傾斜狀,有的坐在鐘上扭動著身軀、坐立不安,有的則圍繞著鐘外側的邊緣行走,像是加西莫多在質問陪伴其長大的鐘——他最愛深的朋友,他對朋友(鐘)深情滿懷,而鐘卻沒有一聲是為他而鳴響,內心不禁若有所失、滿心惆悵。接著他激動地喊出自己終日為別人敲鐘祈禱,而在別人眼中卻視他為無物!在最后A段旋律再現(xiàn)時,激動的音樂逐漸平復下來,這時鐘的上方和下方均有舞者,上方的舞者直立站在鐘的頂端,下方的舞者隨著晃動的大鐘擺動。加西莫多喊出他心中深藏已久的心聲:“告訴全世界,加西莫多愛上了艾絲美拉達!”由此可見,加西莫多在內心斗爭中成長起來,自我意識開始覺醒。
《鐘》中舞蹈演員的表演與加西莫多歌唱相得益彰,形象地刻畫出他內心從疑問、掙扎到覺醒的過程,完成了角色從“怪物”到人的思想轉變,使角色更加豐滿、立體。劇中“歌者不舞、舞者不歌”,歌、舞分離,舞臺像是被切割成兩個窗口。在演員用歌聲詮釋內心感受的同時,舞者通過肢體語言表達出角色的內心。歌者只管縱情高歌,無需擔憂高難度舞蹈動作對聲音的影響,專業(yè)舞者也只須盡情舞蹈,運用肢體語言表達特定的戲劇情境。歌、舞相互補充、相互配合、相輔相成。
3 舞美對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音樂劇《巴》的舞美設計采用了極為大膽、極具現(xiàn)代感的抽象性或寫意性舞臺設計手法。從演出開始到結束矗立在舞臺后區(qū)的一道“墻”由若干“石塊”堆砌而成,混凝土的顏色,上有凹凸的紋飾和可供攀登的抓手、石臺。在“墻”的前面還有三個可以移動的“石柱”,“石柱”頂端靜默地佇立著巴黎圣母院的怪獸神龕雕塑。“墻”、“石柱”、神龕再加上燈光將玫瑰窗的影像投射到舞臺上,這便“組成”了我們心中宏偉的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在巴黎圣母院的“墻”上出現(xiàn)的第一個人便是副主教弗洛諾(Frollo),他身披宗教的黑袍,莊嚴肅穆地站立在“墻”上層的石階處,向衛(wèi)隊長菲比斯下達命令,驅逐非法移民。其音樂采用了宣敘性歌曲、命令式語氣,劇詩既面面俱到又言簡意賅,標識了他作為宗教及社會統(tǒng)治者所應有的良好禮儀修養(yǎng)和至高無上、不可侵犯的尊貴地位。他高高在上,俯視著眾人,一束追光打在他身上,威嚴的弗洛諾和矗立的“石墻”融為一體,他便是故事中統(tǒng)治者至高無上權力的代言人。而那高高的不可侵犯的“墻”也成為阻礙弗羅洛擁有正常人欲望的屏障,使自幼在巴黎圣母院修行的他戴上了禁欲的思想枷鎖。《致命狂戀》(Tu vas me détruire)中,因愛上艾絲美拉達而備受煎熬的弗羅洛被擠壓在兩個巨大的“石柱”中間,而這巨大的“石柱”卻正是曾經(jīng)給他快樂的清修生活的巴黎圣母院的象征。這種矛盾的掙扎使弗羅洛看上去尤為可憐。
輕薄透明的紗簾在歌曲《巴黎城門》(Les portes de paris)中是第一幕上下兩場的分界,也代表了白天和黑夜的交替。歌曲一開始,紗簾降落在舞臺中央,將舞臺分割成前后兩個區(qū)域,風流瀟灑的詩人葛林果(Gringoire)作為故事的講述者站在紗簾的前面,向觀眾講述著紗簾后面——巴黎城的夜晚發(fā)生的事情:“在這狂歡和欲望充斥的夜晚,所有的罪惡都各得其所,巴黎的床第間,欲望正在上演……”而此時,卡西莫多正在奉副主教弗羅洛的命令綁架艾絲美拉達。弗羅洛在白天道貌岸然,夜幕下卻對艾絲美拉達伸出了魔爪,這層紗簾仿佛成了寧靜的夜幕下丑惡的事情最好的隱藏,人性的變化在這層紗簾的升降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一首反應菲比斯內心世界的獨唱作品《撕裂》(Déchiré)中,紗簾再次降落在舞臺中央。菲比斯在紗簾前激動地唱出對埃斯梅拉達和百合難以取舍的愛情掙扎,紗簾后面4個赤裸著上身的男性舞者正在激烈地酣舞。如果沒有紗簾,這個情境像極了我們平日里熟悉的歌伴舞,歌手唱得激情,舞者伴得熱烈。但就是這道紗簾的阻隔,增加了舞者表演的虛幻性,也讓觀眾讀懂了那些舞者用盡全身心的力量表現(xiàn)出的掙扎。因此,舞者的動作是菲比斯內心痛苦糾結的外化。一層薄薄紗簾卻承擔著表達角色內心情感、塑造人物形象的戲劇性作用。
4 結語
音樂劇《巴》運用音樂、舞蹈和舞美對人物角色的塑造中,并未采用傳統(tǒng)歐美音樂劇中由角色本身承擔歌、舞、演的表演模式和寫實性的舞美設計,而是采用了歌手、舞者各司其職的另一種歌、舞、演的組合方式,將音樂、舞蹈和抽象的寫意性舞美在戲劇的框架下進行了有機結合,既各自獨立又相輔相成,共同完成人物角色的戲劇性塑造。而這種“另類”組合的產生,源于劇作者采用了史詩劇的創(chuàng)作模式,通過間離與移情的手法,將發(fā)生在幾百年前的歷史畫面活生生、立體化地呈現(xiàn)在舞臺上,引發(fā)當下的人們對現(xiàn)實生活的深刻思考。這種獨特的組合呈現(xiàn)方式也讓法語音樂作為音樂劇發(fā)展史上的后起之秀,在音樂劇的舞臺上獨樹一幟且大放異彩。
[1]慕羽.西方音樂劇史[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4.
[2]陶辛.流行音樂手冊[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0.
[3]雨果.巴黎圣母院[M].陳敬榮,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4]貝·布萊希特.布萊希特論戲劇[M].丁揚忠,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
[5]張筠青.歌劇音樂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馬丁·艾思林.戲劇剖析[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1.
2016-05-20
山東省濱州學院青年人才創(chuàng)新工程科研基金項目(BZXYQNRW201211)。
姚 穎(1980- )女,講師,碩士,從事音樂戲劇研究。
J80
A
2095-7602(2016)08-01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