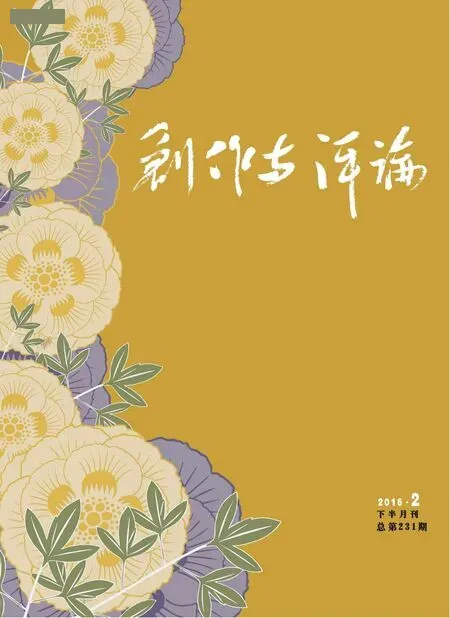靈魂探索之旅——殘雪的寫作實踐與文學價值
○趙飛佘曄
?
靈魂探索之旅——殘雪的寫作實踐與文學價值
○趙飛佘曄
編者按:2015年9月21日,湖南省社會科學院主持舉行的“殘雪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長沙成功召開,來自中國、美國、日本、瑞典等地的30多名專家、學者暢所欲言。大家從殘雪作品的主題與人物、思想文化背景、小說藝術、文本解讀、美學特征等角度,深入研討了殘雪的寫作實踐與文學價值;我們摘錄了此次研討會的部分論文觀點和發言內容,透過這些吉光片羽的文字,相信讀者會受到某種啟發。
約翰·唐納蒂契John Donatich(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社長):“如今的社會,現代人還會墜入愛河嗎?”在我看來,這似乎是殘雪作品中的中心問題。的確,對于她這樣一位嚴苛的實驗主義作家,沉迷于這樣一個個人主題確實令人吃驚。但是如果這樣狹義地去解讀“愛”肯定會錯誤地理解愛情在其作品中的地位。在殘雪的小說《最后的情人》中,殘雪給我們的挑戰是在純粹的愛的努力中認識自我,讓自我響應愛的召喚,走在愛的滿足之前。宇宙的視野使這本書獲得了與國際化小說或者全球化小說相對立的影響力。我們每個人都只是一個欲望的系統,是地球村里的一個微宇宙,感覺自己是整個人類的原子的沖動,但是只能歸入一個更大的過程。殘雪要展示的是對人物生命的把握和掌控的不可能性,她尋求與靈魂的一種非傳遞性的關系,去釋放自我,卸下包袱,讓自己輕松,啟發自我。讀殘雪關于小說寫作的書比讀她的小說要難得多。感覺像一個哲學家在思考她的書:系統的,自省的,在一個封閉的系統里逼迫自我。殘雪自己說她的小說像哲學作品。她的小說世界遵循嚴密的邏輯。讀者必須對在生活中體會生命的方式保持敏感,對存在之流的感官享受保持敏感。殘雪將她對人類的展示置于兩種經典的哲學思維模式——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是西方解讀自我的兩種二分法模式中的一種精神平衡。但無疑,殘雪的作品是中國的。她采用了中國的物質主義,把對現實事物的愛與西方哲學的抽象結合在一起。
夏谷Goran Somardal(瑞典漢學家):殘雪在敘事中總是搜尋更虛幻又往往能觸及的魅力烏托邦,因此她的作品有著更具誘惑力的目的地。殘雪作品中的烏托邦,“無地”則是以完全相反方向運作的敘述力為特征。她的《從未描述過的夢境》沒有構建任何夢見的理論上由命定的幸福鞏固的王國。殘雪世界中的烏托邦意味著從“真實世界”,即歷史的“特定世界”中飄走,但是又沒有離開或沒有明確表示要計劃著離開。而是隨著世俗生命不可思議的可能性和潛能飄到在歷史之外或者歷史之下同時又奇怪地處在那段歷史里。殘雪兩本短篇小說集的前言的標題是“異端世界”,實際上殘雪是采用王國維用來探究詞的本質的原創概念來討論她寫作短篇的初衷。正如王國維的境界指的是藝術作品的內在領域,殘雪的世界不僅是想象中的,而且也是匪夷所思的世界,它也指這個世界而實際表象是作者成功塑造的結果。她的做法是糅合情與景,懸置而不是消除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所見與所想之間的界限。觸摸和描述感知與存在兩者之間的界限或者提供實際的或想象的認知不確定情景往往變成了小說框架中的關鍵的節點。從突圍表演開始,殘雪對她的小說人物的命名方法一直散漫,兩本經常被放在一起,視為一個系列的《最后的情人》和新世紀愛情故事,連同前面的突圍表演,構成了一個三部曲,這兩本書至少為我們提供了一條追蹤殘雪的烏托邦抱負的線索。通過這類別樣的命名策略,殘雪再一次為她的故事發展創造了一個“無地”,或者說,在她特別的文學作品中:一個烏托邦在她的故事中關聯,插入,彼此糾纏。簡單地說:“審美錯覺與指示錯覺的拓展不一致。”《最后的情人》的幾個例子中討論了閱讀活動、生活藝術、感知中的幻影角色及三者之間的關系,并給出了文學形式。殘雪把她的世界向運動開放,與中國和西方經典的烏托邦中明顯的靜止形成強烈對照。靜止是經典烏托邦概念的核心,該核心建立在對一種完美的永恒的假設之上,然而運動/旅行:“離開”構成了殘雪作品中的烏托邦元素的核心。殘雪的烏托邦不指無地,無名之地,而是指別處,別的地方。一種清晰的催眠的品質在這三部小說都存在,例如敘事與類似因果律的協商范式和事件發生的邏輯。比較突圍表演,愛情故事更像一章接一章寫成,比《最后的情人》更加連貫,看起來依然是個故事扎成的花冠,盡管故事之間本質上互相關聯,但是依然都可以看做獨立的小故事。
賀紹俊(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殘雪是新時期以來難得的一位具有獨創性的作家,也是一位其文學價值和意義沒有得到充分重視和肯定的作家。這次研討會是殘雪研究的破冰之旅,殘雪的研究將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殘雪以其獨特的個性于20世紀80年代登上中國文壇,但是,殘雪和當時紅火的先鋒文學代表性作家如余華、馬原、格非、蘇童等有著明顯的不同。新潮小說潮中的先鋒作家們是由外向內的先鋒,而殘雪則是由內向外的先鋒。前者的作品能夠看出明顯的模仿痕跡,而與他們自身的經驗缺乏聯系和溝通,也與他們所表現的對象有所隔膜。因此我把他們稱之為“由外向內”的先鋒。這就是說,他們最初是通過外部的直接效仿西方現代派來顯示先鋒的面貌的,也就是在外部效仿的過程中,他們內部的經驗才逐漸與之相呼應,現代主義的精神也才真正進入到他們的文學世界里。殘雪是從自我經驗出發,思考到了與西方現代派相似的主題,她所反映的現代中國人的特殊心理,如焦慮、恐懼、異化等,以及她所采取的心理感覺敘述,不期然地與西方現代派的敘述方式相重疊。殘雪現象之一,殘雪從內心出發應合了現代派的主題,并不容易被人們理解到。之二,誤以為殘雪就是從學習卡夫卡和博爾赫斯而走上先鋒文學的,于是一切都以卡夫卡和博爾赫斯為標尺來剪裁殘雪的創作,這反而掩蓋了殘雪的獨創性。之三,殘雪的創作在前后期發生明顯的變化,后期的小說更加具有理性。這就是因為殘雪“由內向外”,進入到自覺向外部的現代派學習,在創作上理性意識更明確的緣故。殘雪的“內”既包含著她的文化積累,也包含著她的生長環境和文化性格。比如,江濤論述了湖南亞熱帶氣候的獨特“霉味”是怎樣轉化為殘雪的審美風格的。
近藤直子(日本大學文理學部教授、漢學家):人不可能道盡自己想說的所有事情。文學創作也正因如此,才被延續至今。到底人自古至今都想寫些什么呢?我認為想寫的那個東西一定連接著希望,或者確切地講它就是希望本身。大多數人還是希望比現在更好,更美,更真實。人希望自己更美一些,這絕非是一件羞愧的事。由于存在于自身中的主人與客人這兩個對立主體的相互爭執,使我們個人開始運動,人類以及世界也因為運動而生機勃勃地選擇未來。在此我想重新考慮文學和個人的關系。從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到殘雪和卡夫卡,我講過很多的作品,也講過各種各樣的世界名著。禪宗的臨濟錄里面有這樣一段:“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為什么逢佛就必須得殺佛?其實那是為了賦予佛生命。如果你只是看到了佛,就將這個只有外表的佛擁戴在心中,再或者不加思考地直接接納自己看到的佛,那么你只會變成佛的仆人、門生和奴隸。你只會將佛的話現學現賣,無論遇到任何事,你只會永遠尋求佛說了些什么,完全變成一個沒有自立性的人。所以,如果想尋求對自身而言可稱之為真理的佛,就必須“殺掉”隨處可遇的佛。如果你在路上跟曾在白紙上寫下心目中的有名無名的大作家碰到了,不要猶豫馬上就殺。于是在那之后,你本人就成為了對你而言的佛。請你不要成為奴隸或隨從,而是成為立于潔白紙上,并在正中心的自由人。
泉朝子(日本《殘雪研究》雜志編輯):《我在那個世界里的事情——給友人》寫出來的是在本能支配之下,感性和理性結合而實現理想的過程。這篇小說也可以說是一篇詩歌,仿佛這篇詩歌好容易才成為了小說。感情的洪水吞下去時間、場所、人名等等,能夠幫助讀者把握小說內容的所有線索全部都被感情的波濤沖走,讀者好像走在迷宮里似的。但是盡管如此,這篇小說所具備的美麗仍屢屢打動讀者的心。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為讀者最終也能通過小說受到啟示和幫助,看到了被本能支配著的美麗的心理世界。這篇小說是一個心理觀察記錄。有一天感性突然看到了理想,但感性錯過了傳達給理性的機會,使理性沒見到或意識到理想的存在,所以只有感性有了追求理想的欲望。感性一個人在為追求理想又無法實現而掙扎的時候,親戚們為幫助她,綁住主人公的手腳,還將她關在破廟里,讓主人公徹底體驗到絕望和危機的存在。同時也讓主人公體會到了本能的存在,本能總是在主人公受挫的時候通過親戚給予主人公提示。雖然感性在一步一步接近理想的路上荊棘叢生,但最終主人公還是成功突破了冰凌的世界和理性“牽手”,理想也終于會被實現吧。
殘雪的小說既描寫的是自己,又具備普遍性。不僅將人的心理細節觀察入微還記錄下來。對一系列心理活動中的這個主人公(感性)進行觀察的人是誰?是殘雪嗎?當然可以說是殘雪,因為是她創作了這篇小說。但讀了殘雪的小說后筆者還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就是,小說的一半出自于殘雪,小說的另一半則出自于本能,這個本能是指一種生存的力量,這個力量存在于每個人的身體和精神里,這個力量只是借助殘雪的筆和文字顯現在我們讀者的面前。
鄧曉芒(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凡文學以沖突為第一生命,但沖突有不同的境界,表現為不同的主題,這些境界和主題可以獨立出現,也可以重疊出現,每一種均可達到自身的極致,但相比之下亦有層次和深淺之別,計有如下四層或四大主題:一、現實與現實的沖突,凡現實主義作品均以此類沖突為主題,主要以情節取勝;二、心靈與現實的沖突,將主觀感受帶入情節和題材中,一方面反映現實,一方面抒發情感;三、心靈與心靈的沖突,主要表達精神的復雜關系,常見于心理現實主義作品;四、心靈與自身的沖突,主要表達心靈的內部矛盾,個人主義的精神困境,常見于現代派作家,在中國以殘雪為代表。四個層次有時可以混合、互補,但總地來看呈現出一種歷史趨向,即從第一主題越來越走向第四主題,而第四主題也可以反過來成為揭示前三種主題的隱秘動機的視角,如殘雪的文學評論所做的。
迄今為止對卡夫卡的最深刻的解讀是中國當代作家殘雪的解讀,她在《靈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一書中對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做了一個全景式的系列評論。這些評論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把卡夫卡的每部作品都看作卡夫卡自己的創作談,把其中的各種人物都看作卡夫卡內心靈魂的各個層次或要素的體現,而把那些撲朔迷離的情節和動作看作靈魂向自身內部的不斷深入、向精神的理想目標的不斷接近。關注心靈的自身沖突的作家,在中國是從魯迅開始的。殘雪則是直接繼承了魯迅的這種自省精神的極少數當代作家。而且,由于受到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她的作品擺脫了魯迅那種被迫和消極的黑暗思想,而成為一種進取性的創作源泉。可以說,殘雪所有的作品的主題,都是這種心靈自身的內部沖突,就連她的文學批評都是如此。迄今為止只有殘雪自覺地運用了這種視角來分析和評論了文學史上那些巨匠們的作品,這些評論都是以她自己特有的文學眼光即心靈的自我沖突來展開的,而且不用瞄準,一擊便中,揭示出了這些作品中的“魂”。現在,當我們立足于現代文學的主題來看待整個文學史,我們會突然有種徹悟,我們會看出,心靈內在的自我沖突其實正是一切文學的本質。
譚桂林(南京師范大學教授):30年間,她的小說演繹著的心理制式與思維定性,已經被讀者十分熟悉,而且也曾被殘雪自己不斷復現,現在她終于從所謂“中國式的噩夢”中突圍而出,以一種優美灑脫的姿態顯現出她的精神結構的新的向度,靈魂世界中新的質素。這種新的精神向度與靈魂質素,可以用兩個詞語來概括之,一個是夢想詩學,一個是魅性抒情。前者的意義主要體現在殘雪自身的變化,而后者的意義則不僅是殘雪自身的,而且對中國當下文壇的變局而言,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啟示性。
殘雪的小說以寫夢著稱,這不僅是指她常常直接以人物的夢境嵌入小說的結構之中,使夢成為小說敘事的工具與手段,而且是指她的小說氛圍、情節構造,往往本身就是夢境,人物的語言本身就是夢囈,就是譫語,夢幻與現實化為一體。這種夢性敘事的特色,在《邊疆》中依然故我。《邊疆》在本質上與《黃泥街》一樣,歸根結底乃是作者靈魂深處的夢的再現,或者說是人類某個時代的夢在作者靈魂深處的固結所在。不過,《邊疆》敘事的主體色調與溫度與《黃泥街》大不一樣。《邊疆》中的夢性敘事中出現了一些早期作品中少見的精神質素。在殘雪早期創作中,體現出蓬勃生命力的往往是自然界的惡丑生物,在《邊疆》中,不僅人的生命力得到了張揚,而且人對自身生命力的美好與崇拜也得到深刻的體現。過去殘雪的夢性敘事多受弗洛伊德影響,所以,夢魘多為怪誕變形,是人性本質的異化。而《邊疆》中的夢性敘事則更接近巴什拉的形而上學,夢想趨向光亮溫馨,自由創造,成了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在《邊疆》中,或許正是夢魘的遠去,夢想的展開,終于將殘雪內心深處的抒情沖動釋放出來,得到盡興的、淋漓盡致的發揮。殘雪堅定地走向抒情,但也堅定地保持了她自己一以貫之的晦澀含魅的風格。所以,《邊疆》面世的意義還在于,殘雪把文學的抒情傳統與自己的含魅思維糅合在一起,為中國當代小說創作提供了一種新的抒情方式。我把這種方式命名為魅性抒情,在《邊疆》中,這種魅性抒情鮮明地體現在作者的抒情內容上。無論是夢想詩學的建構,還是魅性抒情的轉型,在我看來,都根基于殘雪對人性的可能性的始終如一的關注。
敬文東(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無論是從袖珍人類史的體態、面容的角度,還是從袖珍人類史對關鍵細節苛刻要求的層面,我都愿意說,殘雪女士寫于1988年的長篇小說《五香街》,正絕好地符合袖珍人類史各項指標的要求。說《五香街》是一部袖珍人類史,倒不是因為它的敘事人在行文中不斷戲謔性地提到過“歷史”“歷史進程”“歷史作用”“改變了歷史”……等撩撥人心的語詞,而是說,它確實在神神道道的敘事結構之內,將幾乎所有關鍵性的歷史細節全部匯聚在了《五香街》當中,并通過敘事行為產生出的奇異的化學反應,揭示了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重大問題;《五香街》既合乎邏輯地充滿了感性(因為它首先是小說),也必然性地具有了高度的抽象性(因為它同時也是概括性的史書)。在《五香街》中,歷史的恍惚性正好構成了歷史的重大問題或重大主題之一,恰好是袖珍人類史和袖珍人類史敘事必須關注的重大問題。所謂歷史的恍惚性,不過是指歷史在自身看似謹嚴的秩序中的不斷搖擺,像吃了搖頭丸一樣。《五香街》通過它詭異的敘事知會我們,歷史遵循的主要規律甚或唯一規律,其實就可以被比喻性地稱作搖頭丸規律。和通常的史書不一樣,作為袖珍人類史的《五香街》,是通過象征而不是仰仗紀實,才完成了它的袖珍人類史身份。從表面上看,《五香街》中匯集的所有關鍵性歷史細節都荒誕透頂,惟其荒誕到極致,才處處體現出它對現實境遇、歷史境遇具有近乎照相般的真實性和說服力。和一切號稱以寫實、紀實為務的作品截然不同,《五香街》在本質上是一種形而上學式的寫作。這種寫作方式的最大特點,就是對事物變動不居的表面不屑一顧或深懷疑懼,傾心向往的,卻是事物的深層結構——它致力于從歷史主義看來無物常駐、變動不居的事物當中,尋找支配各種易于消失的事物的那個巋然不動者、那個恒常恒新的本質。反諷在《五香街》中更具有本體論的色彩。仰仗這一絕技,史官先生才有能力透過無物常駐的事物表面,深入到事物的核心部分。
唐俟(文學評論家):讀殘雪的《思想匯報》,筆者想到了大畫家畢加索,以及和他同時代的二戰“惡魔”希特勒。畢加索的蠻痞本性只向身邊的女人發泄,他對藝術創造的熱愛使得他健康長壽;而希特勒疏遠了藝術,通過政治和戰爭向人類施暴,他是誤入歧途的。殘雪之所以成為創造奇跡的能手,是因為她念念不忘死,時刻“畏死”:“藝術家的邏輯就是通向死的體驗的邏輯。”這種死里求生的運動,能使自己進入“熱情的解脫了常人的幻想的、實際的、確知它自己而又畏著的向死亡的自由之中”。這種自由就是藝術創造。殘雪曾談及自己“是一個愛世俗愛到狂熱的人,但世俗又令我憎恨自己,所以我必須通過升華到另一個世界來實現我的世俗之愛。”藝術家只有借助于自己的原始欲望和對世俗的憎恨,才能升華到“另一個世界”,做出真正的思想匯報。藝術創造類似于生命的孕育生殖,是以孕育語言為目的而由理性堅守著的感性發動,創造者必須與欲望拉開距離而遙控欲望。殘雪感動于自己的發現,如果一個人自己將自己變成了地獄(看到本質了),她也可以由自己進入天堂:她通過藝術創造打通了天堂和地獄,讓自己“永遠沉浸于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
王迅(《南方文壇》編輯部主任):在當代中國文壇,殘雪的創作無疑是一道獨異的風景線。而要真正走進殘雪世界,領略風景內部奇花異草的神韻,我們必先排空先入為主的閱讀經驗,擱置固有的傳統小說觀念。與傳統敘事相比,殘雪小說也是在講故事,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講故事,也不是在文化層次上尋找敘事資源,而是講述人類靈魂的故事。但殘雪對靈魂與靈魂之間的關系并不感興趣(比如史鐵生的寫作),她的小說是對靈魂世界更深層次的勘探。殘雪的好奇心驅使她把筆觸探入靈魂內部,試圖在繆斯現身的瞬間捕捉靈魂突圍的真實圖象。因此,從靈魂自身內在結構出發,讓靈魂自我分裂、自我搏斗,實現對自然結構、藝術結構和哲學結構的深層洞察,就成了文學賦予殘雪的使命。在殘雪看來,精神具有無限的層次,每個人物都是靈魂層次上的一個代表,“最高層次上的人物都是邏各斯(理性)”,但人物精神并不限定于某一層次,而是處于某種翻滾和流動的態勢。因為殘雪的人物建構所遵循的是邏各斯與努斯(原始之力)的同體化原理。某種意義上,殘雪的小說就是邏各斯與努斯之間馬拉松式的角力表演。但這個機制并不表現為木偶式的機械表演,而是在一種詩性的結構中發生作用的。那種靈魂直面虛無的冒險之旅,在反復曲折的折騰中最終沉淀為詩的結構,哲學的結構。那是精神冒險之旅,也是靈魂受難之途,無論對作者,還是對讀者,無不如此。在殘雪看來,這是“詩”與“思”在靈魂內部融合、裂變的過程,也是藝術自我走向虛無圣境的必要途徑。
那么,具體操作中,作者如何能有效地撥動那些最隱秘的“弦”呢?在閱讀中我們發現,人與自然的深層碰撞與強力交合是作品詩美生成的主要動力裝置。長篇小說《邊疆》就是人與自然強力交合的產物。
彭文忠(湖南商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殘雪的“詩性言說”得自于中國文學及其批評的詩性傳統的遞傳與影響。在殘雪創作與批評中,人的主體精神的高揚,從主觀意愿出發,重個人體驗直覺、感受,重心靈交流超強的藝術想象,較少考慮生活自身的特點與邏輯。我們能鮮明地感受到中國文學創作與批評詩性傳統的“魂兮歸來”。殘雪小說是一種詩化小說,這種詩化首先源自于“感覺化”:殘雪不是在講述故事,她所表達的是她自我的感覺,對生活、對藝術的主觀感覺和體驗;不是為了在現實生活中尋找意義,而是對自我靈魂進行反省;更不是對現存世界進行客觀理性的描摹或判斷,而是進行一種主觀感性的體驗和創造。殘雪專注于內心體驗和對超現實世界的感知的表達,為殘雪作品帶來詭異、空靈、詩意的美學風格。殘雪的小說是一種詩化小說,與其作品中超現實物化手段的運用和繁復神秘的意象體系的營造亦有著必然的聯系。詩性對于殘雪小說來說不僅僅是一種文體特色,是一種思維定勢,而且還是一種內在精神。殘雪以對中外經典文本的閱讀介入中國文學批評,與她的文學創作一樣在當下是一個異數。她從個人體驗出發,極少參照前人的解讀經驗,以超強的藝術想象對作品進行“再造”;但另一方面她又試圖回到理論言說的軌道上來,期望能把握藝術的本質特征。以大量隱喻性意象營造其詩的意境與詩的語言是殘雪批評常用的方法。殘雪采用了對應、整合和詩性思維的解析方式,她不打算對作品的形式因素進行肢解,而是以整體性思維來框定某部作品,用一種終極眼光直抵靈魂的底線。閱讀殘雪的詩性書寫,我們能清晰地看到殘雪在藝術生存的層次上追尋“自我”的足跡。殘雪始終在一種充滿神秘詩意的、富有中國特色的旋律中深情呼喚一個真正的、現代的、藝術的“人”。
羅璠(長沙理工大學文法學院教授):殘雪自她的小說傳播以來,便有東方的卡夫卡之稱譽。對殘雪與卡夫卡小說內在的相似性和相異性作出較為全面的揭示和闡釋,此項工作還遠遠沒有進行開來。殘雪十分強調自己寫作方式的獨特性,“潛意識寫作”是她對自己小說創作方式的命名。潛意識寫作作為一種玄想,與卡夫卡的“妙想”“黑暗幽靈”等創作理念達成了某種默契。在對人性的展現與反思方面,殘雪與卡夫卡都站在同樣的平臺上,即對遮蔽的存在的揭示,對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詢是他們一致的小說精神。卡夫卡在文學領域從被遮蔽的存在那里開始了對存在的探詢。她的小說完美地揭示了人的異化和孤獨處境。殘雪則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罅隙中無情地撕開了一道口子,極力揭示被傳統文化厚重的帷幕掩蓋、歪曲、壓抑的人性本源,召喚在荒漠中、曠野里孤獨地游蕩的靈魂。當殘雪和卡夫卡的靈魂在現實生活的掙扎中裂變成藝術家的時候,就開始了將生活藝術化的生命歷程。對卡夫卡來說,生活的藝術化(將寫作作為內在生命的全部),讓他失去了愛情和健康,卻摘取了現代主義小說藝術的王冠;對殘雪來說,生活的藝術化(執著于潛意識與靈魂寫作)不但讓她成為了中國最獨特的作家,也成為了現代藝術的守夜人。殘雪以對卡夫卡作品的解讀來完成對卡夫卡的理解,在某種意義上,她是卡夫卡小說的共謀者,在純文學的美學范疇中,完成了卡夫卡的作品。
吳投文(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在中國當代文壇,殘雪是一個獨特的存在。殘雪一直標舉“純文學”的文學觀,在“實驗文學”的路徑上進行深入的探索,她的作品就是“實驗文學”的有效實踐,是為“真正有精神追求的高層次的讀者而寫作的”。一個首要的問題是,殘雪文學觀的核心與實質是什么?她以一個小說家的身份,以自覺的理論意識,以特殊的文體形式思考文學的深層問題。這體現在她大量的讀書隨筆中。殘雪對卡夫卡、博爾赫斯、但丁、莎士比亞等偉大作家所做的文本分析是非常透徹而充滿個性的,迥異于傳統的批評模式。她往往從自我的觀察視點切入這些作家的深層精神結構中,她的文本分析同時也是一種孤絕的精神突圍,與她自己的創作具有對照的意義。因此,她的這些讀書隨筆所呈現出來的全新闡釋具有一種幾乎駭人聽聞的驚悚效果。這實際上是她另一種形式的小說創作,她不滿足于對這些作家進行言而有據的注釋,而是在對話中延展出自己對文學的深度理解,并進而呼應現代性語境下人類靈魂的普遍掙扎。就此而言,她的這些讀書隨筆具有“改寫”的性質,但此一“改寫”并非靈魂的盲動,而恰恰是靈魂的生長和對大師們的精神呼應。殘雪的文學觀具有非正統的性質,或者說,她的文學觀沒有封閉于在自身的文學傳統之中,而是著意在現代性視野中對接西方文學的先鋒特質。殘雪把自己的表現對象明確定位為“深層現實”,這表明她對社會現實的觀照有自己的獨特視角。她的創作敏感全部凝聚在人類精神世界的混沌與幽暗上。殘雪把現實中的具體真實轉化為荒誕中的抽象真實,無疑具有放大的效應,更能透視人物生存的悲劇性。在殘雪的文學觀中,“深層現實”和“純文學”緊密聯系在一起,這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構架。經由“純文學”的路徑探測“最普遍的人性”,這恰恰是殘雪創作的水到渠成之處。
俞世芬(杭州師范大學副教授):殘雪在成長過程中所接受的文化資源和立足的文學背景具有某種跨文化的特征。誕生于80年代的殘雪小說,無論是在對生命體的物質與精神形態的同等重視,還是對生命的有限性進行超越的理念,以及對人的精神結構的復雜、多層面的揭示,既顯示了她與西方生命哲學與生存哲學等詩化哲學之間的關聯,也顯示了她與中華血緣與母語文化傳統之間割舍不斷的內在關聯。殘雪通過身體與靈魂兩個維度,對中國傳統的文化人格進行了現代審視。殘雪小說中呈現的對傳統文化人格的懷疑進而企圖加以反撥,確立并倡導自由開放的現代人性的努力給讀者帶來了強烈的震撼與啟發。殘雪借早期作品完成的是對有關中國文化負面的核心問題的犀利批判。這種批判首先落在傳統文化中建基于血緣的人倫關系上。批判的鋒芒同樣指向典型體現了傳統文化功利特征的道德。面對已上升為公意倫理與集體意志的道德理念,殘雪以還原世俗生活粗鄙的本來面目為手段,展示了現實生活的復雜性。殘雪以“情欲”為介質,用超現實的筆法揭示出的恰恰是最為真實的人性。在批判與重構中,殘雪確定了現代文化精神的內涵。殘雪塑造的最為經典的人物形象便是這樣一批“異質形象”,這種異類已由個體形象逐漸發展成為群體形象,顯示了作家對人性思考之后的正面引導意味。值得注意的是,在塑造此類形象時,殘雪并未將其與傳統文化人格截然分裂與刻意對立。相反,在表現人物努力開拓生命境界的同時,她充分表達了這些異類回歸現實、向原初的生活狀態靠攏的態勢,從而揭示出其本身固有的精神劣根性。對于人生的虛妄這一難題,殘雪的解決方式是藝術。通過“新實驗文學”的提出,殘雪實際完成了關于文學本質與功能思考的理論提純。
羅如春(湘潭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殘雪的小說書寫具有拉康所謂的無意識的語言結構。殘雪以深層理性悖論性地監控著其無意識的自動寫作。殘雪小說的寫作主體深深地沉入現實,將日常經驗積淀為準先驗的形式,這種準先驗的主體是沒有實際內容的“空白主體”,它不能規范非理性層次的思考,但是卻能夠超越非理性,成為非理性的支撐點,使得殘雪的寫作成為仿自動寫作而非盲目寫作。換句話說,“空白主體”并非虛無,它在“自觀”的層次上有著形式的絕對性,但對于客體卻不能形成絕對命令,它發揮著類似康德主體先驗時空形式的功能,在寫作中將內在的無意識材料不斷納入到“空白主體”之中,形成格式塔的內在變化結構。殘雪的小說書寫與拉康精神分析暗合之處頗多,往往可以成為后者的樣本,成為殘雪精神從想象界、象征界向著實在界竭力突破的象征,或者是實在界呈現給象征界的一個個無法痊愈的傷口。
唐偉(北京大學博士后):殘雪一系列充滿著噩夢囈語的小說,故事情節荒誕不經,精神指向飄忽不定,小說意象怪異多元,時空場景錯亂晦暗。縱觀殘雪所有的小說,其中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詭異現象是,她的小說幾乎到處都充斥著形形色色的動物形象或動物元素。而有意思的是,與常規小說習用的擬人修辭背道而馳,殘雪特別喜歡將小說人物的形象或動作“擬動物化”,或者說形象和動作擬動物化的人物,與小說里的動物其實是處在了同一平面,并沒有主次之分。對于殘雪小說的動物敘事,恐怕很難將其徹底還原到一個理性的邏輯層面上來理解,這正如殘雪自己對藝術的理解那樣,在她看來藝術本身就是不可思議的。殘雪的小說藝術是一種現代版的“創世紀”,殘雪一再在她的小說中表達對世界的排斥與否定。她小說中的人物,大多承擔的是符號意象的功能,是一種人格分裂的存在,或是某個抽象觀念的軀殼,多種欲望的集合體。殘雪的小說藝術之所以念念不忘“自我”的迷津,說到底,是根源于她對人性復雜的深刻領會。殘雪主要通過動物敘事和夢境構造來抵達深層次的人性“自我”,事實上,殘雪這種現代版的“創世紀”仍是依托于東方文化傳統的現實語境,這即是說,她有意摒棄了那種已確定的秩序和諧的文化為寫作價值取向,走向了充滿不確定性的自由,同時也是走向了一種分裂、掙扎的動蕩不安。
卓今(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殘雪是目前僅存的繼續進行先鋒寫作的作家。她的作品結構復雜,信息密度大,內涵豐富,讀者面對這種“向內”的思維模式,理解起來有一定的難度。晦澀難懂的意象,迷宮式的結構,加上詭譎的情節,陰冷的基調,變形夸張的人物形象和“夢魘”“荒謬”的環境。她的作品基本上傾向于表現這種精神困境、異化和藝術沖動,很多習慣閱讀現實主義作品的讀者遇到這種表現手法會出現閱讀障礙,但反過來,這種“有難度的閱讀”反而又激發了讀者挑戰的欲望。如果說一個文學文本的意蘊可分為“本事意蘊”和“審美意蘊”兩個層次的話,在殘雪小說中,本事意蘊(形象、故事、現象層本身固有的客觀意義)是不明朗、不確定的;而審美意蘊所引申出來的象征、隱喻、暗示更加飄忽不定。讀者常常經由本事意蘊進入審美意蘊,這樣一來,就等于由確定進入不確定,難度可想而知。在這種意蘊交叉,歧義叢生的情況下,同時要關照到表層與深層結構,以及文本內在的多重層次,不可避免地要經由“視野變化”或者視角轉換。殘雪的小說中大都存在著這樣的結構,“本我、自我、超我”這三種力量的角逐。這其實是一種不錯的分析方法,容易快速進入殘雪小說內部。從本事意蘊進入審美意蘊實際上要經歷三個層面:感知層面、體驗層面、理性層面。真正讓文本產生多義性的,是意象并置造成的隱含意蘊的平行結構。在殘雪的大量作品中,社會秩序,物質生活飄浮在表層,而難懂惡、丑的印象,恰好也是人性心理結構的里層,殘雪作品的意象所喻示的真正的意義正好與此重合,從這里發現人性,了解心理結構,把精神層次進行多級細化。結合現實意義,揭示每個個體的自我意識覺醒過程,發現靈魂的構造,以此提升人的精神層次。
(作者單位: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湖南省文聯)
本欄目責任編輯佘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