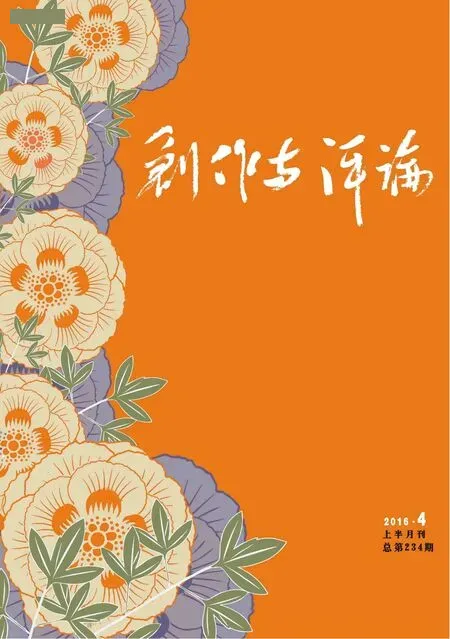“類型”反轉如何傳動歷史反思
——讀潘小樓《喀斯特天空下》
○梁盼盼
?
“類型”反轉如何傳動歷史反思
——讀潘小樓《喀斯特天空下》
○梁盼盼
如若揣測修習電影對潘小樓創作《喀斯特天空下》最突出的助力,我會猜想是類型敘事的著意運用。一個面臨生命與生活中新舊蔓生的多重焦慮的男性知識分子,在女兒陪同下走上一段回鄉之旅,這一敘事類型溫情而不乏挖掘深度,其間敘述節奏把控得當,溫度合宜。但更為核心的,是對“類型人物”的有意塑造與使用。詹優優這一人物顯見是類型化的——她的夸張、乖覺與叛逆,她的活跳跳,她完整統一、自成體系的“網絡語言”或“動漫語言”,她那莊嚴與戲謔并存的儀式化的行動。后二者幾乎形成一層包裹著這一“叛逆少女”與“網絡原住民”的硬殼,一張難以滲透的薄膜,加之其父詹嘉民眼中她的“鈍感”,正如小說點明:“真的像一具眼神空洞,沒有靈魂的玩偶娃娃”。詹優優如此夸張的存在形式也許意在暗示,與其構成對位、形成了她身處故事的敘述體系、作為小說中心人物與主觀視角承擔者的“詹教授”,或同樣是個“類型人物”。
大學中文系教授詹嘉民59歲,面臨退休,生涯與生命漸至末途的焦慮推逼其出現心身癥狀——耳痛。此外,他有著忽視母親生前身后事的愧疚,與女兒存在隔閡、并可能因后者即將出國無法修復父女關系的焦慮,以及被迫背離鄉土的怨念。諸多焦慮癥結,以及小說中,他那幾乎一刻不停的反思與抒情敘述,使這一人物內心滿盈,或者,更具“靈魂”。然而,這位現代知識分子、現代小說中常見的反思與審美主體,其“靈魂”并不因而較詹優優更具“個體特殊性”。小說刻意以一種極為標準化、極度潔凈、優美而詩化的語言去敘述這一人物,包括其內心的自述。這種標準化體現在:在這個返鄉——尋鄉的故事中,詹嘉民自身的語體并無方言色彩。甚至在母親的安息儀式中,在母親在故土的棲息之所——地下溶洞,他看到的,是“正午的陽光直射進來,光束像豎琴琴弦一樣真實”——這世界性、藝術性卻最無“地域性”的意象。這種“潔凈”體現在:詹嘉民的“身體性”降到了最低限度——欲望與感官書寫幾近于無。而優美與詩意最能見出于散落于小說各處詹嘉民對時光的感喟:斜照進二樓梯形教室的“南國五月的陽光,是看得到的清潤,所有的一切,輕盈又易碎,他心里涌起迷霧一樣的傷感”;間隔的時光“透明得如同陽光下蜻蜓的翅膀”;而“極致的美好總讓人傷感,它是光,是風,是羽毛,是天空之下穿越白晝和星夜的飛翔,沒有什么比這更能讓人感覺到時光的沉重,也沒有什么比這更能讓人感覺到時光的輕盈,而你知道它終將破碎。”這些意象格外的纖細、精致、美好、脆弱,簡直近乎“女氣”——這并不意味著詹嘉民是位“娘娘腔”,但你需到小說里發掘,這位“男性知識分子”因何具有了那種因封閉而極度傾注于自我而形成的、敏感、纖巧而脆弱的、被稱為“閨閣氣”的審美特征。
詹嘉民感傷于對鄉土的背離與失落,甚至對攜他離鄉的母親不無怨懟。事實上,最能見出他對鄉土的疏離的,正是他在返鄉——尋鄉過程中對鄉土的指認與呼喚。一路車程,他辨認著故鄉的地界:“右江河谷沖積平原”與“喀斯特地界”。接受與使用這現代地理命名意味著他置身于一個普遍性的知識與空間體系中去返觀這鄉土,意味著他已脫出、遺忘甚至拒絕“舊日”或“傳統”中鄉土自我認知的信仰文化體系,包括其中的人情與人倫關系,因而,他才長久地漠視與遺忘了母親或有入土為安的愿望,他對祭奠葬儀的疏忽漠然才引發堂表弟嘉慶的不豫。這一真正的背離,并非發生于他跟隨母親離鄉的一刻。
詹嘉民的返鄉之旅始于對市航道局的重訪。這一設置與書寫真正見出身為“80后”廣西作家的潘小樓的特異與過人處。這個零碎而頹敗的大院,顯見區別于“現代”得更為純粹的“南寧市國際會展中心”,是除“喀斯特地界”外小說中別具歷史意味的特異空間。事實上,在潘小樓筆下的廣西,這些昔曾輝煌現今衰敗的“單位”,至少是與由紅土、河流、深綠發藍的植物、白亮日光與濕黏空氣構成的村落與自然同等重要的空間與象征物。這些空間的敗落是過往別一種現代性的敗落,然而在潘小樓的小說中,這其中氤氳的并非是《鋼的琴》式的倫理溫情自我救贖,而是荒誕與魔幻:那是詹優優歡呼雀躍的“德古拉伯爵古堡的調性”;在《秘密渡口》,那是趙爾克腳下綿延直鋪到廠區盡頭的灰粉,而在昔日現代性工業遺留的塵埃中,在與廠區連成一片的田野、河流與碼頭上,昔日的工廠工人獨自狩捕著傳說中的水猴。這也許“說明”潘小樓的“80后”調性:她感覺到歷史的荒誕卻并未直接承受歷史的重壓。然而,這同樣“說明”廣西的邊緣性:在這里,這些曾經的現代性空間,從未如在工業重鎮或政治中心那般承載著如此清晰的歷史意義,因而在其傾覆動搖時,也并未帶來如此嚴重的精神重創。荒誕的“淺度”(深度),恰說明作家把握了在“我們”/“他們”——這特定群體中歷史呈現自身的準確方式。
言歸正傳。航道局這一空間的重要性在于:知識分子詹嘉民并非直接從鄉土中脫胎而出,他曾以附屬與零余物的身份尷尬寄生于這單位空間中(作為在職工人的繼子),而后依靠更為窘迫的手段,勉強躋身于單位體制內(到人事處靜坐,以“子承父業”)。依靠那個年代對“知識”(重新命名與指認的“現代知識”)的重視與相應機制的建立,他得以跳出單位體制,獲得新的社會位置。在此過程中,他遭遇了一個創傷性事件:他暗自愛慕的、“對面樓扎長馬尾的姑娘”被“工會主席老婆”拖到“歷來用作集會場所”的籃球場示眾,姑娘為此投江自盡。他趕到江邊看望送別了姑娘的遺體,那死亡的情形極大地沖擊了他的心智感官,迫使他關閉了自己部分的身體感知能力——對女人氣味的嗅覺。這次使他失落/壓抑了部分“身體性”的創傷性事件,必然也使他更為清晰地指認了單位體制與空間及其中人際關系、社會生態的“前現代”“封建性”“非人化”。你可看到詹嘉民始終小心保持在此方向進行批判與反思的能力:甫一退休,對公交車上擠得像沙丁魚罐頭的人們,他竟生起羨慕來,“心想至少他們還在社會流水線上運轉啊。這想法一完形,即刻讓他對自己感到厭惡。他這一代人,總習慣性地把自己當成顆零件,一旦被卸下來,便無所適從。而要他承認自己在精神上無法自主,是不行的。”
需看到,懷抱自主想象的詹嘉民批判與剝離的并非僅是舊有的社會束縛與人際關系,而在事實上幾乎疏離于一切群體與個人。那次直面死亡的經驗使他逃避一切相關的事件與儀式:他從不參加告別式和追悼會,暗自察覺一切的母親,甚至在最后時日,暗中早早將身后事安排妥當,以“盡己所能,來延長他在世間的安樂”。而關于死亡的儀式,既關乎生者與死者的關系,也關乎生者如何共同面對死者的死亡,如何在死者死亡之際、之后延續交往關系,如若不是詹嘉民有著強烈而自然的“現代個人獨立自主”信念,怕不能如此斷然拒絕。然而,這也使詹嘉民失去了在儀式中、在與死者的關系中、在與生者的交往中理解領悟終將到臨的死亡的機會;這也使他的母親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在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時,得不到支持與慰藉——“她一個人跟外人安排身后事的時候,井井有條中該是有多凄惶”。在女性身體上面對死亡的經驗使他關閉的對他者/女性的感知能力又何止氣味感官這一種:你要如何把“躺在身邊的又一個女人”看成“一具人形硅膠”?僅是氣味的缺失么?還是通過“視而不見”她的“靈魂”?對前妻張曉、女兒詹優優,他并不真正洞察她們的內心,只是困惑也厭倦于她們的戲劇性,并驚詫于她們對他的洞察力。更進一步說,他對他者/女性內心的漠視同樣作用于他的母親,于是在母親逝世十余年后,在自己同樣感知到死亡終將臨近之后,他才意識到母親當年獨自面對死亡的孤獨與凄惶,才感念到為求得兩母子的生存背井離鄉的母親,或會有埋骨故土的愿望。
也可以說,正是作為獨立、疏離的個人,現代知識分子詹嘉民才如此輕易又截然地疏離于鄉土:他并不費心重訪與系結與鄉人、親人的聯系,因而也就疏離了鄉土文化與信仰的語境。
于是,我們有了一個地域性與身體性降到了最低限度的知識分子詹嘉民,一個極度困囿于個體自我范疇內,退縮于內心,“敏感、矜持、自負、冷漠”的現代個人詹嘉民。因而,這一人物的表面的“去個性化”與“類型化”,指向的是支撐這一人物類型的意識形態的特征與弊端,是形塑這類型人物的歷史、社會與文化機制。
正因如此,當居于詹嘉民對立面的詹優優向我們吐露內心,便超出了尋常的“戲劇反轉”與“人物深度挖掘”,具有了哲學與精神分析意味。先是COSPLAY概念對“玩偶娃娃”的反轉——詹優優聲明:“這你就不知道了,COSPLAY分兩種,一種有原型,另一種是DIY。我呢,既不崇拜誰,也不想變成誰,我是后一種。”更重要的是對“空洞”的反轉。與其父相似,詹優優也有一次直面他人死亡的經歷。她夜闖墓園,去了靈骨塔,一個與己同歲的小男孩的遺照引起她注意:
“其實我只是想知道,如果他還活著,長到我這么大,他會怎么看世界。說來你可能不信,自從藍精靈公仔擺在我床頭,我每天見過的人,做過的事,印象會特別深,之前我是不在意那些的,它們像鉛筆畫,時間一長就被擦掉了。但現在像有人用鋼筆給它們描了邊,是那樣一種重影。他像是在透過我,去繼續感受世界。我每一天的經歷和感受是雙份的,甚至還要更多,像牛軋糖一樣扎實!”
這段自陳將“內心空洞”的意義翻轉:空洞可以意味著空間與容積,擁有空洞的內心如同一個容器,可以容納他人的苦痛,甚至他人的視角與感受。這并不意味著這是他人對我“反客為主”的取代與占據;自我并未消失,而是獲得了更復雜的視角、更活躍敏銳的感受能力。經歷這兩次反轉,當詹優優在旅程中逐漸除去“哥特洛麗塔”裝扮,換上山村少女的白底藍花裙,與詹嘉民共同立在地洞口,眼神中詹嘉民“在母親眼里看到過,在張曉眼里看到過”的“順服與獨立”就并非是“女性群體特征”或“家族共同特征”的顯現,而出自她對這兩個女性的感知體認達成的的新的自我狀態——“她就仿佛在這一瞬間長大”。
詹優優向我們展現了一種新的自我構型:不同于詹嘉民需通過疏離于他人、通過退守、閉塞內心保持自我的自主與穩定,詹優優的自我更富彈性而開放,通過對他人經驗視角的接受、想象與融合變化生成新的自我。“空洞”概念的翻轉與結構隱喻尤讓人聯想到精神分析女性主義對作為女性心理結構的“內在空間”的設想——或許這正是滋養了這篇小說寫作的秘密資源。然而,需強調的是,潘小樓并非在寫作一個關于自我的“男性結構”與“女性結構”的故事,并非在陳述“女性自我”相對于“男性自我”的完善度或倫理優越性。詹優優提供的同時也是一個“這個世代”的“網絡原住民”可能具有的自我構型,正如詹嘉民展露的是一個在特定歷史時代、在特定的社會與文化中形塑的“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構型。
即便詹優優的自我構型似乎更富彈性,并不意味著詹嘉民可將自我從原有構型中拔出,同樣并不意味著詹嘉民不必探索現有的自我變化生成的可能:小說中,詹嘉民帶著母親的骨灰回鄉,在鄉土喪儀中重新領悟生命與死亡,融通了與母親、與女性親族心靈的交會。他與女兒將母親送入地下河的入口,創造了他們自己的葬儀。在此之后,詹嘉民還是“知識分子詹嘉民”,他的返歸涉足的仍只能是“喀斯特地界”,頭頂的仍是“喀斯特天空”,然而誰能說他絲毫未能接通、延續與創造某種“鄉土傳統”,誰能說他并未擊破身心隔障,去重新接納女性/他者在其生命中的進入與離開?
作為“80后”,潘小樓能以小說敘事形式的機巧去撬動與傳帶歷史反思,這創造力與沖勁見出其年輕,實現構思時的渾然流暢足見其老到。如果說作為讀者,仍有心未足處,便是希望在類型人物反轉之余,能有與類型的撕裂、對類型的撕裂。在詹嘉民,即便作為“類型人物”,對其書寫仍是略“正”,若用電影作喻,色、光、鏡位都走得過于熟習,與鏡語跳脫的詹優優的對位并不那么易于發覺。在詹優優,或會希望在其“空洞”翻轉之余,讓人窺見“外殼”與“內壁”之間的更多肌質、那個能涵容他人靈魂的獨特靈魂。也許這正說明作為讀者的我居于某種“詹嘉民式”的審美結構之中而不自知——誰知道呢,讀完這篇小說,誰下斷語都不能再這么安然。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