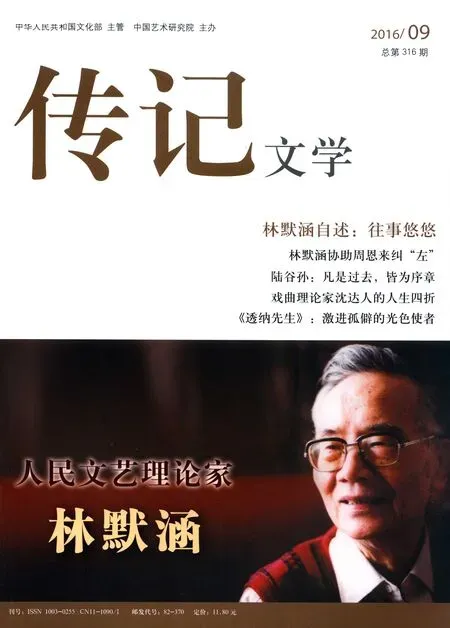“孤島”兒女(九)
文|楊世運
“孤島”兒女(九)
文|楊世運
謹(jǐn)以此作品
獻給為拯救國難而獻出青春和熱血的中華優(yōu)秀兒女們!
【長篇紀(jì)實文學(xué)】
第十二章 義無反顧
三
齊紀(jì)忠約見鄭蘋如,動員她三入虎口。
鄭蘋如默不作聲,但并沒搖頭拒絕。
齊紀(jì)忠心里一喜,看到了希望,滔滔不絕地開始了說服工作:“蘋如,現(xiàn)在全上海都傳開了,說共產(chǎn)黨圣誕節(jié)鋤奸,計劃雖未成功,但行動鼓舞人心,這說明什么?說明日本人和76號并沒懷疑到我們頭上,特別是沒有懷疑你。有一件事,特別能證明我所說的這一點,那就是《中華日報》的報道。《中華日報》報道說,共產(chǎn)黨為報復(fù)國民政府對共黨分子茅麗瑛的懲處,居然利用佳節(jié)之際在鬧市制造槍擊事件,引起了廣大市民不安,是可忍,孰不可忍?這報道得好呀!你想想,《中華日報》是誰的報紙?是日本人和汪精衛(wèi)政權(quán)的報紙,報社主筆是大漢奸文人胡蘭成。連胡蘭成都認(rèn)為圣誕節(jié)行動是共產(chǎn)黨在搗鬼,因此,丁默他怎么可能懷疑你呢?你再想想,汪精衛(wèi)的人最恨誰,最防范誰?當(dāng)然是共產(chǎn)黨!若不,他們?yōu)楹卧凇畤臁隙紝懼垂玻推剑▏⑶野选垂病至性谑孜唬坑辛斯伯a(chǎn)黨給你當(dāng)擋箭牌,你盡管放心大膽繼續(xù)與丁默擺迷魂陣,以期再尋機會。”
見鄭蘋如仍是無語,齊紀(jì)忠繼續(xù)發(fā)揮他能言善辯的絕佳口才:“我們不可退讓,退讓就是承認(rèn)失敗,讓過去的一切努力一切痛苦一切屈辱一切期盼都付之東流,那樣我們就不能原諒自己!這件事我也向陳特派員請示過了,他表揚了你的勇敢,希望你繼續(xù)努力,再接再勵。他分析的一番話特別言之有理,才打消了我的顧慮。本來我是堅決不主張讓你再進76號的,但是特派員比我站得高,比我想得周到。他說,我們只可進不可退。如果讓蘋如小姐繼續(xù)進入76號,敵人就不會懷疑她;相反,如果讓蘋如小姐從此不在76號露面,甚至讓她隱蔽起來,那反而是害了她,敵人會立即懷疑她,到處捉拿她,并且也必然殃及她的父母。蘋如,還是陳特派員有斗爭經(jīng)驗,考慮問題細致周到啊!”
齊紀(jì)忠繼續(xù)乘勝追擊:“蘋如,我還為你想好了兩個萬全之策。第一,76號的人最怕日本人,也最信日本人,因此你可以借日本人當(dāng)保護傘。我想起一個人,日本憲兵隊滬西分隊隊長橫山,這家伙不是老想和你套近乎嗎?你就先找他,讓他陪你進76號,丁默就更不會對你產(chǎn)生半點疑心。第二個萬全之策,你先給丁默打個電話,就說你這兩天待在家里越想越后怕,不知道圣誕節(jié)為什么槍響,責(zé)怪他為什么突然丟下你不管,差點把你嚇?biāo)懒耍∠忍教剿目跉猓羲抢餂]什么可疑之處,你更可放心大膽去行動。
“蘋如,這次你再進76號之后,一定要表現(xiàn)得更加勇敢。你要主動靠近丁默,向他示好,麻痹他的神經(jīng)。他要再叫你和他在同一個辦公室,你就答應(yīng)他,這樣你就更容易掌握他的行蹤,獲得更多的引蛇出洞的機會。不要猶豫,不要彷徨,成大事者立大名,必須有臥薪嘗膽的精神!”
周鶴鳴聽說又要叫鄭蘋如再入虎口,立即要求單獨面見特派員陳而立。見面后,他直言相陳:“特派員,萬萬不可再叫鄭蘋如踏進76號半步!”
陳而立回答:“這事無須你多言,我已交給紀(jì)忠同志,讓他全權(quán)負責(zé)。”
“陳站長,恕我直言,希望您再慎重考慮,難道就沒有其他辦法?”
“其他什么辦法?”
“站長,鄭蘋如她不過是個弱女子呀,讓一個弱女子承擔(dān)這么重的風(fēng)險,我們于心何忍?”
“國難當(dāng)頭,有什么辦法呢?”
“國難當(dāng)頭,要你我這些七尺男兒干什么?”
“你什么意思?你在批評我和紀(jì)忠同志沒盡心不稱職嗎?”
“請別誤會,我是為自己身為一個男子漢而慚愧……”周鶴鳴說著,聲音哽咽。
其實陳而立也在暗自難過:“鶴鳴,別難過了。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也知道蘋如小姐的兄長是你最親密的戰(zhàn)友,按理說,我們應(yīng)該千方百計保護好蘋如,而不是一次次讓她去冒風(fēng)險……”
“站長,76號,那是個虎狼窩呀!”
“我不是不知道,這實在是無奈之舉啊。我們的姐妹們,本應(yīng)當(dāng)受到最好的呵護,讓她們像鮮花一樣生活在春風(fēng)陽光下,可是侵略者闖進了我們的家園,我們的國家在流血流淚……”陳而立再說不下去了,走出小屋,站在狹窄的天井里,抬頭望一孔天空,發(fā)出兩聲長嘆。
四
齊紀(jì)忠的一條條“妙主意”,其實是一道道催命符,最終將鄭蘋如推到了絕境。
事后,陳而立也頓胸跌足,后悔只聽了齊紀(jì)忠的片面分析,不該犯了特工工作之大忌,盲目自信,顧此失彼。要說“心理分析”,丁默這個“老軍統(tǒng)”,他比齊紀(jì)忠更老道!《中華日報》的那篇報道是敵人拋出的誘餌,我們居然上鉤了!
晴氣慶胤一聲冷笑:“好厲害的重慶分子,美人計差點玩到我的頭上來了!趕快行動,抓住她!”
“什么妙計?”
“現(xiàn)在,我趕緊把胡蘭成大主筆請來,讓他在報上發(fā)一條假新聞,就說我們已認(rèn)定今天的槍擊事件是共黨分子所為。有了這條新聞,魚兒保證自動上鉤!“
“為什么?說明白的!”
“我們在報上制造假消息,重慶的軍統(tǒng)或者中統(tǒng)看了一定高興,慶幸我們并沒懷疑到他們頭上……”
“嗯嗯,明白明白的,這辦法大大的好!”
鄭蘋如放下電話,齊紀(jì)忠便得意地拍手:“怎么樣,我說得不錯吧,他們根本沒懷疑你,注意力在共產(chǎn)黨身上!”
鄭蘋如又按齊紀(jì)忠的第二個“妙計”行動,到日本憲兵隊滬西分隊找到分隊長橫山。橫山喜出望外,立即同意用摩托車護送鄭蘋如到76號上班,以免路上又遇上共黨分子,又熱情地向鄭蘋如獻計說:“為了更加保證你的安全,我現(xiàn)在先給76號的澀谷準(zhǔn)尉打個電話,讓他在門口迎接我們!”
橫山親自駕車,前后還有摩托“護駕”,把鄭蘋如送到76號。澀谷已在二門內(nèi)等候,見了橫山,立正敬禮。橫山說:“人交給你了,別弄丟了!”扔下鄭蘋如,上大洋房接待室喝茶去了。澀谷上前拉住鄭蘋如胳膊:“鄭小姐,請上軍車!”
上軍車?在76號的大院里行走,上軍車干什么?鄭蘋如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強作鎮(zhèn)靜回答:“澀谷準(zhǔn)尉,汽車就不必了吧,我自己走到辦公室……”
話音未落,從兩邊平房里涌出一伙特務(wù),個個手里端著長槍、短槍。領(lǐng)頭的便是“殺人魔王”吳四寶,還有“毒彈專家”、第二行動隊隊長林之江。鄭蘋如心里一聲苦喊:“上當(dāng)了!”仍然鎮(zhèn)靜問道:“怎么了吳隊長,為什么這樣看我?”吳四寶“嗬嗬嗬”幾聲狂笑,接著罵道:“小娘們,別再他媽的裝腔做勢了,老子們等候你多時了!”
特務(wù)們“呼啦啦”上軍車,將鄭蘋如押往秘密牢房。
五
鄭蘋如掉進了陷阱,陳而立悔之晚矣,卻又束手無策,他不知道鄭蘋如被關(guān)在哪里,就是知道了也不敢組織營救行動。齊紀(jì)忠更是變成了一只縮頭龜。他們哪會想到,共產(chǎn)黨卻在秘密策劃幫助周鶴鳴營救鄭蘋如。
周鶴鳴對鄭鐵山說:“鐵山,這次行動絕不能讓齊紀(jì)忠知道,以免節(jié)外生枝。”
營救行動的指揮點在蜀鄉(xiāng)公所,指揮者是趙子忱。
從內(nèi)線已得到準(zhǔn)確消息:鄭蘋如被關(guān)押在憶定盤路(今江蘇路)37號。這里是林之江的第二大隊的隊部,也是關(guān)押“重刑犯”的地方。蘋如被關(guān)在第3號女牢。這是一個單人牢房,平房,牢房的隔壁是個棺材倉庫。
特務(wù)機關(guān)里為什么還有棺材倉庫?
這幫漢奸大發(fā)國難財,已經(jīng)到了天良喪盡的地步。他們幾乎天天都在抓人殺人,抓的不完全是抗日分子,更有許多普通市民。他們給被抓的人扣上一頂“抗日”帽子,關(guān)進黑牢后通知家屬拿錢贖命。有許多人抓進來后被打死,就連家屬要求收尸他們也得要錢,不僅索要收尸錢,還得收棺材錢,因為他們不準(zhǔn)死者家屬在棺材鋪買棺材,只能買由“特工總部善事處”提供的棺材,不然死者家屬辦喪事也不得安寧。“善事處”并不自制棺材,他們?nèi)怯靡靶U壓價的手段從棺材鋪買來的,再轉(zhuǎn)手加高價賣給受害者。“善事處”就設(shè)在憶定盤路37號,棺材倉庫里常年備有幾副棺材,以備“急需”。
看管棺材倉庫的人名叫常村,年近40歲。他原是龍華寺里的和尚,法名犁水。他熟悉經(jīng)書,會做法事,因此76號把他從龍華寺給抓進來,命他仍然身穿法衣,守護棺材倉庫。
敵人做夢也不會想到,常村是一名共產(chǎn)黨地下黨員。就是他向黨組織提供了鄭蘋如被關(guān)押的地點,并且請求黨組織為他運進營救的工具。
在憶定盤路的西北方向,有一個蘇州河的渡口,名叫曹家渡。在這片貧民區(qū)有一家蘇北人經(jīng)營的“仙安”棺材鋪。76號“特工總部善事處”的大部分棺材都是在這兒訂做的。棺材鋪老板姓黃,和趙子忱是老熟人,因為蜀鄉(xiāng)公所也從“仙安”買過棺材,每次價錢都給的公道。
前幾日“特工總部善事處”又在仙安棺材鋪訂購了一口棺材,催著快交貨。
六
仙安棺材鋪的黑漆棺材終于做好了,黃老板帶著四個腳夫,抬著棺材送到憶定盤路37號。
守門的特務(wù)大喝一聲:“站住!干什么的?”
黃老板忙上前遞香煙:“長官,你都看清楚了,我們是送‘財’來了,我是‘仙安’的黃老板。”
“棺材里裝有什么東西嗎?”
“有,有啊,哪能沒有?”
“是啥?”
“灰包,給死人當(dāng)枕頭的灰包。你們善事處處長說過,每次送‘財’來也必須搭上‘包’,我們的行話叫它大錢包。”
“打開蓋子我看看!”
“哎,哎,我馬上打開!”
黃老板把棺材蓋抬起一道縫,特務(wù)伸頭朝里頭瞄了一眼,發(fā)現(xiàn)棺材里的確只有一個灰包,便頭一擺說:“進去吧!”
棺材被抬進了庫房。
棺材內(nèi),灰包下面有玄機,藏有幾根鋼釬和一把鐵錘。
抬棺的四個腳夫中有兩人是船工,另兩人是周鶴鳴和鄭鐵山。
棺材倉庫的隔壁就是關(guān)押鄭蘋如的牢房。鶴鳴和鐵山相互望了一眼,千言萬語只在無聲中。
黃老板沉著應(yīng)對,掩護共產(chǎn)黨的行動。他要把戲演足,演得更逼真。他正在“善事處”處長面前苦苦求情:“處長你再給加點錢吧,我這口‘財’漆了兩遍大漆,是上等柏木呀!”
處長聽得不耐煩,回答說:“好了好了,這次就這樣,下次再給你補償。快快,帶著你的腳夫走人!”
四個腳夫離開憶定盤路37號,肩扛木杠和繩子,向南行走不遠,在十字路口東拐,便是愚園路。
愚園路到處都有76號的便衣特務(wù)在巡視,但是這些特務(wù)們卻對四個腳夫不屑一顧。四個腳夫破衣爛衫,身上散發(fā)出汗臭味。周鶴鳴變成了個中年人,胡子拉碴,腳上的布鞋破了兩個洞。鄭鐵山像個小叫花子,也不知從哪兒揀到了半塊燒餅,邊走邊啃。
一直向東走,走到愚園路盡頭,右手就是百樂門舞廳。過了舞廳,便進入公共租界。
不覺間,百樂門舞廳就在眼前。意外情況實然發(fā)生:從舞廳內(nèi)跑出兩個人來,扭在一起撕打。兩個人,一個禿頭肥臉,身穿馬褂;一個風(fēng)流倜儻,西裝革履。
西裝革履者顯然是喝醉了酒,腳步踉踉蹌蹌,和禿頭交手,只有招架之勢,沒有還手之力。禿頭揪住他的領(lǐng)帶臭罵:“他娘的,吃了豹子膽,敢跟老子搶舞女!”
周鶴鳴心里大吃一驚:那個挨打的人是齊紀(jì)忠!
被動挨揍的齊紀(jì)忠,突然發(fā)現(xiàn)了化裝成挑夫的周鶴鳴和鄭鐵山,頓時精神一振,對禿頭吼叫道:“老子一槍斃了你!”
禿頭咧嘴冷笑:“小赤佬,你就吹吧,你他媽的赤手空拳,拿什么斃掉老子?”邊冷笑,邊對齊紀(jì)忠狠踢一腳,“小赤佬,睜開眼睛看看你大爺是誰,說出來嚇破你十個膽!老子是76號的黑老虎,你知道不?你竟敢跟老子爭舞女,有幾條狗命?老子今天絕不會放過你,讓你進76號嘗嘗皮鞭是什么滋味!”
糟了!“黑老虎”這個諢名周鶴鳴聽說過,他是吳四寶的拜把兄弟,現(xiàn)在又是佘愛珍最重用的貼身保鏢,齊紀(jì)忠為什么要招惹了這個人?落在他手里,兇多吉少!
齊紀(jì)忠知道自己難以掙脫“黑老虎”之手,為了自保,他繼續(xù)用暗語向周鶴鳴下達命令:“我斃了你!我一定要斃了你這只黑老虎!”
之所以下達這樣的指令,因為齊紀(jì)忠心里明白,周鶴鳴的身上肯定藏著“掌心雷”手槍。同時他也清楚,一旦開槍,危險便隨之降在周鶴鳴身上。但是,為了保住自己,他顧不得他的部下了,把嗓門叫得更響:“斃了你!老子堅定不移要斃掉你!”
周鶴鳴別無選擇了,向鄭鐵山示意:快帶船工兄弟們離開,這里的事我處理!
齊紀(jì)忠望一眼周鶴鳴,突然一掌推開“黑老虎”,轉(zhuǎn)身向著租界疾跑……
“往哪兒逃?”“黑老虎”撥腿追趕。
突然,“黑老虎”仰身往后,“咚”一聲就倒在了地上!頃刻間,從后腦勺里流出一攤黑血。
營救行動,想不到首先救了齊紀(jì)忠的性命。
七
在憶定盤路37號內(nèi),共產(chǎn)黨員常村,在秘密地進行著對鄭蘋如的營救行動。
關(guān)押鄭蘋如的3號牢房是青磚墻。房子是老房子,磚縫的連接不是水泥,而是石灰摻沙。地面潮濕,墻壁已斑斑駁駁。利用棺材倉庫的掩護,常村用鋼釬小心地把一塊塊青磚的磚縫給掏空。
營救方案的第二步是:等把墻壁掏空一塊,常村通知鄭蘋如做好越獄準(zhǔn)備。這時,“仙安”棺材鋪的黃老板又會帶幾個腳夫來37號,向“善事處”處長借棺材。借棺材的原因是:黃老板的一位蘇北親戚在蘇州河跑船,突患疾病暴亡,身為棺材鋪老板的老黃理當(dāng)給親戚送一口棺材,不巧現(xiàn)在鋪子里沒有現(xiàn)成的,只有兩口沒上過漆的白木棺,怎好給親戚用?萬求處長高抬貴手幫幫忙,先借一口棺材。等鋪子里的兩口白木棺上漆后,借一口還兩口,若不放心先給處長交押金。
貪財如命的處長一定會答應(yīng)這筆白賺的交易。腳夫們從37號抬走一口棺材,而鄭蘋如已在常村的安排下藏身在了棺材里。
鑿墻行動進展順利,已經(jīng)有幾塊磚完全松動,可以拆下來了。常村心中欣喜,在夜幕掩護下把磚拆掉,鉆進牢房同鄭蘋如見面。
可是牢房里卻空無一人!
狡詐的敵人,不停地給“重刑犯”換牢房,鄭蘋如早被轉(zhuǎn)移了。從這天起常村再沒見到過鄭蘋如的身影,他哪里知道,蘋如已被轉(zhuǎn)到76號,關(guān)在了暗無天日的死牢里。
第十三章“掌心雷”手槍
一
“黑老虎”被打死,使吳四寶、佘愛珍兩口子暴跳如雷。
76號內(nèi)像炸了油鍋,兔死狐悲,群丑狂囂。
從“黑老虎”的后腦勺里取出的索命物,又是一粒“掌心雷”手槍的子彈頭,與殺死冀墨清、鄢紹寬的子彈一模一樣!丁默發(fā)瘋了,集合76號所有要職人員召開緊急會議,命令立即重新追查“掌心雷”的線索。前兩次的追查都毫無結(jié)果,這一回絕不可半途而廢。把前兩次被懷疑過的對象再查一遍,而前兩次沒被懷疑的人這次更要重點摸查,尤其要從內(nèi)部及與內(nèi)部有關(guān)連的人查起,不放過任何疑點!就是挖地三尺,把全上海翻它個底朝天,也要把這個神秘的槍手挖出來!行動不力者重罰!行動立功者重獎!
連續(xù)天晴了幾日,魯婉英后悔沒早點兒把周鶴鳴衣柜里的幾件衣服拿到樓下天井里晾曬。今晚她決定把它們先取出來放在自己眼前。取出鶴鳴的呢子大衣時,她感覺到衣服里像是有一件什么小東西沉沉的。摸遍了里里外外沒發(fā)現(xiàn)什么。再仔細摸,發(fā)現(xiàn)了一只暗口袋,從這暗袋里竟然掏出了一支手槍!
魯婉英心里好不驚訝,但她不愿驚動鶴鳴,而是悄悄地去盤問鄭鐵山。
鄭鐵山竟毫不驚訝,神態(tài)自若地點頭說:“是呀,鶴鳴哥是得到了一支手槍呀!”
“啥時候得到的?”
“就昨天呀!鶴鳴哥還沒來得及對你說?”
“在哪兒得到的?”
“在外灘。昨天我陪鶴鳴哥到南京路大新公司辦事,路過外灘,迎面碰上一個猶太人。這個猶太人纏住我鶴鳴哥不放。”
“為啥?”
“他說他是從德國逃難到上海來的,現(xiàn)在身無分文,快要餓死了。他身邊唯一的一件東西就是一支小小的手槍,是德國造,無聲的,是防身的好東西……”
“他一定要賣給你鶴鳴哥,是吧?”
“就是這樣,不買他就不松手,還給我倆跪下了!”
“花了多少錢?”
“鶴鳴哥掏出身上所有的錢,共計200元,全給他了。”
“哎呀,200元?太便宜了!”
“你還覺得便宜?”
“當(dāng)然便宜,才200塊,值!現(xiàn)在這世道,兵荒馬亂,你鶴鳴哥是該有件防身的東西。”
“我還以為你要責(zé)怪他呢!”
“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怎么會責(zé)怪你鶴鳴哥?”
吃晚飯時,魯婉英告訴周鶴鳴,200塊錢就買了支小手槍,揀了個大便宜。不過一定不要叫旁人知道,以免招惹麻煩。
周鶴鳴長長地一聲嘆息。
“鶴鳴,你怎么了?”
“婉英姐,你對我太好了!”
“傻話,我不對你好對誰好?”
“有時候我想……唉!”
“想啥?為何又要嘆一聲氣?”
“有時候我想,我對你,沒有你對我那么好。”
“瞎說!我說你對我好,那就是你對我好!我這輩子,遇上你,算是我最大的福氣了!我還有啥不滿足呢?我可不是那種忘恩負義,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人!”
“婉英姐,假若我突然有一天,生一場大病,死了……”
“呸呸呸!更加胡說八道了!快喝口茶水漱漱口,把這句話吐掉了!”
“我只是說假若。”
“‘假若’兩個字也不許說,真要有了‘假若’這兩個字,我活著還有啥意思?從前,我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有了你我才活得像個人!”
一番話,說得周鶴鳴也感慨萬端:“我了解你,了解你的內(nèi)心……”
“有你說出這番話,我這一輩子,就知足了!鶴鳴,等到不打仗了,天下太平了,我給你多多地生孩子,生兒生女,都要長得像爸爸一樣漂漂亮亮,千萬別長成媽媽這樣的丑八怪。到那時,我們帶著一大幫兒女回你的四川老家,丑媳婦也得見公婆呀。你爹他不嫌我丑,你娘也不嫌我丑,你們一家人都寬宏大量。你出門去做事,我在家上奉老人下育兒女,做一個賢妻良母度光景……
臨睡前,魯婉英突然想起一件要事:“鶴鳴,你把手槍裝在衣服口袋里,怕是不安全吧?”
周鶴鳴回答:“我也這樣想過,可是放哪里呢?——有了,放在鐵山的雜屋間吧,那里最好藏東西。”
魯婉英搖頭:“那里也不是保險的地方。我想到了一個好地方!”
“哪里?”
“放到我首飾盒里,你說是不是最安全最保險?首飾盒的鑰匙你也拿一把,用起來也方便。”
“太好了,就聽你的,”
二
第二日,鶴鳴和鐵山早早地出門去了。
佘愛珍突然來訪。
“四姐,你可真是個稀客,今天刮的是什么風(fēng)?”
佘愛珍隨著魯婉英上樓梯,眼珠子滴溜溜亂轉(zhuǎn),神秘兮兮向道:“七妹,你的白馬王子在不在家?”
魯婉英回答:“不在,逛書店去了。”
佘愛珍忙把嘴巴湊到魯婉英耳邊說悄悄話:“天啦,你就這么放心讓他一個人出去?不怕被壞女人拐跑了?”
魯婉英心里好驕傲,回答說:“我那個男人不值錢,扔給別人別人也不要,哪像你們兩口子,男人香,女人更是香得不得了!”
“七妹,你嘴巴可積點德,別亂說!”
“你一百個放心,什么話該說不該說,還要你四姐交代?上回那件事,你還沒謝我哩!”
“哪件事?”
“裝糊涂了吧?還要我把胡大文人的名字說出來?”
“行了!我今天不是帶著禮物來謝你來了?”
“真的?什么禮物?”
“快上樓,進了屋才能給你看。”
“該不是塊金元寶吧?”
“比金元寶還稀罕!”
進了屋,插死了房門,佘愛珍從懷里掏出禮物,呈到魯婉英面前。魯婉英打眼一直:喲,也是一支小手槍!巧了,怎么跟鶴鳴買來的那一支一模一樣?
佘愛珍落座,手捧小手槍說道:“七妹,你知道我們的冀干爹是被淮打死的嗎?”
“誰?”
“爛腳根。”
“榮炳根?”
“就是他,派他的手下人打了黑槍。”
“他為啥?”
“他眼紅呀,不服氣呀!從前我家四寶拜他當(dāng)干爹,給他開車。后來拜了冀干爹,給冀干爹開車,他就記了仇。他的煙館被冀干爹收了幾家,他更恨。冀干爹成了日本人的紅人,他眼紅得鼻子都擠歪了!”
“想不到,是他殺了干爹……”
“你和你的白馬王子也得當(dāng)心,小心爛腳根的人拿你們開刀!”
“四姐,我們可得靠你和四寶來保護!”
“這還用你交代?我早就想送你一支手槍,給你的白馬王子防身用。不是我舍不得送,是一直沒有我滿意的。你看這一支,終于讓我十分可心了!這可不是中國槍,也不是日本造,它是支德國造,槍名叫‘掌心雷’。別看它槍小,但它射得遠,打得也準(zhǔn),不用退子彈,可以連發(fā)。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它有銷聲設(shè)備,也就是說它是一支無聲手槍。你說,這是不是我的寶貴禮物?想要不想要?說話呀!不想要我可就拿去送別的朋友了!”
“當(dāng)然想要,誰說我不想要?”
“想要就拿著。”
“白送給我的?”
“我本來是想白送,誰要我倆是姐妹呢?可是……”
“‘可是’的話你就別說了,我還不知道你這只鐵公雞?又給我耍這套把戲,想賺我的錢是不是?”
“天地良心,你我姐妹,誰賺誰的?”
“你就會在我面前花言巧語!”
“七妹你聽我把話說完,你真是冤枉死我了!我是花了大價錢,專為你買來的!”
“你花了多少錢?”
“四千。”
“四千?這么貴?”
“這是啥槍呀,當(dāng)然貴!”
“這槍販子是誰,也太貪心了吧?”
“七妹,別指桑罵槐喲,我可不是槍販子喲!”
“你不是,一開口就要我四千,你當(dāng)我是搖錢樹呀?”
“七妹,你急什么,我的話還沒說完哩!既然是我來給你送謝禮,那四千塊錢當(dāng)然不能叫你全出。這樣,你出一半,余下一半算我送禮,這該可以吧?”
“兩千?”
“兩千,兩千不貴吧?”
“還說不貴,這槍,200塊錢就能買到。”
“200?七妹你在說夢話吧,200塊錢你到哪里買這么好的槍,你當(dāng)是買廢鐵呀?”
“我的四姐,不瞞你說,我家鶴鳴還真的只花了200元就買了一支,并且也是一只德國造,跟你這支一模一樣!”
“哎喲喲,我的七妹越來越學(xué)會吹牛了!笑死我了!”
“我就知道你不會相信,現(xiàn)在我就拿出來給你開開眼!”
“那你就拿出來呀!別給四姐我打腫臉充胖子!”
魯婉英從柜子里取出首飾盒,打開來,取出手槍,得意地交給佘愛珍:“看吧,這是不是充胖子?”
佘愛珍“啊、啊”地贊嘆,把兩只手槍比過來又比過去,怎么比也看不出有什么區(qū)別,最后不得不嘆息:“媽的,我又上當(dāng)了,200塊錢的東西我花四千買來,還喜滋滋地跑來送禮呢!七妹,你把你的槍收好,我不多坐了,我要回去找沈翻譯,是她賣給我的槍,小娘們,我問她為什么敢賺我的錢!”
魯婉英也不挽留,只把灰心喪氣的佘愛珍送到樓下,慌忙又回屋,趕緊把小手槍再藏好。今天佘愛珍來賣槍之事,她決定不告訴鶴鳴。對佘愛珍這個花心的美女蛇,魯婉英不能不多存些戒心,盡量避免叫鶴鳴與她接觸,也盡量避免在鶴鳴面前提到“佘愛珍”三個字。
三
一天時間又過去了。
第二天一早,周鶴鳴洗漱完畢準(zhǔn)備出門,叫魯婉英打開首飾盒為他取手槍,他要帶在身邊。周鶴鳴接過手槍,習(xí)慣地在手上掂了掂,突然臉色大變:“昨天有人進過我們的房間嗎?”
魯婉英一愣:“昨天?你怎么啦鶴鳴?”
“你快告訴我,昨天誰動了你的首飾盒?”
“首飾盒,首飾盒怎么了?”
“槍!”
“槍?”
“我們的槍被人掉包了!這不是我們的那一支!”
“噢,鶴鳴你別急,我想起來了!”事已至此,佘愛珍昨日下午來獻槍的事,也不好再瞞著鶴鳴了。魯婉英便把昨天的事一五一十告訴周鶴鳴,最后分析說:“兩支槍太一樣了,一定是她拿錯了,不要緊的,找她換回來就是。”
“這么說,她一定是把兩支槍在手里倒來倒去比較過了?”
“是的,比來比去比不出差別。”
“糟糕,你上當(dāng)了!”
“怎么,這是支假槍?”
“不僅是個假槍的問題,情況危機,你快下樓躲一躲,快!”
“怎么啦鶴鳴?”
周鶴鳴貼近窗臺向樓下一望:來不及了!妙香摟的四周早已布滿了76號的特務(wù)。他再次催促魯婉英:“你快躲!躲到你姑娘們的房間去!千萬別出來!”說著,自己邁開大步走出去。
天井里也已站滿持槍的特務(wù),所有的槍口都對準(zhǔn)了正一步步下樓的周鶴鳴。與周鶴鳴面對面,吳四寶正滿臉冷笑,手槍里壓滿了子彈,搖頭晃腦上樓。兩人在二樓樓梯口相遇,突然,周鶴鳴一伸手,把槍口頂在了吳四寶的腦袋上,同時對著身后的魯婉英一聲高喊:“不要來!與你無關(guān)!”
槍口頂在吳四寶的腦門上,吳四寶鼻孔里卻噴出冷氣:“哼哼,小子,別給老子來這一套,玩把戲你他媽的還嫩了點吧?你難道不知道,你手里的玩意兒是個啞巴,你他媽的想嚇唬誰?識相一點,老老實實跟我走!”說著,一揚手,“啪”一聲打飛周鶴鳴的手槍,周鶴鳴也借勢,一縱身飛出欄桿,跳下一樓天井,驚得樓上樓下的妓女們失聲尖叫。
吳四寶仍站在二樓樓梯口沒動窩,因為天井里全是他的人,周鶴鳴插翅也難逃。一番搏斗,終因寡不敵眾,周鶴鳴被特務(wù)們五花大綁。他抬頭,只見魯婉英又要往下沖,便再次高喊:“別來!與你無關(guān)!”
吳四寶身體一橫,堵住魯婉英去路。
“四寶!你想干什么?”
“七妹子,別喊叫,喊叫對你沒好處!看在你面子上,也看在你干姐愛珍的面子上,四哥我對你已是大加照顧了,讓你和這小子抱在一起又睡了一夜。知道嗎,就為了叫你倆再做一夜夫妻,我的弟兄們,已在你們屋外凍了大半夜了,你不要不知好歹!”
“你放開我家鶴鳴,你為什么抓他?”
“我勸你放聰明些,少他媽管閑事!”
“我就是要管!他是我丈夫,我為啥不管?”
“他是你丈夫?哼哼,你別再自作多情做大夢了!你這叫啥?你這叫寡婦夢到雞巴,一場空!”
“吳四寶!”
“七妹子,你睜大眼睛看看,看看這姓周的小子他是誰?可惜了你的一片癡情,被這小子給耍弄了!你以為他真的對你有情有義?狗屁!他媽的他是個大騙子——你別打岔!聽四哥把話給你挑明白,他,姓周的,這小子是個重慶分子,你聽清楚了嗎?他虛情假意來糊弄你,目的是把你這妓院當(dāng)成他最安全的藏身之地,好掩護他的破壞行動,你知道不知道,我們的大恩人冀干爹,就是這小子給打死的!”
“啊?”
“啊,你也知道啊一聲了?還有,鄢紹寬,我的把兄弟黑老虎,都是死在他的槍下,你該不該恨他?”
“他,他……”
“他什么他,他根本不可能愛上你,你也不端盆涼水照照你的臉!”
“你,你說的都是真的?”
“別再糊涂了我的七妹子!要說情意,你我之間才叫真情意,對不對?你想想,若不是我家佘愛珍聰明,想出了個獻槍掉包計,從他手槍里找到了殺人證據(jù),不知道他還會哄騙你多久呢!七妹子,別不知好歹,你得好好感謝我和佘愛珍!樓下的聽著,給我綁緊了,帶人,走!”
周鶴鳴一言不發(fā),被吳四寶押走了!
魯婉英像掉了魂,攆下樓來,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哭自己命苦,好不容易遇上一個知心知己的男人,卻原是一場夢!他周鶴鳴是怎么的了呀,拿著安安生生的日子不好好過,為什么要去當(dāng)槍手?天啦,我魯婉英為何這般紅顏薄命,往后的日子怎么過?……
(待續(xù))
責(zé)任編輯/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