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圓桌
生活圓桌
游泳滾你個球
北京晴媽

苦瓜
前幾天看見幼兒游泳班招生,我給5歲的女兒晴晴報了名。我從小就羨慕那些泳技好的孩子,在水里就像一條魚,自在又快樂,好像多了一番天地給他們舒展。而且,游泳可以鍛煉孩子的協調性,培養她的意志,可以提升心肺功能……總之好處多多,是個很適合孩子參加的運動。可女兒卻不大喜歡,每次去都別別扭扭。今天又有游泳課了,趁著早上的空閑,我決定和她簡單地討論一下這件事。
我:晴晴,今天晚上有游泳課哦,你又可以去游泳啦,開心嗎?
晴晴:啊?不會吧?我不喜歡上游泳課。
我:上游泳課多好啊,你現在學會游泳,等你上學了,你就可以進校隊,然后就可以參加青少年游泳集訓,然后入選國家隊,參加奧運會,得冠軍,登領獎臺,奏國歌!多棒啊!
晴晴:那是你的夢想。
我:媽媽長大了,不能實現這個夢想了,你能幫我實現嗎?
晴晴:可是,自己的夢想,得自己實現。
我:那你的夢想是什么?
晴晴:是拍皮球可以拍100下!
這是不是應了現在很流行的育兒觀念:把自己的夢想寄托在孩子身上?
不得不愛
吉林曉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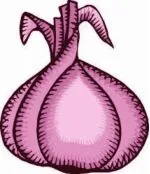
洋蔥
閨密小蘭結婚了,身為伴娘的我忙前忙后,卻一點高興不起來。
小蘭是我大學室友,她跟男朋友郎哥是同學,倆人大一時就處上了,算起來六七年了。小蘭是純純的農村姑娘,對郎哥那是掏心掏肺,郎哥倒不是對她不好,就是有事沒事總對她大呼小叫。我真看不過眼去,曾半開玩笑地對小蘭說:“你對他好得過分了!”小蘭總是笑呵呵說:“我這輩子就跟他了,可不得對他好點,我這樣的,別人也不會要了。”
小蘭這話意思我懂,她打了兩次胎,結婚前第三次懷孕。
誰知郎哥蹬鼻子上臉,老覺得跟小蘭是初戀,自己賠了,結婚前又搞了一個,有一天還帶回了新房。小蘭早就知道郎哥的勾當,老跟我哭。我勸她分手算了,可小蘭還是那句話,“我都這樣了,誰還肯要我呀!”那段時間,小蘭好吃好喝好言語地伺候著郎哥,希望他回心轉意。在父母壓力下,郎哥跟小蘭領了證,但據說跟那女孩還藕斷絲連。
婚禮現場,小蘭一襲婚紗,司儀激情主持,“帥氣的新郎,喊出你最愛人的名字。大膽向她表白吧。”郎哥不含糊,“小蘭,我愛你!”全場歡呼!我忽然想哭,也想吐……
假裝寬厚
河北臨臨

蒜汁
住對門的老劉不知怎么,最近走路好像有點跛。正好今晚在小區里乘涼遇上了,我和樓上的張嬸都問他腿怎么回事。老劉哈哈一笑,“沒啥,出了個小車禍。”
原來老劉騎電動車闖紅燈,和一輛正常轉彎的汽車撞上了,好在車速不快,沒傷筋骨,就是得養些日子才能完全恢復。
張嬸問了不少細節,撞哪兒了,找了交警沒,怎么處理的。說著說著,話題變了味兒。
“老劉,你怎么沒叫他賠啊?”張嬸問。
“唉,等不起,我著急去辦事。一個朋友托我送點東西,晚了人家就趕不上火車了。要不,讓他賠,他就得掏錢。”老劉邊說邊比劃著掏錢的動作。
張嬸豎起大拇指,“老劉,你這人真寬厚,換別人早讓他領著上醫院了。”
“那可不,咱不是那樣人。這回別說上醫院了,連電動車擋板都是我自己花錢換的。”老劉顯然對張嬸的評價非常滿意,頻頻點頭。
我忍不住插了句:“交警不是說你闖紅燈負全責嗎?”
張嬸一拍大腿,“你不懂,一個鐵包肉,一個肉包鐵,老劉又受了傷,要錢肯定能要著。老劉就是人太好,這么輕易就放過了。”
看著老劉又點頭認同,我把到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我想說,闖紅燈受傷沒要錢就是寬厚,那汽車司機無責也賠償算是什么呢?
嘴甜挨訓
遼寧何苦子

辣椒
朋友旦旦從一家不到20人的小民企跳槽到一家股份公司。這家公司夠大,僅他供職的小組就有50多人。旦旦很想大干一場,可剛入職不到一星期,就被組長訓了一通。
“都是稱呼給鬧的。”他告訴我。旦旦原先待的小民企,同事關系挺家庭化,大家都以哥、姐、姨、叔相稱,旦旦覺得那樣挺好。跳槽后,他還沿襲這個習慣,新同事歲數比他大一點的,他叫王哥,跟父母同齡的,他叫孫姨。最初他管組長叫組長,后來覺得太正經,便改叫哥。組長登時拉下臉,訓他:“我早就想說你這個毛病,什么哥呀姐呀的,就我們這個組,姓王姓孫的十好幾位,你在我面叫王哥孫姨的,我知道說誰呢?給我改過來!”
旦旦覺得是這么個理兒,“你跟組長匯報說,趙姐叫我取文件去了,兩三個趙姐,組長哪知道你指的是誰。這大公司和小作坊就是不一樣。”雖然想通了,但習慣不是一下子就能改的。那天,上面的部長來組里給大家開會,因為習慣性稱呼,旦旦又挨了部長訓。
部長給大家開的是座談會,要求大家都說說。聽說旦旦是新員工,部長點名讓他講。旦旦當眾發言不打怵,但說著說著,習慣就露頭了,王哥孫姨的冒出好幾次。他發完言,部長沒客氣,直接點出他的毛病,“組長沒囑咐你嗎?公司內部不準以哥姐相稱,說輕了這是家族化糟粕,說重了是信息傳遞不暢,你不能讓我沒有阻礙地了解你說的那個人是誰。”
旦旦說他心服口服,“都提升到信息傳遞層面了,部長水平就是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