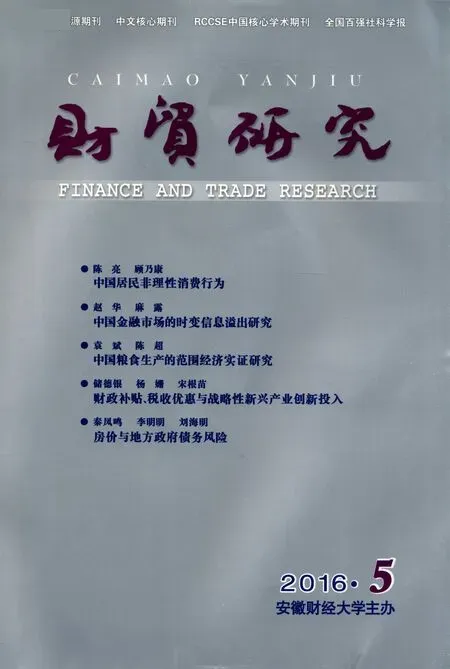國際貿易是否抑制了企業層面產出波動——基于進口中間品多樣化角度
蔣銀娟
(武漢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
國際貿易是否抑制了企業層面產出波動
——基于進口中間品多樣化角度
蔣銀娟
(武漢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利用1999—2007年工業數據庫和海關數據庫匹配信息,運用Heckman選擇模型,從進口多樣化中間品的替代效應、互補效應和創新效應角度出發,分析了企業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產出波動的影響。實證結果表明:進口中間品多樣性與企業產出波動之間存在顯著的“U”型關系;進口中間品多樣化程度較高的東部地區企業 “U”型關系較明顯,而程度較低的中西部地區企業負向關系顯著;出口密集度越高的企業,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產出波動的影響越小。
進口中間品多樣性;產出波動;外部沖擊
一、引言
國際貿易分工對經濟波動的影響一直是學者重點關注的研究領域,已有文獻大都圍繞著出口貿易多樣化、貿易專業化來闡述這一問題。在以初級產品部門為主的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變動會導致外匯收入不穩定,以至出現經濟波動較大的狀況。而貿易多樣性,尤其是出口貿易多樣性成為緩解發展中國家經濟波動的主要渠道。
二戰后,以中間品貿易為主要特征的貿易專業化分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逐步形成,中間品貿易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組成部分。作為重要的國際外包承包方,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出口多樣化產品同時也大量進口中間投入品。通過融入全球價值鏈鏈條體系,中國成為世界貿易大國,同時也承受著來自價值鏈上游價格成本和價值鏈下游市場需求的雙向沖擊。對于企業而言,這一問題主要表現在:進口中間品易受價值鏈上游波動的影響,且難以將波動吸收以轉移傳導到下游。因此,中國企業獲利甚多的同時也有風險波動大的潛在弊端。對這一問題,有研究者已經從外包、國際價值鏈分割的角度進行了探析(張少軍,2013;Escaith et al.,2009; Escaith et al.,2010)。
隨著異質性企業理論的出現,對經濟波動的研究逐漸深入到企業層面,Gabaix(2005)和Giovanni et al.(2014)發現,企業層面波動是形成宏觀經濟波動的主要力量。作為經濟波動的微觀基礎,企業層面波動不僅構成了宏觀層面波動的主要動因,而且反映了微觀層面上資源配置的合理程度,因此,企業產出波動是值得重點關注的問題。然而,目前中國這一領域的研究甚少,考慮到中國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現實背景,本文從分析進口中間品多樣化對企業層面波動性的影響出發,揭示了進口中間品貿易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并對中國從全球價值鏈中獲得福利效應和貿易利得的研究進行補充。
二、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說
探討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企業層面波動性的影響,相關文獻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1)國際貿易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的研究。一種觀點認為,貿易開放增加了經濟體受外部沖擊的可能性。由于貿易條件變動,貿易開放程度越高的部門產出波動越大(Calderón et al.,2005; Giovanni et al.,2009)。另一種觀點認為,貿易開放的經濟體容易通過國外市場來抵消國內的沖擊(Barrell et al.,2004;Bejan,2006;Cavallo et al.,2007)。事實上,由于貿易專業化和貿易多樣化兩種作用渠道不同,貿易開放對經濟波動的作用方向并不確定。
隨著研究的深入,貿易多樣化,尤其是出口多樣化對經濟波動的作用被重視起來。Malik et al.(2009)發現,出口地理市場多樣化可以有效降低經濟波動;Bacchetta et al.(2007)分析了出口產品和出口市場兩種類型的多樣化對經濟波動的影響;Haddad et al.(2010)認為,出口多樣化有類似于資產投資組合的效果,可以降低風險波動。一般而言,出口多樣性與進口多樣性是相互聯系的,出口多樣化需要使用的中間投入品的范圍較大,消費和生產都存在種類多樣化偏好(love-of-variety)(Parteka et al.,2013)。
(2)影響企業波動性因素的研究。隨著金融監管的放松,企業進入債券市場和資本市場更為便捷,更容易為研發投入取得外部資金支持,風險較高的項目也能獲得支持,因而產出波動變大;激烈的市場競爭下,熊彼特式創新導致產品更新替代頻繁,新產品和新款式投入市場后,迅速改變各個企業的市場份額,因而企業層面產出波動更加明顯(Comin et al.,2006,2009)。基于“創造性毀滅”理論,金融市場發展、研發投入加大導致創新性毀滅明顯加劇,進而企業產出波動變大(Acemoglu et al.,1997; Thoenig et al.,2004; Chun et al.,2008)。然而,Koren et al.(2013)認為,研發投入可以通過多樣化技術種類方式降低企業產出波動。當內生技術進步表現為投入品種類不斷增加時,對某類技術生產效率的外部沖擊程度會隨著技術種類的擴大而降低。企業為更多市場提供產品以避免特定市場層面沖擊,也可以減輕對產出波動造成的影響(D′Erasmo et al.,2013;Buch et al.,2009; Caselli et al.,2012; Vannoorenberghe,2012)。這些都說明技術種類、貿易市場多樣化具有降低企業產出波動的作用。
(3)進口中間品及其多樣性對企業影響的研究。許多技術物化在中間投入品中,通過反向工程可以獲取發達國家更先進的技術,因而進口中間投入品是獲得新技術的重要途徑。利用不同國家數據進行實證分析,進口中間品將促進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Coe et al.,1995;Halpern et al.,2010;Goldberg et al.,2010;Amiti et al.,2007;陳勇兵 等,2012)。此外,進口中間品對新產品創新也具有促進作用。利用印度企業數據,Goldberg et al.(2010)發現新增進口中間投入品會促進其國內新產品種類增加;楊曉云(2013)發現進口多樣化中間投入品有助于企業新產品創新。
綜上,現有文獻主要關注進口中間品及其多樣性對企業生產率和新產品創新的作用,尚未考慮到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企業波動的影響。
進口中間品對企業生產具有質量效應和不完全替代效應(Halpern et al.,2009)。如果國內外中間品具有相互替代關系,在國內遭受價格沖擊時,企業會選擇國外中間品來進行替代。類似于資產組合效應,進口中間品種類越多,企業抵消不確定性沖擊能力越強。進口中間品多樣化具有替代效應,可以避免投入要素供給對企業生產的負面影響,從而有效降低企業的產出波動。
如果國內外中間品存在互補效應,國內中間品價格波動對產出的負面影響并不能通過進口來減弱。進口中間品多樣化程度越高,中間品波動傳導到企業生產中可能性越高。同時,中間品進口貿易是發展中國家獲得技術溢出的重要渠道。進口來自發達國家的中間品,通過逆向工程了解其原理并進行模仿和重新制造,進而促進技術創新;進口多樣化的中間品,企業可以獲得技術溢出,學習吸收后促進生產率提升和新產品種類的開發(Goldberg et al.,2010;楊曉云,2013)。當然,開發出新產品會造成原有產品被淘汰,新舊產品迅速更替,企業產出波動變大(Comin et al.,2006)。
綜上所述,進口中間品對國內中間品具有替代效應、互補效應和創新效應;當替代效應發揮主要作用時,進口多樣化的中間品為企業提供了多樣化的避險渠道;而當互補效應和創新效應發揮主要作用時,進口多樣化中間品并不能有效降低企業生產的波動性,反而會通過技術進步、新產品創新等方式讓企業產出波動變得更大。
由此,提出本文的假設:當替代效應的作用更大時,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企業產出波動具有負向影響;當互補效應和創新效應的作用更大時,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企業產出波動具有正向影響。
三、數據說明和處理、實證模型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1999—2007年數據和中國海關數據庫2000—2003年數據。在具體的處理過程中:首先,參照聶輝華等(2012)的辦法,將工業企業數據庫中不符合會計準則和存在明顯統計錯誤的企業刪除;其次,將海關數據中進口中間品的企業按照月度進行匯總,得到進口中間品企業的產品多樣性;再次,借鑒楊曉云(2013)的處理方法,將不同的HS編碼定義為不同產品,根據HS編碼6位數和8位數定義進行構建,并將不同來源國進口的同一產品視為不同產品種類;最后,將工業企業數據庫和海關數據庫按照企業名稱字段、電話號碼進行匹配,得到2000—2003年全樣本企業,未能匹配上的為0。
通常,企業產出波動是根據5年期年增長率標準差計算而得,而倒閉退出企業會造成產出波動值缺失。如果僅使用持續存在的企業樣本進行估計,明顯存在樣本選擇偏誤,因為產出波動偏大的企業更有可能破產和退出,而產出波動偏小的企業則更有可能持續存在。因此,本文使用Heckman(1979)選擇模型進行估計,考慮到企業的產出波動與企業的持續存在的情形,最后模型設定如下:
(1)
其中,若Volatilityit表示企業i的產出波動,使用第t期至第t+4期的工業增加值增長率的標準差來衡量。Durit表示企業i在第t-1期至第t+4期是否持續存在。Durit是一個虛擬變量,當企業在第t-1期至第t+4期都持續存在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2)
企業持續存在的回歸模型表示為:
(3)
企業產出波動的回歸模型表示為:
(4)
其中,zit、xit分別表示影響企業是否持續存在和產出波動的其他解釋變量,μit和vit分別表示式(3)和式(4)的隨機擾動項。考慮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企業產出波動的影響受到替代效應、互補效應和創新效應的影響,替代效應會有效地降低產出波動,而互補效應和創新效應會導致產出波動的上升。加入進口中間品多樣性的二次項,可以分析進口中間品多樣性與產出波動之間在不同階段的非線性關系。可觀測樣本的條件期望為:
(5)
解釋變量ln(import)it變動的邊際效應為;
(6)
其中,ρ是μit和vit的相關系數;σv是vit的擾動項λ(l-w′γ)是逆米爾斯函數。


企業產出波動主要受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外部沖擊,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都受供給和需求的影響,從而會遭受外部沖擊帶來的影響。企業所有制性質是經濟系統中外生性的因素,往往不會直接影響到企業產出波動。同一行業內技術水平、信貸約束以及市場競爭力等因素相似的情形下,是否為國有企業對企業產出波動往往無直接影響。而企業所有制通常是通過信貸約束、市場控制力等因素對企業的經營狀況產生影響。式(3)和式(4)中其他控制變量都相同,具體變量的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定義和處理說明
① BEC(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中代碼為“111”、“121”、“21”、“22”、“31”、“322”、“111”、“42”、“53”等八類是本文要研究的中間品,將BEC代碼與HS編碼進行匹配,具體參見陳勇兵(2012)。

表2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由表2可知,中部地區企業樣本產出波動的均值為-0.481,東部地區為-0.402,而西部地區為-0.423,說明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企業產出波動較大,而中部地區較小。從進口中間品多樣化上看,東部地區企業樣本均值為0.302,中部地區為0.034,西部地區為0.042,東部地區企業進口中間品種類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說明東部地區企業從國外進口中間品種類更多,與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特點一致。
相比中西部地區,東部地區企業規模偏小,這是由于以固定資產作為衡量標準,存在大量加工貿易型中小企業。東部地區企業的出口密集度和勞動生產率遠高于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國有企業占比較大,而東部地區非國有企業地位舉足輕重。
四、實證分析結果
利用匹配后的2000—2003年全樣本企業的面板數據,使用Heckman樣本選擇模型對式(3)、式(4)進行估計,分析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企業產出波動的作用。在數據處理過程中,控制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資本密集度、產品種類、出口密集度等變量,同時控制時間虛擬變量和行業虛擬變量。為了參考對照,除了使用工業增加值,還使用工業銷售額、工業總產值等指標來衡量企業產出。表3是全樣本企業Heckman兩階段模型回歸的估計結果。

表3 全樣本企業的估計結果
注:括號內為估計系數標準誤差,*、**、***分別表示10%、5%、1%的顯著性水平。下表同。
由表3的λ的系數顯著為負可知,樣本存在明顯的選擇偏誤。在第(1)組的回歸模型中,選擇方程中企業進口中間品多樣性的系數為正,二次項系數為負,說明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和企業是否持續存在之間呈倒“U”型關系。在到達某臨界值之前,企業進口中間品多樣化程度越高,則越有利于企業持續存活;到達臨界值后,企業進口中間品多樣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企業持續存活。產出波動的回歸方程中,企業進口中間品多樣性的系數為負,二次項的系數為正,說明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和企業產出波動存在“U”型關系。到達臨界值2.05之前,企業進口中間品多樣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降低產出波動,此時替代效應發揮了主要作用;而到達臨界值2.05后,企業進口中間品多樣化程度越高,產出波動反而越大,互補效應和創新效應發揮主要作用。
企業規模對企業是否持續存在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企業規模越大,企業越容易存活;反之,則說明企業規模越大,企業產出波動越小。資產負債率對企業產出波動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企業的資產負債率越高產出波動越大,這是因為負債高的企業越不穩定,產出狀況也越不穩定。企業產品種類數量對產出波動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企業實行“多元化”戰略也會降低產出波動。
企業勞動生產率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企業生產率越高產出波動也越小。由于生產率水平高反映了企業技術種類多樣化程度也較高,而多樣化可以降低技術受到外部沖擊對產出的影響。出口密集度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出口密集度越高產出波動越小。資本密集度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企業的資本密集度越高產出波動越大。作為選擇方程中額外的工具變量國有企業虛擬變量,估計系數為負,這是由于“國企改革”背景下,因為政策導向,國有企業需要重組和改制,特定階段的生存概率低。
由表3可知,進口中間品多樣性的系數和二次項的系數均不顯著。λ的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P顯著為負,固定效應模型中存在明顯的樣本選擇偏誤,需要使用Heckman兩階段模型進行修正。未被觀察到的因素使持續存在與更低的產出波動相關。樣本選擇偏誤使資本密集度、產品種類系數被低估。由表3第2列和第3列可知,采用工業銷售額和工業總產值等指標進行替換,結論仍非常穩健。
接下來對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和進口中間品種類多樣性進行檢驗,以檢驗結果的穩健性。由表4可知, 在HS8層面上,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及種類多樣性均與企業產出波動之間存在“U”型關系。到達某臨界值之前,企業進口中間品種類多樣化程度越高,則產出波動越小;到達某臨界值之后,進口中間品種類多樣化程度越高,則企業產出波動越大。在HS6層面上,兩者都與企業產出波動存在“U”型關系,與主要回歸結果結論一致,這說明進口中間品多樣性不同的衡量指標并不會影響回歸結果,結論仍很穩健。企業規模、資本密集度等變量的估計系數變化不大。下面為了節約篇幅,不再匯報,以下各表類似。

表4 進口產品多樣化與產品種類多樣化估計結果
接下來將分出口狀態*根據出口交貨值是否大于0,將全樣本分為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樣本。、出口密集度高低分析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企業產出波動的影響,具體結果見表5。由表5可知,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中,進口中間品多樣性與企業產出波動之間存在“U”型關系,說明無論企業是否出口,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產出波動均具有非線性的影響關系。將出口企業進一步分為高出口密集度企業、中出口密集度企業和低出口密集度企業,表5表明出口密集度中等以及較低的企業中,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降低企業產出波動的作用系數偏大;而出口密集度較高的企業作用系數偏小。出口密集度高的企業,通常是“純出口企業”或加工貿易型企業,這類企業對從外國進口中間品的依存度較高,位于全球產業鏈上的中間環節,容易受到上下游沖擊的影響,通過進口多樣化中間品的多樣化效應降低波動的能力較弱。因此,隨著企業出口密集度的增加,進口中間品多樣性的作用系數在變小。

表5 分出口狀態和出口密集度高低企業的樣本估計結果
將全樣本企業分為東部地區企業、中部地區企業和西部地區企業*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11個省(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10個省(自治區),西部地區包括四川、重慶、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10個省(自治區)。該分類參考了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劃分,在具體處理過程中又根據具體情況做出特殊處理,其中,將廣西、內蒙古劃為中部地區,主要考慮到這兩個省份的對外開放程度比其它西部省份更高,這兩者的對外貿易總額遠遠高于陜西、甘肅等典型西部省份對外貿易額的平均值。,分地區研究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企業產出波動的影響。同時考察進口中間品多樣性的一次項對企業產出波動的影響,具體見表6。由表6可知:東部地區企業樣本中,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企業產出波動具有顯著負向作用,進口中間品多樣化程度越高,則企業產出波動越小;中西部地區企業樣本中,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企業產出波動也具有顯著負向作用,結果較穩健。這說明進口中間品多樣性會通過替代效應降低企業產出波動。

表6 分地區企業樣本估計結果
接下來添加進口中間品多樣性的二次項,進一步分析其對企業產出波動的作用,結果見表7。由表7可知:東部地區估計結果與主要回歸模型結論一致,一次項的系數顯著為負,二次項系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東部地區進口中間品多樣性與企業產出波動之間存在“U”型關系;中部地區若以工業增加值來衡量產出,則進口中間品多樣性與企業產出波動之間存在“U”型關系,若以工業銷售額和工業總產值來衡量產出,則該關系并不顯著,因此中部地區存在“U” 型關系,但并不顯著;西部地區企業樣本估計結果表明,進口中間品多樣性與企業產出波動之間的“U”型關系并不顯著;東部地區企業進口中間品多樣性的均值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東中西部地區的估計結果存在明顯的差異,可能由于中國的工業布局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且東部省份企業的外向程度更高。這反映了隨著進口中間品多樣性程度的增加,其“U”型關系更加明顯。

表7 分地區企業樣本估計結果(二)
當進口中間品多樣性程度較低時,替代效應起主導作用,表現為進口多樣化的中間品可以降低企業產出波動;而隨著進口中間品多樣化程度的提高,超過臨界值后,互補效應和創新效應發揮主要作用,多樣化程度越高,企業產出波動越大。東部地區部分企業的多樣化程度越過臨界值,呈現顯著“U”型關系。結合表6的研究結果可知,中西部地區絕大部分企業的多樣化程度尚未到達臨界值,進口中間品多樣性與產出波動呈現負相關關系,即只呈現出“U”型關系的左側。
五、結論和啟示
通過研究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企業產出波動的影響的研究,得到如下結論:
(1)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企業的產出波動具有“U”型關系。在到達臨界點之前,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企業產出波動具有負向作用;到達臨界點之后,進口中間品多樣性程度越高,則企業產出波動越大。這是因為在臨界點之前,進口中間品多樣性主要是通過替代效應、多樣化渠道來降低外部沖擊;到達臨界點之后,進口中間品多樣化程度越高,主要通過互補效應、企業新產品創新發揮作用,導致企業產出波動隨之變大。
(2)無論企業是否出口,進口中間品多樣性與企業產出波動之間均具有顯著的“U”型關系。隨著企業出口密集度的增加,進口中間品多樣性的作用系數變小;東部地區企業中“U”型關系顯著;中西部地區企業進口中間品多樣性對產出波動具有顯著的負向關系,這是因為絕大部分企業的多樣性仍處于“U”型關系臨界點的左側。
(3)企業規模、勞動生產率、產品種類多樣性與企業產出波動具有負向關系。企業規模越大,勞動生產率越高,產品種類越多,則企業的產出波動越小,反之則越大。同時,資本密集度、資產負債率對企業產出波動具有顯著正向作用,資本密集度越高,資產負債率越高,企業的產出波動越大,反之則越小。
綜合研究結論,可以得到如下的政策啟示:企業應當開拓多樣化的進口渠道,從多個國家(地區)進口所需的中間品;增加進口中間品產品種類,以降低產出波動;實行多樣化進口策略,盡可能增加市場關聯程度較低的市場進口量。同時,企業應該加大國內中間品的采購力度,避免過度依賴國際市場,以減輕多方面外來沖擊的影響,規避產出波動負面影響。
陳勇兵,仉榮,曹亮. 2012. 中間品進口會促進企業生產率增長嗎:基于中國企業微觀數據分析[J]. 財貿經濟(3):76-86.
聶輝華,江艇,楊汝岱. 2012. 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使用現狀和潛在問題[J]. 世界經濟(5):142-158.
夏立軍,陳信元. 2007. 市場化進程、國企改革策略與公司治理結構的內生決定[J]. 經濟研究(7):82-95.
楊曉云. 2013. 進口中間產品多樣性與企業產品創新能力:基于中國制造業微觀數據的分析[J]. 國際貿易問題(10):23-33.
張少軍. 2013. 外包造成了經濟波動嗎:來自中國省級面板的實證研究[J]. 經濟學(季刊)(2):621-648.
ACEMOGLU D , ZILIBOTTI F. 1997. Was prometheus unbound by chance? risk, diversification,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4): 709-751.
AMITI M, KONINGS J. 2007.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5):1611-1638.
BACCHETTA M, JANSEN M, PIERMARTINI R, et al. 2007.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s an absorber of external shocks [R]. Preliminary Darft.
BARRELL R, GOTTSCHALK S. 2004. The volatility of the output gap in the G7 [J].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188(1):100-107.
BEJAN M . 2006. Trade openness and output volatility [R]. MPRA Paper, No.2759.
BUCH C M, DOPKE J, STROTMANN H. 2009. Does export openness increase firm-level output volatility [J]. World Economy, 32(4):531-551.
CALDERON C, LOAYZA N, SCHMIDT-HEBBEL K. 2005. Does openness imply greater exposure [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Vol.3733.
CASELLI F, KOREN M, LISICKY M, et al. 2012. Diversification through trade [C]. 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Meeting Papers, No. 21498.
CAVALLO E A. 2007. Output volatility and openness to trade: A reassessment [J]. Economía, 9(1):105-152.
CHUN H, KIM J W, MORCK R, YEUNG B. 2008.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firm-specific performance heterogeneity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9(1):109-135.
COE D T, HELPMAN E. 1995.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9(5):859-887.
COMIN D, MULANI S. 2006. Diverging trends in aggregate and firm volatility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8(2):374-383.
COMIN D, MULANI S. 2009. A theory of growth and volatility at the aggregate and firm level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56(8):1023-1042.
COMIN D, PHILIPPON T. 2006. The rise in firm-level volatility: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D′ERASMO P N, MOSCOSO-BOEDO H M. 2013. Intangibles and endogenous firm volatility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C]. 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 meeting Papers, No 97.
ESCAITH H, GONGUET F. 2009.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real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financial shocks in globalized production networks [R]. WTO Working paper, No.ERSD-2006-06.
ESCAITH H, LINDENBERG N, MIROUDOT S. 2010.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s and trade elasticity in times of global crisis [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taff Working Paper, No.ERSD-2010-08.
GABAIX X. 2005. The granular origins of aggregate fluctuations [J]. Econometrica, 79(3):733-772.
GIOVANNI J D, LEVCHENKO A A. 2009. Trade openness and volatility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1(3):558-585.
GIOVANNI J D, LEVCHENKO A A, MEJEAN I. 2014. Firms, destinations,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 [J]. Econometrica, 82(4):1303-1340.
GOLDBERG P K, KHANDELWAL A K, PAVCNIK P, et al. 2010. 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evidence from India [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4):1727-1767.
HADDAD M, LIM J, PANCARO C, et al. 2010. Trade openness reduces growth volatility when countries are well diversified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46(2):765-790.
HALPERN L, KOREN M, SZEIDL A. 2009. 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8):3660-3703.
HECKMAN J. 1979.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 [J]. Econometrica, 47(1):153-161.
KOREN M, TENREYRO S. 2013. Technological diversification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1):378-414.
MALIK A, TEMPLE J R W. 2009. The geography of output volatility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0(2):163-178.
PARTEKA A, TAMBERI M. 2013. What determines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empirical assessment [J]. The World Economy, 36(6):807-826.
THOENIG M, THESMAR D. 2004.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the rise in firm level uncertainty [R].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4761.
VANNOORENBERGHE G. 2012. Firm-level volatility and expor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6(1):57-67.
(責任編輯張坤)
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Reduce Firm-level Output Volatility:Analysis of Diversification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s
JIANG YinJ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egenrent, Wuhan Uniuersity, Wuhan 430072)
Based on matched information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Dataset and Customs Database from 1999 to 2007, Heckman selection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versification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s on firm-level output fluctu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stitution effect, complementary effect and innovative effect brought by diversification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s.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U” 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ersification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s and output volatility in general.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U” shaped relationship is more obvious in plant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which have imported more types of products, while there is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ersity and output volatility in plants located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influence of diversity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 is less on plants with higher export intensity.
diversification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goods; output volatility; external shocks
2015-09-16
蔣銀娟(1988--),女,湖南衡陽人,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工業化中期階段典型國家經濟發展模式比較分析及對中國的啟示”(11JJD790030) 。
F746.11
A
1001-6260(2016)05-004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