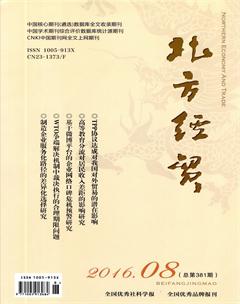無產權車位變相銷售土地增值稅收入確認探討
程偉生
摘要:無產權車位變相銷售,是土地增值稅征稅范圍所確定的轉讓行為的實際表現形式,其因此所取得的收入應計入土地增值稅清算收入,其成本同時也應允許扣除。
關鍵詞:無產權車位;銷售;土地增值稅
中圖分類號:F8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6)08-0097-02
當前社會,私家車數量的不斷增加以及城市空間的不斷縮小,導致人們對車位的需求不斷攀升,很多車主在購置房產時都將房地產開發企業能否提供車位作為考量購買與否的重要標準,甚至有人將購買車位作為投資手段。然而一個現實情況是,房地產開發企業所售車位并非都能辦理產權。無產權的狀態造成了車位轉讓在物權法上的困境,采取變相銷售便成為了轉讓無產權車位的主要途徑,例如有的房地產開發企業與業主簽訂一次性轉讓車位使用權合同,或者通過與業主簽訂為期二十年的車位租賃合同并將二十年之后的車位使用權予以贈送等方式變相銷售車位。然此類因變相銷售地下車位而取得的收入應否作為土地增值稅清算的收入,法律并無明確規定,這就給實務中的處理埋下了爭議的種子,各省規定難以趨同,形成兩類主要意見:一類認為實質重于形式,將無產權地下車位的變相銷售收入確認為土地增值稅清算收入,同時允許成本扣除;另一類則更加贊同形式重于實質,將無產權地下車位的變相銷售收入不確認為土地增值稅清算收入,同時不允許成本扣除。
一、無產權車位變相銷售應否確認收入的處理方式
無產權地下車位一般包括兩種:一種是人防車位,另一種是非人防無產權車位。物權法要求只有不動產的所有權人才能將其享有處分權的不動產進行轉讓。即使房地產開發企業全然不顧物權法的規定,與車位買受人簽訂無產權車位買賣協議,雖然從合同法上并不會否定這份協議的效力,但是從物權法上卻無法得到保護,因為此時的房地產企業身處無權處分的洼地。實務中房地產開發企業通常會采取變相銷售來處理其無法取得產權或者產權不明的地下車位,以實現其最終的商業目的。
第一類處理方式堅持實質重于形式,認為地下車位變相銷售應該視同銷售,第二類處理方式則更趨向于形式重于實質,在處理地下車位的問題上重點考慮車位的產權,如果車位能夠取得產權,則因為轉讓而取得的收入應征收土地增值稅,其相應的成本也允許扣除;而如果車位本身無法取得產權的話,那么房地產開發企業變相銷售所取得的收入便無繳納土地增值稅的必要,其相應的成本當然也無法進行扣除。
二、轉讓行為的確認
遼寧、新疆等省市對地下車位的轉讓,一律采取了“看產權”的態度,對車位能否取得產權將導致兩種截然不同的土地增值稅處理效果。于是我們不禁要問,土地增值稅確定的征稅范圍與車位能否取得產權之間存在必然聯系嗎?如果存在這種聯系,是否增加了一種課稅要素?如果是一種課稅要素,那么《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為何并未明確?到底是條例立法的疏忽,還是稅法與私法協調的空白?在實務中,有產權車位發生轉讓并因此取得收益,應當課征土地增值稅,并無疑問。更多的情況在于,人防車位等無產權車位,能否不考慮產權的因素,進入土地增值稅的征稅范圍。我國現行土地增值稅從開征伊始,就扮演著規范房地產市場秩序,合理調節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角色。作為課稅對象的增值額,便是納稅人轉讓房地產的收入減除稅法規定準予扣除項目金額后的余額。從這一點上講,土地增值稅更像是“第二企業所得稅”,是一種資本利得稅。它不應該因為實際發生轉讓的房地產無法取得產權而裹足不前,因為此時土地增值稅所予以考慮的房地產增值或許已經出現。我們應該明白土地增值稅并不是針對轉讓行為本身征稅,而是對因轉讓行為所引起的增值額進行評價。正因為如此,土地增值稅并未將納稅義務發生時間規定為產權轉移之日,而是將房地產轉讓合同簽訂之日規定為土地增值稅的納稅義務發生時間。房地產轉讓合同的簽訂,往往預示著實際轉讓行為已經發生。
三、土地增值稅沒有法律擬制,何來“視同銷售”
河南、天津、青島等地認為,應當按照與經濟上的事件經過、事實及情況相當的法律形式征稅,于是將變相銷售的行為按照視同銷售進行處理,在此基礎上課征土地增值稅。這種法律形式不是真實存在的,而是被擬制的。我們不禁要問,在《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確定的征稅范圍中,并不存在立法擬制,那么作為各地的規范性文件又何來“視同銷售”?
第一,法學上的擬制,是有意地將明知為不同者,等同視之。是為了實現法的價值,往往通過決斷性的虛構事實,運用類比推理,將不同事物同等對待,以實現相同法律效果,或將相同事物不同對待以實現不同法律效果的法律方法。
第二,稅法本身的不完善以及稅法對穩定性的追求需要法律擬制。稅法漏洞的存在,或嚴格依法將導致呆板甚至不良,從而不能實現其本身所欲實現的價值,即惡法的存在,是法律擬制出現的重要原因,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變相銷售本就應該涵蓋在土地增值稅所規定的“轉讓”行為之中,既然可以涵蓋,說明對于土地增值稅并不存在規定的漏洞,自無進行法律擬制的必要。
第三,法律擬制應通過立法予以固定。站在稅法的維度上考慮,法律擬制固然可以彌補稅法上的漏洞,縮小社會與稅法之間的缺口,實現稅收的公平負擔,但不管怎樣粉飾,都抹不去它謊言的本性,謊言不是真實,而稅法同其他法律一樣,主張要“以事實為依據”,根據事實來判斷是否踏人了課征的門檻。同時如果不對法律擬制加以合理的限制,就有可能使法度和綱紀失去生存空間,稅收法定也將淪為一紙空談。從某種意義上講,法律擬制本身就是一種立法形式,其直接、硬性地將不同稅法事實等同視之,使原本嚴格按照稅收法定原則不需要納稅的行為步入了稅法的殿堂,因而完全屬于立法權的當然范疇,自然應遵循稅收法定原則。綜上所言,且不論河南、天津、青島等地稅務機關以規范性文件作出法律擬制的必要性,就算需要作出“視同銷售”的法律擬制,也應該通過立法的方式在土地增值稅相關法律上予以固定。拋開實務但就法理而言,其擬制效力顯然是值得商榷的。
四、基于稅法的變相銷售合同評價
《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規定對發生轉讓房地產并因此取得相應收益的行為納入征稅范圍,那么房地產開發企業與業主簽訂的旨在實現轉讓的“變相銷售”合同,稅法應該如何評價?是將其看作房地產發生轉讓的標志,還是優先于產權登記,亦或是其他?
從以上的兩個問題可以看出,房地產產權是否轉移到以業主為代表的買受方不再是關鍵,只要通過合同等證據能夠證明確實發生了實質轉讓,受讓方也因為出讓方對合同權利義務的履行而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或者處分房地產的權利,那么課征土地增值稅便理所當然了。這里涉及的一個本質問題便是到底轉讓行為的標志是什么,是變更房地產權屬,還是簽訂的實質轉讓合同?站在民法的角度上,我國《物權法》對于基于法律行為的物權變動,明定債權形式主義。一方面規定,依照該法第9條,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動產物權變動采用登記成立主義;另一方面,該法第15條規定:“當事人之間訂立有關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不動產物權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外,自合同成立時生效;未辦理物權登記的,不影響合同的效力。”此種規定意味著:其一,物權變動的原因行為與物權變動的結果不同。登記并不是針對物權變動的原因行為,而是針對不動產物權變動所采取的一種公式方法。因而,即使未履行登記手續,也不影響物權變動原因行為的效力。其二,盡管作為物權變動的原因行為有效,也不一定必然引起物權變動的效果,但這絕不意味著物權的變動還須當事人達成有別于“債權合意”的“物權合意”,物權能否依法變動實際上還取決于原因行為的當事人是否履行其申請登記或者協助登記的義務,而此種義務是原因行為的當然內容。換言之,要使不動產物權發生變動,只要有當事人之間的債權合意即可,不以登記為必要。它同時要求的“受讓方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或處分該房地產的權利”,也只是表明需要受讓人通過轉讓合同達到獲取不動產的實際控制權罷了。于是我們發現,民法上對轉讓的認定標準顯然與這里的稅法上的規范性文件出現了分歧。站在經濟的實質主義立場,它往往在這個時候強調稅法對借用概念及其標準進行解釋的獨立性,不受其在民法中含義的約束。這種做法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實質課稅的思想,但不得不考慮其溢出稅收法定主義的可能性。然而不可不察的是,《土地增值稅增值稅暫行條例》將納稅義務的發生時間設定為房地產轉讓合同。簽訂之日,并未考慮產權是否登記,也就是說土地增值稅更加關注的是實際轉讓行為的發生,因為此時已經具備了土地增值稅所評價的增值額出現的可能性,而不必非得等到產權發生轉讓,因為像無產權車位本身就不具備取得產權的可能性。
五、結語
現行的地下車位變相銷售土地增值稅處理模式,我們將其歸納為兩類:一種認為實質重于形式,應視同銷售,予以課征土地增值稅;另一種則認為形式重于實質,先看產權,可以取得產權,則進入土地增值稅的課征范圍,相反,不能取得產權,則不予征稅。在分析地下車位變相銷售時,不管采取上述哪種處理模式,都應該回歸到土地增值稅的課稅范圍上進行討論,方有價值。在此基礎上,轉讓行為的判定,也就成為了焦點。土地增值稅所稱的轉讓是房地產通過買賣或者其他方式轉移的行為,從一開始就不應受產權登記與否的限制,而應該把目光集中在實際發生的轉移上。它與民法上物權變更的登記無關,一旦具備了事實上的轉移就應該予以征稅。至于事實上的轉移與否則取決于債權行為和其他行為的實際情況。綜上所述,無產權車位變相銷售,是土地增值稅征稅范圍所確定的轉讓行為的實際表現形式,其因此所取得的收入應計人土地增值稅清算收入,其成本同時也應允許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