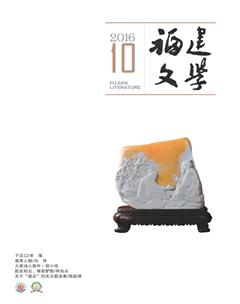隨筆三章
◎傅翔
隨筆三章
◎傅翔

傅翔,1972年生,1994年大學畢業。曾獲曹禺戲劇獎評論獎、田漢戲劇獎評論獎、中國文聯文藝評論獎等獎項。著有《不合時宜的思想》《我的鄉村生活》《小說手冊》等。現為福建省藝術研究院一級作家。
被讒言淹沒的吳起
吳起是戰國時著名的軍事家和改革家,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當時,他的軍事家的聲望是和孫子相比肩的,因為他的兵法和孫子兵法同樣流傳于世,甚至直到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吳起的身世頗多傳奇,包括他的少年,然而,畢竟相距太過遙遠,我們所知道的已經只剩皮毛,想要讀懂這個大人物的企圖也就微乎其微了。
有限的史料觸動我的是吳起近乎堅忍的一生,他那悲劇般的命運與深孚眾望,他那矢志不移的追求與勇往直前的勇氣,他的剛毅與勁直,他的殘忍與不擇手段,他的粗暴與不近人情……而這一切到底何是何非,史料的記載又往往自相矛盾,令人無法感受到真正的吳起的存在。司馬遷的《史記》也曾為吳起立傳,但關于他的身世,后來的史學家又認為此傳“不詳”,甚至有“不少錯誤”。對于我們這些以史論人的后來者而言,這簡直就是一種折磨了,那我們到底應該相信誰呢?
《史記》中有一段是關于吳起少時的事跡的,說的是吳起年少時想用千金家財游歷出仕,但終于沒有成功,而家財耗盡,由此被鄉人嘲笑。吳起一怒之下殺了嘲笑者三十余人,被逼離家逃亡。與母親訣別之際,他咬臂發誓:“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且不說這件事是否可信(因為它是作為魯人誣陷吳起的話出現的),單從這件事本身來看就足以讓我們不寒而栗。畢竟三十多條人命啊,即使就是殺人魔頭也不過如此了,吳起又還有什么資格與心情說那句豪言壯語呢?即便就是做了卿相,他又怎能逃得了干系回衛國呢?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可見,這顯然是誹謗,不足信,不然就連司馬遷也會放他不過,更何談立傳呢!而賢人曾子就更不會收他為弟子了。
以合理的邏輯推論,嘲笑一事可能存在,打架傷人之事亦有可能,吳起一氣之下離國并說那句豪言壯語也即合于情理。畢竟,謠言并非空穴來風,它往往也源于事實基礎上的捕風捉影、夸大其詞。然而,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司馬遷的如椽巨筆還是給吳起下了另一個致命的定論,那就是吳起“殺妻以求將”這一件并不光彩的事。這件事在傳記里提到兩次,一次是作為小人構陷吳起的謠言出現的,另一次則是司馬遷作為史實記錄下來的。說的都是同一件事實,即吳起在魯國為官時,正值齊國來攻打,魯國欲拜吳起為將,可因吳起之妻是齊國人,魯國國君心有余忌,疑而不用,于是吳起只好殺妻以表心跡,從而做了統帥,且大破齊兵。這無疑是一個驚心動魄的事件,如果是真,那就足以說明吳起確實是個兇殘而寡仁寡義的人,不僅為了功名不擇手段,而且薄情寡義到了近乎野獸的地步。畢竟是妻子啊,難道朝夕相處的恩情竟不如一個自信早晚可以獲得的功名,更何況還要親手殺害呢?
顯然,司馬遷在這里犯下了致命的錯誤,那就是他太過于相信民間流傳的口頭歷史了。就從這個傳記本身來說,疑點很多:其一,如果此事是實,那小人就不要拿這事大做文章,甚至于在魯國國君面前去說這件事,因為如此駭人聽聞之事,作為本國的國君不會不知道,更何況還是朝中大臣,而國君也就不會因這樣的讒言而懷疑吳起,甚至辭退他。其二,如果此事是實,那本傳后面記載的關于吳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甚至為士卒吮疽等這些事就不可理解。一面是近乎慘無人道,毫無人情可言,一面又如此“廉平”,且“盡能得士心”,如此的反差我想就是再怎么不擇手段或作秀都是做不出來的。其三,吳起聲名甚著,不僅在魏文侯時如此,而且到武侯時,小人要害吳起,也說他“節廉”,是“賢人”。到了吳起遭讒入楚,楚悼王更是“素聞起賢”,一到就讓他做了宰相(司馬遷的記載此處有出入,實際上是先為宛守,后來才為令尹,即為相)。由是觀之,這個“賢”字在當時的分量就足以否定前面的“殺妻”。在當時儒家禮制大得其道,各國極力推薦“賢人”的背景下,“殺妻”的吳起是無法有如此顯著的聲名的,更不用說出將入相了。
毫無疑問,司馬遷的傳記確實如后來史學家所說的有“不少錯誤”,這篇傳記記載的許多細節也更像是民間流傳的版本,而非真正的史實。如此豐富的對話記載到底依據在哪里?我想是不得而知的。也許,司馬遷正是想用一種文學的方式來為人物樹碑立傳的,它首先求的并不是真實,而是一種生動的形象。而今人卻剛好舍本求末,并不想把它當作傳記來讀,而是當作史實來研究,如此一來,哪能不生出許多疑問?
由此,我們就不能跟司馬遷較真了,而只能細心地去揣摩,因為說到底,民間流傳以訛傳訛的甚多,甚至往往自相矛盾也在所難免。從本傳看來,吳起為將才是被全面肯定的,不僅極富軍事謀略,而且善于帶兵,深得士兵的心。他不僅與士兵同吃同住,同甘共苦,而且極為關心體貼士兵的冷暖,為士兵排憂解難。其間記載的一個細節是他為生病的士兵吮疽,這感人至深的行為本非一般人可為,也非作秀可為,可在司馬遷的傳中卻被消解了。消解來自于這士兵的母親,他母親聽說不僅不高興,反而哭了,哭的理由是這士兵的父親當年就是因為吳起為他吮疽而很快戰死在疆場的,這下,她該擔心同樣的厄運臨到她兒子了。這種擔心自然沒有邏輯上的合理性,但卻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吳起自己口中的一句話,即“使士卒樂死”。能夠為士兵不惜性命的將帥怎不令他的士兵前仆后繼,勇于獻身呢?
對于吳起的將才,就是在魏文侯面前說吳起“貪而好色”的魏相李克也不得不承認,說他“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要知道,司馬穰苴可是春秋時赫赫有名的大將,長于治兵,且有兵法行世。由此可知,吳起當時的兵家地位是相當顯赫的,這一點不會被埋沒。
吳起被埋沒的恰恰是他更為重要的抱負,是作為法家改革家的聲望。這一點連司馬遷也只是點到為止,可在另一些典籍中卻不乏這樣的記載。這些記載恰恰有利于我們全面客觀地看待吳起,也從另一個側面校正了《史記》的錯誤。
重新梳理一下吳起一生的經歷大有必要。吳起生年不詳,為衛國人。年輕時據說曾學于曾子,師事過子夏。初為魯將,曾大敗齊兵,后遭讒赴魏,佐李克改革法制,整頓軍備。接著又受文侯重用,任西河郡守,甚有聲名。武侯時,他被舊勢力王錯排擠,出奔楚國,悼王任他為宛(今河南南陽)守,很快又升為令尹。相楚期間,他堅持明法審令,裁減冗員和無能官吏,使舊貴族至邊地墾種,收其祿,以撫養訓練戰斗之士。曾南收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使國勢日臻強盛。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他避入王宮,被亂箭射死。以此看來,吳起人生有兩個重要階段,一是任西河郡守時,二是任楚相時。在西河,他甚有聲名,這聲名顯然不僅僅是軍事上,而更重要的是治理上的,是政治上的。這點在《史記》上也有含蓄的一筆,講的是年少的武侯乘船視察西河時,對山河之固相當得意,大加贊美,而吳起的對答卻掃了武侯的興致,他說,“在德不在險”,還危言聳聽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接著,吳起在與田文論功時也毫不客氣地自夸“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而賢相田文竟也說不如他。(此處記載有錯,田文為相時,魏國國君為昭王,而吳起早已死去)由此一看,這吳起還真是個能人,治理國家還確實有一套,而不僅僅是一介武夫,難怪楚悼王會“素聞起賢”,并起用他為相了。
這下,吳起終于做了卿相,若當初的誓言為真,他真該衣錦還鄉回衛國一趟了。可吳起似乎根本就無暇顧及這一己之私,他的抱負一般人看不到,也感覺不到。《史記》這樣說他:“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斗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縱橫者。”吳起的思想見解與改革可以考見的就只這一片段,《史記》的簡約由此可見。實際上,吳起和商鞅一樣同為秦、楚時代變法的兩位主角,在法家的歷史上是有著重要地位的。他和商鞅一樣都獲得君主的信任,都敢作敢為地實行自己的主張與理想,最終也都遭到權貴的忌恨與殺害。不同的是商鞅因用秦久而成功,吳起則因用楚短而失敗。
再翻典籍,除了沿用照搬《史記》的外,記載吳起的不多,但卻很重要,現抄錄于下:
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減百吏之祿秩,捐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韓非子·和氏》)
吳起謂荊王曰:“荊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為也。”于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呂氏春秋·貴卒》)
這兩段記載相當真實地印證了《史記》中的那段話,我們由此看到,吳起并非純粹的沽名釣譽之人,他一定深切地為自己的理想與抱負所激勵著,一定有著清晰的看見與獻身于事業的勇氣,不然,他就不可能舍身與強大的貴戚為敵,甚至于到了“刻暴少恩”(司馬遷語)的地步。他敢廢公族,敢收封君之爵祿,敢令貴族開荒,這若沒有極大的勇氣與信念,是不可思議的。
就是這樣一個開時代之先河的法家政治家,他的改革卻沒有像子產作刑書一樣享受“與人之誦”的待遇,雖然也曾讓楚國日臻強盛,但終究還是因樹敵太多,被貴戚找到機會亂箭射死了。這實際上并不僅僅是吳起一個人的問題,也就是說,不能像司馬遷一樣簡單歸罪于他的性格或無德。從他接受過的良好教育看來,他實在不至于如此無德與粗暴,更何況,他還曾勸魏武侯要修德呢,而他的賢名更是遠近可聞,因此,事情遠非這么簡單。
在一個重德的時代里,魯國小人甚至連他少時讀書的事情也不放過而大肆構陷,從而使魯國國君疑而不用吳起。小人說,吳起在曾子門下就讀時,他母親死了,而他竟然一直沒有回家守孝,于是連他的老師曾子也看不起他,而與他斷絕了交往。這件肯定又是無中生有的事與前面提到的兩件事(一是殺謗己者三十余人,二是殺妻以求將)一同構成了致命的中傷,這種攻擊確實非常有力,因為魯國是禮義之邦,只要抓住吳起無“禮”就足以讓他下臺滾蛋。
吳起顯然吃夠了權貴的誣陷與誹謗,他一生幾乎都是在詆毀中度過的,而命運的幾次起伏也都與此有關。可以想象,吳起一定意識到了禮制下貴戚的專橫與權勢,他們因著禮制的保護享受著寄生蟲般的生活與特權。吳起想要改變的恰恰是這些,而這些足以使他與權貴處于勢不兩立的境地,這是毋庸置疑的。誰會容忍一個出身下賤的吳起公然指手畫腳,來管權貴的生活并讓權貴的日子越來越難過呢?想想也是,權貴沒有理由放過這種得勢忘形的“小人”,他們要做的必然是只要一有機會就向國君獻讒,排除異己。要是此路不通,那就必然是沒法推翻這種君王的統治,或者等待機會一舉剪除宿敵。商鞅慘遭車裂,韓非被囚并被毒死,就是這方面的鐵證。
作為法家的改革家,吳起的抱負決定了他的一生就是與權貴不懈地較量的一生。他命運的悲劇也更多是因為法家的抱負造成的,而不是兵家的理想。對于吳起而言,卿相才是他終身以求的地位,而不是為將。雖說當時他兵家的聲望遠高于法家,甚至也有兵法傳世,但這是與權貴的利益密切相關的。權貴更愿意肯定他的無疑就是他的將才,而不可能是他那政治家的改革與志向,因為他的改革恰恰危及了權貴的利益。
想及此,我們終于明白了有關吳起的記載,為什么小人要詆毀他殘忍與不仁不義,為什么李克能肯定他兵家的地位卻又說他貪名好色,而他又為什么總是屢屢遭讒以至于最終被誅射;而在另一面,他卻又能與貧苦的士兵及百姓同甘共苦,深得民心與士心,并且業績斐然,深孚眾望。顯然,這樣一個人物必定是有多種不同的版本的,而司馬遷的版本雖然也極力為他辯護,但他所處的立場決定他只能同情吳起的命運,而對吳起的改革惹怒權貴一事則歸結于吳起“刻暴少恩”。
這無疑可與子產的改革作個比較。子產之所以能“與人之誦”,那是因為他本身就是貴族,他作刑書的目的也僅僅在于“救世”。他做的是改良,而不是從根本上觸動貴族的利益。這點與吳起顯然有著本質的區別。吳起乃平民出身,他站立的是平民的立場,他要消除的正是貴族的特權與社會的不平等,他與貴戚恰恰是勢不兩立的。也正是從這意義上說,吳起作為重要的法家政治家的地位是被淹沒了,而留下來的史料記載就不能不被這漫天的讒言所影響,從而歪曲了歷史的真相。
“猴子變人”還在毒害下一代
女兒從幼兒園放學回來,突然對我說:爸爸,人是從猴子變來的嗎?我不由得一驚:誰告訴你的?女兒說:老師說的。我突然無語了,心中卻是格外難過,為我們的教育,為我們的孩子,為我們的未來!
我知道,我們這些年齡稍長一點的中國人都是相信人從猴子變來,好像天經地義的一樣,不用思考,也不用懷疑。可有一天,我終于知道,人類的起源至今還是科學沒有定論的宇宙十大奧秘之一,就像人無法知道死后往哪里去一樣,人從哪里來,這還是個謎。
是誰告訴我們說,人是猴子變的呢?難道是達爾文?還是馬克思?我想都不是,達爾文只是提出了進化論的思想,只是在《物種起源》的基礎上對人類的起源大膽地進行了一種猜想。這是一種科學允許的猜想,可誰會想到,這種猜想竟會成為中國人信奉的一種教條?馬克思也只是提供了一種理論,也是一種哲學與學說,他從來也沒有說,你們只可相信我說的,因為別的都不正確!沒有人擁有這種絕對的權威,即使希特勒也做不到。那我們應該相信什么?
也許是我們信奉極權與權威太久了,所以我們失去了思考,更失去了懷疑。這么簡單的一個事實,竟會讓我們熟視無睹這么多年!如果人是從猴子變來的,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說,蟾蜍是青蛙變的,烏龜是鱉變的,棕熊是熊貓變的……因為它們都很像,都有進化的可能?好在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好在我們不再像達爾文時代一樣無知,好在我們了解的東西越來越豐富,地球也越來越小了。我們終于知道,它們屬于不同的類,不同的類之間是不能進化的,進化只在同類之間進行,這正是生物學的最高原則。猴子的血注入人體,人就會死。人類就是人類,猴類就是猴類,長尾猴金絲猴不會變成猩猩,猩猩也不會變成人,烏龜也不會變成王八。所以,絕不是用一個模棱兩可的“類人猿”就可以混過去的,“類人猿”畢竟還是“猿”,還是猴類,它不是人,更不會是人的祖先。
如今,地球上還有這樣的祖先,他們是原始人,他們是真正的“野人”。他們三分之二生活在巴西原始的熱帶叢林中,還有一些生活在非洲等地。幾千年來,他們赤身露體,茹毛飲血,甚至自相殘殺,他們與大自然相依為命,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他們知道得很有限,工具也很簡陋,甚至只求果腹,但他們和我們長得一模一樣,身上沒有長毛,智慧也超群,甚至身高體重都沒有什么區別。在這樣一個科技與文明高度發達的時代,看到這些與世隔絕的我們的同胞與“祖先”,我們除了感慨,我們是否還想到了什么?
我們人類還可能是猿猴變的嗎?好在,我們擁有了DNA,檢測變得如此簡單與容易。科學在進步了,可我們的教科書還在教條一樣毒害著下一代,沒有人呼吁,沒有人行動,沒有人去改變……這才是我們的悲哀!
在這個科學家都集體消失的國度,我要告訴我女兒的是,人類的起源至今還是個宇宙間最大的奧秘,是個謎,這個謎希望你們去解開。我還會告訴她,中國遠古有“女媧造人”的神話,《圣經》里有“上帝造人”的記載,只要她想聽,我會慢慢地給她講這里的故事,因為這樣的故事比武斷而沒有科學定論的“猴子變人”好多了。
批評家與孕婦
初為孕婦,由于沒有經驗,常常是要有人給予指導的。在指導者的隊伍中,較為常見的不外三種人:一種是有過此類經驗的家庭婦女;一種是沒有此類經驗但了解相關知識的剛出道的醫生;還有一種就是既有此類經驗又有相關知識的女醫生。
在此,我想特別提到第二種人,即沒有此類經驗但習慣于指導別人的人。這種人因為體會不到別人懷孕的種種反應與痛苦,所以她的指導就變得更為飄浮,從而也更為書面與理論。當然,這種指導也就無法很準確地對癥下藥,因為書本的東西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是籠統的,無法有很強的針對性的。特別是在一些特例與個案面前,它總是顯得蒼白乏力。沒生育過與生育過的人肯定是不一樣的,生育過的人畢竟走過了這段路,她會知道書本知識有多少夸張與不實的成分,也知道不能全按書本的理論去指導別人。
第一種人的局限也是明顯的,那就是她只有個人的經驗而沒有全面的知識,一旦碰到別人發生的情形與她不同,她也就喪失了指導的能力。而一味地按她的經驗來指導,往往又會牛頭不對馬嘴,導致可怕的結果。正是從這意義上說,第三種人是最值得信賴的,她們既有此類經驗又有相關的知識。當然,經驗還是最為重要的,因為經驗本就是一種高度提取的知識,而且,經驗也并不是通常理解的只是私有的,還有多種渠道的經驗。我以為,經驗至少有兩種,一種是個人的經驗,一種是別人的經驗。一般的家庭婦女只限于個人的經驗,而醫生的經驗就多得多,如婦產科的醫生,她天天面對的都是這一類人,即使沒有個人的經驗,但別人的經驗聽得很多,自然也就駕輕就熟了,指導起來也是游刃有余的。作為專門的醫生,她要學習,要鉆研,碰到特殊的情況更是要研究,在書本與實踐經驗中找到一種和諧與統一,從而也就豐富了這一門類的知識。
假如把孕婦比作作家,那第一類人也就是作家,一個作家指導另一個作家的寫作無疑有非常直觀的經驗,但卻顯然不是最好的指導者,因為他的經驗往往不適合另一個人。而第二、三類人就是批評家,一個好的批評家應該就是第三類人,既有豐富的經驗,又有高超淵博的知識,而不是只有理論知識就肆意揮舞棍棒的人。可笑的是,如今的批評家自己沒有“生育”過,卻四處教別人如何“生育”,教寫作常識,教寫作技巧,儼然一個專家。這樣的人不用說都是很可笑的,就像一個沒生育過的黃毛丫頭教別人如何生育一樣,說到底還是無法讓人放心。最值得信賴的批評家還是要有自己的“孩子”,不管這“孩子”如何,至少他“生育”過,知道其中的感受。僅有理論和知識是不夠的,一定還要有豐富的經驗,而這經驗最好有自己的,也要有方方面面的間接經驗,只有這樣,才真正稱得上當之無愧的批評家。
責任編輯 林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