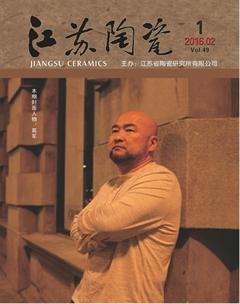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
周曙鋒
常言道:“壺有百象,人有百態。”紫砂壺因其所承載的審美藝術和人文價值而經久不衰,可以說文化內涵是它的生命和靈魂。一把沒有靈魂的紫砂壺只可以作為日常使用的器皿,卻不具備欣賞、把玩的價值,不能讓人為之沉醉。正如人生百態,每把壺也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使命,如果說“用”是基礎,“神”是核心,那“形”則是具體的表現形式與載體,它們將自身的使命凝聚于形,篆刻于魂,等待一位至情至性的人來一探究竟。初成的一把壺總帶著制壺藝人的氣味,他們以自身的心血、閱歷、格調制成一把壺,一只納于掌心的壺,卻深藏著浩瀚乾坤。
縱觀紫砂壺,其基本的器型不過三種:筋紋器、光器、花器。三者制作方法也是相互貫通,但每款壺的姿態不一,獨具各自風韻,清新或樸拙、典雅或神圣,讓人目不暇接、嘆為觀止。人們總說藝術來源于生活,而生活的酸甜苦辣總讓人來不及一一感受和品味,由此說來,紫砂壺這門藝術如此精彩紛呈,也是有緣可循了。
自古以來,梅、蘭、竹、菊便是歷代文人雅士反復吟詩作賦的對象,制壺藝人也偏愛它們。梅、蘭、竹、菊的清俊高雅著實為人所欽佩與嘆服,但此時仔細觀摩著這把“菱花壺”(見圖1),仿若置身于江南的菱花池邊,感受一池菱花以灑脫的行筆勾勒出清麗的風韻。早知曉梅、蘭、竹、菊“四君子”的高風亮節,而菱花之美雖是第一次心有所獲,卻也覺得能與四君子相媲美。
紫砂壺造型有“方匪一式,圓不一相”之說,這把“菱花壺”極好地融合了方、圓二字的精髓。壺身呈菱形花紋,整體圓潤飽滿、筋紋分明,菱花的脈絡清晰可見,線條流暢,未加過多的修飾與雕刻卻將菱花之韻味完美地融于壺身。壺身與壺蓋的銜接處,挺拔有張力而不失秀氣;壺蓋微微向上隆起,表面是惟妙惟肖的花瓣形狀;精致的壺鈕正像是美麗可愛的花蒂,雖小卻也分布紋絡,筋脈清晰;壺把與壺嘴相稱相攜,壺把粗至細,呈拉升的圓弧,細看其紋絡又是方形,握于手中舒適,方便提拿;壺嘴線條更是轉折有度,上部呈平嘴型,玲瓏俏麗,提升了精神氣態與韻味。將“菱花壺”整體穩固地置于桌面,亭亭玉立如清新的少女,又如清晨含露的花,嬌美柔軟而不失筋骨,遠觀光滑圓潤且清新秀麗,實則棱角分明、線條挺括,將“形”完美地表現了出來。
古有駱賓王《王昭君》詩云:“古鏡菱花暗,愁眉柳葉嚬”。“昭君出塞”的故事在歷史上廣為流傳,昭君有“皓月”之稱,集山水陰柔和天地溫和之氣,如此女子不遠萬里嫁去異鄉,促成了匈奴與漢朝友好達半個世紀之久。“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介女流作出如此決定,將自己的后半生都付諸于匈奴與漢朝的友好,猶豫艱辛、輾轉不眠的時光定是難以數計。駱賓王將入宮后的昭君與菱花聯系在一起,菱花清麗婉轉而暗自含香,難能可貴的是花謝后又生長出菱角,繼芬芳過后又以果實奉獻于世人。如果說菱花的氣質是來自于它自身的清麗,那么菱角則是來自于它的勇氣和堅韌不拔的毅力,這與溫潤而又堅毅的昭君正是相互輝映。
一把壺要做到引人共鳴,既要保證效果上的使用協調,又要凸顯藝術審美上的生動雅致,這正是考究其制壺藝人的技藝與審美。賞玩“菱花壺”使人遐思頓起,一種情、一段遙遠的歷史感呼之欲出。菱花清麗婉轉、菱角堅韌不拔,這正是做人所需的精神。年復一年的春夏秋冬,或溫暖、或繁盛、或清冷、或孤寂,都要自持己心,不忘初衷,在適當地時間做適當事,既要活得美麗柔軟,又要有一顆堅韌有余的心來應對波瀾頓起的人生。菱花以暗香、以清麗撫慰人的心靈,又以果實慰藉人的身體口腹,這其中又隱含了一層物盡其用的道理。生命短暫,唯有在漫長的季節里不斷積累成長,再以自身獨特的價值反哺,展現出昂揚的姿態,才不枉來人世一遭。“菱花壺”既給人一目了然的自然清新感受,其內涵更是層出不窮。壺有百態,一把壺、一種情,每位制壺藝人因自身閱歷的不同,所感受的情感也是不盡相同,但世間千姿百態的壺卻是終會覓得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