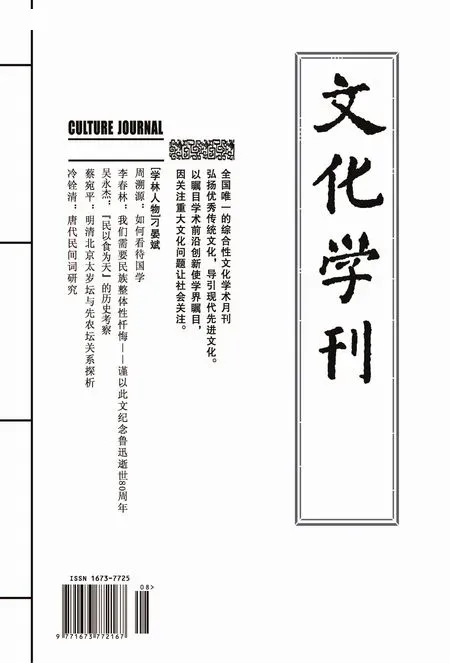明清北京太歲壇與先農壇關系探析
蔡宛平
(首都師范大學,北京 100048)
?
【文化遺產研究】
明清北京太歲壇與先農壇關系探析
蔡宛平
(首都師范大學,北京100048)
太歲壇與先農壇分別是我國古代農業社會對“時”神與“農”神祭祀崇拜的體現,其祭祀時間、活動等都有所差別。太歲壇在明清兩代的地位一直比較穩定,而嘉靖以后先農壇地位上升,逐漸包括其他壇闦。明清遵循追“諸神不罪”和壇闦獨立的原則處理兩壇差異,并形成融洽的關系,是明清兩代認識和處理“農”與“時”關系的集中體現,也是對太歲神特殊神格的尊重。
明清;北京;太歲壇;先農壇;諸神不罪;神格
明清北京的太歲壇與先農壇是皇家祭祀太歲神與神農氏的壇闦。自明永樂時在北京建山川壇,經過一系列變遷,最終形成了太歲壇,即包括祭祀主殿在內的整體建筑位于先農壇內的格局。這一格局容易誤導人們將太歲壇歸為先農壇的一部分,以往部分學者在研究時,也是重視先農壇,輕視太歲壇。太歲壇與先農壇不論是祭祀主神、祭祀時間,還是祭祀場所、祭祀活動都有很大的不同。兩壇在明清兩代的地位也有各自的發展過程。作為明清皇家對“時”神和“農”神的祭祀地點,太歲壇與先農壇的關系一方面體現了兩代對“時”與“農”關系的認識和處理方式,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古代多神崇拜體系下“諸神不罪”以及對“太歲神”等特殊神格尊重思想的重要體現。
對于先農壇和太歲壇,國內外學者曾做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董紹鵬、潘奇燕、李瑩等人研究成果頗豐,先后有《先農神壇》[1]《北京先農壇》[2]等著作,對明清北京先農壇沿革、建筑、相關禮儀進行了詳實、系統的研究。朱祖希兩篇名為《先農壇——中國農耕文化的重要載體》[3,4]的文章,對北京先農壇的建置沿革、建筑布局、文化積淀進行了比較詳細的介紹。姚安的《清代北京祭壇建筑與祭祀研究》一文在建筑沿革以外還初步探討了先農壇祀典陳設、儀式、樂舞和祭祀運作等內容。另外,黃愛平的《清代的炎帝祭祀及其文化內涵》[5]、曲英杰的《神農氏與先農壇》[6]等文章也對神農祭祀文化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然而,因為所研究的目的與視角不同,現今學者的研究大多還是集中于先農壇,對太歲壇多半只是順帶提及,具體到兩者的關系則更是鮮有學者研究。這為進一步探討明清北京太歲壇與先農壇的關系,提取其中所反映的歷史信息留下了空間。
一、明清北京太歲壇與先農壇壇闦關系變化
(一)奠定格局——洪武時期的山川壇
明太祖朱元璋鼎定天下,建都金陵,總結元亡教訓,強調“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7],認為“皆無禮法,恣情任私”[8]是元卒亡的重要原因。于是,他詔令群臣肇定祭祀禮儀。由此,太歲神和先農氏的祭祀禮儀也得到重構。但關于太歲之祀,朱元璋先是將太歲神從祀于圜丘。《明史·禮二》“郊祀之制”條載:“洪武元年,……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9]此后“又合祭群祀壇”,將之納入合祭,并行祭祀。但此時由于祀典未全,“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專祀”[10]。不久,明太祖“命禮官議專祀壇闦”[11],并以太歲、風云、雷雨為天神,以岳鎮、海瀆、天下山川為地癨,“各為壇專祀于國城之南”[12]。洪武三年(1370)二月,又以“諸神陰陽一氣,流行無間”[13]而合二為一,并增四季月將共祭。祀先農以及耕謖之禮也得到足夠的重視。洪武元年(1368)便有禮官議:“皇帝躬祀先農。禮畢,躬耕謖田,以仲春擇日。”[14]朱元璋準,并于洪武二年(1369)二月行謖田禮于南郊,祭先農氏。
制定祭儀的同時,明太祖也加緊在應天(今南京)城外修建祭壇。在建壇之初,明太祖就比較重視太歲壇和先農壇的修建。早在洪武二年(1369)就開始修建山川壇。《明實錄》載:“山川壇建于正陽門外,合太歲、風云雷雨、岳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共祭之。”[15]可見在洪武時期太歲之祭尚未獨立專祀,而是與風云雷雨、岳鎮海瀆等合祀于山川壇內。但按《太常續考》所載:
太祖乃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16]
洪武三年(1370),建山川壇于天地壇西(俗呼為地壇)。正殿七間,凡七壇:曰太歲,曰風云雷雨,曰五岳,曰五鎮,曰四海,曰四瀆,曰鐘山。兩廡各十五間,東廡從祀三壇:京畿山川、夏季月將、冬季月將。西廡從祀三壇:春季月將、秋季月將、都城隍。[17]
可知其時雖然是合祀于山川壇正殿,但已有“太歲壇”的獨立建置。
同是洪武二年二月,明太祖又“始建先農壇于山川壇西南”[18]。開始在山川壇旁的西南一隅修建先農壇。從此記載看,洪武時期的山川壇與先農壇修建之初便具有其獨立性。而對于洪武時期先農壇的規制和位置,洪武時編的《明集禮》另載:“壇在藉田之北,高五尺,闊五丈,四出陛。”[19]可見其建置已初具規模。此外,洪武時期其南的耕謖臺,北邊的神庫、神廚和宰牲亭,亦納于先農壇范圍。(見圖1)

圖1 《明集禮》先農壇圖
洪武九年(1376),包含太歲壇在內的山川壇全面告成,明太祖親自登壇告祀。而自山川壇成,其西南的先農壇、東南的具服殿建筑、壇南的籍田、東邊的旗纛廟、壇后的神倉等建筑便全被納入其范圍,共同組合成山川壇。《明實錄》有載:
建太歲、風云雷雨、岳鎮、海瀆、鐘山、京畿山川、月將、京都城隍諸神壇闦殿成。初,至是,始定擬太歲、風云雷雨、岳鎮、海瀆、鐘山、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隍凡十三壇,建正殿、拜殿各八楹,東、西廡二十四楹,壇西為神廚六楹,神庫十一楹,井亭二,宰牲池亭一。西南建先農壇,東南建具服殿六楹,殿南為藉田壇,東建旗纛廟六楹,南為門四楹,后為神倉六楹,繚以周垣七百一十二丈。……是日成,上告祀焉。[20]
由此可見,雖然洪武時期的太歲壇和先農壇起初各自修建,但最終組合成了“山川壇”(見圖2①[明]官修.洪武京城圖志[A].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24冊[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洪武年間的“山川壇”雖建于應天,但因其格局在永樂遷都后被照搬于北京,成為此后變遷的原本,所以可以說洪武時期的“山川壇”奠定了明清北京太歲壇與先農壇壇闦格局的基礎。

圖2 《洪武京城圖志》山川壇圖
(二)厘正祀典——永樂后明北京太歲壇與先農壇的地位變化
明成祖時,為遷都北京,大規模營建北京城。據《明太宗實錄》“永樂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條載:“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現過之。”[21]由此永樂帝便在北京南郊仿照南京山川壇也修建了一座山川壇。“永樂十八年二月,山川壇成。”[22]永樂帝在興建之初便在山川壇正殿旁增建了旗纛廟,在南京山川壇規制上有所擴大。而永樂所建山川壇便是明清北京太歲壇與先農壇的基礎壇闦。(見圖3)

圖3 《大明會典》山川壇總圖
永樂后至嘉靖間,歷代明帝沒有對山川壇格局進行大的變更,僅英宗天順年間在旗纛廟東邊增建齋宮一所。對此,明徐學聚《國朝典匯》有記:“天順三年二月,詔風雷、山川壇闦,創一齋宮。”[23]天順五年(1461)成書的《大明一統志》記載了嘉靖改制前山川壇的最終格局:“山川壇在天地壇之西,繚以垣墻,周回六里。中為殿宇,以祀太歲、風、云、雷、雨、岳、鎮、海、瀆,東西二廡以祀山川、月將、城隍之神。左為旗纛廟,西南為先農壇,下皆耕田。”[24]
明世宗嘉靖年間,嘉靖帝對太歲壇和先農壇進行規模較大的改制。其一是增建“天神壇”與“地癨壇”,將山川壇正殿中的天神、地癨全都請出單獨祭祀。《大明會典》載:“(嘉靖)十年,建天神、地癨壇于先農壇之南。”[25]其二是增建“神倉”。《春明夢余錄》有記:“嘉靖中,建圓廩、方倉以貯粢盛。”[26]按《明世宗實錄》所載:“恭建神癨二壇并神倉工成。”[27]神癨二壇與神倉皆建成嘉靖十年(1531)。二壇分祀天神地癨,降低了山川正壇的祭祀地位。而神倉的建設使先農之祀更加完備。其三是始建觀耕臺。《明史》記載:“(嘉靖十年)其御門觀耕,地位卑下,議建觀耕臺一。詔皆可。”[28]
另外一個至今爭議最大的改制為“建太歲壇”。嘉靖十年,明世宗依禮臣所奏“太歲之神,宜設壇露祭”[29],下令“建太歲壇于正陽門外之西,與天壇對”[30]。這次太歲壇的“建壇之議”在《明政統宗》中有記載:“(嘉靖九年)建太歲壇于神癨壇內。上命禮官考古太歲壇制以聞。禮部言:太歲之神……亦宜設壇露祭,但壇制無考,宜照社稷規制,少為減小,庶隆殺適宜,而祀儀不忒。報可。”[31]然而,在先農壇內卻完全找不到明代修建露祭太歲的遺跡。對于這一疑問,部分學者認為現存于太歲殿內的明代漢白玉須彌座可能為嘉靖時建的“太歲壇”。然而,早在洪武時所建的山川壇便采用“屋而不壇”的格局,雖名為“壇”,卻不專設露祭外壇。《明太祖實錄》載:“山川壇建二殿,一以棲神,一以望拜。”[32]山川壇成此格局是因為明時祭祀太歲諸神是采用“望祭”形式,其祭祀“拜位”設在殿外,本就屬于“露祭”。因而,承繼山川壇祭祀正殿的太歲之祀也不需要為了“露祭”而另外特意建壇。因此,嘉靖時按照神癨壇規制單獨建“太歲壇”的可能性很小。那么,嘉靖所建“太歲壇”是否為太歲殿內的漢白玉須彌座值得研究。
承上,洪武合祭時雖為合祭,但已有“太歲壇”的稱謂和建置。那么,其“太歲壇”之壇應指在正殿中的壇位。由此觀之,言漢白玉須彌座為“太歲壇”似乎可行。但是,嘉靖改制以后,明末成書的《太常續考》卻是如此記載太歲壇:
太歲壇,建于正陽門外之西,與天壇對。中為太歲殿①按《太常續考》成書于明末崇禎年間,明初《郊廟圖》等文獻皆記有“太歲殿”之稱,可見部分學者“太歲殿之名始自清乾隆帝時期”的論點尚有待商榷。,東廡為春秋月將二壇,西廡為夏冬月將二壇。前為拜殿,拜殿東南為燎爐,西為神庫、神廚、宰牲亭。亭南為川井(即山川壇舊井也),外為四天門,東為壇門。[33]
從這一記載看,太歲壇應指包括太歲殿、東西二廡、拜殿等在內的壇闦體系。若單言“太歲壇”為一個“漢白玉須彌座”而“與天壇對”便顯得有些牽強。另按成書于萬歷四十一年(1613)的《圖書編》載:“歲孟春、歲除遣太常寺卿祭太歲之神于太歲殿,四季月將從祀。”[34]可見,嘉靖改制后,太歲殿成為專祀太歲之所,兩廡也隨之成為其從屬。以此推之,嘉靖時所謂“建壇”可能是將天神地癨請出后,將原有山川壇正殿、兩廡、拜殿等壇闦體系整合,進而改建成以“太歲殿”為主導的壇闦體系,統稱為“太歲壇”。(另《國朝典匯》記:“太歲壇建太歲殿。”[35]從中也可以知道,太歲殿只是“太歲壇”壇闦體系的一部分。另外,這種情況也容易產生如個別文獻專稱先農壇瘞為“先農壇”一樣,單獨稱太歲殿為“太歲壇”的現象,如清初孫承澤所記:“太歲壇在山川壇內,中為太歲壇,東西兩廡,南為拜殿。”[36]即為此例。
對于嘉靖改制以后的“先農壇”,《明史》有載:“永樂中,建壇京師,如南京制,在太歲壇西南。石階九級。西瘞位,東齋宮、鑾駕庫,東北神倉,東南具服殿,殿前為觀耕之所。護壇地六百畝,供黍稷及薦新品物地九十余畝。”[37]由此記載可知,嘉靖以后的先農壇在南京先農壇的基礎上增加了齋宮、鑾駕庫、神倉、具服殿以及六百畝護壇地。其所含建筑和土地面積已大為增加,在整個山川壇壇闦建筑范圍內已占據了大部分面積,這為先農壇在此后發展中壇闦占主導地位奠定了基礎。因此,“萬歷四年,改鑄神癨壇祠祭署印,為先農壇祠祭署印。仍掌行耕謖事務。”[38]至此,包含太歲壇、神癨壇、旗纛廟在內的系列壇闦便統稱為“先農壇”。萬歷以后,先農壇的格局便一直沿襲下來,直到清代。
(三)繼承明制——清代先農壇的主導地位
清代自順治入關,便繼承明制,重建太歲與先農之祀。《清文獻通考》記載:“順治元年(1644),定每歲致祭太歲壇之禮。太歲殿在先農壇之東北,正殿七間,祀太歲之神。兩廡各十有一間,祀十二月將之神。前為拜殿,東南燎爐一。”[39]由此可知,清朝在入關之初便重建太歲神的祭祀,并繼續使用明代太歲壇壇闦體系。另外,《清世祖實錄》“順治十年三月壬申”條載:“詔舉行先農、先醫、及司牲神、祀典。”[40]可見,清帝很早便重視先農祭祀和耕謖禮儀。
清朝自建朝之初便繼承明代的總稱“先農壇”的最終格局。《日下舊聞考》“按語”有記:“天神、地癨、太歲壇位俱在先農壇內。”[41]可見,清朝最初便將天神、地癨、太歲壇皆納入先農壇闦體系。自順治至乾隆初年,先農壇壇闦體系沒有大的變化。(見圖4)

圖4 《郊廟圖》乾隆以前先農壇總圖
乾隆十八年(1753)乾隆帝“諭:朕每歲親耕謖田,而先農壇年久未加崇飾,不足稱朕癨,肅明?之意。今兩郊大工告竣,應將先農壇宇修繕鼎新。”自此開始,乾隆帝對先農壇建筑進行較大規模的改建。同年,乾隆下旨“先農壇舊有旗纛殿可撤去,將神倉移建于此”[42],將原有旗纛廟拆除,移建神倉。
乾隆十九年(1754),又下詔曰:“觀耕臺著改用磚石制造。欽此。”[43]將原本一祭一建的木制觀耕臺建成磚石構造,成為固定建筑。乾隆二十年(1755),皇帝再度下旨:“先農壇齋宮,改為慶成宮。”[44]將原有齋宮增建裝潢,并重新命名為“慶成宮”。至此,清代先農壇壇闦整體建筑體系終于完備。此后雖然多次修葺,但其壇闦格局未再有大的變動。(見圖5①[日]岡田玉山等編繪.唐土名勝圖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圖5 《唐土名勝圖會》先農壇圖
(四)“農”與“時”——兩壇合并格局的意義
明清兩代自洪武時期奠定格局,在經過一系列的變遷最后形成了以“先農壇”為主導的壇闦體系:“先農壇,一名山川壇,在正陽門外西南永定門之西,與天壇相對……中有天神壇、地癨壇、太歲壇、先農壇、耕田俱在其內。”[45]在這一格局中,太歲壇、天神壇、地癨壇與先農壇結合在一起。而太歲在明清兩代皆被歸為“天神”,也曾因此從祀于天壇,那為何反而脫離天壇,與先農壇相合?其實,明清兩代統治者都認為太歲之神既是“天神”又是“時神”。明清皇帝認為作為“天神”的太歲可助興云播雨,發育萬物。洪武年間祭太歲等神《祝文》有曰:“太歲之神、風云雷雨之神、岳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之神:惟神主司民物,參贊天地,化機發育有功,歷代相承有秋報之禮。今農事告成,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用伸報祭。尚享。”[46]而作為“時神”的太歲可調節雨旸,使農時不誤。明人何孟春曾說:“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寒暑行焉。今祭太歲、月將則固時與寒暑之神也。”[47]可見,明代對“太歲”統四時有深刻的認識。清代在“祈?九章”中也強調“雨旸時若”:“雨旸時若兮,玉燭全。粒我蒸民兮,迄用康年。”[48]此外,太歲在明清時更被認為是“統馭”天神、協和六氣之神,與農事順遂息息相關。清代“太歲壇六章”樂章有云:“于赫太歲,統馭百神。……王省維歲,有報有祈。六氣無易,平衡正璣。嘉生蕃祉,澤及?飛。”[49]其中,“六氣”指陰、陽、風、雨、晦、明,皆是農務順利進行的重要條件。太歲既統百神,調節六氣,農時不誤,自然與主管農事的先農神相輔相成。基于這種思想,明代便將兩壇壇闦鄰近建造,并統一管理,而清代則繼承其制。這種壇闦格局的形成體現了明清兩代對“農”神與“時”神關系十分密切的思想認識。
二、明清北京太歲壇與先農壇管理機構與祭祀時間、活動異同
(一)管理機構的重疊與變遷
有明一代,“凡祀事皆領于太常寺而屬于禮部”[50]。祭祀活動的主要管理機構是太常寺和禮部。另外,《大明會典》有載:“每遇祭太歲、月將,本寺官前三日進銅人,奏齋戒。前二日同光?寺官奏省牲,次日復命。”[51]可見在太常寺、禮部官員以外,還有光?寺等機構協助進行祭祀活動。這種制度在清代得到延續。
而太歲壇、先農壇作為壇廟,也有其特有的管理機構,即祠祭署。明清兩代,雖然太歲壇與先農壇的壇闦地位幾度變化,但壇廟的“祠祭署”卻一脈相承。早在明初洪武時期在南京修建山川壇時,便建立了“山川壇祠祭署”以專管山川壇內的太歲、先農、天神、地癨等壇闦。洪武時編成的《諸司職掌》有載:“山川壇籍田祠祭署:奉祀一員、祀丞一員。”[52]可見,該祠祭署常設有奉祀、祀丞兩個職位以處理一些事宜。而這一格局,在永樂遷都后得以繼承。《國朝典匯》記載:“先農壇祠祭署:(舊為山川壇藉田祠祭署,嘉靖九年(1530)改為神祗壇,萬歷四年(1576)改今名)奉祀一員、祀丞二員。”[53]可知,永樂以后北京翻建南京山川壇的同時,也設了“山川壇籍田祠祭署”管理壇闦,嘉靖時更名為“神癨壇祠祭署”,至萬歷四年(1576)方最終改為“先農壇祠祭署”。另外,據《清史稿》載:“天壇、地壇、朝日壇、夕月壇、先農壇,各祠祭署奉祀、從七品。祀丞,從八品。俱各一人。”[54]由此可見,清代直接承繼了明代最后形成的“先農壇祠祭署”,并且官署中所設的官位、官員人數也一脈相承。
(二)祭祀時間和活動的變遷差異
明清皇家太歲神和先農神的祭祀,在祭祀時間和主要祭祀活動上都有所不同。
在祭祀時間上,《明史》有記:“明初……仲秋祭太歲、風云雷雨、四季月將及岳鎮、海瀆、山川、城隍……仲春祭先農,仲秋祭天神地癨于山川壇……其非常祀而間行之者,若新天子耕謖而享先農。”[55]可見,明初對太歲神和先農神的祭祀分別是在“仲秋”和“仲春”。以此可知,兩壇的祭祀時間一開始便有所區別。然而,“仲秋祭太歲”只是一個大概的祭祀季節。按《明史》另載:“(洪武二年)乃定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于城南。”[56]可見洪武時已確定祭太歲時間為“驚蟄、秋分日”。此后,明太祖又進行了一些修改,“太歲……諸神,初具春、秋二祭。(洪武二十一年)至是亦停春祭。惟每歲八月中旬,擇日于山川壇及帝王廟祭之。”[57]將春、秋二祭改成只行秋祭,便形成了“仲春祭太歲”的慣例。但明朝皇帝對祭祀時間的修改仍未停止。之后的明成祖、明世宗等都對祭祀禮儀進行更改,明代最終成為定例的祭太歲時間為“每歲孟春享廟,歲暮舉祭之日,遣官致祭”[58]。而清朝于建朝之初就十分重視“太歲之祀”,清世祖初年就定以孟春擇吉、歲除前一日祭祀太歲之神。《清會典事例》載:“(順治元年定)孟春擇日及歲除前一日祀太歲。”[59]此后,歷代清帝僅做了些小的變動。最后于乾隆年間定制:“(太歲之神)每年正月初旬諏吉及十二月歲除前一日,遣官致祭。”[60]
“仲春祭先農”則是歷代祭先農的上選時節。明代承制,洪武元年明太祖便依臣議:“今議耕謖之日,皇帝躬祀先農。禮畢,躬耕謖田。以仲春擇日行事。”[61]此后,明世宗對祭先農之禮又進行了修改。“嘉靖九年續定:每歲仲春上戊,祭社稷及先農。”[62]經歷此番更改,明代最后確定的祭祀先農時間為“每歲仲春上戊”[63],這一定制被清代繼承。滿清入關以后,“(順治)十一年定,仲春亥日親行耕謖禮,即以是日饗先農。”[64]可見清朝在順治年間就確定了“仲春亥日”的祭先農、耕謖時間。此后歷代清帝皆相承不悖。
上述正常的祭祀時間都只是舉行兩壇例行祭祀活動的時間。太歲在明清兩代被認定為天神,常與山川海瀆眾神共祭,因而還有時間不定,與天神地癨共祭的“春祈、秋報”之祭,以祈福降雨。另外,還有逢旱澇時進行的祈雨謝雨等非正常祭祀。如《清實錄》所載:“為虔求雨澤。遣官致祭天神壇、地祗壇、太歲壇、并四海之神。”[65]而先農壇雖然年年例行耕謖、祭先農活動,但一般年份均為遣官致祭,逢新帝登基方有特殊的“親耕”①清帝為力行勸課,常打破此例以非登基年份親耕。之禮。兩壇日常和特殊祭祀活動如表1。

表1 明清太歲壇、先農壇祭祀時間、活動一覽表據②
(三)明清處理兩壇日常管理祭祀的認識
明清兩代在處理太歲壇、先農壇的管理和祭祀活動時形成了一些認識,這些認識最終成為明清兩代處理兩壇日常管理祭祀活動的原則。在處理神癨關系上,首先,明清兩代都努力地追求諸神和睦。總壇“祠祭署”變遷時一般只更改名稱,職能和辦事地點皆不變,以平靜轉變。太歲壇與先農壇因為壇闦十分接近,在祭祀一方時兩代皇帝都恐會驚動另一方。對于這種擔憂,明清皇帝祭祀一方后有時也會順便向另一方表達敬意,以示共尊之意。例如,清代就有“恭遇皇上行耕謖禮致祭先農禮成,詣太歲壇拈香”[66]的情況。
此外,明清兩代也努力表達對兩壇神癨獨立的尊重。自明開始,兩壇的日常開支就經常獨立撥付,《大明會典》就有“太歲、月將等神,孟秋、季冬二祭共柴八千斤、燒香炭七十斤。先農壇柴一千斤”[67]的記錄。兩壇雖然壇闦接近,但兩代修葺兩壇時,都明確強調兩壇的獨立性。《清會典事例》載:“先農壇北入太歲殿皆三門,角門一。雍正五年奉旨修理。”[68]可見太歲壇與先農壇間是有圍墻隔開的,雙方只能憑門進出。清末大臣那桐在日記中記:“(光緒十七年辛卯年四月)十六日(1891年4月16日)巳刻,到先農壇內太歲殿開工。”[69]只言“先農壇內太歲殿”,可見其仍強調“太歲壇”的獨立性。明清兩代的這些認識為兩壇日常順利運作奠定了基礎,也是兩代“諸神不罪”思想的一種體現。
三、明清北京太歲壇與先農壇供神主殿分布及形成原因
(一)供神主殿分布格局
承上文,明清兩代,北京太歲壇與先農壇雖然壇闦位置鄰近,但壇闦體系相對獨立。因此,其供神主殿也有所區別。“國初肇祀太歲,禮官雜議,因及陰陽家說十二時所直之神,太祖乃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將分祀兩廡。”[70]明初便祭太歲于山川壇正殿,因此當時太歲供神之所應為山川壇正殿。清初孫承澤《天府廣記》記:“嘉靖十一年……別建太歲壇,專祀太歲。”[71]這里的“太歲壇”承上文應指包含供神的“太歲殿”在內的壇闦體系或單指“太歲殿”。由此可知,太歲壇獨立成壇以后的供神主殿就是太歲殿。另據《大清會典》載:“(先農壇)北為殿五間,以藏神牌,東為神庫,西神廚,各五間,左右井亭各一。”[72]可見先農壇的供神主殿是包括神庫、神廚在內的北殿。
太歲殿在規制、富麗程度等各方面都在先農壇神庫之上,由此便形成了太歲壇供神主殿太歲殿規制上反而高于先農壇供神主殿神庫的奇特格局。
(二)奇特分布格局的形成原因
上述奇特分布格局的形成受兩個因素影響。其一是中國古代“諸神不罪”的多神崇拜思想。中國古代的神癨信仰篤信“萬物有靈”,為“多神崇拜”。其信仰神癨包括天神、地癨、人鬼等繁雜神格。因此,諸神并存、并祭的情況屢見不鮮。由此,處理好諸神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古人為處理好諸神關系,在各方面都十分注意,盡力做到“諸神不罪”。例如,跳祭祀舞蹈時,就經常獻舞八方,以饗八方神癨,而非獨悅一神。太歲之神自洪武時期便供于山川壇正殿(后先農壇),而太歲殿規制十分高大,是因為其前身是包括天神地癨在內合祭的山川壇正殿。諸神合祭,一神一壇,故其規制較大。(見圖6)嘉靖改制時,將風云山川海瀆等神癨遷出另祭,使正殿僅存太歲之神。總壇改名“先農”則在改制之后。若為配合改名而強遷太歲,入駐先農,無異于輕太歲重先農,這違背了“諸神不罪”的多神崇拜思想。

圖6 《大明會典》山川壇祭祀圖
其二是對太歲神特殊神格的尊重。雖然明帝重視“諸神不罪”,但仍遷移天神、地癨于殿外另祭,獨留太歲不遷,這與太歲神的特殊神格有密切聯系。明代禮臣曾進言:“太歲者,十二辰之神。”[73]可見太歲神在明代被認定為時辰之神。關于歲,《說文解字》記載:“木星也。越二十八宿,宣陰陽,十二月一次。”[74]太歲即為主一歲之星①太歲實際是古代天文學里假定與真歲星運行正好相反假歲星。古人把黃道附近一周天十二等分,分別命名,歲星(木星)由西向東繞日運行,正好十二年一周天,因此以歲星所在為歲名,但其運行方向與將黃道十二支方向相反,為了方便,古人便設想出一個與真歲星運行方向相反的假歲星,名之“太歲”。。因為太歲主一歲之時運,因此在命學上認為太歲是百神之主,其尊不可犯,所在方位不宜移徙、興造、嫁娶,犯者則必兇。至今民間風水學仍稱觸犯“太歲”為“歲破”。對于此說,早在漢代王充便轉引風水理論著作《移徙法》展開論述:“徙抵太歲兇,負太歲亦兇。抵太歲名日歲下,負太歲名日歲破。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75]可見這種思想很有歷史淵源。明朝統治者對此亦是深信不疑。《明史》有載:“(正統)十年正月庚寅,忠義前后二衛災。是時太倉屢火,遣官禱祭火龍及太歲以禳之。”[76]可見明帝也知曉并堅信太歲在興造、遷移等問題上的權威不可輕犯。因此,嘉靖帝雖然遷天神、地癨于外壇,卻不肯輕易移動太歲神,將之留在原殿,并新建祭壇。此后明清各帝亦相沿,遂形成如今格局。
四、結語
明清北京的太歲壇與先農壇分別是兩代皇家祭祀太歲神與神農氏的壇闦。自明代永樂帝時仿南京建山川壇,歷嘉靖改制,兩壇在經過了各自的發展過程后,最終形成太歲壇包括祭祀主殿在內的整體建筑位于先農壇內的格局。太歲壇與先農壇在祭祀時間、祭祀活動等方面都存在差別。太歲之祀與先農之祭是明清皇家對“時”神和“農”神的祭祀體現,兩壇的關系部分體現了兩代對“時”與“農”關系的認識和處理方式,同時也是中國古代多神崇拜體系下“諸神不罪”及對“太歲神”特殊神格尊重思想的重要體現。
[1]董紹鵬,潘奇燕,李瑩.先農神壇[M].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89.
[2]董紹鵬,潘奇燕,李瑩.北京先農壇[M].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173.
[3]朱祖希.先農壇——中國農耕文化的重要載體[J].北京聯合大學學報,2000,(1):42-45.
[4]朱祖希.先農壇——中國農耕文化的重要載體[J].北京社會科學,2000,(2):135-139.
[5]黃愛平.清代的炎帝祭祀及其文化內涵[J].理論學刊,2009,(6):112-116.
[6]曲英杰.神農氏與先農壇[J].中華文化論壇,1997,(1):38-44.
[7][8][12][13][15][20][32]明太祖實錄[M].上海:上海書店,1982.176.176.963.963.1735.1735-1736.1737.
[9][11][28][29][30][37][50][55][56][58][61][63][73][76][清]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5.1246.1282.1272.1283.1283.1271.1225.1225.1282-1283.1283.1271.1272.1282.462-463.
[10][47][70][明]何孟春.余冬序錄[A].叢書集成初編(卷三三七)[M].北京:中華書局,1985.32.35.35.
[14][53][明]徐學聚.國朝典匯[A].四庫存目叢書[M].濟南:齊魯書社,1996.569.132.
[16][17][33][明]佚名.太常續考[A].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五九九)[M].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152.155-156.155.
[18][25][38][57][62][明]申時行.大明會典[A].續修四庫全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13.511.613.437.94.
[21]明太宗實錄[M].上海:上海書店,1982.2244.
[22][41][清]于敏中.日下舊聞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891.893.
[23][35][明]徐學聚.國朝典匯[A].四庫存目叢書(卷二六五)[M].濟南:齊魯書社,1996.860.862.
[24][明]李賢.大明一統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1.
[26][清]孫承澤.春明夢余錄[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223.
[27]明世宗實錄[Z].上海:上海書店,1982.3058.
[31][明]涂山.明政統宗[A].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640.
[34][明]章潢.圖書編[A].文淵閣四庫全書[M].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190.
[36][71][清]孫承澤.天府廣記[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72.71.
[39][60][清]官修.清文獻通考[A].文淵閣四庫全書(卷六三四)[M].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177.177.
[40]清世祖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578.
[41][42][43][44][59][64][68][清]昆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Z].重修石印本,1899.
[45][清]吳長元.宸垣識略[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210.
[46][52][明]佚名.諸司職掌[A].續修四庫全書(卷七四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94.584.
[48][49][54]趙爾巽.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7.2807.2826-2827.3327.
[51][67]申時行.大明會典[A].續修四庫全書(卷七九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60.565.
[65]清高宗實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5.723.
[66][清]穆彰阿.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6.
[69][清]那桐.那桐日記[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52.
[72]大清會典[A].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9冊)[M].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659.
[74][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8.
[75]王充.論衡[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107.
【責任編輯:周 丹】

漢 當王
K879.1
A
1673-7725(2016)08-0117-10
2016-06-05
蔡宛平(1989-),女,廣西河池人,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城市文化與區域歷史地理、區域歷史文化遺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