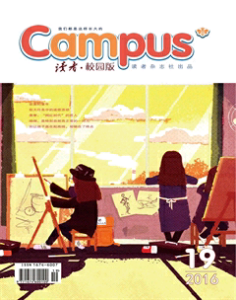鯊魚
韋躍,1985年生。“ONE·一個”“簡書”“知乎”“十五言”超人氣作者,代表作《一個糖水愛情故事》。
在沒有夢想的年代,年輕人也許并不奢求有一天能成為蓋世英雄。大人們已經成功說服我們生活不是熱血漫畫,我們能夠偶爾做做夢,就已經足夠快活了。然而,有時候做夢也是不被允許的。
參加同學會時跟同學聊到的一件小事,讓我產生了上面的想法。上高二那年,班上的肥坤有一個周末去看了鯊魚。星期一到校后,他逢人便講:“好大好長的一條魚,游個不停!”他開始立志要養一條鯊魚,每天陪它游泳。那一個禮拜,沒有人跟肥坤說話,大家都暗笑他在做夢。
我們還聊起那一周的星期五,阿杜穿著一雙新球鞋到處吹噓:“這是從日本帶回來的限量版球鞋,很厲害!我在今年的校內足球賽上要‘大殺四方!”于是,大家忘掉了鯊魚的事兒,轉而開始討厭阿杜,打游戲時沒有人愿意跟他組隊,踢球時也不傳球給他。
即便如此,在當天放學后的練習賽上,阿杜仍然“大殺四方”。阿杜從初中起就入選市少年隊,而對手高三(6)班的同學們又是菜鳥中的菜鳥,所以,阿杜可能早就知道,他根本不需要隊友,一個人就能贏球。
在這所以學業繁重著稱的高級中學,一面倒的球賽很常見。但是,對于高三(6)班的“菜鳥”們而言,即便輸得丟臉,踢球也是他們不可多得的消遣。那場練習賽是他們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場球賽,因為在比賽結束后,他們就宣布退出今年的校內足球賽了。
校內足球賽是我們學校的一個不成文的傳統,每個班的男生組織一支球隊參賽,依照“世界杯”的比賽規則設置賽程,一代代口耳相傳,既沒有組織,也沒有經費,更像高年級的學長們帶著學弟們踢球玩。沒有人知道為什么足球賽在男生們中間那么受歡迎,在大人眼里這有點兒不可理喻,他們經常念叨:“既沒有獎金,又踢不成球星,你們鼓搗這些有什么用?上一所好大學才是正經事。”
然而,有一些年輕人卻把校內足球賽看得比考試還重要,比如我們班的男生。
高一那年,阿杜帶領我們班大出風頭,我們作為一支新生隊伍,居然憑著一股蠻力踢進了決賽,最后以0比1敗給高三(9)班。過了一年,“老球棍”們都畢業離校了,我們班的男生更是摩拳擦掌,憋足力氣要拿當年的冠軍。
傍晚,踢完球后,肥坤約我一起騎車回家。
“我們這屆高三學生踢球的水平也太low了!一群書呆子。”他有一搭沒一搭地說。
我沒說話,只等他進入正題。
后來,他清了清嗓子,說:“我們幾個想再組織一支球隊。我覺得沒有問題,沒有規定不讓一個班出兩支球隊,我們的人也很厲害。”他接著說出了幾個人的名字。
“這幾個人好像打籃球比較多吧?”我問他。
肥坤仰起胖臉望了望天,說:“阿杜太愛吃獨食了,每次比賽時我們都好像圍著他轉一樣。我們已經認真考慮過了,即使沒有他,我們也一樣能贏。”
見我還沒有反應過來,肥坤又說:“況且,你老踢后衛,難道不覺得太憋屈了嗎?我知道因為你和阿杜都是左撇子,他踢了左前鋒,而你只能踢左后衛。其實你要是踢前鋒,球技并不比他差,只不過他的名氣比你大。”
“反正只要能贏球,我怎么都可以。”我含糊地說。
第二天,阿杜也為同樣的事情私下里找我。他對我說:“肥坤那些人根本不懂足球!他們平時就在籃球場上大呼小叫,想要引起女生們的注意。我們今年不要他們踢比賽!把那些高個子換下來,你踢右前鋒,我們雙劍合璧。”
我問:“就咱倆嗎?人夠嗎?”
阿杜擺了擺手,說:“沒事,總有幾個人會聽我的話的。如果實在人不夠,我在其他學校有的是朋友,比肥坤他們強多了。我們都是高中生,請外援也不算犯規。”
我說:“我怎么都行,只要能贏球。”
肥坤和阿杜要各自組織球隊的消息不脛而走。沒過幾天,他們就已分成兩撥人,每撥都宣稱自己是“班級正統”,對方是“異端”,見面時互相翻白眼,連招呼都懶得打。當然,大家暗地里都很用功:早上天還沒亮,一群男生就跟著阿杜在學校球場的跑道上跑步;而下了晚自習,籃球場就被肥坤那一伙人霸占了。
與此同時,我偷練得比誰都勤,因為我太想踢前鋒了。一旦升入高三,就算再怎么努力,父母也不會允許我把寶貴的時間投入到校內足球賽上。所以,我必須牢牢把握住高中生涯最后的光榮時刻,贏得校內足球賽,然后去用功念書。雖然這只是一點點卑微的企圖,但至少比全盤接受生活的禁錮令人振奮一些。
有一天晚上,當我練完球準備離開時,球場大門那邊傳來一陣喧嘩聲,走近一看,原來肥坤和阿杜兩伙人正在爭執。十幾個人圍成一圈,其中有高年級的學長,還有幾個外校學生——他們中有人把頭發染成了黃色,我們學校是禁止染發的。
“你們別吵了,我再說一遍,從來沒有一個班出兩支球隊的先例。”一個我見過但叫不出名字的同學大聲說。
“這樣的話,顯然只有我們可以代表我們班參賽。你看你們,全是其他學校的人!”肥坤指著阿杜那邊的那個“黃毛”高聲說。
“我覺得沒問題啊,以前還找外校老師踢過……”話還沒說完,阿杜一看到我站在旁邊,立馬把我拉過去,“再加上他,我們就一個外援,有什么問題?!”
“他是我們隊的!”肥坤大聲說。
“你平時和我踢球的時間多,肯定是跟我一隊的,對嗎?”阿杜雖然在問我,眼睛卻瞪著肥坤。
“跟他踢什么呀!你給他撿球還是給他傳球?”肥坤指著阿杜的鼻子冷嘲熱諷地說。
阿杜沖過去抓住肥坤的領子罵道:“你懂個屁!”
肥坤揪著阿杜的頭發吼道:“你能,你一個人踢啊!”兩撥人邊喊叫邊互相推搡,眼看就要打起來。
“不要打!”那個“黃毛”擠進人群,用力掰開撕扯在一起的阿杜和肥坤。“干嗎搞得跟古惑仔一樣?踢球的事在球場上解決!”他的這兩句話說得頗有氣勢,在場的所有人都被嚇到了。
“ 既然如此,明天放學后我們踢一場,誰贏誰上。”阿杜說。
“喂,你跟誰?”肥坤直接問我。
一時間,我不知該怎么辦,只是含糊地說了幾句“再說吧”,就立馬騎車逃離。身后有罵聲傳來,我聽得很清楚,只能繼續加速飛奔。
第二天,在早晨的升旗儀式上,我們學校的教導主任突然宣布:“今年不舉辦校內足球賽!”很多男生在聽到這句話時就已經罵起了臟話。接著,教導主任解釋說:“有的學生因為校內足球賽,引社會青年入校聚眾斗毆。”下面開始有人往主席臺上扔水瓶。在我們學校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于是,事情發生不久,校方就通過廣播通報批評了30多個人,并且把足球場的球門都拆了。
與“社會青年”有關的阿杜最慘,他背上了留校察看的處分。與此同時,我們班也成為眾矢之的,所有的人都把責任歸到我們起內訌上。很多人還認為,作為“墻頭草”的我被逼急了,向校方添油加醋地告狀,才導致了校內足球賽的流產。后來,有人在我的椅子上用涂改液寫了“大叛徒”3個字。
我覺得這還算客氣,畢竟校內足球賽沒有了。
一年后,真相大白——這都是高三(6)班的同學們搗的鬼。
參加同學聚會時,我遇到了肥坤。酒到酣處,他搭著我的肩膀問我:“你說句實話,在我和阿杜之間,你當年更愿意跟誰一起踢比賽?”
我對他說:“那時我說‘能贏就行,只是在敷衍你們,因為我實在不知道該怎么選。說來也奇怪,在那個年紀,幾乎做什么選擇都是沒有回頭路的,不光是選一支球隊那么簡單。”
肥坤推了推我的肩膀,說:“你現在也還是在敷衍我啊!”
我說:“如果你現在問我,我還是會說‘能贏就行。不過這次我是認真的。我不像阿杜那樣從小就練球,也不像你有那么多事值得期待,我就是喜歡踢球。那其實是高中最后一次踢校內足球賽的機會,我想贏,可惜我當時并不知道。”
他聽完大笑,我也笑了。
陪他笑了一會兒,我突然記起,高中畢業的那個暑假,我在水族館里第一次看到了鯊魚。好大好長的一條鯊魚,它擠在一個狹小的水箱里,卻一直游個不停,好像永遠不知疲倦似的。據說,鯊魚的腮并不會吸水,它必須不停地向前游,讓水通過口腔流入腮裂里才不會被淹死。它根本沒有資格感到疲倦。
我想我理解那種感覺,肥坤和阿杜也一定都理解那種感覺。高三(6)班的同學們說不定也能理解,只是他們不在乎——有些人太需要精力去巧妙地度過這一生了,沒有時間做英雄夢。
我還記得,那天我在水族館里待了很久,直到燈一盞一盞地熄滅,四周漸漸暗了下來。我努力想看清那條鯊魚,卻只能隱約在玻璃上看到自己模糊的影子。然后,我就被大人們趕出了水族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