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里的導(dǎo)師蔣星煜先生
文 郭 梅
我記憶里的導(dǎo)師蔣星煜先生
文郭 梅

2015年12月一個(gè)陰郁的清晨,我坐在校車上,和往常一樣順手打開微信,孰料大師兄的一條留言赫然入目,瞬即如雷轟電擊——雖然早有預(yù)感甚至有心理準(zhǔn)備,但還是被敬愛的導(dǎo)師蔣星煜先生病逝的噩耗所擊中,雙淚直流,心里直后悔就是幾天前自己還到過上海,但因第二天有課,就“原轎去原轎回”,沒有去探望先生,不料竟永遠(yuǎn)失去了和先生再次晤談的機(jī)會——那天,滿懷深深的痛與悔,我忍著滿眶淚水踏上講臺,心里默默祈念:“老師,請賜給弟子順利完成今天教學(xué)任務(wù)的靜氣和定力吧!”
屈指算來,我和蔣星煜先生的師生緣分,迄今已有26載。在學(xué)術(shù)界,每每被問及師承的時(shí)候,我總是既自豪又忐忑地回答:“我是蔣星煜先生的關(guān)門弟子。”——師承名門的小女子雖說一直沒有疏離戲曲專業(yè),但碌碌無為,委實(shí)觍顏得緊,兀的不愧煞人也。
余生甚晚,我入師門的時(shí)候,先生早已過古稀之年——本科畢業(yè)時(shí),我獲得了母校華東師大首屆直升研究生的資格,并被告知專業(yè)可以在詞學(xué)和元明清戲曲之中任選。年少輕狂的我懵懵懂懂地選了戲曲,理由是“詞乃最愛,不欲以之為飯碗”,況且對戲曲幾乎一無所知,便抱著補(bǔ)課的心態(tài)怯生生地踅進(jìn)了蔣先生的門墻。
先生鶴發(fā)童顏,幽默風(fēng)趣,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對弟子十分寬容——第一次見面,是嚴(yán)肅的入學(xué)面試,我以為一定有很難的學(xué)術(shù)“天問”等著我,不免有點(diǎn)“嚇勢勢”的,但先生只是稍微問了問,說了句“直升的小囡確實(shí)不錯”,就放我過關(guān)了。也許是看出我多少有點(diǎn)緊張,還微笑著加了句:“小姑娘蠻小巧的,我也不高,我們有師徒相哦。”于是,這之后我無論是去先生家里上課還是跟他出去調(diào)研,都學(xué)會了“倚小賣小”,不緊張了。可萬分慚愧的是,我與先生的相似,也一直只有在身量上的差相仿佛了。

《唐詩鑒賞辭典》書影
不過,我很快就感到其實(shí)先生對學(xué)生是非常嚴(yán)格的,因?yàn)殡m然他很少“言教”,即口頭提出具體的要求,但“身教”卻是無時(shí)無刻不在進(jìn)行的。我在先生身邊的時(shí)候,老人家正進(jìn)行《西廂記》版本研究的浩大工程,一篇接一篇的論文,一部接一部的專著,讓我和師兄“不寒而栗”,再怎么用功寫的作業(yè)都不敢給先生看,每每在去先生家的公交車上相互嘀咕推諉:“等一下你先交啊!”如果說,我一開始是稀里糊涂抱著補(bǔ)課的心態(tài)成了先生的入室弟子,那么,在他身邊的日子我確實(shí)在先生身教的無形壓力下,扎扎實(shí)實(shí)補(bǔ)了補(bǔ)課,取得了不小的進(jìn)步。而且,特別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先生年雖高邁,但思想?yún)s從不僵化,對人對事十分通達(dá),而且觀點(diǎn)往往十分“前衛(wèi)”,不拘泥不苛刻,口頭禪是“我看這也沒有什么不可以么”。比如,我曾經(jīng)好奇地問先生,為什么要出版《唐詩鑒賞辭典》,都說詩無達(dá)詁啊,這“鑒賞”如何能夠“辭典”呢?先生大笑,說你這小姑娘年紀(jì)輕輕居然食古不化,誰告訴你“辭典”就必須只有一個(gè)固定的答案?窘得我再不敢想當(dāng)然地以固定思維考慮問題。其實(shí),早在1985 年2月16日,先生就已經(jīng)在《新民晚報(bào)》副刊“夜光杯”上發(fā)表《為辭典多樣化正名》一文,針對有關(guān)質(zhì)疑文章,嚴(yán)肅地指出“《辭海》中有關(guān)‘辭典’的釋文。先生說:“這是二十多年前定稿的,隨著時(shí)代的變化,今天辭典更豐富多樣化了,這一條釋文不能適應(yīng)新的形態(tài),加以修改我看是必要的,不能根據(jù)這條釋文來否定《唐詩鑒賞辭典》。”并且強(qiáng)調(diào):“我覺得這不僅是一個(gè)學(xué)術(shù)問題,也是一個(gè)思想方法問題。”近年,先生又就這個(gè)問題在《文匯讀書周報(bào)》上發(fā)表了《〈唐詩鑒賞辭典〉的編輯出版與影響》一文,強(qiáng)調(diào)“早在抗戰(zhàn)之前,就有了顧鳳城的《作家描寫辭典》”,而在1983年上海古籍版的《唐詩鑒賞辭典》出版之前,日本也早就出版了同名辭典。所以,先生明確“肯定了《唐詩鑒賞辭典》是辭典形式、內(nèi)容、風(fēng)格、體例多樣化的顯著成果的一例”,而且“這一類辭典有著較強(qiáng)的可讀性,歐美日本諸國早就有了”,“《唐詩鑒賞辭典》第一次印刷20萬冊,成了供不應(yīng)求的暢銷書。至于鑒賞性質(zhì)的書籍能否稱為辭典,《辭海》中‘辭典’條目的釋文作何解,廣大讀者并沒有注意,即使注意到了,也沒有影響他們對這本書的熱愛”,何況“迄今已經(jīng)發(fā)行了200余萬冊,香港等地還出版了繁體字版本,影響非常深遠(yuǎn)”。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唐詩鑒賞辭典》帶來的鑒賞辭書熱潮已逐漸趨于冷卻,上海辭書出版社則仍在細(xì)水長流地進(jìn)行編輯出版工作。只有這一系列的鑒賞辭典在讀者中享有較高聲譽(yù),在市場能經(jīng)久地暢銷,經(jīng)濟(jì)效益也好,其他出版社的鑒賞辭典即使質(zhì)量沒有什么問題,也難以與之競爭。質(zhì)量低劣地印了一次,也就無法再印了。
據(jù)最近的消息,上海辭書出版社準(zhǔn)備對已出版十年以上的鑒賞辭典進(jìn)行修訂,猶如他們對《辭海》那樣,這體現(xiàn)了他們嚴(yán)謹(jǐn)?shù)某鰰鴳B(tài)度和新的大手筆。
話說回來,即使當(dāng)初上海辭書出版社在出書方面,并沒有分工上的規(guī)定與限制,我認(rèn)為“鑒賞辭典”的稱謂仍舊可以成立。事物總是發(fā)展的,總是從無到有,從簡到繁的。事實(shí)上《辭海》1989年修訂本確實(shí)把‘辭典’的釋文作了修訂,舉例時(shí)也增加了類別,雖未列上鑒賞性辭典,但把辭典作用擴(kuò)展了,除“加以解釋”之外,也有“提供某種信息”,當(dāng)然也包括鑒賞了。
先生從理論到事實(shí),層層剖析,將“鑒賞”不能“辭典”之論徹底駁倒,且文風(fēng)平實(shí)、語氣溫和,端的是大家風(fēng)范。試問,現(xiàn)在文科大學(xué)生的案頭,誰沒有一冊《唐詩鑒賞辭典》?我在中文系任教二十余年,也從未遇到一個(gè)學(xué)生問過我當(dāng)年請教先生的“愚蠢”問題。
不過,筆者私心以為,另外一個(gè)并不廣為人知的例子更能夠體現(xiàn)先生的“泥古能化”“老而不僵”。
記得,先生第一次考我應(yīng)該是在我們?nèi)ド綎|曲阜調(diào)研的路上,大家飯后散步,閑閑的,先生說,我考考你們,《三國演義》里有哪些人物的名字是單姓雙名的?誰能夠說出三個(gè)以上,就算及格。天!要知道,在四大名著里,我最喜歡最熟悉的是《紅樓夢》,對打打殺殺的《三國》《水滸》,我可是怵得很。《三國演義》里的帝王將相、英雄豪杰絕大部分是單名,一下子怎么想得出雙名的人物?于是一路走,一路搜索枯腸,想到一個(gè)就大叫:“諸葛亮的老丈人——黃承彥!”先生頷首稱是。我得了鼓勵,又喊:“孫尚香!”先生微微一笑,道:“孫夫人在《三國演義》里始終叫孫夫人,‘尚香’這個(gè)閨名是戲曲里才有的。不過,你能想到,也算不錯啦。”哎呀,阿彌陀佛,也許是因?yàn)閹熜诌B一個(gè)都沒說出來的緣故吧,我雖然只說出了一個(gè),遠(yuǎn)遠(yuǎn)不到合格的標(biāo)準(zhǔn),但先生卻又輕輕放我過關(guān)了。
當(dāng)然,先生的“輕”,在我,就是“舉重若輕”。這以后,我惡補(bǔ)《三國》《水滸》,雖然遠(yuǎn)遠(yuǎn)未能達(dá)到先生所要求的水準(zhǔn),但現(xiàn)在勉強(qiáng)能夠勝任元明清文學(xué)“教頭”之職,端的是拜先生當(dāng)年“舉重若輕”之賜。
我畢業(yè)離開先生之后,先生源源不斷地寄贈新作,令我慚愧,無地自容——先生已是八旬老人,卻仿佛不知耄耋將至,不斷研究,碩果累累,即便是他研究的副產(chǎn)品——雜文筆記小品文等,也犖犖大觀。如前幾年他作《〈三國演義〉的單姓雙名人物》,道:
我過去以為諸葛亮在臥龍崗未出山時(shí)的三位好友都是單姓雙名,但是現(xiàn)在我有些懷疑。因?yàn)榈?7回:“(司馬)徽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穎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為密友。”司馬徽稱徐庶為徐元直,用的是“字”不是“名”,因此我認(rèn)為崔、石、孟三人肯定另外有“名”,這里也是用的“字”。
這段考證讓我又一次深深體認(rèn)了先生的“舉重若輕”——因?yàn)楫?dāng)年關(guān)于這個(gè)問題,先生給出的“標(biāo)準(zhǔn)”答案中,就有“崔、石、孟”三人,而我也一直信之不疑,并且在課堂上也如此這般地講給我的學(xué)生聽。沒想到先生卻在繼續(xù)思慮考證,推出更新更有說服力的結(jié)論。相形之下,我端的萬分愧對先生!
先生的新書《文壇藝林滄桑錄》收錄了有關(guān)現(xiàn)代文學(xué)藝術(shù)方面的回憶33篇,多以和先生過往甚密的人物為主線,記載確鑿,從不同的視角反映文壇藝壇的風(fēng)貌。如《計(jì)鎮(zhèn)華的表演藝術(shù)》,分章評述計(jì)鎮(zhèn)華所塑造的舞臺形象:《十五貫》里的況鐘、《長生殿》里的李龜年等,閑閑敘來,評論精當(dāng),可讀,可思。文末,先生還沒忘記談一談計(jì)鎮(zhèn)華客串越劇《人比黃花瘦》那件事:“在此劇演出中,逢唱的時(shí)候,只要‘作唱狀’,口型與唱詞保持一致即可,另有人配唱的。這樣計(jì)鎮(zhèn)華是否省力呢?并不,反而比唱吃力得多,別扭得多,有一種‘唱不出來的苦處’。他卻把趙明誠演得栩栩如生,付出的代價(jià)不小。”于是,讀者和觀眾對計(jì)鎮(zhèn)華在表演上的造詣和人格魅力,就都有了深刻的印象。
先生每每送我新付梓的著作,總是會題上“給郭梅賀歲”“供郭梅參考消閑”之類的字樣。但我知道,先生其實(shí)是“舉重若輕”,是在用他一貫的方式鞭策我勉力前行。而“舉重若輕”,在艱深的古代文學(xué)史料堆里鉤沉輯佚,又發(fā)為深入淺出的絕妙文字,其實(shí)也是先生眾多隨筆集子的共同特點(diǎn)。

2008年,在《關(guān)于古典文學(xué)與曹操的翻案問題》的專題講座中,蔣老謙恭的為人、嚴(yán)謹(jǐn)?shù)闹螌W(xué)、風(fēng)趣的言語給同學(xué)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dāng)然,先生的敢于推翻前論自我否定,在學(xué)術(shù)界也是有口皆碑的,比如在完成了《西廂記》版本研究的巨大工程之后,轉(zhuǎn)入《桃花扇》傳奇的研究,并出版了新著《〈桃花扇〉研究與欣賞》等。有學(xué)者指出,“關(guān)于《桃花扇》的歷史真實(shí)和藝術(shù)真實(shí)方面,蔣著研究了幾個(gè)重要劇中人物與史實(shí)的關(guān)系。如侯方域,指出他的政治立場和性格表現(xiàn)軟弱,孔尚任放大了他的這個(gè)缺陷。侯被動地入道,與他軟弱動搖的性格是一致的。侯筑壯悔堂,悔的是應(yīng)清廷科舉;孔尚任寫《桃花扇》也是宣泄出仕清廷的內(nèi)疚:‘孔尚任在不知不覺中也可能以侯方域自況’。又如辨析了柳敬亭的身世、演唱何種曲藝等疑問和史可法死難真相。楊龍友是傳奇中作者著墨最多的一個(gè)人物。蔣著先是論述作品中楊龍友作為一個(gè)兩面派文人的典型是成功的,然而創(chuàng)作離開基本史實(shí),貶低歷史人物楊龍友,違背了‘確考時(shí)地,全無假借’的創(chuàng)作宗旨,損害了《桃花扇》作為歷史劇的價(jià)值。但后來蔣先生又發(fā)掘了有關(guān)楊龍友的一些史料,記載著楊許多為官的劣跡,故又著文提出‘楊龍友蓋棺難論定’,期待史料的繼續(xù)發(fā)現(xiàn)。蔣先生認(rèn)真負(fù)責(zé)的態(tài)度值得稱道。”(宋光祖《孔尚任創(chuàng)作思想的深度探索——談蔣星煜〈桃花扇〉研究的豐碩成果》)須做考證方面的課題,怕自己承擔(dān)不了。不過,先生仿佛總是能夠洞察我的內(nèi)心,很早就放了我一馬:“考證么,你可以五十歲以后再做的。”于是,我自己選了“元明清女曲家”這個(gè)當(dāng)時(shí)很偏的題目來做,雖然很不對先生的胃口,但他毫不以忤,就像我始終宣稱愛煞《紅樓夢》而不喜《三國演義》,先生也只是一笑置之。于是,我學(xué)會了在踏上講臺之后堅(jiān)持在課上課下給學(xué)生強(qiáng)調(diào):最最希望你們提出和我不同的意見,當(dāng)然,要盡量自圓其說。當(dāng)然,我也始終習(xí)慣于在先生的著述中尋找修正教案的新材料新觀點(diǎn)。比如,近年我如果在戲曲課上講到《千金記》《霸王別姬》,或者在女性文學(xué)的課堂上評述張愛玲,總會引用先生的《稗海中被遺忘的驪珠——張愛玲及其〈霸王別姬〉》:

蔣星煜著《〈桃花扇〉研究與欣賞》書影
我發(fā)現(xiàn)她(張愛玲)在1937年寫過歷史小說《霸王別姬》,按年齡,她這時(shí)是個(gè)17歲的女少年,還不是女青年,但是,她筆下的虞姬的人物形象卻比沈采《千金記》的虞姬飽滿。梅蘭芳的《霸王別姬》誠然比《千金記》有所豐富,主要是在歌舞方面,而張愛玲則對虞姬的內(nèi)心世界進(jìn)行了開挖和剖析。故事從項(xiàng)羽和虞姬住宿的帳蓬展開,蠟燭油淋淋漓漓地淌下來,“含著稀薄的嗆人的臭味的煙裊裊上升”。項(xiàng)羽在計(jì)算所剩無幾的糧食,自己騙自己,也是為騙虞姬,假裝出一股樂觀的神氣,說:“三天之后,我們江東的屯兵會來解圍的。”虞姬表面上相信項(xiàng)羽的推算,卻仍舊擺了一擺可怕的近乎絕望的事實(shí):“大王,我們只有一千人,他們卻有十萬……”項(xiàng)羽仍舊想把局面說得稍稍好一點(diǎn),虞姬不再和項(xiàng)羽爭辯,就請項(xiàng)羽“先休息一會吧!”甚至項(xiàng)羽如何去休息也沒有交代,用了一句“侍候他睡了之后”,就完全是虞姬的行動了。她“一只手拿了燭臺,另一只手護(hù)住了燭光,悄悄地出了帳蓬”。她在夜色中,透過迷蒙的薄霧,聽著戰(zhàn)馬的悲嘯、守夜人的更鼓,停留在一座營帳前,諦聽里面士兵們的談話和夢囈。她看到了山下一座大營,那正是漢王屯集十萬大軍的地方。她不禁回憶起和項(xiàng)羽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十余年來的軍旅生活,她卻又“懷疑這樣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標(biāo)究竟是什么”。然后,她聽到了漢軍營盤里傳來的凄楚的畫角。終于,再度陷入反思和遐想之中。“——啊!假如他成功了的話,她能得到些什么呢?她將得到一個(gè)‘貴人’的封號,她將得到一個(gè)終身監(jiān)禁的處分。……當(dāng)她結(jié)束了她這為了他而活著的生命的時(shí)候,他們會送給她一個(gè)‘端淑貴妃’或‘賢穆貴妃’的謚號……”當(dāng)虞姬強(qiáng)迫自己停止反思和遐想時(shí),她聽到了山下傳來的楚歌聲,她先是惶惑,然后驚惶……回到了她和項(xiàng)羽住宿的帳蓬。起初決定不告訴他所看到的聽到的一切,最后還是要項(xiàng)羽聽一下四面?zhèn)鱽淼某琛?/p>
顯然,張愛玲的歷史小說《霸王別姬》這則材料是絕大多數(shù)教材里所不曾提及的,先生的分析又詳細(xì)周到,鞭辟入里,自然成了我講課的“利器”,所向披靡,效果很好。換言之,作為一個(gè)戲曲史研究的大家,先生正是最擅長在史學(xué)、文學(xué)與戲曲相交集處獨(dú)辟蹊徑而鉤沉致遠(yuǎn)的。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當(dāng)然,先生之所以會注意到張愛玲的歷史小說,自然和他自己也是一位優(yōu)秀的歷史小說家和明史專家不無關(guān)系。在他的歷史小說中,先生就猶如一位風(fēng)趣而智慧的長者向讀者娓娓講述那古老而遙遠(yuǎn)的故事。他總是選擇某個(gè)歷史人物或者某段史實(shí)加以合理的新編,情節(jié)生動、人物豐滿,又很有啟發(fā)意義。他追求人物形象的形神兼?zhèn)洌鴮v史環(huán)境的描繪又完全嚴(yán)格按照時(shí)空和邏輯順序進(jìn)行演繹,做到唐宋各異,明清有別。比如,《捉刀人曹操》《柳公權(quán)書法諫君》《蘇東坡畫竹》《湖陽公主外傳》《進(jìn)士及第》等,當(dāng)年我都曾和同學(xué)們一起讀得津津有味。當(dāng)然,先生和明代諍臣海瑞之間的故事更是曲折不已,體現(xiàn)出先生和海瑞一樣堪可景仰的硬骨頭風(fēng)采,人所共知,本文就不贅述了——毫無疑問,海瑞是先生漫漫人生路上的一個(gè)重要的關(guān)鍵詞,這從先生將書齋題名為“西海書屋”亦可見一斑:西者,《西廂記》也;海者,海瑞也。

蔣星煜與毛時(shí)安、葉長海、陳明正等游覽千島湖中的海公(瑞)祠
當(dāng)然,先生在創(chuàng)作方面的成就并不僅僅限于歷史小說,竊以為,他創(chuàng)作方面的貢獻(xiàn)更在于大量的文史隨筆——以學(xué)者的眼光、作家的筆調(diào)進(jìn)行寫作,下筆前總會考慮如何把文章的題目、角度寫得更吸引人、更引發(fā)讀者的興趣,所以往往能夠以小見大,深入淺出,涉略廣泛,影響深廣。同時(shí),他也誨人不倦,常常給后學(xué)指點(diǎn)迷津。比如,他曾對喜歡研究古陶瓷的作家錢漢東如是說:“過去顧頡剛、夏鼐等考古前輩都用半文不白的語言寫考古文章,顧頡剛等學(xué)者因是從舊學(xué)過來的,情有可原。現(xiàn)在考古學(xué)者寫的文章,也摹仿,實(shí)在是個(gè)誤區(qū),有的甚至認(rèn)為自己的文章別人讀不懂,說明學(xué)問高深,其實(shí)不然。考古學(xué)者應(yīng)從高樓深宅里走出來,面向大眾,并為讀者所理解所接受,這才是有意義的事情。但是你要注意寫文章所用的史料必須準(zhǔn)確無誤,處理好與考古界同仁的關(guān)系,主動和他們交朋友并逐步得到他們的認(rèn)同。”并在《新民晚報(bào)》上以《作家學(xué)者化》為題,對錢漢東的作品進(jìn)行評論,給了錢漢東莫大的鼓勵。其實(shí),作家學(xué)者化、學(xué)者作家化,不正是先生自己一貫主張和身體力行的么?先生的學(xué)術(shù)和創(chuàng)作齊頭并進(jìn),互相融合,各具千秋,各創(chuàng)高峰,犖犖大觀,是我國現(xiàn)當(dāng)代學(xué)術(shù)史和文學(xué)史的寶貴財(cái)富。
先生2011年出版的集子《史林新語》是一部兼涉歷史、文學(xué)、戲劇、民俗、上海人文、茶藝知識等多種門類的通俗學(xué)術(shù)著作集,全書分為“三國群英神采”“唐宋風(fēng)云人物”“明代朝野珍聞”“朝廷內(nèi)外禮俗”“春申江濱掌故”“戲劇歷史掌故”和“茶事茶藝探秘”7個(gè)部分,共收入71篇文章,無不融趣味性和知識性于一爐,如:《劉伯溫被神化的歷史背景》《劉基與日鑄茶、平水茶》《劉基談苦茶》《三個(gè)完全不同的武則天》《曹操的妻妾侍女》《諸葛亮夫人的貌、才、德》《諸葛亮三次升值》《杜甫自稱“讀書破萬卷”》《黃道婆的身份》等等,生動有趣,既可作為茶余飯后的談資,擴(kuò)大了讀者的知識面,又給人不小的啟迪。比如,一般人都認(rèn)為諸葛亮的夫人黃氏相貌丑陋,但先生卻指出此說不實(shí),認(rèn)為所謂“丑女”乃諸葛亮岳父的謙詞,其實(shí)她并不丑。又如,先生考證認(rèn)為上海的第一位城隍爺是西漢權(quán)臣霍光,讓人耳目一新。可以說,無論男女老少,不管士農(nóng)工商,不同的讀者都能在《史林新語》這部書中找到自己的興趣點(diǎn)。而這部書,只是先生通俗學(xué)術(shù)著作的冰山一角而已。同時(shí),也許還應(yīng)該補(bǔ)充說明的是,這部書出版的時(shí)候,先生已是92歲高齡,過了鮐背之年,但依然思維敏捷,精神矍鑠,記憶力不凡,讓一些后輩驚佩得呼之為“文壇老妖”——所謂妖者,凡人難以企及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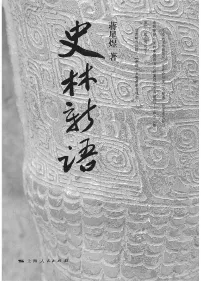
蔣星煜著《史林新語》書影

蔣星煜著《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書影
時(shí)光如梭,一晃,我畢業(yè)二十余年了。除了去上海先生寓所得先生耳提面命之外,我和先生之間的交流大部分依靠書信和電話。先生對我,依然十分寬容而嚴(yán)格——他很少正面批評,但輕輕一句話會讓我汗為之下,比如:“我20歲出頭就出版了《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你呢?”“我在你這個(gè)年紀(jì)的時(shí)候,已經(jīng)……”“你最近發(fā)表的東西,讓我還有點(diǎn)面子。”是啊,先生成名很早,抗戰(zhàn)時(shí)期就已從事新文學(xué)活動,表現(xiàn)出不凡的實(shí)力,尤其是文學(xué)評論,說理透徹,文氣極盛。比如1944年在《大公報(bào)·文藝》副刊上發(fā)表一版半長文《東北作家論》,次年在陳原主編的《民主評論》上刊發(fā)長文《論〈華威先生〉》,至今仍是研究張?zhí)煲淼闹匾Y料;也是1945年,在《新文藝》上發(fā)表的《論阿Q周圍的人物》在55年后的2000年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選入高三語文教科書,可見其影響之深遠(yuǎn)。抗戰(zhàn)時(shí)期重慶的《中央日報(bào)》副刊由孫伏園主編,其辦刊口號是“不管左中右,文章好就發(fā)”。1941年,先生根據(jù)某些電訊寫了一篇描寫意大利人民反抗墨索里尼法西斯統(tǒng)治的短篇小說《威尼斯的憂郁》,投給孫伏園先生,孫先生相當(dāng)喜歡,用了整版的篇幅一次刊登完畢,從此,他倆成為忘年交。眾所周知,孫伏園是魯迅的學(xué)生,和魯迅一起辦過《語絲》,但他從不借魯迅的聲望抬高自己,讓當(dāng)時(shí)還很年輕的先生從這個(gè)為人和氣、衣飾平常的書生身上看到了中國傳統(tǒng)文人的本色和風(fēng)骨。而先生自己,其實(shí)亦是如此。
2015年12月27日, 我又一次去浙江人民廣播電臺做“相約女作家”節(jié)目。照例是晚上九點(diǎn)開始直播,照例是八點(diǎn)出門,但不同的是,這一次,從未因直播而緊張的我竟然公交車坐過了站——因?yàn)椋@次直播,是我為導(dǎo)師蔣星煜先生送上的一瓣心香,是我和戲曲界學(xué)人前輩一起送別先生的特別節(jié)目。我的恩師們,華東師大齊森華、趙山林教授和蘇州大學(xué)周秦教授等都滿懷深情地回憶起山高水長的蔣公之風(fēng)。還有中山大學(xué)康保成教授強(qiáng)調(diào):“蔣先生對我有知遇之恩!”二十多年前的一個(gè)清晨,他從廣州到上海蔣先生寓所去拜訪,先生開門納客:“如果你是上海本地的我就不開門了,因?yàn)槲野疽构ぷ鳎瑒倓偛盘上隆!闭绺=ㄠu自振老師所言,雖然蔣先生的入室弟子并不多,但學(xué)界受先生影響的學(xué)者卻有一大批。近年來先生因年事已高,很少參加學(xué)術(shù)會議。我在會議上就常常遇到同行前輩說:“幫忙給老人家?guī)€(gè)好啊,老先生對我的幫助很大的。”睿智、嚴(yán)謹(jǐn),樂于提攜后進(jìn),就是我們印象中共同的蔣公星煜。
節(jié)目直播到一半,主持人陳芒問:“郭老師,在今天的節(jié)目之前,可能聽眾朋友們并不太熟悉蔣老先生,現(xiàn)在大家都知道了,蔣老是戲曲專家,是《西廂記》《桃花扇》專家,學(xué)問很棒,為人很好,特別值得我們懷念和敬重。不過,老人家除了是很有成就的學(xué)者、作家以外,還有什么讓后輩印象深刻的呢?老人家是不是特別嚴(yán)肅,特別不好親近呢?”哦,那自然不是的。在我的記憶里,印象深刻的是除了先生的書房汗牛充棟,還有每次上課我和師兄享用的正宗的西餐——尤其那羅宋湯特別美味。先生還喜歡跳交誼舞,每次學(xué)校辦舞會他都樂意出席,弄得百分百舞盲的我緊張萬分——得事先給先生找好合適的舞伴啊,這可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務(wù),似乎會跳的師姐師妹們都被我央及遍了吧。好在先生很lady first,對我總是網(wǎng)開一面,不僅從不曾要求我學(xué)會跳舞,而且每次去先生府上,他都按照約定的時(shí)間在陽臺上迎候,而且有好茶好咖啡招待,書啊,小禮物啊,我似乎也總是能比師兄先得贈的。而從學(xué)校幫先生借《綴白裘》等大部頭典籍之類的差事,則往往落到師兄的頭上。上課之余,還常常跟我們說點(diǎn)小掌故,比如建國初他參加的一項(xiàng)工作是審看大量的影片,白天黑夜地看,很累。其中一部片子是以妓女解放為主題的《姐姐妹妹站起來》。先生說,好不容易都看完了,他們就“哥哥弟弟倒下去也”,惹得我噴茶。還有,在談到一位著名戲曲學(xué)者的時(shí)候,先生說,那位先生因?yàn)樵谝粋€(gè)級別低的單位供職,一輩子沒有機(jī)會評正高,所以,挽聯(lián)可以是“生亦為人員(即是研究人員而非研究員),死亦為鬼員”,冷幽默中透著冷峻悲憫,至今恍如昨日聽聞。
先生一直穿洋裝,我從沒見過他有古典文學(xué)界習(xí)見的古雅中裝“扮相”。他也支持我進(jìn)劇場看戲,說搞戲曲的埋頭做案頭工夫是一種路子,注重場上自然也是一條正路。而他自己更是有不少紅氍毹上的好朋友,沒有一絲一毫輕賤戲子的傳統(tǒng)觀念……
這樣的先生,如果一定要用一個(gè)詞來概括的話,也許可以是“老克勒”——一位上海灘的“老克勒”,注重生活品質(zhì),自由出入中西,儒雅大方,很有腔調(diào),或者,用現(xiàn)在流行的詞,就是超有范兒。
今年年初,我開始致力于蔣星煜先生紀(jì)念專輯的約稿工作。也許,這是我為先生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先生,當(dāng)您看到《傳記文學(xué)》雜志上的這份答卷,不知道,您會給我打幾分?
責(zé)任編輯/胡仰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