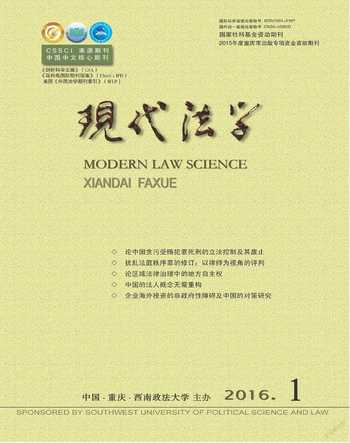論《刑法修正案(九)》關于恐怖犯罪的規定
摘要:《刑法修正案(九)》關于恐怖犯罪的規定,在總體上具有法益保護早期化、處罰范圍擴大化與處罰程度嚴厲化的特點。從構成要件的角度來說,則存在幫助犯的正犯化、預備犯的既遂化與構成要件的交叉化三個特點。幫助犯的正犯化與對幫助犯單純設置量刑規則,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法律規定;《刑法修正案(九)》所增加的第120條之一第2款以及被修正的第1款,對幫助犯實行了正犯化;對于實施上述兩款行為的,應當作為正犯處理;教唆、幫助他人實施該兩款行為的,應認定為兩款犯罪的教唆犯與幫助犯。《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第120條之二第1款,對預備犯實行了既遂化(獨立預備罪);該款規定的行為屬于實行行為,而不再是預備行為;教唆、幫助他人實施本款規定行為的,成立準備恐怖活動罪的教唆犯、幫助犯;為他人實施恐怖活動進行準備的行為,也可能成立準備恐怖活動罪;按獨立預備罪論處導致處罰程度輕于從屬預備罪時,應按從屬預備罪論處。《刑法修正案(九)》關于恐怖犯罪構成要件的規定存在大量交叉現象,但不能將這種交叉關系解釋為法條競合,而應認定為想象競合,從而發揮想象競合的明示機能,實現預防恐怖犯罪的目的。
關鍵詞:《刑法修正案(九)》;恐怖犯罪;幫助犯的正犯化;預備犯的既遂化;構成要件的交叉化
中圖分類號:
DF62
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1.03
《刑法修正案(九)》第5條至第7條是關于恐怖犯罪的規定,其中不僅修改了《刑法》第120條與第120條之一,而且在《刑法》第120條之一后增設了5個條文。
總的來說,《刑法修正案(九)》關于恐怖犯罪的修改內容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是法益保護的早期化。一般來說,法益保護的早期化主要表現為增加危險犯(尤其是抽象危險犯)、預備罪的規定,使刑法對危險犯、預備罪的處罰由例外變成常態。《刑法修正案(九)》對法益保護的早期化主要表現為,在恐怖組織或者相關人員的行為僅對公共安全產生抽象危險時,就作為犯罪處理。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第120條之六規定:“明知是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圖書、音頻視頻資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持有宣揚恐怖主義的物品的行為,對公共安全僅具有抽象危險,而沒有產生具體危險與實害,將這種行為規定為犯罪,是法益保護早期化的典型表現。第二是處罰范圍的擴大化。處罰范圍的擴大化與法益保護的早期化不是等同含義,但又有密切聯系。雖然法益保護的早期化意味著處罰范圍的擴大化,但處罰范圍的擴大化并不意味著法益保護的早期化。至為明顯的是,刑法增設某種實害犯時,雖然是處罰范圍的擴大化但不是法益保護的早期化。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第120條之四將“利用極端主義煽動、脅迫群眾破壞國家法律確立的婚姻、司法、教育、社會管理等制度實施的”行為規定為犯罪,這一行為實際上是實害犯(至少是具體危險犯)。《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其他恐怖犯罪,都可謂處罰范圍的擴大化。第三是處罰程度的嚴厲化。處罰程度的嚴厲化主要表現在,對新增設的犯罪,不管是實害犯還是危險犯,都規定了較重的法定刑。另一方面,對幫助犯與預備犯直接規定法定刑,也導致處罰更為嚴厲。因為按照刑法總則的規定,幫助犯與預備犯都可能減輕處罰乃至免除處罰,但《刑法修正案(九)》對幫助犯與預備犯直接規定法定刑后,使得部分恐怖犯罪的幫助行為與預備行為不可能被免除處罰。此外,《刑法修正案(九)》還擴大了財產刑的適用。例如,《刑法》第120條對組織、領導、積極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的行為僅規定了主刑,而沒有規定附加刑,對其他參加者在規定主刑的同時,僅規定了可以單處剝奪政治權利。《刑法修正案(九)》則對組織、領導、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罪增加了沒收財產與罰金的附加刑,并對新增加的恐怖犯罪都規定了財產刑。這是因為,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恐怖活動往往需要大量資金,增加財產刑有利于預防恐怖犯罪分子再次犯罪。
從構成要件層面來說,《刑法修正案(九)》關于恐怖犯罪的規定,有三個值得研究的立法現象(特點):一是幫助犯的正犯化,二是預備罪的既遂化,三是構成要件的交叉化。前兩個立法現象不僅直接加重了幫助恐怖活動、準備恐怖活動行為的處罰,而且間接擴大了恐怖犯罪的處罰范圍;后一個立法現象涉及法條競合與想象競合的區分。
本文擬對幫助犯的正犯化、預備罪的既遂化與構成要件行為的交叉化三個問題展開討論。因為這三個問題并不限于恐怖犯罪,而是涉及刑法分則規定的其他犯罪。研究這三個問題,不僅有利于對恐怖犯罪的定罪量刑,而且有助于解決其他犯罪的相關問題。
一、幫助犯的正犯化
刑法典一般在總則中規定共犯(教唆犯與幫助犯),分則所規定的構成要件行為通常是正犯行為,對于教唆、幫助正犯的行為則適用總則的規定,以共犯論處。所謂幫助犯的正犯化,則是指刑法分則條文直接將某種幫助行為規定為正犯行為,并且設置獨立的法定刑。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只要分則條文對幫助犯設置了獨立法定刑,就是幫助犯的正犯化。總的來說,分則條文對幫助犯設置獨立法定刑時,存在兩種情形:一是幫助犯的正犯化;二是單純的量刑規則
關于量刑規則的含義,參見:張明楷.加重構成與量刑規則[J].清華法學,2011(1).。在后一種情形下,分則條文并沒有將幫助犯提升為正犯,幫助犯依然是幫助犯,只是因為分則條文對其規定了獨立的法定刑,而不再適用刑法總則關于幫助犯(從犯)的處罰規定。
首先,幫助犯被正犯化后,不再按照刑法總則規定的從犯處理,因而不得適用《刑法》第27條關于對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的規定,而必須直接按分則條文規定的法定刑處罰,這便沒有免除處罰的可能性
當然另具有免除處罰情節的除外,但該“幫助”行為本身不可能成為免除處罰的情節。。同樣,對幫助犯單純設置量刑規則后,也是直接適用分則規定的法定刑,而不再適用總則關于對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的規定。就此而言,區分幫助犯的正犯化與單純對幫助犯設置量刑規則沒有實際意義。
其次,幫助犯被正犯化后,不再以正犯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不法行為為前提。眾所周知,根據共犯從屬性說的原理以及作為通說的限制從屬性說,只有當正犯實施了符合構成要件的不法行為時,才能將教唆犯、幫助犯作為共犯處罰
當然,由于我國刑法處罰預備犯,所以,在正犯實施了預備行為時,教唆者、幫助者也可能成立預備犯。這一結論同樣符合共犯從屬性說的原理。。例如,甲認識到乙將要殺害丙,而將丙的行蹤提供給乙。然而,乙并沒有實施殺害丙的任何行為。根據共犯從屬性說的原理,對甲不能以幫助犯論處。但是,在幫助行為被正犯化之后,就不需要以其他正犯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不法行為為前提。這并不意味著幫助犯的正犯化采取了共犯獨立性說,而是原本的幫助行為已經被提升為正犯行為,故不需要存在另外的正犯即可成立犯罪(而且成立的是正犯)。但是,倘若對幫助犯設置獨立的法定刑只是一種量刑規則,那么,該幫助犯的成立仍然應以正犯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不法行為為前提。顯然,就此而言,必須區分幫助犯的正犯化與幫助犯的量刑規則。
最后,幫助犯被正犯化后,由于原本的幫助行為提升為正犯行為,于是對該正犯行為的教唆、幫助行為又能成立共犯(教唆犯與幫助犯)。眾所周知,教唆犯是指唆使他人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不法行為,教唆他人實施幫助行為的,并不是按教唆犯處罰,而是按幫助犯處理
參見:大谷實.刑法講義總論[M].東京:成文堂,201:440;山中敬一.刑法總論[M].東京:成文堂,2008:899.例如,A得知B要殺害甲,于是教唆C將殺人兇器提供給B,B使用該兇器殺害了甲。A并沒有唆使他人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只是唆使他人實施幫助行為,故只能認定為幫助犯。;幫助犯是指幫助正犯者
例如,日本《刑法》第62條第1項規定:“幫助正犯的,是從犯。”其中的從犯就是指幫助犯。,所以,單純對幫助犯進行幫助,而沒有對正犯起幫助作用的,并不成立幫助犯,因而不得處罰
國外刑法理論對此存在爭議。例如,日本《刑法》第61條規定,教唆教唆犯的(即間接教唆)按教唆犯處罰,但沒有規定對幫助幫助犯的(即間接幫助)按幫助犯處罰。于是,對幫助幫助犯的能否處罰,就存在爭議。肯定說與否定說可謂勢均力敵。持肯定說的有平野龍一、前田雅英、山中敬一、山口厚等教授;持否定說的有團藤重光、福田平、大塚仁、西原春夫、川端博等教授。肯定說的理由是,幫助犯的處罰根據在于使正犯行為更為容易,因此,使正犯行為更為容易的間接幫助,也成立幫助犯。否定說則認為,刑法沒有規定處罰間接幫助,如果幫助行為使正犯行為更為容易,就要認定為對正犯的幫助,而非認定為對幫助犯的幫助。(參見:大谷實.刑法講義總論[M].4版.東京:
成文堂,2012:447-448.)但在本文看來,肯定說與否定說所爭議的并不是對幫助犯進行幫助的行為能否成立幫助犯,而是對幫助犯的幫助是否均能對正犯起幫助作用。。但是,一旦對幫助犯實行正犯化,就意味著原本的幫助行為成為刑法分則規定的正犯行為,故教唆他人實施該正犯行為的,就成立對正犯的教唆犯(而非幫助犯),幫助他人實施該正犯行為的,也會成立對正犯的幫助犯(而非不處罰)。但是,對幫助犯規定單純的量刑規則時,幫助犯的性質并沒有改變,所以對幫助犯的教唆依然僅成立幫助犯,單純對幫助犯的幫助,就不成立幫助犯。就此而言,幫助犯的正犯化與幫助犯的量刑規則的區分,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
例如,《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刑法》第120條之一,所增加的第2款規定:“為恐怖活動組織、實施恐怖活動或者恐怖活動培訓招募、運送人員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倘若認為本款規定屬于幫助犯的正犯化,那么,首先,對于實施本款行為的人不得依照《刑法》總則第27條的規定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只能直接按照第120條之一第1款的法定刑處罰。其次,招募、運送行為本身就是正犯行為,不以他人(正犯)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恐怖活動、恐怖活動培訓為前提。最后,教唆、幫助他人實施上述招募、運送行為的,成立第120條之一第2款犯罪的教唆犯與幫助犯。但是,倘若認為本款規定只是對招募、運送這類幫助犯設置了量刑規則(適用獨立的法定刑),那么,招募、運送行為本身仍然是幫助行為,其成立犯罪以正犯實施了符合構成要件的恐怖活動、恐怖活動培訓為前提;教唆他人實施招募、運送行為的,就不成立教唆犯,僅成立幫助犯;單純幫助他人實施招募、運送行為,而沒有對正犯行為起作用的,就不受處罰。
顯然,對幫助犯的正犯化與幫助犯的量刑規則不可能進行法律形式上的判斷(因為二者的法律標志完全相同,都是規定了獨立的法定刑),只能進行實質判斷。在進行實質判斷時,要根據共犯從屬性的原理、相關犯罪的保護法益,以及相關行為是否侵犯法益及其侵犯程度得出合理結論。
例如,《刑法》第244條第1款規定了強迫勞動罪的構成要件與法定刑,第2款規定:“明知他人實施前款行為,為其招募、運送人員或者有其他協助強迫他人勞動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要區分本款規定是幫助犯的正犯化,還是對幫助犯的量刑規則,必須進行如下實質判斷。
首先要判斷的是,在A明知B將要或者正在強迫他人勞動,便采取發微信的方式為B招募人員到B的工場,B接收A所招募的人員并強迫他們參加勞動時,A的行為是否侵犯了法益以及侵犯法益的程度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強迫勞動罪的保護法益是公民是否參加勞動的權利或者公民是否參加勞動的意志決定自由。不言而喻,由于B的行為直接造成了侵害他人人身權利的結果,而A的行為與該結果之間具有物理的因果性,所以,對A的行為應以犯罪論處。
其次要判斷的是,在甲明知乙將要或者正在實施強迫他人勞動的行為,便采取發微信的方式為乙招募人員到乙的工場,但乙并沒有接收甲所招募的人員,或者雖然接收了甲招募的人員,但根本沒有強迫他們參加勞動時,甲的行為是否侵犯了法益以及侵犯法益的程度如何?顯而易見,在上述情況下,乙對甲所招募的人員的行為既缺乏強迫勞動罪的構成要件符合性,也缺乏違法性即沒有侵犯甲所招募的人員是否參加勞動的權利。甲的行為既沒有作為正犯直接侵犯他人是否參加勞動的權利,也沒有作為共犯間接侵犯他人是否參加勞動的權利。既然如此,對甲的行為就不應以強迫勞動罪論處。
不難看出,《刑法》第244條第2款雖然對強迫勞動的幫助行為規定了獨立的法定刑,但該幫助行為成立犯罪以正犯實施了符合強迫勞動罪構成要件的不法行為為前提,故該款規定并不是幫助犯的正犯化,只是單純的量刑規則而已。
再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第284條之一第1款規定了組織考試作弊罪的構成要件與法定刑,第2款規定:“為他人實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幫助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那么,倘若甲為乙組織考試作弊提供了作弊器材,但乙沒有實施組織考試作弊罪的任何行為時,對甲應如何處理?由于甲的行為既沒有直接也沒有間接侵犯任何法益,故對甲的行為也不可能以犯罪論處。所以,《刑法》第284條之一第2款的規定也屬于量刑規則。
那么,《刑法修正案(九)》所增加的第120條之一第2款的規定,是幫助犯的正犯化還是幫助犯的量刑規則呢?可以肯定的是,第2款規定的“為恐怖活動組織、實施恐怖活動或者恐怖活動培訓招募、運送人員”并非限于為本人實施恐怖活動或者恐怖活動培訓招募、運送人員
倘若為了本人實施恐怖活動招募、運送人員,則同時屬于預備犯的既遂化。,而是包括為他人組織、領導的恐怖活動組織以及他人實施恐怖活動或者恐怖活動培訓招募、運送人員。那么,在后一種情形下,如何判斷招募、運送人員行為的可罰性呢?
可以肯定的是,當A招募、運送的人員已經成為恐怖活動組織成員,或者正在實施恐怖活動,或者正在接受恐怖活動培訓時,就意味著正犯已經實施了符合相關恐怖犯罪的構成要件的不法行為,而且A的行為與正犯結果之間具有物理的因果性,A的行為具備可罰性。但對此得出肯定結論,還不意味著第120條之一第2款對幫助行為實行了正犯化。需要討論的是,甲明知乙要組建恐怖活動組織、組織他人實施恐怖活動或者組織他人進行恐怖活動培訓時,為乙招募、運送了人員,乙接收了甲所招募、運送的人員,但還沒有著手實施相關恐怖活動、培訓活動時,即作為真正正犯的乙還沒有著手實施符合恐怖犯罪構成要件的不法行為時,甲的行為是否侵犯了法益以及侵犯程度如何?對此,可以聯系相關法條規定的犯罪進行判斷。
根據《刑法》第120條的規定,組織、領導、參加恐怖活動組織本身就是正犯行為。這種行為對公共安全雖然只有抽象的危險,但由于恐怖活動組織實施的犯罪具有極大的法益侵害性,恐怖活動組織本身具有實施恐怖犯罪的極大危險性,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的必要性大,所以,將這種抽象的危險行為規定為犯罪具有正當性。當今各國刑法也都對恐怖組織及其活動采取嚴厲打擊的態度,因而針對恐怖犯罪設置了大量的抽象危險犯。既然上述甲招募、運送的人員被恐怖組織或者人員接收,就表明甲的行為增加了恐怖活動組織實施恐怖犯罪的危險性,當然應當作為犯罪處理。換言之,“為恐怖活動組織、實施恐怖活動或者恐怖活動培訓招募、運送人員”的行為對公共安全法益的侵犯程度,并不一定輕于積極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的行為。因此,將這種行為作為正犯處理即承認幫助犯的正犯化,能夠使法條之間保持協調關系。
一般來說,在甲與恐怖犯罪分子乙具有通謀的情況下,乙通常都會接收甲所招募、運送的人員。如果乙接收了甲所招募的人員,使恐怖組織成員增加,即使乙還沒有組織他們實施恐怖活動,對甲也應適用第120條之一的規定定罪量刑。問題是,在甲與恐怖犯罪分子乙沒有通謀的情況下,甲為乙實施恐怖活動招募、運送人員,但乙沒有接收的,應當如何處理?在本文看來,由于乙的行為產生了擴大恐怖組織及其恐怖活動的危險,對此完全有可能認定為未遂犯,因而能夠肯定《刑法》第120條之一第2款的規定屬于幫助犯的正犯化。倘若A誤以為他人會實施恐怖活動而為他人招募、運送人員,但他人根本不實施恐怖活動的,可以認為A的行為屬于不能犯,故不應以犯罪論處。顯然,即使對A的這種行為不以犯罪論處,也只是因為該行為沒有侵害法益的抽象危險,因而不能否認《刑法》第120條之一第2款的規定屬于幫助犯的正犯化。
接下來還需要考慮的是,教唆、幫助他人實施招募、運送行為的,應否作為教唆犯、幫助犯處罰?答案也是肯定的。因為根據《刑法修正案(九)》所增加的第120條之二、之三與之五的規定,積極參加恐怖培訓活動的,宣揚恐怖主義或者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的,以及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戴宣揚恐怖主義服飾、標志的行為就成立犯罪,既然如此,教唆、幫助特定他人為恐怖犯罪活動招募、運送人員的行為,更值得科處刑罰。
由上可見,《刑法修正案(九)》所增加的第120條之一第2款,對幫助犯實行了正犯化。因此,對于實施本款行為的,應當作為正犯處理,教唆、幫助他人實施本款行為的,應認定為本款行為的教唆犯與幫助犯。基于同樣的理由,《刑法》第120條之一第1款的規定,基本上也是幫助犯的正犯化
稱“基本上”是因為可能存在例外。亦即,事后資助行為雖然不成立幫助犯,但也可能成立《刑法》第120條之一規定的犯罪。。
順便指出的是,由于幫助犯是對正犯的幫助,單純對幫助行為進行幫助的不成立幫助犯,故應區分某種行為是對正犯的幫助還是對幫助的幫助。本文的看法是,只要幫助行為與正犯結果具有因果性(即使正犯沒有意識到這種幫助行為),就應認定為對正犯的幫助,因而成立幫助犯。例如,乙得知丙進行恐怖活動培訓,便為丙招募人員,甲知道乙的行為真相,為乙招募人員出主意,使乙招募到大量人員并接受了恐怖活動培訓。在這種情況下,表面上是甲幫助了乙,實際上甲的行為與丙的正犯結果之間具有物理的因果性。因此,甲實際上是對丙的幫助,因而直接成立《刑法》第120條之一第2款的正犯,而不是成立該款的幫助犯。
二、預備犯的既遂化
一般來說,刑法將準備行為作為基本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實行行為)之前的行為予以規定的情形,就屬于從屬預備罪;刑法將準備行為規定為獨立的犯罪類型時,就屬于獨立預備罪。
在我國,從屬預備罪不是由分則規定,而是由總則規定。《刑法》第22條第1款與第2款分別規定:“為了犯罪,準備工具、制造條件的,是犯罪預備。”“對于預備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當行為人為了實行分則的具體犯罪而實施預備行為,因而成立犯罪預備時,不僅要引用分則條文的規定,適用分則所規定的法定刑,而且要適用總則第22條的規定。
獨立預備罪的行為則由分則條文具體描述為構成要件行為。由于刑法分則一般規定的是實行行為,而且以既遂為模式,所以,獨立預備罪的設立可謂預備犯的既遂化,或者稱為預備行為的實行行為化。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第120條之二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一)為實施恐怖活動準備兇器、危險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的;(二)組織恐怖活動培訓或者積極參加恐怖活動培訓的;(三)為實施恐怖活動與境外恐怖活動組織或者人員聯絡的;(四)為實施恐怖活動進行策劃或者其他準備的。本款所規定的行為原本是恐怖活動的預備行為,但該款將其規定為獨立的犯罪(準備恐怖活動罪),使之成為既遂犯罪,不再適用刑法總則關于預備犯的處罰規定。
關于獨立預備罪,有以下幾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第一,獨立預備罪是否存在實行行為?
德國刑法理論不使用實行行為的概念,日本刑法理論對預備罪是否存在實行行為一直存在爭議。否定說認為,預備行為是無定型、無限定的行為,是實行行為之前的行為,因此,不管是從屬預備罪還是獨立預備罪,都不具有作為構成要件的實行行為的特點。肯定說認為,從屬預備罪與獨立預備罪均存在固有的構成要件,因而均有實行行為。折中說認為,獨立預備罪中存在實行行為,從屬預備罪中不存在實行行為。
本文原則上贊成折中說,認為刑法所規定的從屬預備罪的行為不屬于實行行為,獨立預備罪的行為則是實行行為。首先,如果認為從屬預備罪的行為是實行行為,會導致實行行為概念的混亂。日本刑法將從屬預備罪規定在分則中,因而有可能認為從屬預備罪也有實行行為;與之不同的是,我國刑法將從屬預備罪規定在總則中。因此,在我國,既能夠以預備罪是由總則規定還是由分則規定來區分從屬預備罪與獨立預備罪,也可以原則上肯定總則規定的是預備行為,分則規定的是實行行為
但應注意的是,刑法規定的預備罪中的行為是否屬于實行行為與實行行為能否成立預備罪,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倘若承認著手與實行行為的分離,主張實行行為可能存在于著手之前,那么,著手之前的所謂“實行行為”完全可能僅成立預備罪。例如,A為了殺害B,于2015年8月1日中午從甲地通過郵局將有毒食物寄給乙地的B,B于8月3日中午收到但沒有打開郵件,8月6日中午B正要吃食物時發現異味而將有毒食物扔棄。關于著手的認定,形式的客觀說會采取寄送主義,即A于8月1日中午寄送時就是殺人的著手。但這種觀點明顯使著手提前,為本文所不采。危險結果說既可能采取到達主義(8月3日中午為著手),也可能采取被利用者標準說(8月6日中午為著手)。應當認為,只有當B準備或者開始吃有毒食品時,才產生死亡的緊迫危險,故被利用者標準說是合適的。認定著手后,A寄送有毒食物的行為便理所當然成為殺人的實行行為。(參見:山中敬一.刑法總論[M].2版東京:成文堂,2008:714.)但是,倘若有毒食物還沒有到達B手中時案發的,則由于沒有著手而只能認定為殺人預備(參見:松原芳博.刑法總論[M].東京:
日本評論社,2013:297-302.),此時沒有必要將寄送有毒食物的行為認定為殺人的實行行為。即使有人堅持認為寄送行為是實行行為,也只能認定為預備犯。。其次,從共犯從屬性的原理出發,也不應當將從屬預備罪的行為當作實行行為。例如,甲知道乙將要搶劫銀行而為其準備兇器時,甲在什么情況下成立預備犯?如果認為甲本人實施了預備罪的實行行為,那么,即使乙沒有實施任何行為,甲也成立預備罪。但本文難以贊成這種結論。因為按照共犯從屬性說的原理,只有當乙至少實施了預備行為時(如攜帶兇器前往犯罪現場等),才能對甲以預備罪的幫助犯論處。倘若乙著手實行了搶劫行為,甲當然也成立幫助犯。所以,否認從屬預備罪的行為是實行行為,可以貫徹共犯從屬說的原理。最后,獨立預備罪的行為,在分則條文得到了具體描述,并非無定型、無限定的行為,因而從形式上說完全具備實行行為的特點。從實質上說,刑法分則對極個別預備犯實行既遂化,就是因為該預備行為的抽象危險十分嚴重,值得作為既遂犯處理。所以,獨立預備罪的行為也具備了實行行為的實質屬性。基于上述理由,本文認為,《刑法》第120條之二第1款所規定的四項行為,均被提升為實行行為,而不能再作為預備行為處理。
第二,規定獨立預備罪的分則條文沒有描述的其他預備行為,能否適用刑法總則關于從屬預備罪的規定?
就上述《刑法》第120條之二第1款而言,似乎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因為該款第4項規定了“其他準備”。不過,倘若認為第4項中的“其他準備”只是第4項的兜底規定,而不是本條第1款的兜底規定,依然存在上述問題。
從表述形式上看,“其他準備”似乎只是第4項的兜底規定。但是,倘若這樣理解,那么,第120條之二第1款前三項的規定就沒有任何意義。因為相對于“為實施恐怖活動進行策劃”而言,前三項的規定都屬于“其他準備”。所以,只能認為,“其他準備”實際上是第120條之二第1款的兜底規定,故其他準備行為都能夠包括在其中。亦即,對于“其他準備”行為必須直接適用《刑法》第120條之二第1款的規定,并直接根據該款規定的法定刑處罰,而不必適用刑法總則關于從屬預備罪的規定。
但是,不排除以后的立法可能對獨立預備罪不設置諸如“其他準備”的兜底規定,也不排除有人認為第120條之二第1款第4項的“其他準備”只是第4項的兜底規定,因而僅限于與為實施恐怖活動進行策劃相當或者同類的準備行為。所以,關于獨立預備罪的規定總會產生上述問題,因而需要研究。
本文看法是,倘若刑法分則規定獨立預備罪是為了限制預備罪的處罰范圍,那么,對于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的預備行為就不應當適用刑法總則關于從屬預備罪的規定。這是容易被人接受的結論。但是,倘若分則規定獨立預備罪是為了擴大預備罪的處罰范圍,并且加重對預備罪的處罰,那么,對于分則條文沒有明文規定的其他準備行為,就必須適用刑法總則關于從屬預備罪的規定。從《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例來看,在分則條文設置獨立預備罪,不是為了限制預備罪的處罰范圍,而是為了擴大預備罪的處罰范圍,并且加重對預備罪的處罰。我國刑法總則雖然規定原則上處罰預備罪,但司法實踐對預備罪的處罰極為有限。所以,《刑法》第120條之二第1款設置獨立的準備恐怖活動罪,就是為了擴大對恐怖犯罪的處罰范圍,而且使得恐怖犯罪的預備行為不可能免除處罰。所以,倘若認為某種恐怖犯罪的預備行為沒有被第120條之二第1款所包含,仍可適用刑法總則關于從屬預備罪的規定,判處輕于獨立預備罪的刑罰。
第三,教唆、幫助他人實施獨立預備罪的,應當如何處罰?
如前所述,教唆犯是指唆使他人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不法行為,幫助犯是指幫助正犯者。那么,教唆、幫助他人實施獨立預備罪的行為,是否成立教唆犯與幫助犯呢?例如,A唆使B積極參加恐怖活動培訓的,是否成立準備恐怖活動罪的教唆犯?再如,在乙為實施恐怖活動而欲與境外恐怖活動人員聯絡時,甲將境外恐怖活動人員的聯系方式提供給乙的,是否成立準備恐怖活動罪的幫助犯?本文對此持肯定意見。
首先,從形式上說,準備恐怖活動罪已經不再是刑法總則所規定的預備犯,它雖然在理論上被稱為獨立預備罪(這種稱謂只是因為條文使用了“準備”或者“預備”的表述),但實際上已經被實行行為化或者既遂化。而且如前所述,準備恐怖活動罪的行為,已經不再是預備行為而是實行行為;實施了《刑法》第120條之二第1款規定的行為的,就不再按預備犯處罰,而是作為既遂犯處理。既然如此,上述A的行為便符合唆使他人實施符合構成要件的不法行為的條件,因而成立教唆犯;上述甲的行為則符合幫助正犯的條件,因而成立幫助犯。
其次,從實質上說,對《刑法》第120條之二第1款規定的準備恐怖活動罪實施的教唆或者幫助行為,與刑法分則其他條文規定的恐怖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相當,因而具有處罰的必要性。例如,《刑法》第120條之二第1款規定的準備恐怖活動罪包括“組織恐怖活動培訓”的行為,而《刑法》第120條之一第1款明文將“資助恐怖活動培訓”規定為犯罪行為,而資助行為是明顯的幫助行為。這足以說明,準備恐怖活動罪的幫助行為,具有處罰的必要性。再如,《刑法》第120條之三將宣揚恐怖主義規定為犯罪,與之相比,教唆特定的他人實施準備恐怖活動罪的行為,也同樣具備處罰根據。
第四,為了實行獨立預備罪而實施的準備行為(可謂獨立預備罪的預備行為),能否適用刑法總則第22條關于從屬預備罪的規定?
《刑法》第22條將“為了犯罪”規定為預備罪的主觀要件。預備罪中的“為了犯罪”顯然是指“為了實行犯罪”。因為預備行為是為實行行為制造條件的,實施預備行為就是為了進一步實施實行行為。“為了犯罪”的字面意義包括為了預備犯罪與為了實行犯罪,但為預備行為實施的“準備”行為,不能認定為犯罪預備。例如,為了實行殺人購買毒藥的行為,可能是預備行為;但為了購買毒藥而打工掙錢的行為,不是犯罪預備行為。可見,由于犯罪預備是犯罪,而為了實施犯罪預備行為所進行的“準備”又不是犯罪預備,故應將“為了犯罪”理解為“為了實行犯罪”。由于獨立預備罪的行為已經被提升為實行行為,于是產生了另一問題:對獨立預備罪之前的預備行為,能否按照《刑法》第22條的規定以預備犯論處?
從形式上說,既然獨立預備罪的行為已經是實行行為,那么,為了實施獨立預備罪而實施的準備行為,也符合從屬預備罪的“為了實行犯罪”“準備工具、制造條件”的成立要件。但本文認為,對此還必須進行實質判斷。換言之,雖然《刑法》第22條的規定似乎表明處罰所有的預備犯,但對第22條的解釋以及對預備犯的認定,還必須以《刑法》第13條的“但書”為指導,不能將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認定為預備犯。另一方面,獨立預備罪實際上已經擴大了預備罪的處罰范圍,如果一概將獨立預備罪之前的準備行為認定為犯罪,必然導致處罰范圍的不當擴大。
所以,本文認為,對于為了實施《刑法》第120條之二規定的準備恐怖活動罪而實施的準備行為,只能通過實質判斷認定其是否值得科處刑罰。例如,為了組織恐怖活動培訓,已經聯系了講授人員與參加人員,或者準備了培訓場所的,應按照《刑法》第22條的規定,以預備犯(從屬預備罪)處罰。但是,為了準備危險物品而閱讀相關書籍或者在網絡上查詢相關資料的行為,不能認定為預備犯;為了購買兇器而掙錢的行為,也不能認定為預備犯。概言之,只有當行為對法益具有一定的抽象危險時,才可能認定為預備犯。
第五,為他人實施恐怖活動而進行準備的行為是否成立準備恐怖活動罪?
如前所述,犯罪預備的主觀要件是為了實行犯罪。從文理上解釋,為了實行包括為了自己實行犯罪(自己預備罪)與為了他人實行犯罪(他人預備罪)。自己預備罪沒有疑問,亦即,為了自己實施恐怖活動而實施《刑法》第120條之二規定的準備行為,當然成立準備恐怖活動罪。問題是,為了他人實行恐怖活動而實施《刑法》第120條之二規定的準備行為的,是否成立準備恐怖活動罪?亦即,是否承認他人預備罪?對此,日本刑法理論上存在肯定說、否定說與二分說。
肯定說認為,為了他人實行犯罪而實施的準備行為,完全符合預備罪的特征。因為預備與實行的著手具有性質上的差異,兩者間存在質的斷絕,故預備行為不限于為了自己實行犯罪;為了他人實行殺人或者搶劫而實施預備行為時,如果他人還沒有著手,就成立預備罪的共犯(包括共同正犯)。日本也有判例采取了肯定說
參見:日本最高裁判所1962年11月8日判決,載日本《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16卷第11號,第1522頁。。眾所周知,日本《刑法》第153條規定了準備偽造貨幣罪(“以供偽造、變造貨幣、紙幣或者銀行券之用為目的,準備器械或者原料的,處三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懲役”),日本刑法理論的通說認為,為了他人偽造、變造貨幣而準備器械或者原料的,也成立本罪
參見:團藤重光.刑法綱要(各論)[M]. 3版.東京:創文社,1990:255;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M].4版.東京:成文堂,2012:436;西田典之.刑法各論[M].6版.東京:弘文堂,2012:333;前田雅英.刑法各論講義[M].5版.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1:495;山口厚.刑法各論[M].2版.東京:有斐閣,2010:428.。
否定說認為,為了他人實行犯罪而實施的準備行為,只不過是對預備的幫助,而且行為的危險性很小,不應當作為預備罪處理。例如,大塚仁教授指出:“預備罪、陰謀罪本來所處罰的是為了特定既遂犯的實行而實施的準備行為。在這個意義上說,應認為預備罪、陰謀罪的構成要件是分別對該既遂犯的構成要件進行修正而形成的……因此,預備罪、陰謀罪的故意,原則上與各罪的既遂犯所要求的故意沒有區別,預備行為者與陰謀行為者必須以自己實現犯罪為目的進行準備。雖然有見解認為,為了他人實現犯罪而實施的準備行為即他人預備行為(不真正預備行為)成立預備罪,但這樣擴張預備罪的觀念并不妥當。”但是,大塚仁教授在討論日本的準備偽造貨幣罪時也認為,行為人以供他人偽造、變造為目的而準備器械或者原料時,成立準備偽造貨幣罪的幫助犯。由此看來,大塚仁教授也承認為了他人實行犯罪而實施準備行為的,成立獨立預備罪的幫助犯。
二分說認為,只有當刑法條文特別承認為了他人實行的預備行為時,才屬于他人預備罪;此外的情形則不成立預備罪。如平野龍一教授指出:“自己預備罪,是指只有以自己(或與他人共同)實施實行行為為目的而實施預備罪的情況……與此相對,像準備偽造貨幣罪那樣,規定‘以供偽造、變造貨幣、紙幣或者銀行券之用為目的,準備器械或者原料’時,就不限于以自己偽造為目的的情況,也包括供他人偽造用的情況。”
本文采取限定的肯定說。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為了……”都不限于為了自己,而是包括為了他人。從文理上說,《刑法》第120條之二第1款第1、3、4項所規定的“為實施恐怖活動”,既包括“為自己實施恐怖活動”,也包括“為他人實施恐怖活動”。所以,承認《刑法》第120條之二第1款規定的犯罪包括他人預備罪沒有法律障礙。但是,倘若甲以為乙將要實施恐怖活動,而為乙準備兇器時,乙根本不實施恐怖活動的,則難以認定甲的行為具有可罰性(屬于不能犯)。換言之,在甲為了乙實行恐怖犯罪而實施準備行為時,只有當乙至少實施了恐怖犯罪的預備行為時,甲才成立他人預備罪。
第六,按獨立預備罪論處導致處罰程度輕于從屬預備罪時,應當如何處理?
《刑法》第120條之二第2款規定:“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例如,為了實施恐怖活動而非法購買大量槍支、彈藥的行為,同時構成非法買賣槍支、彈藥罪,并且屬于情節嚴重。對此,應以非法買賣槍支、彈藥罪論處,適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問題是,上述第2款規定的“其他犯罪”是否包括相應的從屬預備罪?
《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第120條之二第1款雖然對準備恐怖活動罪設置了獨立的法定刑,而且最高刑為15年有期徒刑,但是,由于刑法總則第22條規定對預備犯只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因而在特殊情況下也可能不從輕、減輕處罰與免除處罰,所以,必然出現這樣的現象,即按第120條之二第1款規定的法定刑處罰,可能輕于按從屬預備罪(即行為人準備實行的恐怖犯罪的預備犯)處罰,在這種情況下,能否按從屬預備罪處罰?
假如甲、乙等人為實施大規模殺人的恐怖活動進行了策劃,準備了大量危險兇器,并且對參加人員進行了培訓。在這種情況下,倘若認定為準備恐怖活動罪(即獨立預備罪),按《刑法》第120條之二第1款規定的法定刑處罰,最高刑為15年有期徒刑。但是,倘若按故意殺人罪的預備犯(即從屬預備罪)處罰,并且根據案件事實不應從輕、減輕處罰時,則完全可能判處無期徒刑。如果后者更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則應按后者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的預備犯。所以,《刑法》第120條之二第2款所規定的“其他犯罪”包括相應的從屬預備罪。
三、構成要件的交叉化
只要閱讀《刑法修正案(九)》關于恐怖犯罪的條文,就會發現條文所規定的構成要件之間存在大量交叉現象。
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第120條之二第1款第2項將組織恐怖活動培訓規定為獨立的犯罪,如前所述,該行為實際上是預備犯的既遂化,而且根據前述分析,預備犯被既遂化,意味著預備行為被實行行為化,于是,“資助”恐怖活動培訓的行為,就是第120條之二第1款第2項的幫助犯。但是,第120條之一第1款將“資助恐怖活動培訓”規定為另一種正犯行為。于是,準備恐怖活動罪的幫助犯(第120條之二第1款第2項的幫助犯),同時也是幫助恐怖活動罪(第120條之一第1款)的正犯。
又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第120條之五規定:“以暴力、脅迫等方式強制他人在公共場所穿著、佩戴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服飾、標志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被強制穿戴上述服飾、標志的人,如果并沒有喪失自由意志的,是否成立《刑法修正案(九)》所增設的第120條之三所規定的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犯罪?倘若得出肯定結論,那么,對強制者是認定為強制他人穿戴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服飾、標志罪的正犯,還是認定為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罪的教唆犯?在被強制穿戴上述服飾、標志的人喪失自由意志時,雖然被強制者不成立犯罪,那么,強制者是成立強制他人穿戴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服飾、標志罪的正犯,還是成立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罪的間接正犯?概言之,第120條之五的正犯與第120條之三的教唆犯、間接正犯形成的交叉,應當如何處理?
再如,《刑法修正案(九)》所規定的各種恐怖活動犯罪與刑法分則其他章節的犯罪也可能產生交叉關系。《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第120條之四規定:“利用極端主義煽動、脅迫群眾破壞國家法律確立的婚姻、司法、教育、社會管理等制度實施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條規定與《刑法》第278條規定的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刑法》第300條規定的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利用迷信破壞法律實施罪是什么關系?《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第120條之二規定的“為實施恐怖活動準備……危險物品”與《刑法》第125條規定的非法制造、買賣、儲存槍支、彈藥、爆炸物罪及非法制造、買賣、儲存危險物質罪是什么關系?
上述問題可以歸納為兩類:第一類情形是,準正犯(被正犯化的幫助犯)或準既遂犯(被既遂化的預備犯)同時構成另一正犯時,以及此罪的幫助或者教唆行為同時構成彼罪的正犯時,應當如何處理?以下將這類情形稱為廣義共犯的交叉(包括恐怖犯罪的共犯與其他共犯的交叉)。第二類情形是,法條規定的構成要件行為存在的交叉是屬于法條競合還是屬于想象競合?以下將這類情形稱為構成要件的交叉。這兩類情形的區分也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換言之,前一類情形事實上也存在構成要件的交叉現象。
總的來說,在處理兩類問題時,必須以《刑法修正案(九)》關于恐怖犯罪的立法宗旨為指導,同時實現罪刑相應與罪刑協調(罪與罪之間的均衡)。一方面,《刑法修正案(九)》對恐怖犯罪的規定旨在擴大恐怖犯罪的處罰范圍,并且加重了恐怖犯罪的法定刑。另一方面,“罪數論·競合論是在實體上經過了對某一行為的違法、責任的判斷階段后,為量刑提供基礎的領域的討論。”換言之,罪數論也好、競合論也罷,就是為了解決量刑問題,“正確的刑罰裁量終究是整個競合理論的目的。”所以,不考慮罪刑相應與罪刑協調的要求,單純從形式邏輯出發研究《刑法修正案(九)》中的構要要件交叉現象或者其他分則法條的構成要件交叉現象,為本文所不取。
(一)廣義共犯的交叉
《刑法修正案(九)》既有將幫助犯正犯化的現象,也有將預備犯既遂化的現象。可以認為,幫助犯被正犯化后是一種準正犯,預備犯被既遂化后是一種準既遂犯
為了避免混淆,不得不使用準正犯與準既遂犯的概念。。
其一,在正犯的法定刑高于或者同于準正犯(被正犯化的幫助犯)的法定刑時,如果準正犯的行為同時符合正犯的構成要件,應按正犯處罰。例如,為實施恐怖活動準備危險物品的行為(第120條之二第1款第1項)同時屬于非法儲存爆炸物罪的正犯時,應適用非法儲存爆炸物罪的法定刑予以處罰
這實際上是構成要件的交叉現象,如后所述,不是法條競合,而是想象競合犯。。
其二,在既遂犯的法定刑高于或者同于準既遂犯(被既遂化的預備犯)的法定刑時,如果準既遂犯的行為同時符合既遂犯的構成要件,應按既遂犯處罰。例如,為境外恐怖活動組織招募人員,并且以剝奪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運送招募的人員偷越國(邊)境(該行為原本屬于預備犯,但被第120條之一第2款既遂化),倘若不符合數罪并罰的條件,就應適用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既遂犯)的法定刑科處刑罰
這種情形也是構成要件的交叉現象,屬于想象競合。。
其三,在按幫助犯處罰應當適用刑法總則的從寬規定,而按(準)正犯處罰更能實現罪刑相應與罪刑協調時,應當適用(準)正犯的規定。例如,對資助恐怖活動培訓的行為,以及為恐怖活動培訓招募、運送人員的準正犯提供幫助的行為,不應認定為準備恐怖活動罪(第120條之二)中的“組織恐怖活動培訓”的幫助犯,而應認定為幫助恐怖活動罪(第120條之一)的正犯。
其四,輕罪的正犯同時構成重罪的教唆犯或者間接正犯時,應當按重罪的教唆犯或者間接正犯處罰。例如,《刑法》第120條之五規定的強制他人穿戴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服飾、標志罪的最高刑只有3年有期徒刑,而第120條之三規定的宣揚恐怖主義罪的最高刑為15年有期徒刑。如果強制他人穿戴上述服飾、標志的行為,同時成立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罪的教唆犯或者間接正犯,就應適用后罪的法定刑。
(二)構成要件的交叉
構成要件的交叉是否屬于法條競合,在國內外存在不同觀點。德國的法條競合理論并沒有承認法條競合的交叉關系,日本則有部分學者承認法條競合的交叉關系。
所謂交叉關系,表現為屬于A概念的事項中有一部分屬于B概念,屬于B概念的事項中有一部分同時屬于A概念。換言之,A法條與B法條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存在部分重合時,就屬于交叉關系。例如,日本《刑法》第224條規定:“略取或者誘拐未成年人的,處三個月以上七年以下懲役。”第225條規定:“以營利、猥褻、結婚或者對生命、身體的加害為目的,略取或者誘拐他人的,處一年以上十年以下懲役。”山口厚教授認為,在以營利、猥褻等目的略取、誘拐未成年人這一部分,略取、誘拐未成年人罪與營利目的等略取、誘拐罪就形成交叉關系,適用重法條優于輕法條的原則。
為什么德國的競合論不承認法條競合的交叉關系呢?這涉及法條競合與想象競合的區別。承認法條競合的交叉關系時,雖然適用一個重法條,但由于法條競合時只能適用一個法條,所以其他法條被排斥適用。與之相反,想象競合時并不是只適用一個法條,而是同時適用行為所觸犯的數個法條,在判決中應當明示被告人的行為觸犯數個罪名(想象競合的明示機能),只是按其中最重犯罪的法定刑量刑而已。正因為如此,法條競合時仍屬單純一罪,而想象競合原本為數罪只是作為科刑上一罪處理
參見:前田雅英.刑法總論講義[M].6版.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5:392,399;山口厚.刑法總論[M].2版.東京:
有斐閣,2007:365,379;井田良.講義刑法學·總論[M].東京:有斐閣,2008:523,532.。誠然,“如果將想象競合與法條競合的法律后果相比較,就會證實一個論斷,即除了在法條競合里也可能優先適用較輕的刑罰,它們的法律后果幾乎沒有差異。”但“不應由此得出結論認為,除了特殊關系,法條競合的其他情況都可以被當作想象競合處理。”
就日本《刑法》第224條與第225條而言,雖然形式上存在外延上的交叉關系,但是,當行為人以營利、猥褻等目的略取、誘拐未成年人時,如果僅適用第224條,就沒有評價其不法目的;如果僅適用第225條,就沒有評價略取、誘拐未成年人這一內容。只有認定為想象競合,在判決中明示行為同時觸犯第224條與第225條,才能實現全面評價。不難看出,只要重視想象競合的明示機能,就可以否認法條競合的交叉關系。
長期以來,我國刑法理論基本上采用了單一的形式標準區分法條競合與想象競合,甚至通過介入案件事實判斷兩個法條之間是否存在包容(包攝)與交叉等關系,結局是將大量的想象競合納入法條競合。例如,有學者指出,當行為人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招搖撞騙,騙得財物時,就成立外延上的交叉關系。據此,《刑法》第266條與第279條存在交叉關系,屬于法條競合的交叉關系,適用原則是重法條優于輕法條。可是,第279條所規定的招搖撞騙罪并沒有將財物作為保護法益,因而不以騙取財物為要件,如果僅適用其中一個法條,就沒有對不法內容進行全面評價。亦即,如果僅認定為招搖撞騙罪,就沒有評價行為對財產的不法侵害內容;如果只認定為詐騙罪,就沒有評價行為對國家機關公共信用的不法侵害內容。只有認定為想象競合,在判決中明示行為觸犯上述兩個罪名,只是適用一個重法定刑,才能全面評價行為的不法內容。
再如,前述為境外恐怖活動組織招募人員,并且以剝奪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運送招募的人員偷越國(邊)境的情形,倘若不符合數罪并罰的條件,就不得并罰。但是,如果僅認定為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就沒有評價恐怖活動對公共安全的不法侵害內容;如若僅認定為幫助恐怖活動罪,就沒有評價行為對國(邊)境管理秩序的不法侵害內容。所以,應當認定為想象競合,在判決中明示行為同時觸犯兩個罪名,最后僅適用一個重法定刑。
同樣,《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第120條之四規定的利用極端主義破壞法律實施罪與《刑法》第278條規定的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存在交叉關系。即當行為人利用極端主義煽動群眾暴力抗拒國家法律實施時,同時觸犯了兩個法條。如果僅認定為利用極端主義破壞法律實施罪,就沒有評價其中的煽動群眾“暴力抗拒”的不法內容;如果僅認定為煽動暴力抗拒法律實施罪,就沒有評價其中的利用極端主義的不法內容。所以,只有認定為想象競合,在判決中明示行為同時觸犯兩個罪名,最后僅適用一個重法定刑,才能實現全面評價。
那么,在上述案件中,為什么不能僅適用一個法條,承認二者之間為法條競合呢?或者說,為什么雖然最終按一個重罪的法定刑量刑,而必須認定為想象競合,并在判決書中明示其行為同時構成兩個犯罪呢?
首先,刑法的機能是保護法益和保障國民自由。對任何一個案件的不法內容,只有既充分、全面評價又不重復評價,才能既保護法益,也保障國民自由。如果一個人的行為同時侵害了公共安全與社會管理秩序,而法官僅評價其行為構成恐怖犯罪,便沒有對社會管理秩序予以保護,這不利于實現刑法的保護法益機能。如前所述,競合論或者罪數論都是為量刑服務的。量刑的基準是責任,或者說是有責的不法。如果A法條的不法內容(程度)完全能夠包容B法條的不法內容(程度),那么,就只需要適用A法條,而不可能適用B法條。如果A法條的不法內容不能包容B法條的不法內容,當甲的行為同時存在A法條的不法內容與B法條的不法內容時,那么,適用其中任何一個法條,都不能對甲的行為內容進行全面評價。在這種場合,就必須認定為想象競合。在德國,“一個行為(犯罪事實)的不法內容,只要適用一個刑罰法規就能夠窮盡全部評價時,便是法條競合;在有必要適用數個刑罰法規進行評價時,就是想象競合(觀念的競合)。”這是因為,“通過設立想象競合,能夠在判決中充分評價行為人的法益侵害態度(想象競合的明示機能)……對一個行為必須在妥當的、所有的法律觀點之下做出判斷。”
其次,刑法雖然具有行為規范的一面,但刑法不是針對一般人制定的,而是針對司法人員制定的。一般人實際上是借由媒體通過了解判決內容來了解刑法的。判決是對刑法的活生生的解讀,解讀得越明確,刑法的內容就越容易被一般人理解,刑法就越能發揮行為規范的作用,從而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就本文所討論的問題而言,要發揮刑法的行為規范的作用,就必須注重想象競合的明示機能。想象競合的明示機能,是指由于被告人的行為具有數個有責的不法內容,在判決宣告時,必須將其一一列出,做到全面評價,以便被告人與一般人能從判決中了解行為觸犯幾個犯罪,從而得知什么樣的行為構成犯罪。例如,在為境外恐怖活動組織招募人員,并且以剝奪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運送招募的人員偷越國(邊)境的案件中,倘若判決僅宣告被告人的行為成立幫助恐怖活動罪,可能使被告人與一般人誤以為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的行為不構成犯罪;反之,倘若僅宣告被告人的行為成立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就可能使被告人與一般人誤以為為恐怖活動組織招募、運送人員的行為不成立犯罪。這樣的認定顯然不利于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再如,《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第120條之六規定:“明知是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圖書、音頻視頻資料或者其他物品而非法持有,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其中的“持有”既可以是秘密的,也可以是公開的,既可以藏于家中,也可以攜帶于公共場合。倘若攜帶于公共場合的行為同時觸犯了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罪,那么,如果判決僅宣告被告人的行為成立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品罪,則可能使被告人與一般人誤以為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行為不成立犯罪;反之,如若判決僅宣告被告人的行為成立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罪,就可能使被告人與一般人誤以為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品的行為不成立犯罪。只有在判決中明示上述行為同時觸犯兩個罪,才有利于實現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目的。
總之,在法條之間雖然存在交叉關系,但僅適用一個法條不能全面保護法益時(兩個法條的保護法益不同),或者不能全面評價行為的不法內容時(雖然侵害相同法益,但不法內容存在區別),不應當認定為法條競合,而應當認定為想象競合。換言之,法條競合的確定,并不是一個純粹的邏輯問題。“必須通過對被排除適用一方的構成要件的不法程度進行目的論的考量予以補充的現象并不罕見。”基于同樣的理由,對于《刑法修正案(九)》有關恐怖犯罪的規定所形成的交叉關系,通常應認定為想象競合,而不宜認定為法條競合。
參考文獻:
[1]高橋則夫.刑法的保護の早期化と刑法の限界[J].法律時報, 2003, 75 (2):16.
[2] 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71以下.
[3]曾文科.強迫勞動罪法益研究及其應用[M]//陳興良.刑事法判解.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207以下.
[4]王燕飛.恐怖主義犯罪立法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64以下.
[5]張明楷.未遂犯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49-451.
[6]大塚仁.刑法概說(總論)[M]. 4版.東京:有斐閣,2008:324.
[7]平野龍一.刑法總論II[M].東京:有斐閣,1975: 350-351.
[8]福田平.刑法總論[M].東京:有斐閣,2001:251.
[9]張明楷.犯罪預備中的“為了犯罪”[J].法學雜志,1998(1):7-8.
[10]正田滿三郎.犯罪論或問[M].東京:一粒社,1969:14-17.
[11]大塚仁.刑法概說(總論)[M]. 4版.東京:有斐閣,2008:254.
[12]大塚仁.刑法概說(各論)[M]. 3版增補版.東京:有斐閣,2005:421.
[13]平野龍一.刑法總論II[M].東京:有斐閣,1975:340.
[14]只木誠.罪數論·競合論[M]//山口厚,甲斐克.21世紀日中刑事法の重要課題,東京:成文堂,2014:73.
[15]Ingeborg Puppe.基于構成要件結果同一性所形成不同構成要件實現之想象競合[J].陳志輝,譯.東吳法律學報,17(3):321.
[16]山口厚.刑法總論[M]. 2版.東京:有斐閣,2007:368.
[17]只木誠.罪數論の研究[M].東京:成文堂,2009:187以下.
[18]岡特·施特拉騰韋特,洛塔爾·庫倫.刑法總論I——犯罪論[M].楊萌,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45-446.
[19]陳興良.規范刑法學[M]. 2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277-279.
[20]張明楷.責任刑與預防刑[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239以下.
[21]只木誠.觀念的競合における明示機能[J].研修,2011,754(4):6.
[22]H.Jescheck,T.Weigend.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M]. Duncker & Humblot,1996:718.
[23]張明楷.明確性原則在刑事司法中的貫徹[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4).
[24]H.Jescheck, T.Weigend.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M]. 5th. Aufl. Duncker & Humblot, 1996:718.
[25]C.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M]. Band II. C.H.Beck,2003: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