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自媒體時代的刑法修正
王琳
刑法變遷:在爭議中修法
2015年8月29日下午3點,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以153票贊成、2票反對、4票棄權,表決通過了這部修正案。刑法修正案(九)共計47條,刪去1條(199條),修改28條,新增條(款)22處。
這其實并不是刑法的第九次修正,而是“97刑法”的第九次修正。俗稱的“97刑法”其實也是一次修正。只不過,那次修正比較大,原“79刑法”的192條在修訂之后,增加到了452條。1997年刑法大修,在修正的條款數量上早已超過了一部新法的規模,更不用說“97刑法”還在立法理念上實現了轉向:被詬病已久的類推制度即在這次修訂中被廢除,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等原則,也是在這次修訂中得到確立。
1997年刑法大修的目標就是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它也曾被認為是新中國歷史上最完備、最系統、最具有時代氣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刑法典。也正因為1997年刑法大修的整體性,“97刑法”常被稱為“新刑法”。但追根溯源,它仍是1979年刑法的修正版。

“79刑法”的出臺有其歷史背景,它誕生在那個“百法(廢)俱興”的特殊年代。也正是“79刑法”的開創性,開啟了新中國法制恢復重建的新時代。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領域全方位巨變,“79刑法”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與此同時,借由放權而產生的社會混亂又導致了刑事管控的進一步收緊。80年代,各種刑法決定和補充規定(包括80年代初著名的“嚴打決定”)相繼出臺。此時的刑法已不僅僅是一部《刑法》典,而是包括20余項法律文件在內的刑法體系。
與“79刑法”同一天通過的還有刑事訴訟法。1996年,刑訴法先于刑法大修。2012年,刑訴法再次大修。其時,筆者在一篇專欄文章中如是評價:在一個缺乏法治傳承的國土上推進法治,總是變化多于守成,挑戰多于安逸。立法本追求穩定,急劇轉型的中國又逼迫法律無法穩定。這是一個“修法時代”,修修補補幾乎成了法律的宿命。在爭議中修正,也成了刑事訴訟法的“命”。
毫無疑問,這一論斷也適用于刑法的修訂。頻繁的修訂,并非立法者所愿,奈何時勢逼人。“97刑法”出爐后,不少刑法學者樂觀預測,至少20至30年內,這部相對完整和系統的法典無需再次大修。但是今天我們都知道了,“97刑法”之后的修正案已經有了第9號。雖然這些修正案并沒有上百條的規模,但刑法修正案(九)也多達52條,修正內容覆蓋了廢死、反恐、反腐、打拐、打謠等多個領域,一些社會關注、輿論熱議的焦點問題也借由這次修訂獲得了立法回應。
體現民意,改觀昔日立法博弈格局
嫖宿幼女罪和打擊拐賣犯罪中的“雙打制”是近期占據諸多媒體版面的熱議話題。值得關注的是,在火花四濺的激烈爭議中,刑法修正案(九)最終選擇了社會的多數共識。對前者,“取消現行刑法第三百六十條第二款規定的嫖宿幼女罪,對這類行為可以適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關于奸淫幼女的以強奸論、從重處罰的規定,不再作出專門規定。”對后者,“修改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對于收買婦女、兒童的行為一律作出犯罪評價”,原來選擇性的“雙打制”變成了強制性的“雙打制”。
不過,仍有一些刑法學家和司法實務工作者對這兩處修正持不同意見。當年設立嫖宿幼女罪和選擇性“雙打”拐賣收買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這些專家意見。在那個互聯網剛剛傳入中國的特定年代里,可供多數民眾參與修法的制度化管道并不多。與當下這個以“消解”和“去中心化”為特征的網絡輿論場截然不同,專家意見在18年里很少受到挑戰,立法博弈主要在少數“精英”之間展開。
精英立法未必能帶來精致立法。精英強于立法的技術性,卻也容易落入精英的自負與權力的專橫。普羅大眾參與度的不足,使得立法博弈難以充分展開,帶入了自負與專橫的精英立法由此也變得粗糙起來。以嫖宿幼女罪為例,盡管不少刑法學家堅持認為這一罪名的起刑點較之強奸罪還要重,但他們卻選擇性地忽略了將與未滿14周歲的幼女發生性關系區分“嫖宿”與強奸,貌似區分了 “交易”與“強迫”的不同性質,但這一邏輯卻是建立在幼女也有進行性交易的處分權之上的。這明顯與幼女尚處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階段相悖。“嫖宿”也在事實上將被害幼女貼上了“賣淫女”的標簽,這實是立法對被害幼女的二次傷害。
當年的立法精英們還巧妙地將嫖宿幼女罪置入“妨礙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中,這一設計清晰地表明,此罪名所要保護的法益實為被“嫖娼”所妨礙的“社會管理秩序”,而不是幼女的人身權利。如此價值偏差、邏輯混亂,稱之為“修法粗糙”毫不為過,由于其時多數民意無法經由制度管道對立法精英們的自負和專橫構成制約,才導致了這樣糟糕的個罪出現,并擾亂了性侵幼女司法實踐長達18年。
刑法修正案(九)中有關收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行為將一律追究刑責的條款,也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這被認為是我國打擊拐賣犯罪立法的根本轉變,即改變以前的“單打制”(單獨懲處拐賣者),為“雙打制”(拐賣、收買皆罰)。
打拐中的“買賣同罰”,根植于“沒有收買,就沒有拐賣”這一簡單的邏輯。當然,過去也并非一律不打擊收買方。從文本上理解,刑法中的“可以不追究”是指已構成犯罪,但情節輕微可以免責。而且只是酌定的“可以”免責,并非肯定的“應當免責”。但問題恰恰就出在,舊法中的“可以免責”常被警方擴大化適用,從而使有限的“雙打制”事實上被異化成了僅針對賣方的“單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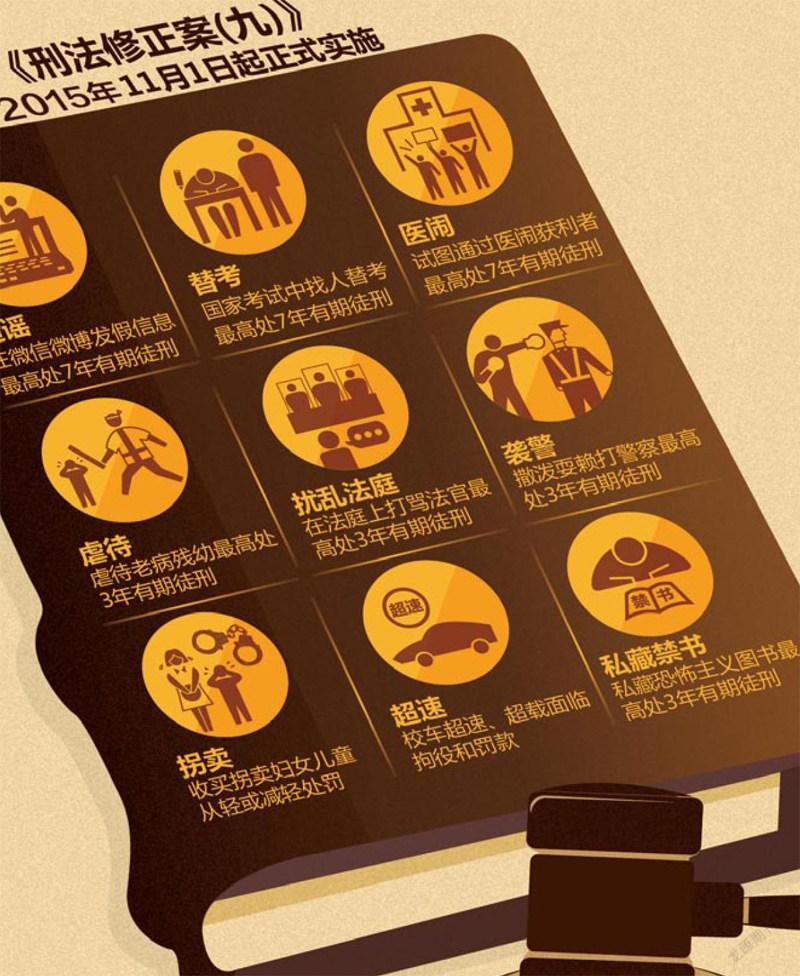
辦案部門在打拐行動中樂于將“雙打”變“單打”,意在盡可能保護被拐賣婦女、兒童的安全,并鼓勵收買人善待被拐人。這種承認“既成事實”的執法,固然易于操作,成本也較低,但其損害法律尊嚴,刺激拐賣犯罪多發的負面效應也極為明顯。輿論呼吁日久的拐賣、收買“雙打制”,如今已經取得了立法成果。但公眾期待的“天下無拐”,仍須偵查部門的嚴格執法與司法機關的公正司法來實現。
尊重民意,但并非一味迎合
輿論并不都是對的。刑法也并不能滿足所有的社會期待。“醫鬧入刑”和死刑存廢之爭就是典型的例子。
輿論關注“醫鬧入刑”,與近年來多起慘烈的醫患沖突事件相關聯。但刑法修正案(九)并未對“醫鬧”予以特別關照。
修正后的相關條款其實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醫療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顯然,這一條款針對的并不僅僅是“醫鬧”,而是覆蓋了包括醫院在內的幾乎所有公共場所(工作、生產、營業、教學、科研、醫療)的社會秩序。借用通俗的語言來表達,“校鬧”、“廠鬧”、“訟鬧”、“店鬧”、“拆鬧”等等,也都隨“醫鬧”一起入刑了。
“醫鬧”入刑也不是從刑法修正案(九)才有的。因為“醫鬧”本就不是一個嚴謹的法律概念,且“醫鬧”的外延頗廣。在“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之外,若“醫鬧”對醫生護士等構成了人身傷害,行為人可能涉嫌故意傷害罪;如“醫鬧”的目的是非法獲利,且對醫院采取了威脅、要挾等敲詐勒索手段的,行為人還可能涉嫌敲詐勒索罪。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所要懲處的“醫鬧”,更多指向在醫院聚眾鬧事情節嚴重,影響了正常的醫療秩序,且造成了嚴重損失的行為。
從字面上理解,這些條件應同時具備,刑事責任才會啟動。如果達不到犯罪要件標準,也并非無法可依,因為還有行政執法可以銜接。《治安管理處罰法》上同樣可以找到對“醫鬧”的規制條款。
值得關注的是,公共輿論對“醫鬧”入刑并不樂觀,不少論者甚至視“醫鬧”入刑為“然并卵 ”。隨手抄錄其時在網上被轉載頗多的兩則評論標題如:《“醫鬧”入刑解決不了“醫鬧”問題》《“醫鬧”入刑是和諧醫患關系的一廂情愿》。
不難看出,輿論的指向并不在修法,而是在社會語境中提出了更為宏大的“醫鬧”治理問題,這顯然是刑法不堪承受之重。在社會治理上,刑法只是“必要的惡”,具有“最后手段性”。
“醫鬧”入刑當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醫鬧”問題,更不能構建出和諧醫患關系,那都不是刑法的功能。刑法只是要為正常的醫療秩序劃出一道底線,并以刑罰來告誡和震懾“醫鬧”的行為人。在刑法之外,加強醫療糾紛調解體系建設,疏通醫療糾紛司法救濟渠道,乃至探索推進醫療責任保險等風險分擔機制,都是和諧醫患關系的應然路徑。多管齊下的治理體系,本就應并行不悖。
“醫鬧”入刑雖然解決不了“醫鬧”,但也不能否定“醫鬧”入刑的重要價值。
多數民意與立法的沖突還集中體現在死刑的存廢上。繼刑法修正案(八)減少13個死刑罪名、保留55個死刑罪名之后,刑法修正案(九)再次減少了9個死刑罪名。應當說,這樣的結果也是妥協的產物。在網絡輿論場上,力挺死刑的聲音明顯占了上風。死刑存廢之爭的“輿論向左,學界向右”仍沒有實質改變。
對那些堅定的“廢除死刑論”者來說,一次取消9個死刑個罪也不算是一個最好的消息,因為還有包括貪賄犯罪在內的諸多死刑個罪有待廢除死刑。如阮齊林教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直言,“刑法修正案(九)再減少9個死刑罪名。但這仍然不夠,我國目前還保留死刑的罪名有46個,而且死刑還包括了非暴力犯罪,顯而易見是不太合理的,與國際死刑評價體系還有較大出入。”
但從漸進式的死刑廢除之路來說,一次取消9個死刑個罪,已是重大進展。死刑的廢除關乎一國的司法傳統、社群理念以及大眾對生死的理解等等。以貪賄犯罪的死刑廢除來說,立法機關考量的,不但有刑罰現代化層面的人文精神,更有留存于多數民眾心中的樸素正義觀。
少數學者批評輿論噬血或迷信死刑的威懾力,但以“前腐后繼”的腐敗態勢來證明死刑對貪腐官員在預防犯罪上的無效,也失之于復雜問題簡單化。“前腐后繼”,一方面是有些領域、有些位置上的公權力還沒有被裝進籠子里,這是腐敗犯罪多發的前提;另一方面,也在于過往對貪賄犯罪的處罰力度太輕、太軟、太過寬容。
“刑罰的威懾力不在于刑罰的嚴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 這是死刑廢除論者常常援引的貝卡利亞的一句名言。法學史上這一著名論斷在貝卡利亞所生活的那個特定時段的意大利,或許適用。但對于當下的中國,“嚴格立法、普遍違法和選擇性執法”的怪現狀,令法律權威長期不彰。在缺乏法治傳承的國度里推進現代刑事法治建設,刑罰的嚴厲和刑罰的不可避免其實缺一不可。刑罰的不可避免強調刑罰的確定性及公平性,而刑罰的輕重應與犯罪行為相適應。
對于目前尚留存的死罪個罪來說,死刑總是最后的、同時也是最嚴厲的罰責,它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所謂“罪行極其嚴重”,在司法實踐中通常指手段極其殘忍、后果極其嚴重、性質極其惡劣、社會影響極壞的情形。一個“初犯的貪賄官員,涉案金額不多、影響不大”較之一個“累犯的貪賄官員,涉案金額以億元計,對一地的官場風氣影響極壞”,在刑罰的選擇上當然應區別對待。保留貪賄犯罪死刑,是一種潛在震懾,在今天這樣一個反腐倡廉的關鍵節點上十分必要。
就如刑罰的嚴厲與刑罰的不可避免,本應同時存在一樣;防止貪賄的制度建設和保留貪賄犯罪死刑也不是一道“二選一”的單選題。一些論者以前者來否定后果,缺乏邏輯關聯。保留貪賄犯罪死刑對加快預防貪賄腐敗的制度建設,還將起到督促和警醒的作用。相反,廢除貪賄犯罪死刑,預防貪賄腐敗的制度建設也未必就能迅速鋪開。貪賄犯罪死刑最終將取消,而把權力趕進籠子里,以嚴密的廉政制度阻塞貪賄犯罪的空間,是廢除貪賄犯罪死刑的最好路徑。讓貪賄犯罪逐漸減少,死刑對于這一個罪自然會成為不必要。這也意味著,更多死刑個罪的廢除,將在后續的刑法修正中漸次推動。
自媒體的飛速發展為公民參與立法提供了輿論平臺,也為民意表達中的自然正義與專業表達中的技術控制提供了博弈和交融的平臺。這一切關鍵在于立法博弈平臺的搭建,以及開門立法和公民參與立法的制度化保障。必須承認,法律應具有相對穩定性。頻繁修改不利于法的執行,但對于修法的失誤,也要勇于承認錯誤和糾正錯誤。修法是多數人意志的體現,不論是立法官員還是法律專家,都應俯下身來,傾聽民意,尊重民意,汲取民意——當然這也并不是要求修法全然迎合民意或對民意照單全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