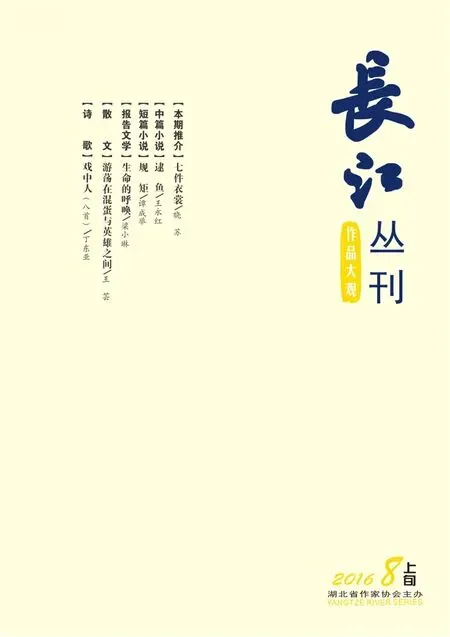田園生活
■蘭云峰
田園生活
■蘭云峰

蘭云峰,1977年生于湖北鐘祥,從軍西北十二載。2000年開始文學創作,發表小說、散文和故事八十余萬字,出版有小說集和散文集,偶有作品獲獎,部分作品被轉載或收入叢書與年度選本。
一
多事之秋!江襄掐滅煙蒂,喟嘆一聲。
十三年前,大學生江襄考取公務員,分到省局機關。魚躍龍門,光耀門庭,前程徐徐鋪陳似錦。哪料世事多變幻,期間,單位換了不少,別人是步步登高,處處見喜,他卻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從局機關貶到二級單位,從大辦沉淪到小處,現在更好,直接發配到退管中心,給退休的老頭老太們做服務搞保障,窺不見絲毫升官發跡的跡象。
談話在龔處長辦公室進行。內容簡明扼要,讓江襄卷鋪蓋走人。江襄呵呵地笑,反正是皮球,往哪踢在哪蹦,無所謂。在龔處長手下待了八個月,話沒多說嘴沒少頂,基本處于劍拔弩張狀態。龔處長手握領導權,始終占上風,對江襄的無所謂并不在意,笑著說,當然啦!你有充分選擇的權利。你去我們歡送,你不去,我們不強求,如果七天內你不去報到,那就說明你自動離職。
領導和顏悅色,溫言細語,卻頗具殺傷力。江襄躊躇不決,其實連躊躇的資格都沒有。對于他這個微末小吏來說,領導可以變著花樣玩,但他玩不起,只有認栽的份。
悄悄認栽可不是他江襄的風格,他哈哈一笑,對龔處長說,領導,我一直想給您說句掏心窩子的話。領導洗耳恭聽。你,個,王,八,蛋,我操你十八輩祖宗!說好只一句,但卻蹦出兩句。江襄鄭重地罵完,又笑。領導的臉由紅變白,但很快恢復常態,對下屬的心里話報以意味深長的笑。
江襄有自知之明,之所以在單位混得每況愈下,全是拜嘴所賜。剛到單位,江襄的嘴還是比較得體的,該說的說,不該問的不問,該守口如瓶的絕不漏半個字的風聲,再加上手快腿勤,平常領導表揚,同仁認可,一年下來自我評分是優秀。但年底評先表模時,以老同志必須照顧,新人需要錘煉為由,竟把唯一不稱職的指標給了他。畢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眼窩子淺,事物發展看不長遠。雖然未當面頂撞,但臉黑著,私下發了些牢騷。
匪夷所思的是,翌日,領導找他談話,圍繞他的牢騷嚴厲批評。經領導轉述的部分牢騷脫離事實,但不容江襄辯駁。組織蓋棺定論,江襄同志思想偏激,不可重用。此后,江襄成了孤家寡人,牢騷更甚,凡遇不平事必牢騷之,此去多年便造就了現在的江襄——江大俠。
罵歸罵,罵把肚腹里的牢騷泄去不少,但組織的決定卻要執行。到退管中心報到,中心吳主任早聞大名,貌似熱情歡迎道,工作安排不急,隔幾日再定。事已至此,江襄對工作安排已很漠然。嬉哈幾句,便打道回府。
路上,江襄依然一臉愁容。倒不是為公事,是家事。老婆林小魚是省城土著,下嫁從農村進城的江襄,主要看他一是名牌大學生,二是省局機關公務員。屬于藍籌股,升值潛力無限。但時間證明,林小魚的操盤眼光并不精準。
林小魚自小嬌慣,與江襄結為秦晉時,雖出脫的婷婷玉立,花容月貌,卻很有些飛揚跋扈。再加之地域上的優越感,從一開始,林小魚便掌握著主動權。江襄農家子弟,仕途多遇梗阻,底氣不足,對她只會俯首聽命。
江襄的父親,曾官至村支部書記,雖屬無品之官,但事事講政治,處處講正氣。得知兒子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前兩天從老家趕來,大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慷慨。老爹跟老婆擰上了勁,一時劍拔弩張,搞得硝煙味甚濃。江襄左右為難,兩頭受氣,卻又無計可施。
凄惶回家,老父未在,林小魚輔導兒子做作業。因江襄旗幟不明,一心只想和稀泥,林小魚很惱火,就寢不同床,見面不搭話。江襄笑嘻嘻打個招呼,林小魚眼皮都不抬,他只好摸進廚房,擇蔥剝蒜,籌備晚飯。
稍頃,老父回來。在廚房門口瞅瞅,見江襄當了火頭軍,不禁搖頭嘆息,折回客廳。在廚房燒飯的江襄,隱約聽到老爹與老婆打起了嘴仗。老爹吭哈幾聲,我說兒媳婦,這男人是女人的天,你這婦道人家總讓大老爺們燒火做飯,這成何體統?林小魚也不是善茬,喲!看您老人家說的,他江襄要真有能耐,我天天把他供著拜著,您那兒子是肉,可他是上不了正席的狗肉啊!
兩人在客廳指桑罵槐,唇槍舌劍,糾纏不休。江襄進退維谷,飯菜都已燒妥,但怕把自己扯進戰火,遂掏了支香煙點燃。煙霧蒸騰間,內心一片茫然。煩啊!江襄抓頭,手掌攤開,一把頭發慘臥。
晚上,林小魚帶兒子睡了。老父從客房出來,見江襄睡沙發,教訓說,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個小女人不打不成器。江襄苦笑,心說,只要林小魚不母虎發威,把自己搞個滿臉花,已算萬幸了。老父繼續慫恿,拿出點老爺們的氣概來,要是你老婆執迷不悟,就把她休了。
這主意忒餿了,想想也不靠譜,真要讓林小魚聽到那還得了。江襄一臉畏懼,擺擺手說,天不早了,您睡去吧!我明天還得上班呢!說著,扯起被子蒙頭。
二
早上上班,吳主任召見。吳主任賊,一雙小眼睛骨碌碌轉。轉的是計謀,是城府。但人家的話熱情,又會遣詞造句。吳主任笑瞇瞇地說,小江啊!根據工作需要,你就到活動中心,好不好?
能不好嗎?江襄心里憤懣。吳主任依然笑。你我工作上是上下級,但生活上是絕對的兄弟,既然走到一起那是緣份。我知道兄弟你懷才不遇,落難此處只是暫時的,相信不久的將來你定會被重用,到那時莫忘了我這個老哥呀!
江襄臉上笑著,但心里極不爽。他媽的,這種口是心非的東西,怎么處處都有?正在心里牢騷,手機響了。向吳主任抱歉地笑笑,起身接了電話。林小魚在手機里暴跳如雷,叫罵,江襄,你給老娘趕緊回來,要不回來就永遠別回來。沒等詳問,手機一陣忙音。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看來老爹跟老婆的仗干大了,自己想躲是躲不開的。跟吳主任告假,吳主任臉上不悅,想借此重申紀律。江襄想,把你當個日頭,你還真想普照萬物?不待吳主任發話,江襄身子一擰,推門而去。
出了單位,江襄本想打的,但出租車費不低,跑一趟三四十塊。摸摸衣兜,放棄了打的的念頭,跑到站牌下等公汽。
左等右盼,公汽姍姍來遲。坐車的人不少,車門一開,眾人擁擠而上。江襄投了硬幣,抓著扶手站穩。車走沒多遠,一個急剎車,把車里的人搖晃得一陣喊叫。江襄锃亮的皮鞋被人踩了一腳,雖然不痛,但心里惱火,朝踩他的人嚷,你眼瞎了!踩了我知道不?那人灰頭土臉,一看就是土包子。
江襄見那人沒言語,又罵,你怎么這么沒素質!那人被罵惱了,嘴角一斜,甩手一巴掌扇來,打得江襄一個趔趄,金星滿目。待站穩后,那人罵,素質?你狗日的跟老子講素質!
對方體壯如牛,氣勢更甚。江襄的火焰立時委頓下來,不再吱聲。車上的人都噤了聲,也有人看,像看電影的一個鏡頭;也有人笑,掩藏不住的幸災樂禍。但統統漠然,好像不是同類。
江襄感覺自己是待宰羔羊,無人伸手相救不說,甚至連絲毫同情都不肯施舍。他只好捂著火辣辣的臉,垂著腦袋,用駝鳥辦法把尷尬和難堪捂起來。
時間近乎停滯,好不容易捱到一個站臺,車門嘣地打開,江襄拎著公文包狼狽而下。車門合上,徐徐駛離站臺。望著公交車屁股,江襄吐了口壓抑已久的惡痰,迫切渴望,該車自燃,或者側翻,方解心中惡氣。
回到家,林小魚正悲憤欲絕,窩在沙發里哭得稀里嘩啦。林小魚見了江襄,破口大罵,你老爸還當自己是玉皇大帝,敢教訓起老娘來了!
江襄隱約猜到,今天林小魚歇班在家,老爹抓住戰機,借此劈頭蓋臉訓斥,沒準上綱上線。江襄趕緊息事寧人,姑奶奶啊寶貝的,病急亂投醫。林小魚讓江襄劃清界線,江襄哪有回旋余地,好在老爹不在場,剛把拳頭舉起來,要發誓表忠心,一定唯老婆馬首是瞻。可門鈴響了。
開門,老爹背著手,臉上陰得要淌水。老爹對江襄說,兒子,拿出爺們的氣概來,這樣的女人要了作甚?難不成讓她在你頭上做窩?雙方再動干戈。江襄左右為難,悶著頭也不勸也不說。林小魚委屈萬分,罵了江襄幾句,收了些衣物,哭哭啼啼投奔娘家去了。
短兵相接,略有小勝,老爹感到解氣,掏出香煙在客廳里吞云吐霧。江襄愁死了,苦著一張臉長吁短嘆。老爹頗有大將風度,手臂一揮,兒啊!做人一定要硬氣。愁啥?男人只要硬氣,啥樣的女人求不到?
江襄不接話,心里的火一陣陣往上躥。怕與老爹起沖突,便出了門,在街上閑逛。想找人說說話,一吐心中塊壘,但斟酌了十多個人,都不對路,只好作罷。
閑逛一陣,實在無趣。江襄一頭扎進網吧,瘋狂玩起賽車、CS之類的游戲,將憂愁煩惱統統拋到腦后。
直玩得頭暈眼花,饑腸轆轆,江襄才從網吧搖晃著出來。正是傍晚,一些夜市攤點開始攬客。江襄找了一家坐下,要了烤脆骨、豆腐干一類的食物。肚子填了半飽后,又要了瓶酒,自斟自飲,借酒澆愁。
酒一杯杯進肚,那些愁緒不但沒澆滅,反倒潛滋暗長,愈發招搖。江襄仰脖又是一杯,自語道,我容易嘛!我他媽的容易嘛!一連幾聲喟嘆,引得旁桌的食客紛紛側目。江襄已有幾分醉意,對此渾然不覺。
搖晃著回到家。林小魚未回來。老爹沒在,估摸著取得階段性勝利,班師回朝了。家里驟然清靜下來,江襄本想倒在沙發上睡下了事,可真躺下,那些煩心事又跑過來,襲擾得坐臥不寧。
單位的,家里的,前途啊婚姻啦!諸事交織在一起,像長勢旺盛的爬山虎,枝枝蔓蔓爬了江襄一頭。梳不順,理不清,江襄氣急敗壞地想,老子出家當和尚,了卻世間塵事算球。但這想法可操作性不強,正規寺廟都單位化了,講專業對口,講定崗定編。那就離家出走。往哪兒走?溫飽問題怎么解決?日后怎么辦?這些問題都很棘手。
想來想去,江襄想到了袁尚。袁尚與江襄是大學同窗,上下鋪的兄弟,關系鐵得比鋼還硬。袁尚成績優異,畢業后留校任助教,這在同學中已算極好歸宿。
怎么說呢?袁尚這人古怪。用譽美的詞講,他是性情中人,講求率性而為,適情而止。用大白話說,他這家伙純粹二球,想一出是一出,不計后果。
幾年后,袁尚升任副教授,日子有聲有色,前途無限光明。誰料瑣事雜蕪,難免與人生出齷齪,其間是非曲直很難說清。袁尚率真,不喜虛與委蛇,最惡口是心非,與那些道貌岸然的偽君子不合群,難免成為眾矢之的。
糾纏了數個回合后,一氣之下,袁尚決定遠離俗世紛擾,歸隱田園,做一個現代版的陶淵明。經過實地考察,袁尚辭去大學教授,到一處僻靜的山村隱居下來,過起了詩情畫意的田園生活。
臨行時,袁尚邀幾位朋友惜別,江襄位列其中。那時,江襄心氣正盛,對前程功名有著迫切渴望,曾力勸袁尚不要頭腦發熱,逞一時之快,往后后悔怕都來不及。袁尚去意已決,如同千年前的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瀟灑地掛印而去。
現在看來,袁尚的選擇太正確了。這種爾虞我詐、一地雞毛的狗屁生活糟糕透了。哪里是什么生活,完全是煉獄,是折磨,是凌遲,等受盡所有痛苦,熬枯所有夢想,流盡最后一滴血,生活也就結束了。
江襄想,袁尚才是真正的生活大師。真正的生活是什么?真正的生活就是菊淡茶香,就是雪夜煮酒,就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就是種豆南山下、草長豆苗稀。
三
袁尚的田園生活已有六年了。六年中,袁尚并非與世隔絕,只是他拋棄了現代通信工具,以書信的形式,同江襄,或者也有別人,保持著聯絡。
一年中,江襄總會收到袁尚的幾封信。信封是牛皮紙的,信箋是豎條的,那些文字很有文采,與龍飛鳳舞的草書相得益彰,把他的幸福生活勾勒得纖毫畢現。
江襄忽然想,袁尚可以,自己難道不可以?翻出袁尚寫來的信,讀著那些散發著田園生活氣息的文字,江襄感到一股神奇的力量將自己托起,那種超脫感讓自己迅速強大起來。
當晚,江襄決定前去拜訪袁尚。一則老友相聚,二來去打前站。如果可行,也應了那句古語,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真是那樣就好,與袁尚比鄰而居,一起煮酒論詩,一起談古論今,那真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第二天,江襄不打招呼不報告,拿出“仰天大笑出門去”的氣概,按照通信地址去找袁尚。路途不算太遠,六七百里的樣子。乘火車,轉汽車,江襄一路興致勃勃,內心的不快轉瞬間遁逃得無影無蹤。
路上,江襄情緒好,往事歷歷在目。
三年前的秋天,袁尚曾回過省城。袁尚打電話說人在省城時,江襄很詫異,約了幾個同學好友,在一家餐館聚了聚。
幾年的田園生活,讓袁尚變化不小。之前的袁尚體形瘦削,脾性孤傲,透現著一股迂酸的書生氣。現在身體壯實了一些,目光里多了謙和,但又絕非是那種讓人小覷的普通農民的謙卑。總之,讓人難于捉摸。
席上,袁尚相當活躍,話題始終圍繞他的田園生活展開。哈哈……莊稼才是最有意義的,從育種、栽植、施肥、祛蟲、收割,一直到搬回糧倉,它的過程就是我們人生的縮影。
辛苦是相對的。人活著,身體和靈魂都在受苦。身體的苦是流血流汗,那是鍛煉。靈魂的苦是錐心蝕骨,就是劫難。看看我,手起了繭,面皮黑了,指節粗了,但是我的靈魂啊!超脫了一切世俗,離天堂更近了。
我喜歡躺在麥地里,閉著眼,屏住呼吸。因為那樣,我就能聽到麥子們說話的聲音,有時候,它們還會唱歌,圍著你呀!不停地唱,唱得你心里充滿了感動。
嘖嘖!那些日子真的太好了,想起來都嘎嘣脆。
被震撼了,絕對震撼。熱氣騰騰的火鍋,各種鮮美菜肴,都為此遜色,他們只對袁尚的田園生活饞涎欲滴。江襄知道,盡管自己焦頭爛額的生活與之相形見絀,也十分渴望一些改變,但自己只是葉公,僅僅好龍而已。
車至一小鎮。鎮子不大,一派塵世繁華。江襄下車,幾個摩的擠過來攬客,個個熱情得夠嗆。江襄說到青楓灣。幾個摩的司機遲疑,大概這活兒有難度,或者不愿跑這趟路。
一個中年漢子報價,三十塊錢,咋樣?江襄不屑笑笑,心說,屁大點事!就背著背包,跨上摩托車后座。到青楓灣的路況一般,先是一段柏油路,再走下去是砂石路。
江襄打聽,青楓灣有個大學教授,聽說過嗎?中年漢子見怪不怪,哈哈大笑。名人嘛!哪個不曉得?只是這人腦子有毛病,做的事都不靠譜。江襄奇怪,怎么不靠譜?
你說說吧!在城里當教授,那是多安逸的事,他卻要種地,這神經了吧!種地就種地,春天得育苗整地,他卻山上山下胡球轉。眼看要下雨了,他不但不搶收,反倒神神道道又唱又跳。我日,這樣的人沒毛病才怪。
江襄不悅,但又不便發作。自我寬慰說,這樣的鄉野村夫哪能理解田園生活的真正蘊意?
再往下走,坡陡路窄,格外崎嶇。翻過一道山埡,中年漢子指著谷邊崖下的一處房舍說,大學教授就住那,你自己去吧!江襄掏了三十塊錢,中年漢子接過錢,絕塵而去。
四
正是晌午,陽光燦爛的秋天里,稻田山坡一片金黃。江襄張開雙臂,深呼吸幾口,空氣里彌散著稻子的芬芳和草木清香,那是從未感受過的氣息。
穿過一片稻田,越過一面坡地,一座農家小院隱現在樹林間。院門虛掩,竹籬笆年久失修,幾只雞從窟窿里自由出入。院子里一派雜亂,花池里有菊花數枝,但荒草瘋長,看不出絲毫情趣。
江襄喊,袁尚,你在家嗎?連喚幾遍,一個中年男人伸著懶腰從屋里出來。中年男人頭發蓬亂,胡須老長,他揉揉眼,懶洋洋地問,你誰呀?
江襄確認,眼前就是袁尚。袁尚,我是江襄呀!袁尚身體一顫,像打了針清醒劑,猛然清醒過來。江……江襄,你怎么來了?袁尚結巴了,被江襄的突然造訪搞得很緊張。
江襄上前擁抱袁尚,我是投奔你來了。兩人進屋,喝茶寒暄。得知江襄的來意后,袁尚說,我們兄弟多年不見,難得呀!江襄四下打量,屋子里一片狼藉,桌椅滿塵,衣物亂扔,讓人難以相信,屋主人曾是大學教授,這就是袁尚田園生活的真實寫照?
袁尚看出江襄的心思,說你看看,我這兒像豬圈吧!江襄附和著笑笑。實話跟你說吧!這就是真正的田園生活,真本色,真性情,無拘無束,自由自在。袁尚撓撓長滿胡茬的臉,笑呵呵地說。
午飯簡單。袁尚煮了飯,到菜園扯了菜,在雞窩里摸了幾個雞蛋,隨意對付了事。
飯后,袁尚帶江襄在青楓灣四下走走。看了袁尚的稻田和菜園,也爬到附近山上登高望遠。袁尚像他鄉遇故知,心情奇好,滔滔不絕講述他的田園生活。
晚上,倆人把盞言歡。借著酒意,江襄像終于找到了組織,向袁尚大倒苦水。你說說,這是他媽的什么生活?沒有幸福,沒有希望,純粹是條在干涸河床上蹦達的魚。
袁尚端著酒杯,眉目含笑,專注傾聽。江襄哀嘆一聲,他便頷首以示回應,似乎江襄的糟糕生活是他的重大關切。也會很古典地呷口酒,但不露聲色,有點高深莫測。
終于,江襄的苦水傾倒得所剩無幾。袁尚感嘆說,江襄啊!你是不是認為我過得挺苦?江襄剛要辯解。袁尚手掌一擋,是啊!住在這山旮旯里,一切都要自己動手才能豐衣足食,不像在城市,有超市,有菜市場,有飯莊酒吧,生活豐富多彩,個個衣著光鮮,感覺特體面。而我呢?汗滴禾下土的農夫。
袁尚手指敲擊桌面,話鋒一轉。你看到的只是表象,我的同志啊!那只是表象。我的表象挺慘,但我的實質很富有。這里空氣新鮮不說,吃的綠色住的環保不說,更重要的是心靈的自由。在這里我不用去想心思,不用琢磨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不用害怕被陰暗心理和惡毒伎倆所傷害,不用為了狗屁前途去裝聾作啞當孫子。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追求內心的安寧和生活的自由。
江襄太向往了,美好的田園生活就在眼前,觸手可及。袁尚,我這次來就是想看看你怎么樣,既然這么愜意,那我也辭了破工作,跟你一起過這樣的田園生活?
袁尚一怔,若有所思說,不急不急,這好多事情得再三考慮。江襄不好再說,倆人繼續喝酒說笑。袁尚興致頗高,即興吟誦:“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喂馬、劈柴,周游世界……”
五
日上三竿,江襄才起床。
晌午,院外走進一個女人。女人有幾分姿色,見了江襄,點頭含笑。女人儼然是這屋的主人,手腳麻利地抹抹掃掃,又抱著一盆衣物到溪邊去洗。
望著女人的背影,江襄抓住袁尚。這女人誰啊?老實交待。袁尚很喪氣,抵不住百般盤問,如實道來。
女人姓林,寡婦,住對面坡上。估計是袁尚的教授光環分外耀眼,從一開始就引起了林寡婦的關注,幫著他拆拆洗洗,種種菜,喂喂雞。一日雨夜,孤男寡女共處一室,袁尚定力不夠,再加上酒迷心性,結果失身于林寡婦。醉意盎然中,袁尚在下,寡婦在上。情動處,寡婦大喊,教授啊!我親親的教授。袁尚倏然驚醒,才知道木已成舟。事后,袁尚騎虎難下。
聽袁尚說完,江襄笑得岔氣。
因有林寡婦的參與,晚飯相當豐盛。飯前,袁尚請來一位客人,青楓灣的村主任,姓高。袁尚把江襄作了介紹,高主任伸出蒲扇般的大手,連握帶搖,粗放地嚷,哎呀狗日的,歡迎省城來的大領導啊!江襄哭笑不得,只能陪著打哈哈。
高主任長得魁梧壯實,酒量是缸一級的,端著酒杯左右開弓。作為主人,袁尚要敬酒。敬了江襄,敬高主任時,高主任說,兄弟,正好江領導在,咱們可要當面鑼對面鼓地敲哦!
袁尚很謙恭,說您是青楓灣的父母官,有話直說。高主任人粗,但心思不粗,說,你看這青楓灣多好啊!山好水好人好空氣好,你連大學教授都不做,到這青楓灣落戶,說明你很有眼光。袁尚和江襄點頭稱是。
誰料高主任話鋒一轉,跟袁尚又走了一個,斟滿酒說,兄弟,咱們可都是大老爺們,你球快活了,可甭想打馬虎眼,難得我妹子看得上你,要是這事辦好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要是揣著花花腸子,別說在青楓灣過日子,只怕哪天少了啥物件你都不知道。
這話明顯有恫嚇的意味,江襄擱下酒杯,剛要理論幾句,袁尚在桌下踢了他一腳,又朝他眨了眨眼。江襄隱約知道用意,便裝聾作啞,作壁上觀。
一場酒喝下來,高主任沒事似的,像得勝將軍,趾高氣揚地走了。林寡婦收拾碗筷,見江襄在,也不便久留。袁尚醉得不淺,先是趴在桌上睡,酒勁上來后,止不住把肚里的東西傾倒出來,過程簡單,但數次反復,把自個兒折騰得夠嗆。
江襄喝酒少,除了稍稍頭暈,并無大礙。想起酒桌上的不甘,便對袁尚說,那姓高的什么東西,還跟你虎個屁的臉!袁尚苦笑,擺擺手說,對你來說他屁都不是,可我得看他的臉色。
盡管袁尚說話顛三倒四,但江襄還是聽懂了他的苦衷。袁尚的田園生活并不如意。剛開始,荷鋤晚歸,飲酒讀詩,遠離瑣事紛擾,很是愜意。但時間一長,農活的艱辛沉重,經濟上入不敷出,讓袁尚感到,所謂的田園生活并不是想像中的那般美好。再加上村里有幾個二流子,不是今晚偷雞,就是明天摸瓜,要么欺負他是外來人,誆吃騙喝,搞得袁尚苦惱不堪。還有高主任,表面上與林寡婦兄妹相稱,實際上早已明鋪暗蓋,逼他與林寡婦結婚,不過是為了掩人耳目。
江襄開導說,袁尚,既然你過得不順心,那就回省城好了。袁尚看上去很虛弱,嘆息一聲。回省城?我回去過,想繼續當我的教授,可他們都嘲笑我,刁難我,說你不是陶淵明嗎?路讓自己斷了,回不去了啊!
其實,我在這鬼地方早呆夠了。田園生活?狗屁!那是騙你們的,也是騙我自己罷了!
兄弟,你還在尋找這樣的田園么?我告訴你,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是江湖就會有紛爭,有紛爭就會有煩惱。你到哪能找到桃花源呢?
袁尚雙手抱頭,哭得一塌糊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何必當初啊!嗚…嗚嗚……江襄手足無措,不知如何安慰。袁尚哭累了,倒在床上沉睡過去。
那一夜,江襄久久不能入眠。他踱出院子,此時,月上中天,一片靜謐。點燃一支香煙,江襄失落地想,何處是田園?所謂的田園是不存在的,要有也只出現在采菊東籬下之類的詩句里。想起老婆兒子,想起擁擠的公交車,想起那些糟糕透頂的生活,心里竟有了淡淡的溫情。江襄似有所悟。
六
第二天,江襄要走。袁尚揉揉倦怠的雙眼,終沒吐出一字。兩人出了院子,江襄有些傷感,說既然這樣,那你就多保重。袁尚連連點頭。袁尚一路送著江襄,幾次讓袁尚止步,他嘴上應著,腳步卻不停。
兩人就這樣默不作聲走了很遠。江襄再次道別時,袁尚支吾著,臉色窘得通紅,好半天才說,江襄,求你件事……你回去后,見了同學們就說我過得很好。江襄明白袁尚的用意,說放心吧!我說你的田園生活很好。說完,頭也不回地走了。
走出去很遠。翻過一處山埡,江襄駐足回首。袁尚已遙遠得像個墨點,在色彩斑斕的秋天里,那墨點有點突兀,有些怪異,像……江襄苦笑,一聲嘆息。
小說責任編輯:鄭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