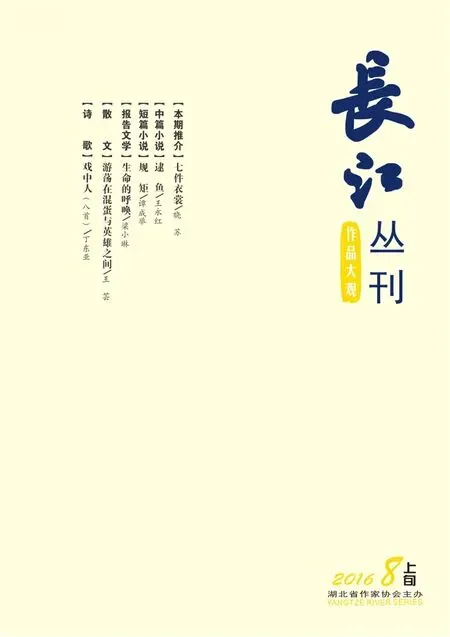七件衣裳
■曉 蘇
七件衣裳
■曉蘇
1
在我的老家油菜坡,人們都習慣于把衣服稱為衣裳。與衣服比起來,衣裳不僅說起來悅耳動聽,而且還給人一種柔軟溫馨的感覺。我在老家生活了十七年,在那十七年中,我已記不清穿過多少件衣裳,但有七件,我卻至今難以忘懷,并且還經常在夢中與它們重逢。
我是從小學三年級那年開始注意自己的穿著的。在那以前,我似乎沒有關心過我的衣裳,父母給我縫什么衣裳,我就穿什么衣裳,無論是大還是小,無論是新還是舊,無論是白還是黑,我都往身上穿,從來不管它是否合適,是否好看。但是,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突然對穿著產生了興趣。
說句笑人的話,我那時對穿著產生興趣與一個女同學有關。那個女同學姓宗,與我坐一張桌子,是我們班主任的侄女。她長得很漂亮,穿得很干凈,學習也好,特別會唱歌。有一次上體育課,老師教我們玩一個游戲。那個游戲是兩個人一組,并且是一個男同學和一個女同學自由組合。開始我以為姓宗的女同學會主動跟我一組,因為她畢竟與我同桌。可她卻沒有選我,她只看了我一眼就把目光投向了一個姓劉的男孩,很快與他組合到一塊兒了。這件事對我打擊很大,我于是就想,她為什么選擇別人而不選擇我呢?我很快想出了原因,原來姓劉的男孩穿的比我好,他穿著一件燈芯絨褂子,而我身上的褂子卻是用土布染的。這是一個重要發現,就是這個發現,使我開始注意自己的穿著了。

曉蘇,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作家。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先后在《收獲》《人民文學》《作家》《花城》《十月》《中國作家》《大家》《上海文學》等刊發表小說五百萬字。出版長篇小說《五里鋪》《大學故事》《成長記》《苦笑記》《求愛記》5部,中篇小說集《重上娘山》《路邊店》2部,短篇小說集《山里人山外人》《黑燈》《狗戲》《麥地上的女人》《中國愛情》《金米》《吊帶衫》《麥芽糖》《我們的隱私》《暗戀者》《花被窩》《松毛床》12種。另有理論專著《名家名作研習錄》《文學寫作系統論》《當代小說與民間敘事》等3部。作品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刋》《新華文摘》《中華文學選刊》等刊轉載40余篇,并有作品被譯成英文和法文。曾獲湖北省第四屆“文藝明星”獎、首屆蒲松齡全國短篇小說獎、第二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第十六屆百花文學獎、第三屆、第四屆、第五屆湖北文學獎、第六屆屈原文藝獎。《花被窩》《酒瘋子》《三個乞丐》分別進入2011年度、2013年度和2015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
那時候,我是多么想我也有一件燈芯絨衣裳穿啊!但那個想法不切實際,只能在心里想一想。當時,我們家非常困難,兄弟多,勞力少,父親雖然在鎮上工作,但每月只有三十七塊五角錢,母親一個人在農村勞動,每年都要給生產隊交一百多塊錢的口糧款。在那個歲月里,我們兄弟能穿上土藍布衣裳已經很不容易了,哪里還能奢望穿燈芯絨衣裳啊!
不過沒過多久,母親給我縫了一條黑布褲子。在那之前,我每天放學后都上山挖黃姜,一連挖了半個月。半個月后,母親把我挖的一背簍黃姜背到供銷社賣了。也許母親想獎賞我一下吧,她在用賣黃姜的錢買了鹽和煤油之后,便用剩下的錢買了一塊黑布,給我縫了一條褲子。
開始把那條褲子穿到身上時,我并沒有感到它有什么特別。那是一條很普通的褲子,用卡嘰布縫的,無論是顏色還是樣子,都很普通。
但是穿到了學校里,那個姓宗的女同學卻睜著圓圓的眼睛把我的黑褲子看了好半天,她還說,你穿這條黑褲子真好看!我一聽就激動了,渾身上下麻酥酥的。課間操的時候,那個姓宗的女同學還偷偷地給了我一把紅棗。就這么,我深深地喜歡上了那條黑褲子。后來一連好多天,我都舍不得脫掉它,差不多天天穿著它去上學。母親說,你怎么天天穿這條黑褲子?也該換下來洗一洗了。星期天,我總算把那條黑褲子脫下來讓母親洗了。但到了第二天,我又把它穿到了學校。
大概是穿得太多的緣故吧,我那條心愛的黑褲子不到兩個月就破了。最先破的是膝蓋頭那里,破了一條小口子,接著屁股上也破了一個洞。黑褲子破了,我傷心極了,還流了許多眼淚。
2
到了過年,父親手頭再緊也是要給我們兄弟縫一套新衣裳的,用父親的話說,叫一年一個新頭兒。我的老家油菜坡,長期流傳著這樣兩句話,大人盼種田,小孩盼過年。小孩盼過年,無非就是盼吃盼穿,過年可以吃臘肉和米花糖,可以穿新衣裳。父親當時在單位上很忙,差不多每年都是在大年三十的頭一天晚上才能回家。父親在一年當中至少也要回十幾次家,但他這一次回家是最受我們歡迎的,因為他進門不久,便要打開提包,從中拿出他為我們過年縫的新衣裳。父親開提包時,我們的眼睛都睜得有雞蛋那么大,一眨不眨地看著父親的那雙手。父親的動作很慢很慢,他一點一點地扯著拉鏈,像是要故意吊我們的胃口。當他打開提包掏出新衣裳的那一剎那,我們都會禁不住嘩地驚叫一聲,然后像雞子展翅一樣,張開雙手朝新衣裳跑了過去。
長期以來,父親過年時給我們兄弟縫的新衣裳都是一樣的布料,要么都是黑的,要么都是藍的,要么都是灰的,我們兄弟穿著新衣裳站成一排,就像是一個部隊的。然而,在我讀五年級的那一年,父親卻給我縫了一件與幾個弟弟不大相同的褂子。幾個弟弟的褂子都是用灰布縫的,那灰布的顏色很不正,看上去新不新舊不舊的樣子,并且也很薄,摸在手上像皮紙。而我的那一件,卻是板栗色的,一看就賞心悅目,而且布料也厚實,摸起來特別舒服。開始我并不知道我的褂子與幾個弟弟的不一樣,父親要我們穿著試一下大小,等我們都穿上新衣裳站在一起的時候,我才猛然發現我的與眾不同。我頓時一愣,用異樣的目光看著父親。父親這時走過來,摸著我的頭笑著說,你已經長大了,應該穿得好一點兒!聽了父親的話,我心頭陡然一熱,一股溫暖的泉水很快涌遍我的全身。而我的幾個弟弟,卻有些不高興了,一個個翹起小嘴巴,用怪怪的眼神看著我。母親這時用手把他們攬在懷里,說,等你們長大了,爸爸也給你們縫板栗色的衣裳。
當時在我們油菜坡,有一個過年給軍屬送對聯的習俗。一到大年三十的早晨,生產隊就要組織一群人,敲鑼打鼓將大紅的對聯送到軍屬的門口,先扭一陣秧歌,然后再把對聯貼在軍屬的大門上。給軍屬送對聯,每家每戶必須去一個人,這是政治任務。以往給軍屬送對聯,我們家都是母親去。而在我父親給我縫板栗色褂子的那一年,父親卻讓我去了。父親對我說,你已經長大了,替你媽去給軍屬送對聯吧。我一聽就跳起來,差點兒高興得發了瘋。說實話,好幾年前我就盼著加入那個給軍屬送對聯的隊伍了。
毫無疑問,我那天是穿著那件板栗色的褂子去給軍屬送對聯的。送對聯的隊伍有半里路長,我穿著那件板栗色的衣裳,在隊伍里穿來穿去,跑前跑后,像一只發了情的小公狗。我發現,我的那件板栗色衣裳在那條隊伍中是最好看的,好多人都用羨慕的目光看著我。也許正是因為穿了那件板栗色衣裳的緣故,在往軍屬門口貼對聯的時候,民兵隊長特地派我去刷了漿糊。
3
小時候,我的褲子破得最早的往往都是兩個膝蓋頭。一是我們那個地方山路多,走山路就要不住地彎膝蓋頭,一彎膝蓋頭就要磨褲子上的那一塊。二是我喜歡跪在田里扯豬草,跪著扯豬草又快又省力,但卻非常費褲子,尤其是褲子的膝蓋頭那里。因為家里窮,褲子破了還要接著穿。好在母親很勤勞,又特別盡職盡責,每當我褲子的膝蓋頭破了,她都要及時找來一塊舊布將那破處補起來。在一條褲子的兩條褲腿上,左邊的那個膝蓋頭常常又是先破,因為我用左腿跪地的時候偏多。母親補褲子,當然是什么地方破了就補什么地方,比如左邊的膝蓋頭破了就補左邊的膝蓋頭,她不可能把右邊的那個膝蓋頭也同時補上。雖然過不了多久右邊的膝蓋也會破,但那也只能等它破了以后再補。
在一條褲子右邊的膝蓋頭還沒破而左邊的膝蓋頭上已經出現補疤的時候,我是很不情愿穿著這條褲子去上學的。因為那樣子太難看,一邊有補疤,一邊沒有,就像是一只眼睛睜著,一只眼睛閉著,越看越像一個獨眼龍。但是,這條褲子你不情愿穿也得穿,當時我基本上只有兩條褲子換著穿,換著洗,當那一條褲子洗了,你不穿這條獨眼龍褲子穿什么呢?總不能光著屁股去上學吧?每當穿著這條褲子到學校,我都覺得非常自卑,見人就臉紅,脖子發粗,抬不起頭來,下課了也不敢出教室去玩,一心只想著把兩條腿子藏在桌子下面。
我們初中的老師,一般是沒有誰穿補疤衣裳的。但有一天,我卻發現代我們初一年級體育課的劉老師的褲子上出現了兩個補疤,左邊膝蓋頭上一個,右邊膝蓋頭上一個。因為兩邊都有補疤,所以看上去并不難看,好像還別有一種味道。下課后,我斗膽問劉老師,你的兩個膝蓋頭都破了嗎?劉老師說,只破了一個。我馬上問,那你為什么兩個膝蓋頭上都補了疤呢?劉老師說,為了對稱嘛!劉老師的話,像是在我面前劃然了一根火柴,我兩眼頓時豁然一亮。
那天我穿的是一條藍布褲子,左邊的膝蓋頭上補著一塊刺眼的補疤,而右邊的膝蓋頭上還是好好的。傍晚放學回到家里,我一進門就換了一條褲子,然后找來一把剪子,咔嚓一聲就把那條藍褲子右邊的膝蓋頭剪了一個洞。天黑后母親從生產隊收工回來,她一進門我就對她說,藍褲子的另一個膝蓋頭也破了,你給我補一下吧。母親說,吃了晚飯補。晚飯后,母親一收拾好碗筷就進了她放針線的那間屋。沒過多久,母親突然喊了我一聲,讓我快去。我馬上去了。我剛一進門,母親便一手把我按在了地上,接著就用一只拳頭拼命地打我的屁股,她一邊打一邊罵,你這孩子真是個敗家子,好好的褲子剪一個洞干什么?那晚,母親真是氣壞了。她一口氣把我打了好半天,疼得我殺豬似地亂叫。不過她打了我一頓之后,氣也消了,接著就在那條藍褲子的右邊膝蓋頭上補了一個疤。
第二天,當我穿著那條兩個膝蓋頭上都有補疤的褲子上學的時候,我突然感到這條藍布褲子比以前好看多了。這時,我怎么也回憶不起來頭天晚上挨打時的那種疼痛的感覺了。
4
在缺衣少食的少年時代,我最崇拜的有兩種人,一是廚師,再就是裁縫。粗糙的米到了廚師手里,就會變成香噴噴的飯,毫無形狀的布料到了裁縫手里,就會變成漂亮的衣裳,他們真是心靈手巧,我非常崇拜他們。當時我還想,我長大后要么就當一名廚師,要么就當一名裁縫。在我記憶的屏幕上,我認識的第一位裁縫叫石膏兒,她住在一條小河邊上,縫衣裳的那間房子正好臨河,她可以一邊踩著縫紉機一邊傾聽水聲,如果抬頭從窗口看出去,就可以看見清清的河水以及漂在水上的那群白色的鴨子。石膏兒長得很白很嫩,臉和脖子,還有那雙手,都像是用豆腐捏成的。我當時想,石膏兒天生就是一個當裁縫的。
我是在讀初二那一年的夏天認識石膏兒的。一個慢長的春天過去后,當我脫下那件穿了幾個月的黑夾衣的時候,母親突然說我長高了。我的確長高了,母親找出我頭一年穿過的那件灰襯衣,我怎么也穿不得了。母親面對長高的我,顯得既驚喜又憂愁。后來她終于咬咬牙對我說,走,我們到供銷社去。母親那天是提著一籃子雞蛋去供銷社的。在供銷社賣了雞蛋后,母親就去扯了一塊灰布,然后就把我帶到了石膏兒那里。
母親把那塊灰布放在石膏兒的縫紉機上,對她說,給我兒子縫一件襯衣吧。石膏兒草草地看了那塊灰布一眼,很快就把眼睛轉到了我身上,她的眼睛很亮,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好久,然后,她又扭頭朝那塊灰布掃了一眼。母親以為石膏兒是怕那塊灰布的尺寸不夠,就說,布不會少的。石膏兒說,布肯定不會少,我是覺得這塊布料不適合你兒子穿。母親問,為什么?石膏兒說,你兒子皮膚這么白,應該穿一件白襯衣。那塊灰布太老氣了。石膏兒說著,又扭過頭來看著我,并且還對我笑了一下。她的牙齒也很白,笑起來特別好看。母親這時說,他一直穿灰布襯衣的,白襯衣難洗。我突然說,難洗我自己洗!石膏兒聽我這么說,又對我笑了一下,然后勸母親說,那你就給你兒子縫一件白襯衣吧。母親猶豫了一會兒說,灰布已經買了,再說……石膏兒不等母親說完便說,灰布買了不要緊,我帶你們去供銷社退掉,再換一段白布,供銷社的經理跟我很熟的。聽石膏兒這么一說,母親就不好再說什么了,只好點頭同意。
供銷社的經理果然與石膏兒很熟,我們一去就換了布。那段白布比那塊灰布要貴幾毛錢,石膏兒要經理免了,經理真的就沒要。這讓我母親對石膏兒充滿感激,我當然更是感激不盡。
從石膏兒家到供銷社有好幾里路,一去一來花了一個小時。石膏兒生得白皮嫩肉,但她并不嬌氣,一回到家里就開始給我量尺寸。她兩手捏著一條皮尺,一會兒量我的肩,一會兒量我的膀子,一會兒又量我的胸脯,動作十分嫻熟。我聞到石膏兒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氣,像百合花的味道。在給我量胸脯的時候,石膏兒的手指頭無意中按了我一下,我頓時有些緊張,臉一下子紅到了耳朵。
石膏兒當時就把那件白襯衣給我縫好了,并親自給我穿在了身上。那件白襯衣真不愧是比著我做的,穿在身上要多合身有多合身。母親看著穿上白襯衣的我,嘴笑得差點合不攏了。石膏兒這時對母親說,怎么樣,你兒子穿白襯衣好看吧?接下來她又摸了一下我的頭說,看,簡直像個小新郎了!
說一句難為情的話,那件白襯衣差不多讓我激動了大半年,每當穿著它,我就顯得特別有精神,無論是在學校讀書,還是回家里干活,渾身都有使不完的勁兒。我穿得也非常珍惜,生怕弄臟了它。那件白襯衣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動手洗,每次都是輕輕地搓,輕輕地揉,輕輕地抖,像是害怕弄疼了它。
5
我讀初三的時候,油菜坡來了好幾個支農干部,有的來自鎮上,有的來自縣城。這些干部很特別,他們在村里走動時,你一看就知道他們不是油菜坡的人,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從外面來的,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干部。這不光是因為他們戴著手表,也不單是因為他們挨家挨戶吃派飯,還因為他們每人都穿著一種很瀟灑的褲子。那褲子是咖啡色的,很薄,走起路來一蕩一蕩的,沒有風吹也蕩,鄉親們都稱這種褲子叫蕩蕩褲。他們由于穿著這種蕩蕩褲,走到哪里都受到人們的尊敬,大家忙著給他們讓座,忙著給他們遞煙遞茶,忙著給他們做好吃的。我是非常羨慕那些干部的蕩蕩褲的,每當他們穿著蕩蕩褲從我面前走過時,我會睜圓眼睛看他們的腿子,并且轉著身子跟著看,他們走遠了,我的眼睛還久久收不回來。不光我羨慕那些干部的蕩蕩褲,就連我們油菜坡的隊長和會計也羨慕得要命。他們雖然也是干部,但穿的都是與油菜坡一般農民沒有什么區別的布褲子,看起來就顯得土里土氣,根本不能和那些外面來的干部相比。我曾經注意過隊長和會計的眼神,他們一看到外面那些干部的蕩蕩褲就目光發花,恨不得撲上去將別人的蕩蕩褲扒下來穿在自己的身上。
隊長說起來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雖然臉上有一塊火燒疤,頭上沒有幾根毛,但他的兩顆綠豆小眼一轉就是一個點子。當時,我們油菜坡已經開始使用化肥了。化肥是按計劃供應的,大部分是縣城化肥廠生產的碳酸氫氨,也有少量的日本尿素。日本尿素是用一種小口袋裝的,那口袋很薄,摸起來光滑如水。隊長很快把這種裝尿素的口袋與那些干部的蕩蕩褲聯系起來了。他于是就用幾個口袋縫了一條褲子,又買回幾包咖啡色的染料,將那褲子染成了咖啡的顏色。隊長剛開始把那種褲子穿出來的時候,鄉親們一下子都傻了眼,差點兒把他當成了外面來的干部,一看他臉上的火燒疤,才發現他就是本村的。隊長用尿素口袋縫的這種褲子,初看上去與外面那些干部的蕩蕩褲沒有多大區別,走路也是一蕩一蕩的,只是將眼睛貼攏去看時,才會發現褲子的前后都有字,前面兩個字是日本,后面兩個字是尿素。但這并不要緊,誰經常把眼睛貼到那褲子上去看呢?隊長穿上蕩蕩褲不久,會計也穿上了一條,后來就沒有誰穿了。生產隊里的日本尿素都是隊長和會計管著,其他的人去哪里弄那種口袋呢?所以大家只能眼巴巴地望著隊長和會計穿。
我當時做夢都想穿蕩蕩褲,哪怕是用日本尿素口袋縫的我也想。有一次,父親從鎮上回來時,我終于向他開了口,求他在鎮上碰到了日本尿素口袋后給我弄兩條。父親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答應將這事放在心上。約摸過了半個月,父親突然回了油菜坡,他說這回是專門為我回家的。父親說著就從包里掏出一條蕩蕩褲。這是一條半新不舊的蕩蕩褲,父親說是鎮上的一個化肥倉庫保管員為他兒子縫的,可他兒子皮膚不好,穿了這種褲子兩腿發癢,于是就不穿了。我接過蕩蕩褲喜出望外,差點叫了一聲毛主席萬歲。父親有些擔心地說,但愿你穿上腿上不癢。我說,絕對不會癢的,我的腿子絆了漆樹都不癢。
第二天我就把蕩蕩褲穿出去了,村里人見了我都像看一個天外來客。有人問我,你是不是當上隊長了?我說,沒有。那人就說,那你肯定是當上了會計!我還把蕩蕩褲穿到了學校,一下課就在校園里蕩來蕩去,好多女同學都對我刮目相看,一時間我覺得我簡直成了全校最風光的人。
然而母親卻對我穿蕩蕩褲不以為然,她認為褲子應該穿得穩重才好,說蕩蕩褲蕩來蕩去十分輕浮。她希望我以后少穿這條褲子出門。但我沒有聽母親的,我把她的話當成了耳邊風。后來一連好多天,我照樣穿著蕩蕩褲出門,并且專門朝人多的地方跑。母親見我這樣非常不滿,看見我就板著臉。
有一天我把蕩蕩褲脫下來洗了,曬在門口的竹桿上。等我晚上放學回家時,那條蕩蕩褲卻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問母親,母親威嚴地對我說,我用剪子把它剪了!
6
我至今忘不了那個名叫云朵的女人,她也是個裁縫。云朵是鎮上的人,家住街頭第一家。云朵在當時是全鎮最有名的裁縫,據說壟斷了大半個鎮的縫紉生意。說來也怪,當年鎮上三個最有名的手藝人都住在街頭那里。除了裁縫云朵,還有剃頭佬老曹和鐵匠劉麻子。云朵那時候四十出頭,臉長長的,瘦瘦的,短發齊耳。她見人話不多,但總是笑笑的,兩只眼睛挺漂亮。
我是讀高一那年住到鎮上去的,高中設在鎮上,我在學校住讀,每周回一趟油菜坡。父親就在這個鎮上工作,他工作的單位離街頭不遠。記得就是在我讀高一的那一年,父親把我帶到了云朵的縫紉店。
那是高一下學期剛開學的時候,學校團委書記突然在全校大會上宣布說,學校要成立一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愿意參加的同學可以報名,但報名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必須有一件胸前有兩個口袋的黃軍裝。事實上我們班上有不少同學早已穿上黃軍裝了,黃軍裝是當時最時尚的服裝,穿上它雄糾糾氣昂昂,高人一等。擁有黃軍裝的同學大都是家里有人在部隊當兵,要么就是有人在武裝部工作。我家一沒當兵的,二沒人在武裝部,所以我一直穿不上黃軍裝。其實我是非常想穿一件黃軍裝的,作為一個十四五歲的青春少年誰不希望自己英姿颯爽呢?但我沒有門路,只好心甘情愿穿我的百姓布衣。然而,一聽說要成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我的心就熱血沸騰了。這時候我想,我一定要想方設法弄一件黃軍裝,然后加入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我首先找到我們班的體育委員,聽說他哥哥在部隊當連長,他已經穿過好幾件黃軍裝了。但體育委員沒有給我這個面子。他的學習很差,只會打籃球,而我的學習很好,還當著班上的學習委員。我對體育委員說,你幫我弄一件黃軍裝,我每天幫你做作業。我以為我這個主意不錯,沒想到恰恰傷了體育委員的自尊心。這樣事情就沒弄成。接下來我找到了我們的生活委員,他舅舅是武裝部的副部長,每年負責征兵工作,手中捏了不少黃軍裝。但生活委員很貪婪,他說幫我弄一件黃軍裝可以,但必須給他十塊錢。作為一個窮學生,我到哪里偷錢去?事情于是又泡了湯。后來沒有辦法,我只好去了父親的單位,苦苦哀求他買段黃布給我縫一件。不到過年,父親平時是從來不肯花錢為我縫衣裳的,他每月就是那么三十七塊五角錢,必須一分一分數著用,不然日子就過不下去。那次我去求父親,開始他怎么都不同意,后來我流淚了,他的心才軟了下來,答應拿出五塊錢,給我買段黃布縫一件。
父親買了黃布帶我去云朵那里時,正是傍晚時分,太陽剛落,紅霞滿天,云朵的縫紉店也被晚霞染紅了,云朵的臉上像是打了胭脂。父親把黃布交給云朵,請她為我量一下身體。而云朵沒有量我的身體,只是睜大眼睛將我前前后后打量了好半天。她倒是量了那段黃布。量完黃布,我發現她好看的眉頭突然皺了一下。父親也發現云朵皺了眉頭,便問怎么啦?云朵說,這段布不夠!父親說,你還沒量我兒子的身體呢,怎么知道布不夠?云朵說,誰說我沒量他的身體?我的眼睛比尺子還準。父親說,這布應該是夠的呀!云朵說,如果做學生裝當然夠,但要做軍裝的樣子就不夠了,學生裝只有一個口袋,而軍裝有兩個口袋,并且還有口袋蓋。父親想了想說,那就做學生裝吧,他本來就是學生嘛!我這時突然急了,趕緊說,不,我要軍裝!父親頓時有些生氣,黑著臉說,要軍裝干什么?你又不是當兵的!他說著就拉著我的手,將我扯出了縫紉店。走出店門后,父親回頭對云朵說,就做學生裝,他明天來拿。我這時候忍不住哭了,我哭著回頭朝縫紉店看了一眼,發現那里的晚霞都變成黑的了。
第二天我沒去云朵那里,我覺得那件只有一個口袋的學生裝對我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然而在我上晚自習的時候,父親卻突然來到了教室門口。他遞給我一個紙包說,這是你要的黃軍裝,云朵師傅自己買布給你做了兩個口袋。我頓時欣喜異常,立刻打開了紙包,看見那件黃衣裳上面果然有兩個口袋。當天晚上,我就穿著云朵為我縫的黃軍裝去團委書記那里報了名。第二天,我加入了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
7
高二那年我從鎮中轉入了縣城一中。
縣城里那時候正流行一種的確良黃褲子。無論在大街上,還是在小巷里,你到處都可以看到那些穿的確良黃褲子的人,他們有的騎著自行車在馬路中間飛奔,有的沿著街道旁邊的人行道款款而行,由于他們都穿著的確良黃褲子,所以一個個都顯得很高貴,神氣得不得了。在縣城里,除了城里人,也會有一些來自鄉下的人。這些人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們當然是沒有的確良黃褲子穿的,大都穿著皺巴巴的布褲子,有的還一條褲腿卷著,另一條褲腿吊著。這些人到城里來,說到底就是給城里人當陪襯的。
我們學校也有許多穿的確良黃褲子的人,他們大都是縣城的學生。一中的學生大部分家住縣城,來自鄉下的很少很少。比如我們班上,四十個人中只有六個人從鄉下來。誰是城里的,誰是鄉下的,只要看看他的褲子就知道了。城里的學生差不多每人都有一條的確良黃褲子,而我們幾個鄉下的學生,幾乎穿著清一色的布褲。
說句心里話,我是很欣賞的確良黃褲子的。它顏色純正,而且布紋細膩,一看就有檔次,實在是一種好衣裳,我不能睜著眼睛說瞎話,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愛美之心,人皆有之,我當然也希望自己能有一條的確良黃褲子穿一穿。我想,造的確良的人又不是專為城里人造的,鄉下人為什么不能穿呢?不過我知道暫時是穿不上的,我想等我有錢了一定縫一條穿在身上。當然,那段時間我也沒有過多地去考慮穿著問題,很快就要參加高考了,我必須把精力放到學習上。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春天就過去了。春天一過,天氣便熱了起來,這時候縣城里穿的確良黃褲子的人就越發多起來了。大家都知道,的確良黃褲子布料很薄,穿在身上輕快而涼爽。也就在這個時候,我開始犯愁了,因為入夏以后我身上還一直穿著那條厚厚的灰布褲,悶熱時刻襲擊著我,有時候我不得不合攏手中的書本,把褲腳高高地挽起來,透透風,散散熱。每當這時,我就特別羨慕那些穿的確良黃褲子的城里學生,我想,他們的腿子裝在的確良黃褲子里面該是多么舒服啊!
父親正是在這個時候來到縣城的。他到縣城一方面是因為單位的差使,一方面是為了給我送糧票,算是公私兼顧。父親在校園里找到我已是黃昏了,但光線還很明亮。在黃昏的天光下,我一眼看見父親穿著一條的確良黃褲子。一發現這條的確良黃褲子,我的眼睛就不動了,像是釘在了那條的確良黃褲子上。父親很快發覺了我神情不對,便伸手在我的灰布褲上摸了一把。父親問,這條褲子穿著是不是很熱?我想了一下說,還好,不是太熱。父親本來打算在校園里看看我就和我分手的,但這會兒他卻改變了主意。父親對我說,跟我到旅社去一趟吧。
開始我以為父親只是讓我送送他,好讓父子倆多說幾句話,到了旅社以后,我才發現父親是有重要事情要做。父親一到旅社就打開了他的提包,從中找出一條半新的布褲,接著就把身上的那條的確良黃褲子換下來了。我看著父親的舉動,正感到疑惑時,他把脫下來的的確良黃褲子送到了我手里。父親說,天氣太熱了,這條褲子給你穿吧!我捧著父親的的確良黃褲子,淚一下子就流出來了。
后來的兩個月,我差不多每天都穿著父親的那條的確良黃褲子,復習非常認真,可以說是把全部身心都撲在了學習上。七月,我參加了高考。九月,我接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十月,我穿著父親的那條的確良黃褲子,從油菜坡出發,經過鎮上,經過縣城,上了省城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