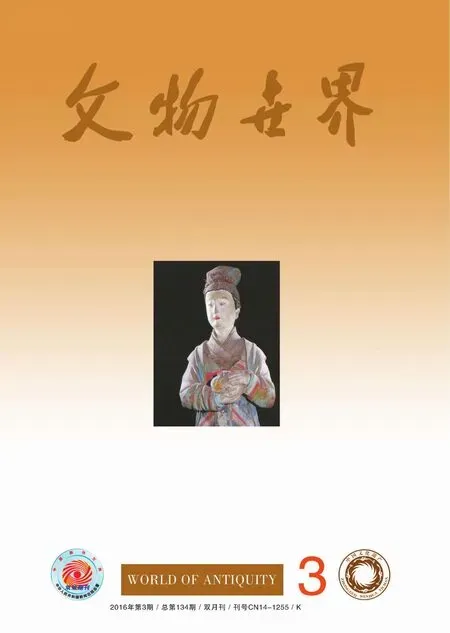深圳博物館藏明清買地券考釋
□ 周加勝
深圳博物館藏明清買地券考釋
□周加勝
我館珍藏的幾則明清買地券皆為深圳本地出土,從字體來看有朱書、墨書兩種,從質地看有磚券、瓦券。器身多有殘缺,文字也模泐不清,經與碑志或史志相互校勘,多能補齊成為完整券文。從時間上看,券文遠承北宋以來固化的書寫格式,近接元代;從空間上看,與福建地區出土的券文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另外全部券文概為江西地師所做,墓穴風水亦為其所堪輿。買地券的一些內容不僅體現了當時儒、釋、道三教合流的趨勢,也為研究深圳本地的民間信仰提供了獨特的范例。
買地券明清朱書
在全國第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過程中,發現我館有幾則明清時期的買地券未經整理,考古發掘報告亦未發布,現將其錄文并考釋如下。
一、朱書黃氏買地券
1984年于西鄉崩山39號墓出土,是一長方形薄磚,長22.2、寬13、厚2.5厘米,重0.882千克。一面四邊畫紅框,有朱書行楷九行,行字不等,約24字左右,每行字中皆劃刻直線以分行。另一面文字已完全模糊,不能辨識。中部斷裂粘合,邊角殘傷,字跡多有漫漶,字體清秀優美。
錄文如下:
維大明天順元年歲次丁丑,九月二十一日壬午,具位黃八三處士于景泰七年正月初二日歿故。龜筮葉從,相地惟吉,于東莞縣上都土名凹頭,壬山行龍丙向之原,為宅兆安厝。謹用錢玖萬玖阡玖柏玖拾玖貫文兼五綵信篦,買地壹穴。東止左青龍,西止右白虎,南止前朱雀,北止玄武。內方勾陳,分掌四域。丘丞墓伯,護肅界封,道路將軍,齊整千陌。若輒干犯訶禁,將軍、亭長收付河泊。今以牲禮酒饌共為信誓,財地交相分付。工匠修營,永保無咎。若違此約,北府主吏自當其禍,主人內外存亡悉皆安吉。急急如五帝主者,女青律令!
據《明史》卷十二《英宗后紀》[1]載:“景泰八年正月壬午,改元天順”,查陳表[2]正月丙寅朔,依此推算即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改元。由此,黃處士從歿至葬長達一年九個多月,以嶺南地區多雨潮濕的條件看,不可能停柩如此之久,故很可能是二次葬。
二次葬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存在這種習俗,仰韶文化時期的半坡遺址[3]、山東大汶口遺址[4]、安陽后崗遺址[5]等都存在二次葬的現象。石峽文化的氏族公共墳墓里,就有單人二次葬的葬址,有一座墓從隨葬器物、種類、數量上推測兩次埋葬的相隔時間不會很長[6]。此外,還有火燒墓穴及一墓存兩套隨葬品的情況。
從文獻記載來看,二次葬習俗亦遍布我國大江南北。《墨子》卷六《節葬下第二十五》[7]亦記載:“楚之南有炎人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后埋其骨,乃成為孝子。”這是關于二次撿骨葬最早的一條記載。居于我國東北的沃沮人“其葬作大木淳,長十余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均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用取骨置槨中。家人皆共一停,刻木如生,隨死者為數焉”[8]。衡陽地區也有二次洗骨葬的習俗,“山民有病,輛云先人為禍,皆開家破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9]。江西上饒一帶二次葬時,因爭風水而發生諸多盜墓、訴訟等問題,“江西廣信府一帶風俗,既葬二三年后,輒啟棺洗骨使凈,別貯瓦瓶內埋之,是以爭風水者,往往多盜骨之弊”[10]。在貴州地區有些苗族人甚至有多達七次的洗骨葬習俗,“人死,葬亦用棺。至年余,即延親族至墓前以牲酒致祭,發塜開棺取枯骨,刷洗至白為度,以布裹骨復埋一二年余,仍取洗刷至七次乃止,凡家人有病,則謂祖先骨不潔云”[11]。至清代,這一風俗在嶺南地區愈演愈烈,出現了停柩兩三年再葬的情況,被視為傷風薄俗之舉。“或有惑于風水之說,停柩期年三年而后葬者;或有葬不數年,啟土剖棺,納骸骨于瓦罐,名曰金城,遷葬他所者甚。且委諸荒郊野寺、榛莽無人之處,風吹日炙,牛羊踐踏,久而或失其罐。此誠傷風薄俗,慘不可言,所望仁人孝子之挽其頹也。”[12]
關于東莞縣,“莞,草名,可以為席。邑在廣州之東,海傍多產莞草,故名。”[13]深圳地區在此時屬于廣州府東莞縣管轄范圍,“東莞,府東南。南濱海,海中有三洲,有南頭、屯門、雞棲、佛堂門、十字門、冷水角、老萬山、零丁洋等澳。”[14]至萬歷年間,才劃歸廣州府新安縣管轄。“新安,府東南。本東莞守御千戶所,洪武十四年八月置。萬歷元年改為縣。”[15]據當時記載,東莞縣屬于中都,“東莞縣,……元定為中縣,以隸廣州,國朝因之”[16],然券中稱為“上都”,概俗之夸大之詞。
此買地券相對于其它幾則買地券,字跡清秀,或書寫者水平有限,別字頻出。如“五綵信篦”應為“五彩信幣”,“齊整千陌”應為“齊整阡陌”,“將軍、亭長收付河泊”應為“將軍、亭長收付河伯”等。
二、朱書曾文氏買地券
1989年鐵崗村地堂山5號墓出土,有兩塊,瓦質。一塊長25.4、寬24.6、厚1.1厘米,重0.972千克。凹面僅有一“上”字,凸面有一道教符錄,并寫“九玄女律令”幾個字,一角斷裂粘合(圖一)。另一塊長25.3、寬24.6、厚0.9厘米,重0.975千克。其凸面有一“上”字,凹面朱書十五行,行字不等,約21字左右,右上角斷裂粘合,字跡多模糊不清(圖二)。

圖一 曾文氏買地券

圖二 曾文氏買地券
錄文如下:
三皇一□極八卦開面天地人間物……風水之止聚其地也居之……立券何以為憑今據大明國廣東道廣州府新安縣三都恩德鄉……顯妣曾母孺人文氏,生于癸丑年八月十四日亥時,歿于□酉年六月初九日吉時。當俻衣棺錢土在□□□青仙師在吉龍崗上尋得黃龍福地一穴,坐落土名合口納□□之源,東震西兌,南離北坎,上至青天,下至黃泉,以上四至明白,托張堅固、李定度。文氏近前承買土白陰地一穴用脩,費錢九千九萬九百貫文,塟山之后,如有魑魅魍魎、古墓伏尸前來侵,都□九天玄女依律問罪施□。地仙熊應明。尋地白鶴、青鳥,作中證張堅固、李定度,孝男維棟、維檁、維材。
皇明萬歷四十三年歲次乙卯孟春月甲寅朔吉旦
查陳表[21],萬歷四十三年正月為戊申朔,而非甲寅朔,故文末用朔有誤。
文氏的孺人稱號:《禮記·曲禮下》記載:“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到明代為七品官之母或妻的封號,據《明史》載:“外命婦之號九。……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22]故文氏可能為七品官曾氏夫人。深圳地區曾氏聚集區有兩處[23],一在龍崗坪山大萬世居,為客家人后裔;另一支為沙井新橋村曾氏,廣府人后裔,離此買地券出土地點較近。查兩支曾氏族譜,皆不見有曾維棟等人之記載,常理推論,七品官在家譜中應該有記載,后世傳抄不至失漏。另有可能曾氏不是七品官,此孺人僅是一尊稱而已,明代小說中常見這種對婦人的稱呼,如“小娘叫對你說,明日老太太同孺人們下園來看花,……”[24]
關于三都恩德鄉:自萬歷元年深圳才屬新安縣轄區,現存最早的是天順年間盧祥所撰《東莞舊志》,其卷三“紡鄉”條載前四都屬文順鄉,第五到八都屬歸城鄉,第九到十二都屬恩德鄉,第十三到十六都屬延福鄉,第十七到二十都屬歸化鄉[25]。從券中三都恩德鄉的記載來看,深圳劃歸新安縣后并沒沿用原來歸東莞縣管轄時的行政區劃,據此后康熙靳文謨所撰《東莞縣志》記載,當時新安縣共三鄉,下轄七都,前三都俱恩德鄉,四都、五都俱延福鄉,六都、七都俱歸城鄉[26]。由此可見,當時新安縣是由東莞縣的三個鄉劃撥而來,雖鄉名相同但管轄區域少了很多,由原來的三鄉十二都變為七都。券中都鄉位置倒置,不合傳統敘事邏輯,此處或可理解為恩德鄉第三都之意。
文氏生年:查陳表,距萬歷四十三年日期最近的癸丑年是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文氏作為母親生于此年是不可能的,上推一個甲子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文氏有可能生于此年。
文氏卒年:券中記載為“某酉”年,從立券之年往前推,距萬歷四十三年最近的是己酉年,即萬歷三十七年。如此,則自歿至葬長達六年。由此,可以肯定的是,此買地券亦是二次葬時所立。再上推,則為丁酉年,即萬歷二十五年,如此,則自歿至葬則長達十八年。再上推,則為乙酉年,即萬歷十三年,如此,則自歿至葬長達三十年。從上文來看,二次葬一般發生在期年、三年、五年、十年,偶有十五年甚至二三十年后再葬。故其卒于萬歷三十七年是較為合理的推測。如此推測,則文氏生于嘉靖三十二年,歿于萬歷三十七年,終年五十六歲。
白鶴與青鳥:此二禽皆為凡人羽化升仙之中介,道教中就有金蟬子跨青鳥飛升一說,青鳥在后世道教的價值構建體系中逐步弱化了升仙的作用,而作為信使出現[30]。“白云能送客,青鳥解傳書”,《抱樸子·極言》亦有:“黃帝相地理,則書有青鳥”之說。白鶴因其長壽又暗合道教追求長生的終極目標,有“千歲之鶴,隨時而鳴”之說,不僅仙人道士求騎鶴飛天,世俗之人也為之向往[31],《全宋詞》中就有“翠袖更能舞,騎鶴上揚州”之語。
“仙師在吉龍崗上尋得黃龍福地一穴”:據沙井曾氏族譜記載,其后代多葬于一個叫大龍崗的地方,偶有寫做九龍崗,此地大概是其家族墓地,概與文中吉龍崗或為同一地方。如對熙積公的記載:“謙公三子,……配文氏,合葬大龍崗。”
又如其孫應華也葬于大龍崗,“長壽公長子,……合葬大龍崗……”其另一孫應麒及應麒的兩個兒子亦葬此地,應麒字夢吉,……葬大龍崗尖山仔午丁向,生二子:朝孔、朝斗……;朝孔字道源,……葬大龍崗尖山仔……[32]
三、墨書李公買地券
1983年采集于南山后海地區,瓦質。凸面無字,長25.9、寬25.8、厚1.2厘米,重0.7千克。凹面墨書十三行,行字不等,約20字左右,左下角斷裂粘合,右下角缺失,字跡多模糊(圖三)。
錄文如下:

圖三 李公買地券
今據大明國廣東廣州府東莞縣第十都東……孝男李詞稱有父李公在家患病終世……白鶴二仙人到來嶺涌棟倒盤龍大地一穴……住坐俻到銅錢九千九百九十貫,交與地主武夷王買□……,東至甲乙,南至丙丁,西至庚申,北至壬癸,中至戊己。四味(?)茅草竹木山林園□圳具條亡故住坐上下別神無分,別鬼無爭。如有按行爭,一仰橫天將軍手挑銅刀一張,破頭三寸七分,掛在柯羅樹上。今恐無憑,立此為照。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地主武夷王契
見正錢人天上月作仲人水內魚
伐(代)書人北斗星見錢人天上鶴
鶴讀了上青天,魚讀了歸深潭,鬼神何處藏(咸?)難尋覓。
“廣州府東莞縣第十都”:據盧天祥《東莞舊志》卷三《坊鄉》載天順年間東莞縣共計管轄五鄉二十都,而靳文謨《新安縣志》卷三《地理志》“都里”條載至康熙年間新安縣共計管轄三鄉七都。今深圳地區自萬歷元年方改為新安縣管轄,之前屬于東莞縣管轄。由此,正德年間坊鄉建制應該延續自天順年間,故有第十都之說,屬于恩德鄉管轄范圍。
“銅錢九千九百九十貫”與“見錢人天上鶴”:此二“錢”字為“”或“”字的俗寫變體,即“錢”字。前者見于《中華字海·乙部》,后者見于《宋元以來俗字譜·金部》[33]引《古今雜劇》、《三國志平話》、《太平樂府》,此種寫法在明代概為常見時俗杜撰字[34]。然后者釋為“錢”字,跟文中內容有重復,因為上文有“見正錢人天上月”,下文又出現“見錢人天上鶴”,與文理頗不合。但這兩個“錢”字從寫法上看完全為同一字,故“見正錢人天上月”與“見錢人天上鶴”或有一個為誤寫。另外文中“鬼神何處”的“處”字:類似“”字的異體字,亦見于《宋元以來俗字譜·虍部》引《嬌紅記》。
橫天將軍:這應該是道教本土化的一個地方神,屬于本地的民間信仰習俗,典籍記載中有唐代歸州有橫天檐力之神[35]與之名稱相類似,然未知是否為同一神祀。
柯羅樹:這是佛教中的一種樹名,又叫家尼柯羅樹[36],在此券中與道教中的橫天將軍一起出現,這充分反映了此時佛教與道教在民間信仰領域的融合。
武夷王、天上鶴與水中魚:1962年前后廈門市蓮坂村出土的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葉豐叔買地券》[37]和本券類似在券末出現了武夷王、天上鶴、水中魚等語句。此前有人將其命名為《武夷王買地券》,或為不妥[38]。此券陶質板狀,呈豎長方形,正面近邊緣用陰刻線框邊,高40、寬35、厚2厘米,正面鐫刻券文。現存于廈門博物館[39]。
這兩則券書末尾行文的相似性反映出了閩粵兩地的民間習俗在時間和空間上具有某種關聯性,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對比樣本。
四、小 結
此次普查工作中發現的館藏買地券,大多可補縣志記載之簡略。從時間、地域、內容等都與江西、福建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江右地師在民間看風水有著悠久的傳統,伴隨著地師們走南闖北,他們勘輿風水的理論也隨之在江西、福建、廣東等地傳播,同時以買地券的形式日益固化在人們的喪葬習俗之中。從史書來看,自《周禮》、《儀禮》直至清代的官修史書中,對喪葬的內容及其儀式都有詳盡的規定和明確的闡述,其核心即儒家的孝道和“事死如生”的觀念。自秦漢以降直至明清的墓葬,絕大多數是現實生活中的模仿,例如喪禮中加入僧、道做法事的內容,墓地中埋入買地券等,這些一起構成了中國古代特有的冥世觀念。
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了深圳博物館張小蘭副研究員、容達賢研究員、楊榮昌研究員,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張一兵研究員、彭全民研究員等人的悉心指導,文中圖片由深圳博物館黃詩金先生拍攝,在此一并致謝!
[1][清]張廷玉等撰《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4月。
[2][21]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3月。
[3]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原始社會聚落遺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
[4]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漢口一新石器時代墓葬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大汶口續集-大汶口遺址第二三次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97年。
[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71年安陽后崗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2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72年春安陽后崗發掘簡報》,《考古》1972年第5期。
[6]廣東省博物館、曲江縣文化局石峽發掘小組《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7期,第3頁。
[7]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中華書局,1993年10月,第268頁。
[8][南朝]范曄《后漢書》卷八五《東夷列傳》“東沃沮”條,中華書局,1965年5月。
[9][唐]姚思濂等撰《梁書》卷五二《顧憲之傳》,中華書局,1973年5月。
[10][清]趙翼《陔馀叢考》卷三十二“洗骨葬”條,中華書局,2006年3月。
[11][清]靖道謨、杜詮纂《貴州通志》卷七《苗蠻》“六額子”條,四庫全書本。
[12][清]劉溎年、張聯桂修,鄧掄斌、陳新銓纂《光緒惠州府志》卷四十五《雜識·風俗》“喪禮”條,《中國地方志集成·廣東府縣志輯⒂》,上海書店,2003年影印本。
[13][明]盧祥纂《天順·東莞志》卷一《縣名》見張一兵點校《深圳舊志三種》,海天出版社2006年5月,第29頁。
[14][15][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45《地理志》“廣州府”條,中華書局,1974年4月。
[16]同[13],第28頁。
[17]竹林居士編著《佛教難字字典·八部》,臺北縣新店市:常春樹書坊出版,民國79年。
[18]沈富進《增補匯音寶鑒·兼上平聲》,文藝學社總發行,民國七十三年二月第廿九版。
[19]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第44-45頁。
[20]魯西奇《福建所出唐宋元時期買地券考釋》,《閩臺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第35頁。
[22][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72《職官一》,中華書局,1974年4月。
[23]蕭國健《深圳地區之家族發展》,香港:顯朝書室出版,1992年10月,第69-82頁。
[24]不題撰人著《梼杌閑評》第四十一回《梟奴賣主列冠裳惡宦媚權毒桑梓》,齊魯書社,2008年4月。
[25]同[13],第189頁。
[26][清]靳文謨纂《康熙·新安縣志》卷三《地理志》“都理”條見張一兵點校《深圳舊志三種》,海天出版社2006年5月,第250頁。
[27][清]邢澍撰《金石文字辨異》光緒劉世珩校刊本,影印華東師大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五年刻本,續修四庫全書本,第240冊。
[28][漢]司馬遷《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中華書局,1974年4月。
[29]竹林居士編著《佛教難字字典·大部》,臺北縣新店市:常春樹書坊出版,1990年。
[30]孔令宏《中國道教史話》,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 年3月。
[31]胥洪泉《白鶴與道教》,《文史雜志》2008年第3期。
[32]深圳博物館藏《寶安縣沙井鎮新橋村曾氏族譜》手抄復印本。
[33]劉復、李家瑞編《宋元以來俗字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1930年。
[34][明]郭一經《字學三正》,北京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
[35][北宋]張君房編、李永晟點校《云笈七簽》卷一一九《道教靈驗記部三·歸州黃魔神峽水救船驗》,中華書局,2003年。
[36]《中華大藏經》第28冊《舍利弗阿毗曇論第十六》,中華書局,1985年5月。
[37]同[20],第38頁。
[38]吳詩池《廈門考古與文物》,鷺江出版社,1996年,第202頁。
[39]何丙仲編纂《廈門碑志匯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4年,第475頁。
(作者工作單位:深圳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