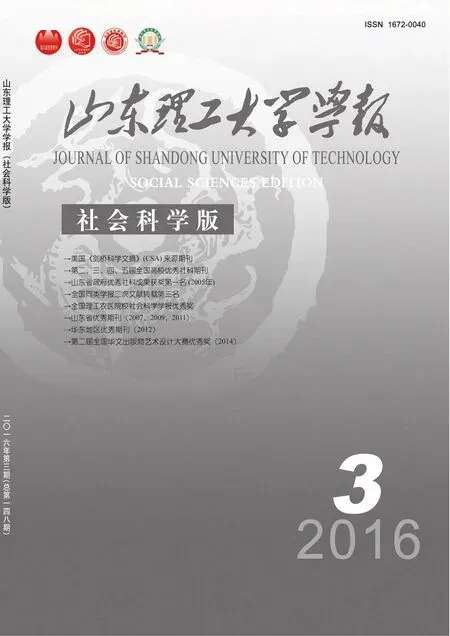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關系探討
孫智勇,劉 瀟
(1.山東理工大學商學院,山東淄博255000;2.青島大學經濟學院,山東青島266071)
?
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關系探討
孫智勇1,劉瀟2
(1.山東理工大學商學院,山東淄博255000;2.青島大學經濟學院,山東青島266071)
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變動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熱點,但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認識。使用中國28個省級行政區1990~2012年的面板數據,利用基于數據包絡法(DEA)的Malmquist指數法,測度我國近年來全要素生產率變化情況及其分解,構建動態面板模型,利用系統GMM方法,以金融發展為核心解釋變量并控制其他變量,對TFP及其分解進行分別回歸,研究發現:第一,以信貸總額與GDP之比為測度指標的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變動不是單純線性關系,而是存在顯著非線性關系,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變動呈正U型;第二,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中間途徑是影響技術進步而非規模效率變化。
金融發展; 全要素生產率; Malmquist指數; 系統GMM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快速、穩定增長,創造了令人矚目的“中國奇跡”。世界銀行認為生產率的提高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基礎,然而保羅.克魯格曼則發出“亞洲國家具有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但生產效率并沒有提高,甚至降低了”這一聲音。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究竟是源于資本大量投入還是源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這一問題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大量學者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不同方法的測算與分析,不少學者通過理論模型或是實證檢驗探索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影響因素。顯然,中國30年來巨大的金融發展是我們探討經濟發展問題中不容忽視的因素。雖然目前普遍被接受的觀點是金融發展促進了全要素生產率的進步,然而也有學者得出不同結論,所以,這一問題仍有待探討,本文收集我國28個省1990~2012年的面板數據,利用系統GMM方法再次探究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
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來源于兩部分——效率變動和技術進步。將全要素生產率進行細分,并對各個分解部分也納入經驗分析,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及產生這種影響的作用途徑,找到促進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的可行方法,為實現中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支持。然而目前國內對金融發展作用于全要素生產率中間通道的研究尚不多見,本文借助數據包絡法(DEA)和Malmquist指數對我國各省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估計,這種方法能將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細分為效率變動和技術進步,將運用此方法得到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及其分解作為被解釋變量,使用同樣的模型進行逐個回歸,對比各個回歸結果,有助于我們判斷金融發展是通過效率通道還是技術通道來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本文試圖為已有的關于金融發展和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做出探討中間渠道這一視角的補充。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究竟是線性還是非線性這一問題值得做出探討,雖然目前大部分學者所做的研究都是以一次冪線性關系做回歸,其中很多文章發現設定的某些衡量金融發展的指標對全要素生產率變化的影響為負,結果看似不合常理且找不到合理的解釋,研究者便懷疑所設定的金融發展指標有誤,但研究者往往忽略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本文將設定線性模型和加入核心解釋變量的二次項的非線性模型,探討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究竟是線性還是非線性,以及可能存在怎樣的非線性關系。
另外,基于中國省際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往往會存在內生性問題,且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不僅受到金融發展及其他控制變量影響,同時也受其滯后期影響,故本文的實證模型中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為保證模型參數估計的有效性,必須選擇合適的估計方法來消除因滯后項而引起的內生性問題。一般的面板數據回歸方法如固定效應回歸和隨機效應回歸都無法解決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動態面板系統GMM ( System GMM)中的兩步法(two-step system GMM)來合理控制內生性問題并得到回歸結果。
二、文獻綜述
關于金融發展能夠通過何種渠道促進生產率提高進而促進經濟增長這一問題,很多學者對此進行了理論模型分析。Bencivenga和Smith(1991)認為金融中介能夠幫助企業有效控制流動性風險,銀行存款為企業提供資金來源,故企業可把更多資本投入生產而不是置于流動性狀態[1]195。金融機構有收集和處理信息的功能,借助這種功能,金融機構能主動將資金投向回報率更高的項目。有效的金融制度分散了流動性風險,因此,企業可不為預防流動性風險預留過多資金而是將資金轉向回報率更高的用途,從而提高生產率。
技術創新實際上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大量學者以金融發展促進技術創新作為切入點研究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King和Levine(1993)認為,金融機構能夠評估企業所進行的風險性創新活動然后考慮是否提供融資[2]513;同時金融機構能緩解創新型企業的外部融資約束,通過提高創新的成功率,金融發展對生產率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發達的金融市場可以為最有效率的投資活動提供足夠資金,并且分散創新活動產生的風險,故金融機構對企業創新有重要影響,進而影響生產率。
Dela Fuente和Martin(1996)基于企業家努力程度決定了企業創新成功的概率這一假設,認為金融中介作為監測企業家努力程度的代理監督者,能夠督促企業家更加努力,從而提高企業創新成功的概率[3]769,同時,金融中介能降低監督成本,企業更容易獲得貸款,從而產生更高水平的創新活動。
在經驗研究方面,代表性的文章為King和Levine(1993),他們設定了一系列測度金融發展程度的指標,利用跨國面板數據研究發現,金融發展與資本積累效率提升和經濟增長之間表現為顯著正相關關系[4]717。但他們的研究并未考慮內生性問題。使用國家層面的數據,Levine 和 Zervos(1998)通過分析資本市場發展、銀行發展和長期經濟增長間的關系,發現資本市場流動性和銀行發展對生產率增長具有積極影響且較為穩健,他們認為分散的、并且更好的金融服務能夠提高經濟體的生產技術水平[5]1169。Beck等(2000)為控制內生性,創新性地利用法律起源作為金融發展的工具變量,他們的研究認為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具有顯著正面影響,且其影響穩健[6]261。他們的跨國分析表明,63個國家的金融中介在長期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了較大的積極影響,并最終促進了經濟增長。
然而,對金融發展是否一定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這一問題存在許多爭議,如 Benhabib 和 Spiegel (2000)發現并不是所有的金融指標都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顯著正面效應[7]341。甚至Guariglia等(2008)發現,他們所構建的金融發展指標與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關系顯著為負[8]633。
基于中國數據的經驗分析也日漸豐富。Aziz和Duenwal(2002)使用十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研究發現銀行貸款與GDP之比對我國TFP無顯著影響[9]。張軍、金煜(2005)同樣使用我國省級面板數據回歸發現,金融發展顯著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10]34。Guariglia和Poncet(2008)設定了多個金融發展指標,以1989~2003年省級面板數據為基礎,利用系統GMM方法進行估計,研究發現,固定資產投資中銀行貸款/財政撥款顯著促進TFP的增長;其他如銀行貸款與GDP之比甚至對TFP的增長具有顯著負面影響[11]633。
需要指出的是,在已有文獻中,研究者大多研究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而很少有學者考慮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的中間渠道。在這一方面,Arestis等(2006)基于數據包絡(DEA)方法探討了金融發展促進TFP增長的中間渠道,研究發現金融發展具有技術效率增長效應[12]417。Jeanneney等(2006)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利用數據包絡分析(DEA)Malmquist指數將TFP進行分解,發現金融發展對TFP的增長及其技術效率的增長具有顯著正面影響[13]27。本文借鑒前人的研究,利用基于數據包絡分析(DEA)的Malmquist指數,進一步探討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作用渠道。
另外,有研究發現金融發展對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可能是非線性的,如Rioja和 Valev(2004)認為,單純的線性關系可能無法很好解釋指標復雜的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14]127,本文以此為啟示,利用我國省級面板數據探討二者之間是線性關系還是非線性關系,以及可能存在怎樣的非線性關系。
三、理論機制分析
金融發展能夠通過多種渠道促進生產率的提高進而促進經濟增長,概而言之,金融發展提高TFP的途徑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金融發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TFP;另一種是金融發展→促進技術進步→提高TFP。
(一)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金融中介降低了流動性風險,有效的金融制度分散了流動性風險, 企業可不為預防流動性風險預留過多資金而是將資金轉向回報率更高的用途,銀行存款為企業提供資金來源,故企業可把更多資本投入生產,而不是讓資金處于流動性狀態,從而有效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就是優化資源配置。金融中介收集信息能夠獲得規模經濟,能夠有效對各個可供選擇的投資項目進行準確評估,從而資源將被分配到回報率更高的項目中去,即金融發展能夠促進資源配置優化,進而提高TFP。
(二)促進技術進步
內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創新是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這也是本文所列金融發展促進生產率提高的第二種途徑。大量學者以金融發展促進技術創新作為切入點研究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金融機構有信息優勢,隨著金融發展程度的不斷深化,金融機構能夠利用這一優勢更好地發揮其中介作用,有助于提高資本的邊際產出率,從而可減少一部分投入生產的資本,而將這部分資本用于生產研發,促進技術進步從而提高生產效率。
隨著金融發展不斷深化,儲蓄率得以提高,提高儲蓄率能夠促進技術進步從而促進TFP。金融抑制理論認為金融自由化一個重要方面是取消利率上限,使利率處于市場均衡水平。利率上升會提高私人儲蓄率,更好地發揮金融體系動員儲蓄的功能。儲蓄增加,金融中介便有能力向更多的創新型企業提供融資服務,從而推動技術進步。內生增長理論同樣認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需要大量研發資金投入,這從另一角度肯定了提高儲蓄對技術進步的正面作用。因此,金融發展可以進一步提高儲蓄率,加快技術進步,并最終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金融市場能夠評估企業所進行的風險性創新活動,然后考慮是否提供融資,即通過風險分散來促進技術進步,進而影響TFP 。研發過程中充滿不確定性,這使得創新型企業面臨巨大不確定性風險,而一個完善的金融市場能夠有效地對風險進行跨期分散,提高企業技術創新成功率。金融市場分散投資風險從而鼓勵企業采用更加專業化的技術;同時健全的金融機制能為創新性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緩解創新性企業可能面臨的外部融資約束,進而鼓勵企業進行創新活動,從而有效地促進技術進步,促進TFP發展。
金融中介作為監測企業家努力程度的代理監督者,能夠督促企業家更加努力,從而提高企業創新成功概率;同時,金融中介能降低監督成本,企業更容易獲得貸款,從而產生更高水平的創新活動。姚耀軍(2011)認為金融發展能夠使金融中介更好的發揮其監督作用,為技術創新以及為企業提供融資服務來推動技術進步[15]144。
四、實證檢驗
(一)指標說明與模型設定
1. TFP的測算。生產率通常可分為單要素生產率(Single Factor Productivity ,SFP)和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本文所要研究的對象是全要素生產率,它是指“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通常被看作是科學和技術進步的指標。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包括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產創新。
經濟增長不僅取決于資本、勞動等要素投入,還取決于全要素生產率。目前全要素生產率的測算方法有多種,大致可分為生產函數法、生產前沿面法和指數法。生產函數法也稱索洛余值法,該方法首先由索洛提出,其基本思想是估計的總生產函數,產出增長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長率后計算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目前已有很多學者利用這種方法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進行測算,如張軍(2003)[16]35、郭慶旺等(2005)[17]60、涂正革等(2006)[18]22等。但該方法有缺陷和不足:全要素生產率實際上會因投入要素度量的不準確以及生產函數中必需的變量考慮不全面而引起計算誤差;同時,生產函數法需設定函數參數,而參數估計的準確性難以保證。
本文采用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數法,原因主要如下:首先,Malmquist指數法屬于非參數方法,不需要生產函數進行參數設定,這樣就不會出現模型設定錯誤;其次,也是本文選擇此方法的最主要原因,即利用Malmquist指數法所獲得的TFP增長指數還可以被進一步分解,同時將TFP增長指數與其分解的各項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分別進行回歸,有助于我們在分析金融發展對TFP影響的同時,找到這種影響的中間渠道。
本研究依據的理論基礎是經濟增長理論中的生產函數。DEA模型對投入產出變量的選擇要求十分嚴格,研究的具體投入變量和產出變量的指標設定和數據來源見表1。

表1 測算TFP所需指標說明
本文使用永續盤存法估算資本存量,估算方程為:
Kit=(1-δ)Kit-1+Iit
其中,δ為固定資本投資的折舊率(采用5%),Ιit為i省(市)第t年的固定資本投資額(使用1990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進行平減)。基年為1990年,用gi表示樣本時期內i省(市)固定資本投資平均增長率,基年固定資本存量可由下式計算得到:
Ki1990=Ii1990/(gi+δ)
本文使用Deap2.1軟件,把每一個省看作一個生產決策單位,得到1990~2012年中國28個省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動情況。表2為中國1990~2012年各省全要素生產率年度平均值的變化。
2.金融發展水平的衡量。衡量金融發展的最常用指標包括M2/GDP、現存金融資產總額/國民財富,即金融相關比率等,本文將金融發展(FD)構造為信貸總額占GDP之比。
3.控制變量說明。除不斷深化的金融發展過程導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很多其他因素也推動或阻礙了生產率進步,在檢驗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時需要控制這些變量。
城市化水平(URBAN)。各省城市化水平為各省城鎮人口與其總人口之比,我們預期城市化水平對TFP有正向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FDI)。外商直接投資是發展中國家技術變遷的重要源泉之一。理論上說外商直接投資可以把優質資本、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轉移到本國,從而改善本國的TFP,但FDI也存在擠出效應,故而FDI與TFP的關系有待進一步分析驗證。
對外開放(TRADE)。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進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本文使用各省份進出口額占GDP比重作為對外開放程度的代理變量。
政府支出規模(GOV)。我們用政府財政支出與各省GDP之比來衡量政府支出規模,而政府支出有增長效應和擠出效應,前者對經濟發展有正向推動作用,后者則表現出抑制作用,所以若其增長效應強于擠出效應或不存在擠出效應則政府支出規模對TFP顯現正影響;若其增長效應弱于擠出效應或不存在增長效應則顯現負向影響。
教育(EDU)。各省份人力資本存量或者有關教育發展程度的數據無法從官方統計資料中直接獲取,故本文借鑒陳釗等的估測方法來估計我國各省份的教育發展水平。具體計算方法為:人均受教育年限=(樣本含小學文化程度人口數×6+初中×9+高中×12+大專及以上×16)/六歲以上抽樣總人口。

表2 TFP測算結果
資料來源:1990~2008年數據來自《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匯編》,2008~2012年數據來自2008~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其中FDI自2009~2012年數據來源于CEIC數據庫。
各指標對應:Effch——技術效率變化;Techch——技術進步;Pech——純技術效率變化;Sech——規模效率變化;Tfpch——全要素生產率變化。
(二)變量統計性分析
重慶1997年成為直轄,對比《新中國50年統計匯編》和《新中國60年統計匯編》,本文發現1990~1996年重慶和四川的數據比較混亂,而年鑒上并未給出明確說明,查閱各方資料也未找到準確解決辦法。為保證數據的準確性,本文將重慶和四川從樣本中剔除。西藏數據缺失嚴重,且已有的數據準確性難以保證,故本文也將其剔除。同樣,這里不含港澳臺,故本文使用中國28個省級行政區1990~2012年的數據,測算出時間長度為22年TFP的Malmquist指數,參與回歸的所有變量均包含616個觀測值,各變量均值、方差、最大值和最小值如表3。

表3 變量統計性分析
(三)模型設定
本文使用的估計模型統一如式(1):
Yit=αi+βlagYit+γFDit+∑λitControljit+εit
(1)
其中,Y表示被解釋變量,由于TFP的變化不僅受金融發展影響,也受其自身滯后一期的影響,故本文使用動態面板模型,其中lagY 表示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本文用全要素生產率變化以及它的各項分解:效率變化、技術變化、純技術效率變化、規模效率變化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FD為各省不同年度的金融發展水平;Control表示控制變量; α 、β、 λ、 γ均為待估計參數。
TFP不僅受到金融發展及其他控制變量影響,同時也受其滯后期影響,故本文的實證模型中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故模型中必定存在內生性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本文使用系統GMM法 ( System GMM),并進行Sargan檢驗;同時,本文就殘差項是否存在一階和二階序列自相關進行了檢驗。
(四)回歸結果及分析
本研究使用Stata12.0軟件,根據回歸方程(1)對TFP及其分解分別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4。

表4 線性回歸結果
注:括號內為t統計量,*、** 和 *** 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列(1)為以TFP變化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列(2)~(5)分別是以效率變化、技術變化、純技術效率變化、規模效率變化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
表4中各個回歸均通過Sargan檢驗,說明本文GMM估計方法選取的工具變量是有效的,AR1各列P值均小于0.1,拒絕不存在序列相關的原假設,說明一階序列相關,AR2 各列P值均大于0.1,接受原假設,即二階序列不相關,上述檢驗結果表明本文使用系統GMM是合理有效的。
由表4可以看出,被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作為解釋變量加入回歸方程的回歸結果均非常顯著,說明TFP及其分解的各指數均受自身上期影響。而核心解釋變量金融發展(FD)系數在列(1)(2)(3)(5)中均為負,僅在列(4)中為正,且不顯著,這與我們所預期的金融發展能夠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不相符。本文認為出現這種結果可能是因為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并非為簡單的線性,而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為考察是否有非線性關系,本文將金融發展指標的二次項加入回歸,得到調整后的回歸方程(2)。
(2)
根據回歸方程(2)得到的回歸結果如表5。
對于上述計量結果的可靠性,本文對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和模型設定正確與否進行了檢驗:Sargan檢驗的結果表明不能拒絕工具變量為過度識別的原假設,即工具變量的選擇是有效的;殘差序列相關的檢驗中AR(2)的P值大于0.05,可以推斷原模型的誤差項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性,從

表5 非線性回歸結果
注:括號內為t統計量* 、 ** 和 *** 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
而保證了模型使用的合理性。
表5中列(1)中金融發展一次項(fd)系數顯著為負,二次項(fd2)系數顯著為正,表示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關系呈現U型,即先下降再上升,金融發展程度越高,越阻礙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當金融發展程度到達一定門檻值時,其開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產生促進作用。這種U型關系在列(3)以技術變化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中也非常顯著(金融發展的一次項和二次項系數均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而在列(2)(4)(5)中金融發展的系數均不顯著,這也說明金融發展是通過影響技術進步從而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其對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的中間途徑是影響技術進步而非規模效率變化。
我們來看列(1)中各控制變量的回歸情況,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有正向影響,且影響較為顯著,外商直接投資的系數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而對外貿易的系數顯著性水平為1%,這符合本文理論預期,也與大部分研究結果相一致。
城市化水平(urban)和政府支出(gov)的系數均為正,但均不顯著,而在表5(5)中教育水平(edu)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這與理論預期背道而馳,一般來說,地區的教育水平越高,其越能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為試圖修正這一不合理結果,本文在模型(2)中加入教育水平的二次項(edu2),回歸結果顯示:教育水平的二次項系數為負,而其一次項系數為正,整體呈現正U型,即受教育水平的升高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但受教育水平達到一定臨界值后則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產生負面影響。本文認為出現這種結果的可能解釋為:受教育水平在一定范圍內的提高能促進技術進步,而當其超過這個范圍后這種技術促進作用逐漸減弱,出現不良競爭作用從而抑制了生產率增長。
對比列(1)和其他各列,我們發現在列(1)中系數顯著的變量在列(3)中也均顯著,而在剩余各列中不顯著,這進一步說明,在本文所設定的模型下,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是通過影響技術水平變化來實現的。
五、結論
本文利用中國28個省級行政區1990~2012年的數據對各省全要素生產率(TFP)變動進行了估算,并以TFP及其分解的各個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利用系統GMM法進行回歸,得到以下結論。
以信貸總額與GDP之比為測度指標的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變動不是單純線性關系,而是存在顯著的非線性關系。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變動呈現正U型,金融發展程度越高,越阻礙全要素生產率越的增長,當金融發展程度到達一定門檻值時,其開始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產生促進作用。這種U型關系在以技術變化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中也非常顯著。金融發展通過影響技術進步從而對全要素生產率產生影響,其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的中間途徑是影響技術進步而非規模效率變化。
新古典增長理論表明,長期來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唯一源泉,進一步分析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影響對保持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實現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政策性意義。本文研究發現金融發展與全要素生產率變動存在非線性關系,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可能存在門檻效應,具體表現為何種門檻類型以及門檻值為多少這一問題還未解決,這將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內容。
[1]Bencivenga V R,Smith B D.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2).
[2]King R G, Levine R.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3,(3).
[3]De la Fuente A,Marin J M.Innovation,bank monitoring,and endogenous financial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6,(2).
[4]King R G,Levine R.Finance and growth: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3).
[5]Levine R, Zervos S. Capital control liberalization and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J].World Development, 1998, (7).
[6]Beck T,Levine R,Loayza N.Finance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0,(1).
[7]Benhabib J, Spiegel M M.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growth and invest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0, (4).
[8]Guariglia A, Poncet S. Could financial distortions be no impediment to economic growth after all?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8, (4).
[9]Aziz J, Duenwald C. Growth-financial international Nexus in China[J]. IMF Working paper, 2002.
[10]張軍, 金煜. 中國的金融深化和生產率關系的再檢測: 1987~2001[J]. 經濟研究, 2005, (11).
[11]Guariglia A, Poncet S. Could financial distortions be no impediment to economic growth after all?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8, (4).
[12]Arestis P, Chortareas G, Desli 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ve efficiency in oecd countrie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J].The Manchester School, 2006, (4).
[13]Guillaumont Jeanneney S, Hua P, Liang Z. Financial development,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J].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2006, (1).
[14]Rioja F, Valev N. Finance and the sources of growth at various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Economic Inquiry, 2004, (1).
[15]姚耀軍, 曾維洲. 金融發展和全要素生產率: 一個文獻回顧[J]. 浙江社會科學, 2011 ,(3).
[16]張軍, 章元. 對中國資本存量 K 的再估計[J]. 經濟研究, 2003,(7).
[17]郭慶旺, 賈俊雪. 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估算: 1979-2004[J]. 經濟研究, 2005, (6).
[18]涂正革, 肖耿. 中國經濟的高增長能否持續[J].世界經濟, 2006,(2).
(責任編輯魯守博)
2016-02-21
孫智勇,男,山東淄博人,山東理工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劉瀟,女,山東日照人,青島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
F830.2
A
1672-0040(2016)03-0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