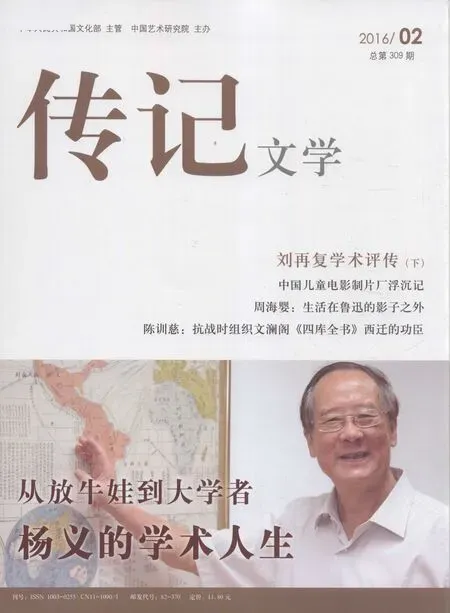智慧之妙與性情之真:楊義先生的學(xué)術(shù)人生
文 常 彬
智慧之妙與性情之真:楊義先生的學(xué)術(shù)人生
文常 彬

楊義先生
先生今年年庚七十,照常人說(shuō)法,應(yīng)是進(jìn)古稀之年,成古稀之人。可看先生那精神氣,那對(duì)學(xué)術(shù)的憧憬與激情的目光,那陶醉其中怡然自得的笑意,那聊起學(xué)術(shù)就如長(zhǎng)江黃河決口滔滔奔涌,不時(shí)濺起智慧的浪花,涌起無(wú)限的創(chuàng)造力能量,伴著那富有感染力、音量十足的爽朗笑聲,以及那揚(yáng)挫有致的廣式普通話(huà),拍打著他先秦諸子、楚辭李杜、古今敘事、民族史志、魯迅及20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貫通研究的學(xué)術(shù)堤岸,激起沁人心脾的智慧漣漪,滋養(yǎng)學(xué)子的心房,令人驚嘆先生永不枯竭的學(xué)術(shù)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且不說(shuō)先生早年名冠京華的《魯迅研究綜論》,那生猛猛的學(xué)術(shù)銳氣,那讓學(xué)界為之一震的三卷本百余萬(wàn)字的《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史》,開(kāi)個(gè)人獨(dú)立撰寫(xiě)文學(xué)史之先河,被譽(yù)為“新一代治小說(shuō)史、文學(xué)史的第一人”;《中國(guó)敘事學(xué)》不效顰不趨步于西方敘事學(xué)套路,而是扎根于中國(guó)文學(xué)文化的豐厚土壤,尋找中國(guó)人的思維方式講故事的智慧,建立屬于中國(guó)智慧的敘事學(xué)體系。先生那立志于建設(shè)大國(guó)學(xué)術(shù)氣象的使命感,在現(xiàn)代文學(xué)深耕廣種、厚積薄發(fā)十余年之后,折身洄游于唐宋文學(xué)與“邊緣活力”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研究,《李杜詩(shī)學(xué)》《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圖志——宋、遼、西夏、金、回鶻、吐蕃、大理國(guó)、元代卷》,在“重繪中國(guó)文學(xué)地圖”中馳騁其貫通古今的學(xué)術(shù)抱負(f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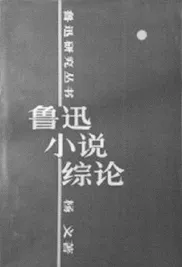
楊義著《魯迅小說(shuō)綜論》書(shū)影
卸下中國(guó)社科院文學(xué)研究所行政職務(wù)的先生,2011年受聘于澳門(mén)大學(xué)講座教授,他的學(xué)術(shù)暢游,又從長(zhǎng)江黃河的中段游向“江河源文明”——諸子還原:《老子還原》《莊子還原》《墨子還原》《韓非子還原》。關(guān)于諸子還原,先生說(shuō)他的治學(xué)路徑是從五條“脈絡(luò)”入手,分別是家族脈絡(luò)、地理脈絡(luò)、諸子游歷的脈絡(luò)、年代沿革的脈絡(luò)以及諸子的編輯學(xué)即成書(shū)的脈絡(luò)。發(fā)生和還原的關(guān)鍵點(diǎn),是要回復(fù)諸子生命的原本,這可以概括為兩句話(huà):一、觸摸諸子的體溫;二、破解諸子文化的DNA。發(fā)生學(xué)就是返本學(xué),返回事物發(fā)生之根本的學(xué)問(wèn)。把先秦諸子還原成活生生的人,尋找其生命的痕跡。每每談到自己新的研究成果,先生都有無(wú)盡的快慰:“給本科生和研究生講課時(shí),我比較喜歡講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因?yàn)槟抢锇业男掳l(fā)現(xiàn)、新智慧,講起來(lái)就會(huì)很帶激情,能夠盡興。最近,我講的較多的是‘先秦諸子還原研究’,包括老子、莊子、《論語(yǔ)》、墨子、韓非子、《孫子兵法》的發(fā)生學(xué)和文化基因問(wèn)題。這些研究以新的材料、角度和深度,理清了兩千年來(lái)許多令人困惑的謎團(tuán)。每次我講的時(shí)候,都會(huì)有變化,沒(méi)有固定的內(nèi)容。上課前,我最多列個(gè)提綱,上課時(shí)就隨意而談,旁征博引。面對(duì)博士生及以上,就把學(xué)理講得更深入一些;面對(duì)本科生和社會(huì)聽(tīng)眾,就會(huì)多講些故事。總之,談笑風(fēng)生,帶點(diǎn)幽默感,講課的效果會(huì)比較好。”
這哪是年屆七十之人,其雄心與激情,充滿(mǎn)好奇的探索興趣,就是一標(biāo)準(zhǔn)的學(xué)術(shù)青年;其豐沛的成果、從容的氣度、蓬勃的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力,又是步入佳境、游刃有余、爐火純青的人生盛年。很少有人能在先生的年紀(jì)抱著年輕人的情懷,干著年輕人的事情,出著人生盛年的豐碩成果,智慧之妙、性情之真,總是不禁令人感嘆:先生是天生做學(xué)問(wèn)的人,別人做得奇苦,先生做得奇樂(lè);別人皓首窮經(jīng),勉力而為;先生年屆七十,還壯志滿(mǎn)懷,才思泉涌,力作頻出。但先生卻不這么認(rèn)為,他說(shuō)自己是放牛娃出身,少時(shí)家貧,能讀的書(shū)有限,也不是天資很聰穎的人,唯有勤能補(bǔ)拙。在撰寫(xiě)《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史》時(shí),先生“剛拿到碩士學(xué)位,只是助理研究員,初到文學(xué)研究所工作,想用一個(gè)略大一點(diǎn)的項(xiàng)目,強(qiáng)迫著自己系統(tǒng)地閱讀現(xiàn)代文學(xué)的原版書(shū)刊。就像農(nóng)人一樣,認(rèn)認(rèn)真真地耕種一畝二分地,只事耕耘,不計(jì)收獲,看到田壟上長(zhǎng)出一行行的幼苗,心里就高興。農(nóng)家子弟不怕吃苦,一本本地讀書(shū),一本本地做筆記。讀完一個(gè)作家再讀另一個(gè)作家,心無(wú)旁騖,毫不松懈。十年堅(jiān)持下來(lái),就讀了那么多書(shū)。讀得多了,每個(gè)作家、每個(gè)流派的特性和變化軌跡,也就漸漸地了然于心。以此建構(gòu)起來(lái)的現(xiàn)代文學(xué)發(fā)展的總體結(jié)構(gòu),是經(jīng)得起時(shí)間的考驗(yàn)的”。十年磨一劍,先生就是這樣來(lái)打磨他的學(xué)術(shù)人生的。

本文作者(右二)與楊義先生和韓國(guó)學(xué)生,2005年11月于韓國(guó)
先生的智慧之妙與性情之真,接觸過(guò)他的人,都會(huì)有很深的體會(huì)。2005年我初到中國(guó)社科院文學(xué)所,在先生那里做博士后,恰逢韓國(guó)學(xué)者樸宰雨聯(lián)系先生,想在韓國(guó)教育部申請(qǐng)立項(xiàng)一個(gè)韓、中、日學(xué)者參與的國(guó)際合作課題:“晚清以來(lái)中國(guó)作家的對(duì)韓敘事變遷研究”,因慕先生之名特邀先生作為中方領(lǐng)銜學(xué)者參與課題,先生推薦我為課題組成員,負(fù)責(zé)抗美援朝文學(xué)部分。于我而言,這是一個(gè)很大的挑戰(zhàn),我之前的研究主要在女性文學(xué)上,從未涉及過(guò)戰(zhàn)爭(zhēng)文學(xué)。尤其是與韓國(guó)學(xué)者合作,研究抗美援朝文學(xué),敏感度、復(fù)雜性就更高。這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是冷戰(zhàn)時(shí)代的一場(chǎng)熱戰(zhàn),是東西方意識(shí)形態(tài)對(duì)峙較量的一場(chǎng)區(qū)域性的國(guó)際戰(zhàn)爭(zhēng)。作為社會(huì)主義陣營(yíng),中國(guó)支持北朝鮮抗擊美國(guó)為首的聯(lián)合國(guó)軍和南韓軍。《新中國(guó)的英雄贊歌——抗美援朝文學(xué)研究》是我當(dāng)時(shí)提交給韓國(guó)方面參加研討會(huì)的論文,約五萬(wàn)字,主要從英雄敘事入手。對(duì)戰(zhàn)爭(zhēng)文學(xué)研究不太熟悉的我,沒(méi)有很好地與文本拉開(kāi)距離上升到學(xué)理層面。在韓國(guó)首爾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主辦的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上,韓國(guó)的一些學(xué)者提出,我在論文中以贊賞口吻提及的《誰(shuí)是最可愛(ài)的人》,作品本身就是宣揚(yáng)“大中華主義”;《東方》里連長(zhǎng)郭林手持機(jī)槍打美國(guó)飛機(jī)是中國(guó)文學(xué)的“胡編亂造”,機(jī)槍怎么可能打飛機(jī)?有趣的是后來(lái)我閱讀到的韓國(guó)人寫(xiě)的朝鮮戰(zhàn)爭(zhēng)作品,也有描寫(xiě)韓軍用機(jī)槍打下志愿軍飛機(jī)的情節(jié)。總之,討論中我們有很多觀(guān)點(diǎn)和立場(chǎng)的激烈交鋒,互不相讓?zhuān)踔劣才鲇矤?zhēng)執(zhí),以至于那個(gè)下午的研討會(huì)變成了多位韓國(guó)學(xué)者對(duì)我“發(fā)難質(zhì)疑”的專(zhuān)題會(huì)。在男性至尊的韓國(guó),男性學(xué)者很不習(xí)慣女性學(xué)者與他們的平等論爭(zhēng),況且我們所探討的問(wèn)題又是如此地敏感特殊,涉及歷史語(yǔ)境、國(guó)家立場(chǎng)、民族情感、意識(shí)形態(tài)等多方面問(wèn)題。正當(dāng)我們的爭(zhēng)論陷入死結(jié)時(shí),一直靜聽(tīng)發(fā)言靜觀(guān)論爭(zhēng)的先生開(kāi)口了,他以極為學(xué)理的思路、中肯的分析、委婉的口吻、高屋建瓴地化解了這場(chǎng)爭(zhēng)論,既體現(xiàn)了中國(guó)學(xué)者的民族立場(chǎng),又有極具學(xué)理高度以理服人,韓國(guó)學(xué)者對(duì)先生的發(fā)言最終是心服口服。在當(dāng)晚的聚餐會(huì)上,一位白天態(tài)度激烈的韓國(guó)學(xué)者說(shuō),如果不是楊教授這么能夠以理服人,他可能就吃不下這頓飯了。
事后先生予以諄諄教誨:學(xué)術(shù)交流要體現(xiàn)在“交流”上,對(duì)于一些敏感性的問(wèn)題,既要有自己的立場(chǎng)觀(guān)點(diǎn),又要有交流溝通的意識(shí),學(xué)理的服人和讓對(duì)方接受的方式二者都很重要。而且,該課題的敏感性所限,更多地要從抗美援朝文學(xué)的異國(guó)書(shū)寫(xiě)、文化地域、風(fēng)土人情上去另辟蹊徑,從文化上去交流,這樣才能找到中韓學(xué)者都能接受的共生共鳴點(diǎn)。這件事對(duì)于我,感受尤其深切,感動(dòng)也特別多。甚至在一些看似事小實(shí)則事大、不知如何拿捏的細(xì)節(jié)上,先生的啟發(fā)體現(xiàn)了一位治學(xué)者的高度智慧。
在做課題的過(guò)程中,先生親自為我修改部分章節(jié),那時(shí)先生還不會(huì)電腦打字,都是手書(shū)墨寶,字跡漂亮,落地生根,思維的清晰體現(xiàn)在一字不改的書(shū)寫(xiě)上,整整齊齊,無(wú)一字多余,令人嘆服稱(chēng)奇。這份修改過(guò)的文稿成為我經(jīng)常捧讀在手、學(xué)習(xí)治學(xué)的絕好范本,也承載著無(wú)盡的師恩令人銘記。與先生在《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合作發(fā)表論文,先生出力甚多,卻堅(jiān)持將我的名字署在前面,以此提掖后學(xué)之人。

楊義著《中國(guó)敘事學(xué)》書(shū)影
先生近年來(lái)在做先秦諸子的還原研究,他總能把兩千年來(lái)人們熟讀的文獻(xiàn)典籍讀出生命的氣息,讀出與人不一樣的理解和新的發(fā)現(xiàn),也就是先生常講的地上地下,從文獻(xiàn)史料、族譜姓氏、居住地、游歷經(jīng)歷,到地下考古發(fā)現(xiàn)的相互激活相生印證,從中發(fā)現(xiàn)古人生命的痕跡。讀《論語(yǔ)》,他從文本的篇章結(jié)構(gòu)中發(fā)現(xiàn)其政治學(xué)密碼,成書(shū)過(guò)程經(jīng)歷了孔門(mén)弟子和再傳弟子在四五十年中的三次編撰,最終形成日后傳世的模樣,其間既蘊(yùn)含著孔子及其弟子的思維習(xí)慣、行為習(xí)慣和用語(yǔ)習(xí)慣,又體現(xiàn)出不同編纂主體思想張力的豐富性、篇章政治學(xué)的多維性,先生從文本的縫隙中、空白處發(fā)現(xiàn)問(wèn)題。先生指出,文本中的稱(chēng)謂就是發(fā)現(xiàn)問(wèn)題的窺孔之一,《論語(yǔ)》中多數(shù)篇章是孔門(mén)弟子的回憶錄,文中彼此稱(chēng)字不稱(chēng)名。因?yàn)榉Q(chēng)名是私稱(chēng),稱(chēng)字是公稱(chēng),以示弟子間相互尊重的“共同稱(chēng)呼”,是其編纂思想之一;文中稱(chēng)孔子為“子”,但也有兩次例外,稱(chēng)孔子為“夫子”,前者為春秋時(shí)的稱(chēng)謂,后者為戰(zhàn)國(guó)時(shí)的稱(chēng)謂,一字之差卻差了五十年。從縫隙中發(fā)現(xiàn)《論語(yǔ)》編纂時(shí)間的不同。這是先生采取以裂縫為切入口“撬瓶蓋”的方法,在裂縫中多問(wèn)幾個(gè)為什么,是發(fā)現(xiàn)問(wèn)題的關(guān)鍵所在。
先生認(rèn)為,由于諸子的家世、生平資料在先秦兩漢載籍中缺乏足夠的完整性,存在著許多缺失的環(huán)節(jié),歷史留下的空白遠(yuǎn)遠(yuǎn)大于歷史留下的記載,這就使得諸子生命的還原成為學(xué)術(shù)史上難題中的難題。但是空白并不等于不存在,認(rèn)真地考究為何留下這樣的空白,比如《春秋左傳》為何不載孫武,《戰(zhàn)國(guó)策》為何不載屈原,《史記》為何墨子面目模糊,如何通過(guò)史料和考古材料上的蛛絲馬跡去破解這些空白,反而往往能夠得到更深刻的意義存在。這里存在著一種重要的學(xué)術(shù)方法,以敏銳的感覺(jué)進(jìn)入有意義的空白,清理和發(fā)現(xiàn)諸子的生命如何溝通著他的文本與他生存于其間的部族、家族、民俗、信仰、口頭傳統(tǒng)之間的聯(lián)系,就是有可能進(jìn)入思想原本的深刻處。這種學(xué)術(shù)方法就是“于文獻(xiàn)處著手,于空白處運(yùn)思”。以莊子為例,莊子身份音影模糊,為何生長(zhǎng)在宋國(guó)蒙地的莊子充滿(mǎn)著只有楚人才有的思想?有三個(gè)千古之謎需要回答:一、為什么楚威王會(huì)禮聘只是小小的宋國(guó)漆園吏的莊子去做大官而莊子還不愿意?二、在那個(gè)學(xué)在官府的時(shí)代,窮困潦倒的莊子知識(shí)從何而來(lái)?三、地位低下的莊子憑什么資格破衣襤褸地與諸侯將相打交道?莊子是誰(shuí)的問(wèn)題不解決,許多問(wèn)題都難得要領(lǐng)。這就要調(diào)動(dòng)各種各樣考據(jù)手段,從先秦時(shí)期家族制度、姓氏制度角度入手解決問(wèn)題,考證出莊子為楚人,乃一疏遠(yuǎn)的貴族家庭逃亡宋國(guó)所生,這是莊子身世和莊子著書(shū)之間留下的不可能為官方文獻(xiàn)直接載錄的空白。用“空白哲學(xué)”來(lái)考察諸子文化基因的遺傳和變異問(wèn)題,就可能發(fā)現(xiàn)空白的深處隱含著千古的奧秘和無(wú)限的意義。這就是先生對(duì)莊子還原的重大發(fā)現(xiàn)。
魯迅研究是先生最早的學(xué)術(shù)起家,正如先生自述“最初的魯迅研究,是我后來(lái)研究并出版《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史》,以及孜孜矻矻探尋中國(guó)古往今來(lái)的文學(xué),乃至整個(gè)中國(guó)思想文化的本源和本質(zhì)的第一個(gè)驛站”。選擇這個(gè)學(xué)術(shù)思想的驛站,在與魯迅進(jìn)行一番思想文化和審美精神的深度對(duì)話(huà)之后,再整裝前行,對(duì)古今敘事、民族史志、諸子學(xué)術(shù)進(jìn)行長(zhǎng)期專(zhuān)研,先生由此儲(chǔ)備了彌足珍貴的思想批判能力、審美體驗(yàn)?zāi)芰臀幕€原能力。
早期北平時(shí)期的魯迅,讀佛經(jīng)拓古碑勘古籍,搜集漢石畫(huà)像,以此打磨這段生命中最黯淡孤寂的時(shí)光。魯迅的金石情結(jié),常被研究者當(dāng)做私家愛(ài)好而未引起思索關(guān)注。先生卻不同,他形象地把魯迅比喻為一口特別材料制作的洪鐘,小叩則小鳴,大叩則大鳴。他的眼光總是犀利如炬,穿透力文化審視力極強(qiáng)。先生對(duì)魯迅藏漢石畫(huà)像的研究,叩響的鐘鳴與以往的學(xué)界研究大為不同,他把新文學(xué)的魯迅引入古典金石學(xué)、考據(jù)學(xué)、畫(huà)像學(xué)研究的領(lǐng)域,將百年新文化巨人與一兩千年前的漢唐文化相對(duì)接,從魯迅收藏的幾百幅漢畫(huà)像石拓片中,尋找這位文化巨人以其深厚的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功底溝通古今的文化苦心,從漢石畫(huà)像“氣魄深沉雄大”中深刻感悟漢民族形成之初,漢人對(duì)自己作為世界一等大國(guó)的自豪感,以及海納百川接通西域文明、南亞文明的磅礴氣勢(shì),意在用中國(guó)淵源深遠(yuǎn)的力之美去激活近世中國(guó)孱弱頹敗的生命之火,重建剛健清新的民魂和國(guó)魂,由此推進(jìn)剛健質(zhì)樸的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重振東方藝術(shù)之美。先生以“魯藏”漢石畫(huà)像為橋梁,打通了新文化的魯迅和新古典學(xué)的魯迅,新文學(xué)的作家魯迅、新興版畫(huà)推動(dòng)者的魯迅,與金石學(xué)考據(jù)學(xué)畫(huà)像學(xué)舊學(xué)的魯迅,獨(dú)步了一個(gè)魯迅研究中相當(dāng)空白的新古典學(xué)領(lǐng)域,為魯學(xué)研究別發(fā)新枝另辟天地,先生的學(xué)術(shù)智慧,可謂匯通古今悟奇思,“魯學(xué)”鑿出金石聲。
許多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者受海外學(xué)者影響,認(rèn)為五四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使現(xiàn)代文學(xué)跟古典文學(xué)出現(xiàn)了裂痕,最后造成了中國(guó)文學(xué)的斷層和傳統(tǒng)文化的稀薄。這一觀(guān)念曾在相當(dāng)長(zhǎng)時(shí)期內(nèi)影響了人們對(duì)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和新文學(xué)的評(píng)價(jià)。先生則從文學(xué)存在的大文化背景著手,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問(wèn)題的癥結(jié)所在——中國(guó)的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實(shí)際上是“二四之學(xué)”,即“四庫(kù)之學(xué)”和“四野之學(xué)”。“四庫(kù)之學(xué)”指的是按照王朝的價(jià)值系統(tǒng)建構(gòu)的知識(shí)形態(tài)(如《四庫(kù)全書(shū)》),“四野之學(xué)”則是被王朝價(jià)值體系邊緣化或在這個(gè)系統(tǒng)之外的學(xué)問(wèn)資源。隨著近代以來(lái)的西學(xué)東漸,大量外來(lái)的思想文化涌入還產(chǎn)生了“四洋之學(xué)”。一些學(xué)者所持有的五四時(shí)期文學(xué)和文化的“斷裂說(shuō)”,實(shí)際上是無(wú)視中國(guó)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文學(xué)的劃分,一味以“四庫(kù)之學(xué)”作為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而忽視了“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這些先驅(qū)者,基本上是站在‘四野之學(xué)’的立場(chǎng)上,應(yīng)用‘四洋之學(xué)’來(lái)瓦解了‘四庫(kù)之學(xué)’的價(jià)值結(jié)構(gòu),對(duì)整個(gè)文學(xué)進(jìn)行了一個(gè)重新的整合和轉(zhuǎn)型”。先生以其博大精準(zhǔn)、高屋建瓴的學(xué)術(shù)定位,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在學(xué)界產(chǎn)生重要影響并成為學(xué)人耳熟能詳、反復(fù)提及使用的專(zhuān)有術(shù)語(yǔ)“楊氏詞匯”:除了上述提及的“四庫(kù)之學(xué)”、“四野之學(xué)”、“四洋之學(xué)”,先生治學(xué)講究“感悟”、“匯通”,追求文學(xué)與文明互訓(xùn)、中原與邊緣互動(dòng)、文獻(xiàn)傳統(tǒng)與口頭傳統(tǒng)互生、古代與現(xiàn)代互貫的“大文學(xué)觀(guān)”,考察漢民族文學(xué)文化的“中原凝聚力”與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文化的“邊緣活力”互為激活滲透共生所構(gòu)成的中華文明,以此重繪“中國(guó)文學(xué)地圖”,“江河源文明”、黃河文明、長(zhǎng)江文明的“太極推移”原理,其中的巴蜀文明、太湖文明形成了它的“太極眼”,民族遷徙中由西北向西南遷移、由東部向西南遷徙所形成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文化版圖的“剪刀軸”等。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間不斷地以各種形式“交兵交和、交惡交歡、交流交鋒、交手交心、交通交涉、交手交心、交通交涉、交好交合,上演一幕幕驚天動(dòng)地、悲歡離合的歷史悲壯劇,從而衍生出燦爛輝煌、多姿多彩的審美文化創(chuàng)作,并最終形成了一個(gè)血肉相連、有機(jī)共生的偉大的民族共同體”。排比句的“交交”句型,將民族融合相互交揉的多樣性歸納得何其精煉準(zhǔn)確。

2005年11月,與楊義先生去韓國(guó)參加課題研討會(huì),攝于首爾外國(guó)語(yǔ)大學(xué)。前排:楊義先生(右二)、樸宰雨教授(右三)、藤田梨那教授(右四,郭沫若外孫女)、本文作者(右五)
先生是性情中人,學(xué)術(shù)是生命、是生活,生活是學(xué)術(shù),是生活的方式,快樂(lè)的所在,二者融為一體,我你不分。先生在擔(dān)任行政職務(wù)期間,有很多事務(wù)性工作要處理,有經(jīng)常性的學(xué)術(shù)會(huì)議要參加,人在“仕途”、在旅途,身不由己。先生的法子,一是能推便推,私下里很性情地說(shuō):“我又不是專(zhuān)門(mén)開(kāi)會(huì)的,我是學(xué)者,學(xué)者的時(shí)間不能打得七零八落。”說(shuō)活的神情,很有幾分任性的恣意;二是書(shū)不離身、筆不離手,走到哪里“書(shū)齋”便搬到哪里,旅途中能閱讀,坐下來(lái)能寫(xiě)作,從時(shí)間的海綿中將別人用來(lái)喝咖啡、打撲克、聊閑篇的零碎光陰擠了出來(lái),淡定入局,很快進(jìn)入心靜自然涼的讀書(shū)思考寫(xiě)作狀態(tài)。這既是定律,更是性情,淡泊名利,遠(yuǎn)離喧囂,心遠(yuǎn)地自偏,學(xué)問(wèn)勤中起;三是充分發(fā)揮先生倡導(dǎo)的人文學(xué)研究方式上的“五學(xué)”,即眼學(xué)、耳學(xué)、手學(xué)、腳學(xué)、心學(xué),田野調(diào)查屬于腳學(xué)。文學(xué)的田野調(diào)查讓人進(jìn)入情景,就會(huì)不斷地在天地山川的遼遠(yuǎn)空間中,追尋著、思考著人與土地之魂。先生每每利用外地開(kāi)會(huì)的機(jī)會(huì),實(shí)地走訪(fǎng)他的研究對(duì)象。先生談起他“曾經(jīng)去過(guò)李賀的故鄉(xiāng),在河南西部偏遠(yuǎn)縣份的一個(gè)鄉(xiāng)鎮(zhèn)里,街頭上有一個(gè)小亭,名為李賀故里紀(jì)念亭,旁邊墻壁上是一幅畫(huà)著大美人的摩托車(chē)廣告,不遠(yuǎn)處一條幾乎斷流的溪流,感覺(jué)到它可能就是昌谷。找到了當(dāng)?shù)氐睦钯R研究會(huì)的會(huì)長(zhǎng),一個(gè)地方農(nóng)業(yè)銀行退休干部,熱心地帶先生去看李賀故居,找到了一座元代石碑,記載著李氏家族在哪。碑體橫臥在地上,斷成兩截,農(nóng)民還在碑身上曬大蔥呢。出了村子,又看到一座乾隆年代的魁星樓,找到了一座唐代古塔。想當(dāng)年,李賀騎著一頭瘦驢,沿著昌谷去尋找詩(shī),有了好的句子就寫(xiě)下來(lái)扔到口袋里,此情此景,就進(jìn)入了一種疏野荒涼的臨場(chǎng)感”。講到這些收獲體會(huì),先生津津樂(lè)道,眼神發(fā)亮,笑容天真,聲音洪亮,煙卷一根接一根,指間繚繞的是煙篆,語(yǔ)氣中自得的是因探險(xiǎn)好奇而獲得的快樂(lè)滿(mǎn)足收獲之感。

楊義著《老子還原》書(shū)影
說(shuō)來(lái)有趣,先生開(kāi)會(huì)經(jīng)常“逃會(huì)”,溜出來(lái)抽煙。記得2009年在揚(yáng)州大學(xué)開(kāi)會(huì),眨眼功夫先生離席,有人找先生,我自告奮勇出門(mén)尋找。左右不見(jiàn),忽聽(tīng)遠(yuǎn)處有笑聲,側(cè)耳一聽(tīng),原來(lái)是先生。只見(jiàn)空曠的門(mén)廳里有一孤零零的獨(dú)椅,先生坐在那里,抽著香煙,遠(yuǎn)遠(yuǎn)近近圍了不少學(xué)生,先生將學(xué)術(shù)講壇搬到了“臨時(shí)會(huì)場(chǎng)”,正在興致勃勃地給學(xué)生聊學(xué)術(shù)“上大課”,言語(yǔ)幽默,語(yǔ)氣歡快,神情陶然,還未說(shuō)完自己先“呵呵呵”地笑得開(kāi)心,感染著學(xué)生也以愉悅的笑聲回應(yīng)。先生在笑,學(xué)生在笑,年輕的心不分年齡,融在了一起。先生癡迷醉心于學(xué)術(shù),與人打交道的興趣點(diǎn)總是撥到學(xué)術(shù)這根弦上,開(kāi)了頭就收不住尾,從老子到莊子,從《論語(yǔ)》到《天問(wèn)》,長(zhǎng)江黃河,滾滾滔滔,性情之人做性情之事,先生的可愛(ài),由此可見(jiàn)一斑。有一年,先生到我校做講座“重繪中國(guó)文學(xué)地圖”,我陪同先生參觀(guān)河北易縣清西陵,每一座陵寢,先生都要走到,點(diǎn)點(diǎn)評(píng)評(píng),興致盎然。導(dǎo)游送了幾張清西陵的明信片,先生童心大發(fā),要將明信片寄回北京,他在收信欄寫(xiě)上自己的地址姓名,寄信欄署名“河北易縣清西陵昌陵孝淑睿皇后寄”,然后交給導(dǎo)游請(qǐng)她幫忙郵寄。昌陵是嘉慶皇帝和孝淑睿皇后喜塔臘氏的陵寢,在迷信人眼中,也許這種署名方式會(huì)有些犯忌,但先生全然沒(méi)有這種顧忌,而是快樂(lè)地馳騁想象揮灑性情,學(xué)術(shù)的天地,有童心滋養(yǎng),這是一種多么難得的養(yǎng)心養(yǎng)身的自在愜意。
一想起先生,總覺(jué)得很快樂(lè),因?yàn)樗目鞓?lè)感染了我記憶中的美好,那笑聲、那陶醉的眼神、那自信的樂(lè)觀(guān)、那智慧的妙性情的真,都包含在對(duì)學(xué)術(shù)的敬畏和孜孜以求。我們追逮不上先生的著作等身貫古通今,卻可以從先生的學(xué)術(shù)人生中獲得執(zhí)著與熱愛(ài)的養(yǎng)分,不斷活出自信的真。
責(zé)任編輯/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