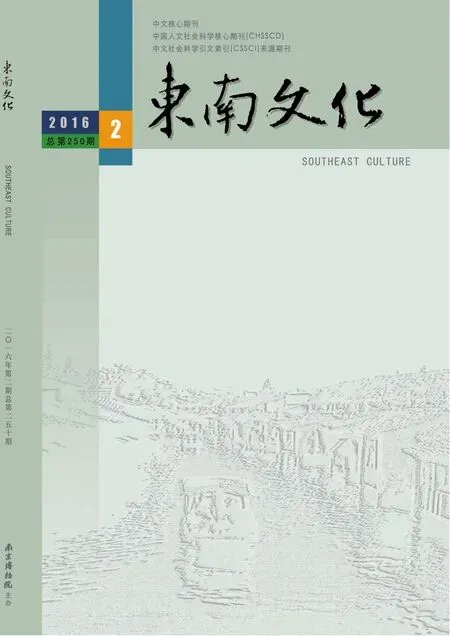古物陳列所的建立與民初北京公共空間的開辟
王謙(安慶師范大學文學院 安徽安慶 246011)
?
古物陳列所的建立與民初北京公共空間的開辟
王謙
(安慶師范大學文學院安徽安慶246011)
內(nèi)容提要:民國初年,利用紫禁城開辟古物陳列所反映了清末民初教化興國的社會輿論環(huán)境與北京政府欲通過新建公共空間以啟蒙民智的努力。古物陳列所的建立,部分解構(gòu)了紫禁城原有的封閉空間格局,開辟了新型的城市公共空間,為北京市民提供了新的休閑方式與活動場所,具有劃時代的社會文化意義。然而,北京政府又利用高昂的門票對古物陳列所實行變相的空間控制,使它的公共性質(zhì)受到了限制。
關(guān)鍵詞:古物陳列所開放民初公共空間
1934年,末代皇帝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在回到英國后回憶他在紫禁城的生活時寫道:“從前被包括在紫禁城內(nèi)的一部分重要宮宇,如今也已喪失了它頗富于傳奇色彩的權(quán)力。南面用圍墻圍起來的很大一部分(雖然沒有東西大門的守護),在皇帝退位后,即被民國當局占據(jù)。兩個最大的宮殿建筑(武英殿和文華殿)變成了博物館,收藏了部分以前用來裝飾熱河和沈陽行宮的精美藝術(shù)品。這些藝術(shù)品現(xiàn)在是被‘借’來而尚待民國政府購買的皇室藏品。”[1]莊士敦所指的博物館,正是下文所要論及的民國成立后建立的中國早期官辦博物館——古物陳列所。
在近代中國公共博物館的發(fā)展史中,古物陳列所與故宮博物院僅一墻之隔,然而,由于古物陳列所從1914年開放至1948年并入故宮博物院,僅存在了短短的30余年,逐漸被歷史所遺忘,它作為近代中國開辟公共空間努力的社會歷史文化意義也未受到應(yīng)有的重視。近年來,先后有學者通過搜尋相關(guān)的歷史資料重現(xiàn)了古物陳列所成立的歷程,如段勇細致地爬梳了古物陳列所的成立與衰落歷史[2],傅連仲梳理了古物陳列所與故宮博物院的歷史關(guān)系[3]。但是,在封建統(tǒng)治滅亡與民國新立的時代背景下,古物陳列所作為一個新型公共空間在北京出現(xiàn)的社會、文化價值還需要進行重新審視。
一 民初北京帝制空間的解體與現(xiàn)代博物館的籌辦
民國既立,清皇室失去了對紫禁城的管制權(quán),但根據(jù)民國政府制定的“清室優(yōu)待條件”,清皇室仍可“暫居宮禁”,雖沒有規(guī)定居住的具體期限,卻“劃定了宮禁范圍,在乾清門以北到神武門為止這個區(qū)域”,盡管末代皇帝溥儀在宮禁內(nèi)“仍然過著原封未動的帝王生活,呼吸著十九世紀遺下的灰塵”[4],但溥儀被允許的活動范圍實際僅是紫禁城的“生活區(qū)”,而紫禁城宮禁之外的區(qū)域如三大殿等核心地帶已歸民國政府管轄,這些區(qū)域正是昔日皇權(quán)的象征。對于如何處置這塊象征皇權(quán)的宮殿空間,民國政府業(yè)已有了新的計劃。早在1912年1月,曾協(xié)助袁世凱脅迫清皇室退位的梁士詒就曾致電給孫中山與黃興,其電文就如何處理紫禁城的用途做出了安排:“腐舊宮殿,毋論公署,私宅皆不適用,將來以午門外公園、交通馬車、三和殿為國粹陳列館,與民同樂,則乾清門內(nèi)聽其暫居,亦奚不可。”[5]可見,將昔日的帝王宮殿辟為圖書館、博物館等現(xiàn)代公共空間在推翻帝制之前就已有預(yù)案,這個預(yù)案的用意,正是著眼于開放原來的宮禁,與平民共享帝王空間,以體現(xiàn)新型國體的優(yōu)越性。
無獨有偶,曾力主創(chuàng)辦博物館的張謇此時也看到了紫禁城特殊的空間意義,又提出了利用紫禁城的空間優(yōu)勢創(chuàng)立國家博物館、圖書館的必要性:“自金元都燕,迄于明清,所謂三海三殿三所者,……則所以為地興事者,非改為博物苑、圖書館不可。”[6]至于博物館、圖書館的選址,則“以為博物院宜北海”[7],顯然,張謇所看重的正是開放紫禁城封閉空間格局的特殊意義。從官方到民間,將民國所管轄的皇宮地區(qū)開放并加以利用已成為共識。
實際上,此時民國政府也確實開始了籌建博物館的實踐,教育部、內(nèi)務(wù)部都在北京著手建立現(xiàn)代博物館。
民國成立伊始,蔡元培受袁世凱之邀出任教育總長。蔡元培早年曾在德國學習,又游歷法國、意大利、瑞士等國,對當?shù)氐拿佬g(shù)館、博物館尤為注意,并認為博物館與美術(shù)館、動植物園、影戲院一樣,都是發(fā)展社會美育應(yīng)專設(shè)的機關(guān),是科學研究、學校教育的有益補充[8]。蔡元培出任教育總長后,聘請魯迅擔任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長,主管博物館、圖書館等事宜,很快在蔡元培與魯迅等人的努力下,以“搜集歷史文物,增進社會教育”為宗旨的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在北京國子監(jiān)成立,收集太學的禮器為基本陳列品[9]。教育部選擇國子監(jiān)為創(chuàng)建博物館之所有著實際的考慮。文廟與國子監(jiān)在民國后由教育部接管,教育部認為,“國子監(jiān)舊署,毗連孔廟,內(nèi)有辟雍、彝倫堂等處建筑,皆于典制學問有關(guān),又藏有鼎、石鼓及前朝典學所用器具等,亦均足為稽古之資,實于歷史博物館性質(zhì)相近,故教育部即就設(shè)立歷史博物館,設(shè)歷史博物館籌備處”[10]。1914年,教育部又以“歷史博物一項,能令愚者智開,囂者氣靜,既為文明各國所重,尤為社會教育所資”為由[11],申請將文廟劃歸籌備處兼管。可以看出,教育部籌建歷史博物館的意圖,是利用古物的文化功能對社會實施教化,將原來的帝王廟堂轉(zhuǎn)變?yōu)樾滦偷慕袒臻g,這一意圖在日后創(chuàng)辦古物陳列所時得到了延續(xù)。
然而,國立歷史博物館的籌備工作始終沒有實質(zhì)的進展,一是因為力主創(chuàng)建博物館的蔡元培上任半年后就辭去了教育總長之職,其繼任者又多頻繁調(diào)動,走馬觀花,興辦博物館的主張難以貫徹;二是缺乏創(chuàng)辦經(jīng)費,“歷史博物品之搜集,歐式博物館房舍之增建,陳列器具之制造,種種擴張計劃則皆以絀于經(jīng)費,未能大舉興辦”,國子監(jiān)原有的古物與其他所搜集的古物,“僅敷保存之用”[12]。曾參與過歷史博物館籌建的魯迅先生后來回憶說:“其時孔廟里設(shè)了一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處長是胡玉縉先生。‘籌備處’云者,即里面并無‘歷史博物(館)’的意思。”[13]盡管歷史博物館未能在短期內(nèi)正式對外開放,但博物館籌備工作的展開已表明北京創(chuàng)辦博物館的社會、文化條件已經(jīng)成熟,同時也開啟了利用古物籌建博物館的先例。
另一個嘗試籌建博物館并在短期內(nèi)取得成功的是內(nèi)務(wù)部。如果說教育部籌辦博物館的出發(fā)點在于補助教育、開啟民智,那么內(nèi)務(wù)部所創(chuàng)立的博物館(即后來的古物陳列所)則首先意在保存古物。民國甫一成立,內(nèi)務(wù)部就以保存古物事宜向袁世凱上書:“查古物應(yīng)歸博物館保存,以符名實。但博物館尚未成立以先,所有古物,任其堆置,不免有散失之虞。擬請照司所擬,于京師設(shè)立古物保存所一處,另擬詳章,派員經(jīng)理。至各省設(shè)立分所之處,應(yīng)從緩議。”[14]設(shè)立古物保存所的動議很快得到了落實,內(nèi)務(wù)部禮俗司經(jīng)過緊張的籌備,只用了短短三個月的時間便完成了古物保存所的開放工作,于1913年1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雖然我們從現(xiàn)有的文獻中沒有見到官方開辦古物保存所的公文檔案,但由古物保存所發(fā)布在《正宗愛國報》上的開放公告記錄了它的開放歷程:
本所以保存古物為主,專征取我國往古物品,舉凡金石、陶冶、武裝、文具、禮樂器皿、服飾錦繡以及城郭陵墓、關(guān)塞壁壘、各種建設(shè)遺跡,暨一切古制作物之類,或搜求其遺物,或采取其模型,或舊有之拓本,或現(xiàn)今之攝影,務(wù)為博雅之觀,藉存國粹之寶,爰就永定門街西先農(nóng)壇屋宇,為開辦地點。惟是規(guī)劃伊始,征取各省古物,一時驟難運致,僅就京師原有舊物,擇要陳列,以資觀覽。此外尚有評古社、古藝游習社、古物保質(zhì)處、古學研究會、琴劍俱樂部、古物雜志社、古物萃賣場,以及秋千圃、蹴踘場、說禮堂等處,種種設(shè)備,以期逐漸推廣,務(wù)使數(shù)千年聲明文物之遺,于此得資考證,藉以發(fā)思古之幽情,動愛國之觀念。茲訂于民國二年一月一號共和大紀念之日起,至十號止,為本所開幕之期。是日各處一律開放,不售入場券。……凡我國男女各界,以及外邦人士,屆時均可隨意入內(nèi)觀覽。[15]
古物保存所的開放吸引了眾多游人,魯迅當天也前來游覽,并在日記中記道:“午后同季市游先農(nóng)壇,但人多耳。”[16]當時的民眾對古物保存所持什么態(tài)度呢?有人在報上表文認為,開辦古物保存所“這件事看起來好像不要緊,其實存國粹,鞏固國基,輔助共和,裨益教育,關(guān)系實非淺顯,不可視為等閑哢。中國未變法之先,壞在好古而不考古,簡直的是食古不化,才弄得國是日衰,自變法而后,又壞在棄古而不法古,把古人一筆抹倒,所以仍是雜亂無章,過猶不及”,“前人手澤所存,都要陳列起來,任人觀覽,還要從旁加上注解,說明此物之由來,為的是發(fā)起人民愛國之心,作后人前車之鑒,也頗有很大的關(guān)系呢”,“現(xiàn)在陳列古物,任人游覽,正是一個近切的要圖,要不然偌大的中華民國,將要忘卻本來面目了”[17]。保存古物的目的歸根結(jié)底還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利用中國古代的物質(zhì)資源,培育民眾的民族認同、愛國熱情,這也正是博物館的功能之一。
在先農(nóng)壇設(shè)立古物保存所,既是解古物失散之虞,也是為將來創(chuàng)辦博物館做前期準備,后來成立的“保存古物協(xié)進會”的章程也明確規(guī)定:“本會為籌辦博物院之預(yù)備,暫時附屬于古物陳列所,專事征求中國歷史上應(yīng)行保存之古物,以協(xié)贊陳列所之進行。”[18]可見,盡管“古物保存所”與“古物陳列所”的稱謂有別,功能有異,前者重在收藏、保存,后者重在陳列、展覽,但保存古物只是手段,展覽古物才是目的。杭春曉經(jīng)過考證也得出了1913年9月之前的“古物保存所”是“古物陳列所”的前身的結(jié)論[19]。可以認為,民國初年籌設(shè)的古物保存所正是古物陳列所的原始形態(tài)。
盡管古物保存所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博物館,但內(nèi)務(wù)部選擇在前清的祭神場所先農(nóng)壇開辦古物保存所,對皇家的帝王空間進行改造、開放,實質(zhì)上也是為后來的博物館空間的選址進行了探索。無論是教育部在孔廟設(shè)歷史博物館,還是內(nèi)務(wù)部在先農(nóng)壇設(shè)古物保存所,這些新型公共空間的創(chuàng)建實踐都宣告了帝都北京空間秩序的解構(gòu),同時也預(yù)示了一種新型空間秩序的到來。
二 古物陳列所的成立
1913年12月,《內(nèi)務(wù)部公布古物陳列所章程》的頒布標志著古物陳列所的建設(shè)邁入實質(zhì)階段,內(nèi)務(wù)部以“我國地大物博,文化最先,經(jīng)傳圖志之所載,山澤陵谷之所蘊,天府舊家之所寶,名流墨客之所藏,珍赍并陳,何可勝紀。顧以時代謝,歷劫既多,或委棄于兵戈,或消沉于水火,剝蝕湮沒,存者益鮮”,又“默查國民崇古之心理,搜集累世尊秘之寶藏,于都市之中辟古物陳列所一區(qū),以為博物館之先導”[20]。內(nèi)務(wù)部創(chuàng)建博物館保存古物的努力也得到了民間輿論的贊同,在陳列所開放之前,有市民在《順天時報》上發(fā)文表示:“保存古物一事,歐美文明列邦異常鄭重,良以古代遺物非屬歷史名人所遺,即系昔時美術(shù)之特產(chǎn),誠能加意保守,并公諸社會,任人觀覽,不獨可助科學之進步,致美術(shù)之發(fā)達,促工藝制造之改良,且可使一般人民目睹本國特別發(fā)達之文明及數(shù)千年來先民所遺之手澤,其愛國思想自當油然而生。今世談教育者,莫不首重社會教育,而古物陳列所實社會教育上一最重要之機關(guān)也。”[21]當時的輿論環(huán)境對于保存古物多持肯定態(tài)度,保存古物不僅有益于發(fā)揚中華文明,進而還可起到教育國人的作用。
另一方面,古物陳列所的創(chuàng)辦也符合了當時的社會政治潮流,后期的管理者在回憶陳列所創(chuàng)辦伊始時的形勢時說:“我國為數(shù)千年文明古國,歷代文物之所萃,品類最宏,舉凡金石、書畫、陶瓷、珠玉之屬,罔不至珍且奇,極美且備。雖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藝術(shù)特征,而宇宙神秘磅礴之氣,固悉于斯而孕育包涵,此東亞天府之雄,所以早為世所驚羨也。惟數(shù)千年來囿于帝制,所有寶器,大都私于一姓,匿不示人。”[22]陳列所將前朝深藏宮內(nèi)、私于皇室的古物開放展覽,將封閉空間改為開放的公共空間,恰好順應(yīng)了由帝制向共和時代變革的大勢,響應(yīng)了共和與平等的新觀念。
除了有利的輿論、文化環(huán)境外,這一時期發(fā)生的“熱河行宮古物盜案”也促成了古物陳列所的正式對外開放。民國成立后,熱河行宮管理逐漸松散,行宮內(nèi)的古物經(jīng)常被盜,更有管理人員監(jiān)守自盜的情況出現(xiàn),結(jié)果古物大量流失,以致北京的古玩市場也有大量的行宮古物出現(xiàn)。熱河行宮古物盜案使民國政府認識到了保存古物的迫切,并決定將清朝存放于熱河與沈陽清宮的古物都運至北京加以保存。1913年10月至次年10月,共經(jīng)7次搬運,共從熱河向北京搬運了1949箱,約110700余件,另有1877件附件。1914年1月至次年3月底,共經(jīng)6次共運回古物1201箱計約114600余件[23]。
數(shù)量如此龐大的古物運至北京,如何存放旋即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原來的古物保存所由于偏居城南的先農(nóng)壇,位置偏遠,影響力不足以輻射全京師,且原有的陳列空間有限,面對如此數(shù)量的古物顯然已不敷使用。這時,“由內(nèi)務(wù)總長朱啟鈐呈明大總統(tǒng),先后將遼寧、熱河行宮所藏各種寶器,陸續(xù)輦而致之北京,派護軍都統(tǒng)治格兼籌備古物陳列所事。指定就紫禁城外廷武英殿一部,先行修理,辟為陳列室及辦公處”[24]。隨著古物的陸續(xù)抵京,武英殿亦無法完全容納,遂將陳列所擴至與武英殿相對的文華殿。
朱啟鈐將古物陳列所的地點選在紫禁城內(nèi)的武英殿與文華殿顯然有著多方面的考慮:就地理位置而言,這兩處宮殿位于故宮內(nèi)南部,與同期開放的中央公園相鄰,都處在京城的核心位置,交通便利,將陳列所設(shè)立于此,有利于全城市民前來觀覽;就文化象征意義而言,武英殿與文華殿在明清兩代或作為皇帝召見臣子之處,或作為祭祀之所,都象征著皇權(quán)的威嚴與帝制社會的等級秩序,將這兩處作為陳列古物之處并對公眾開放,開啟了民國開放故宮的序幕,其意義遠大于創(chuàng)辦博物館本身。
與中央公園開放時經(jīng)費緊張相比,古物陳列所在籌辦的過程中并沒有遇到經(jīng)費短缺的問題,原因是經(jīng)朱啟鈐與外交部協(xié)調(diào),從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中撥出二十萬元作為陳列所的籌辦費用。當時的報紙報道了陳列所的創(chuàng)辦進度:“工程由德國公司承辦,費銀六萬元,其各殿墻壁梁棟一切照舊,惟窗門改換新式,分成內(nèi)外兩層,外層為菱花式,以綠色鐵紗護罩,內(nèi)層鑲嵌玻璃,可以自由開閉;于武英、敬思兩殿間加筑過廓一道,頂上□雙層玻璃,光線可以從上方射下,非常明亮。”[25]經(jīng)費充足是古物陳列所能在短期內(nèi)順利開放的客觀原因之一,由此也可見民國政府對于開放陳列所的重視程度遠高于創(chuàng)辦現(xiàn)代公園。
更重要的是,經(jīng)過前期的輿論宣傳,博物館的保存古物與補助教育兩大功能深入人心,因此,古物陳列所還在籌辦過程中即受到市民的歡迎,有人在報上發(fā)文表示:“古物陳列所,由本年國慶日開放(即十月十日),聽一般人民隨意入覽,數(shù)千年來秘密之寶藏一朝發(fā)泄,國民于精神上、實質(zhì)上所得這利益,定非淺顯。故吾人聞此不禁欣忭異常,并望朝野人士皆以國家公益為念,倘有家存古物者,從事取出,寄于陳列所中,則一般人民均受其賜,固不僅發(fā)揚國光已也。”[26]在政權(quán)更替、國運不穩(wěn)的朝代背景下,古物陳列所以保存古物為出發(fā)點,以開啟民智為宏旨,借此以達到培育國人的國家意識,在國勢弱小、列強威脅的形勢下形成思想文化層面上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正是出于這層考慮,民國政府才將古物陳列所的開幕日期定為10月10日國慶日。
1914年10月10日,經(jīng)過整修布置妥當?shù)奈溆⒌顚ν忾_放,標志著古物陳列所的正式成立,“于是我民族數(shù)千年文化生活之結(jié)晶,數(shù)千年精神所系之史料,如得薈萃保存,以公諸國人”[27],也有人稱古物陳列所的開放“為我國數(shù)千年來開一公共覽古之新紀元”[28],肯定了其作為公共空間的意義與價值。《申報》報道了開幕當天的情形:“昨,古物陳列所開始售入覽票,下午二鐘,覽者紛集,……所列古物之多,美不勝述。然此尚為五分之一余,有每星期一易之說。……計昨售票已達二千有余。”[29]古物陳列所開放后,吸引了大量的學者文人到此參觀,歷史學家顧頡剛常常到此賞玩,據(jù)他回憶,“陳列所分兩部分,文華殿里是書畫,武英殿里是古代的彝器和宋以來的各種工藝品。我們進文華殿時,頓使我受一大刺戟。這里邊真有許多好東西,尤其是宋代的院體畫和明代的文人畫,精妍秀逸之氣撲人眉宇”[30]。魯迅與周作人兄弟也常到陳列所觀摩,查閱周作人的日記,古物陳列所出現(xiàn)的頻率頗高,1917年10月7日“入東華門觀文華殿書畫,又游承運、體元二殿,出西華門”[31];同年10 月30日,“霞鄉(xiāng)亦來,同至東華門觀文華、武英兩殿陳列,出西華門返寓”[32]。一月之內(nèi),周作人就兩至陳列所,可見,對于文人學者來說,古物陳列所的開放,為他們研習古董、賞玩古物提供了新的去處,新辟了一種交往、娛樂空間。
從古物保存所到古物陳列所,回顧民初北京創(chuàng)辦公共博物館的歷程可以見出,推動北京近代博物館創(chuàng)立的力量,除了保存、利用北京既有的歷史文物的現(xiàn)實因素外,更重要的動力還是北京當局對于寄希望于博物館來教化市民、開啟民智的推動。有學者就指出,“在民族國家建立后,國民教育成為建立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礎(chǔ),國家往往利用空間對民眾進行身體與心靈的塑造”[33]。民國初立,政府的一個重要任務(wù)就是要建立起新的國家認同,培育新的市民階層與民眾精神,這種異于帝制時代等級秩序的新型社會理念,在開放式的公共空間中可以得到有效的培養(yǎng),特別是經(jīng)過改造后的北京帝王封閉空間,在開辟為現(xiàn)代公共空間后,在教化市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三 作為一種新型公共空間的意義與局限
開辟古物陳列所的意義是巨大的,它與天安門廣場改造、開放皇家禁苑一樣,在民國初年的北京踐行著開辟現(xiàn)代公共空間的努力。天安門廣場的改造打破了舊時皇家廟堂廣場的封閉模式,變成了群眾集會的公共廣場。中央公園將清王朝的社稷壇開辟為市民公園,亦是構(gòu)建公共空間的努力,使原來皇家的祭祀場所轉(zhuǎn)變?yōu)槭忻竦墓步煌臻g,豐富了北京市民的娛樂、生活空間。相比之下,因為紫禁城地位的特殊性,古物陳列所的開放因而具有更加厚重的政治文化意義。臺灣學者宋兆霖亦指出:“民國肇興,清室退位,北洋政府隨之將紫禁城前朝開放,使帝王宮禁、私府琳瑯終得公諸于世,不僅深具反對封建帝制復辟勢力之政治作用,尤富以遜清離宮所藏希代之珍為全民所共有共享之文化意涵。”[34]古物陳列所作為一種新型的公共空間,像其他博物館一樣,“從早期私人的、受控制的、排外的社會空間中分離出來,經(jīng)過重新設(shè)計,進而成為具有培養(yǎng)人們文明行為功能的組合空間”[35]。古物陳列所之于北京的意義,并不在于保存了多少歷史遺產(chǎn),而在于打破了昔日由皇家所專享的紫禁城的封閉空間,在政治層面消除了因空間管制而形成的社會階級差異,使共和制度在北京城市空間中有了物質(zhì)層面的體現(xiàn),使廣大市民在現(xiàn)實生活中感受到了階層的平等。
然而,古物陳列所開辟的現(xiàn)代公共空間又有著歷史的局限性。民國政府在當時還不能完全無視清室的影響,而且當時的北京社會仍涌動著一股復辟的風潮,北洋政府為避免刺激仍居宮禁的遜清皇室,在處理古物陳列所開放事宜時比較低調(diào),沒有大肆宣傳[36]。作為對清室的妥協(xié),北洋政府任命了一位滿人擔任古物陳列所的首任所長,而這位所長的名字也出現(xiàn)在1917年張勛復辟時公布的《引見大臣簽》中,并被封為“廂紅旗蒙古都統(tǒng)”,因而有學者認為:“古物陳列所的形成并不是革命的直接結(jié)果,而是辛亥革命的妥協(xié)產(chǎn)物——《清室優(yōu)待條件》的一個變種。”[37]作為一種新型的公共空間,古物陳列所從誕生之初就成為多種政治力量交織的場所,使其承載了多重的社會價值。在這種背景下,古物陳列所的運營不得不采取低調(diào)進行的策略,無形中限制了陳列所的社會影響力。
與此相關(guān),古物陳列所對外收取高昂的門票費用,“每張售價大洋一元”[38],文華殿開放后,“武英文華兩殿游覽券各售大洋一元”[39]。顧頡剛對這種高票價就表示不滿:“在這生計枯窘的時候,定出這樣貴的票價,簡直是拒絕人家的進去。”[40]而同期開放的中央公園的門票則為每張一角。據(jù)孟天培與甘博對1900年至1925年間北京普通工人家庭收入的調(diào)查,一名普通手藝大工的日工資不到四角,而小工則不到三角,收入中僅有5%的雜費用于交通、醫(yī)療、教育、娛樂等支出[41]。陶孟和對20世紀20年代北京48戶家庭的生活費用調(diào)查也證實,被調(diào)查的家庭僅有3.1%的支出花費在社交、教育、娛樂等項上[42]。對于大多數(shù)的北京市民來說,中央公園一角的公園門票他們都難以承擔,更何況大洋一元的陳列所門票?從實際生活來看,盡管人們逛公園的頻率要遠遠高于參觀陳列所的次數(shù),但即便如此,高昂的票價還是嚴重影響了人們進入紫禁城參觀陳列所的意愿。《順天時報》中的一篇報道證明了這一事實:“救國儲金團上次在中央公園開會時,蒞會者甚眾,故有由該園西北地方新建之橋,徑至古物陳列所前,嗣因觀覽券甚昂,致多掃興而回,故經(jīng)陳列所定于今日將展覽券減收半價,俾免望洋興嘆之感云。”[43]但門票減價并沒有成為常態(tài),即便陳列所的門票按半價收取,普通收入的民眾仍不能承受。
因此,除了開放之初幾天的熱鬧之外,古物陳列所在開放后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都門庭冷清。盡管陳列所也制定了優(yōu)惠政策,但也只面向“制服完整之國內(nèi)軍人、國內(nèi)各學校團體與由外交部專函介紹或經(jīng)內(nèi)政部準予優(yōu)待之外國人士或團體”等特殊人群[44]。而莊士敦也證實,“1916年以后,宮廷博物館里的貴重物品就一直使成千上萬的從世界各地來的參觀者感到驚奇和興奮”[45]。古物陳列所對于中國民眾的影響程度要小于對吸引外國游客前來獵奇的效果。
自1919年起,除業(yè)已開放的武英殿、文華殿外,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開始偶爾接待外賓,有時也舉辦賑災(zāi)會等特殊活動,為三大殿的正式開放做了前期鋪墊。1924年,馮玉祥授意其部下鹿鐘麟將溥儀逐出紫禁城宮禁,整個紫禁城均歸民國政府所有。1925年8月,古物陳列所向內(nèi)務(wù)部申請正式開放三大殿:“查本所存儲各項物品,向在文華、武英兩殿選擇陳列,供人瞻覽,酌收券價,藉以補助經(jīng)費。近因整頓所務(wù),月支日增,開支不敷甚巨,自非另籌辦法擴充售券地點殊不足以增收入而資挹注。擬將向來不能陳列之重大物品分別在太和、中和、保和各殿布置陳列。”[46]自此,古物陳列所的范圍將三大殿囊括在內(nèi)并對外正式開放。

圖一// 古物陳列所全圖(采自北平古物陳列所:《古物陳列所二十周年紀念專刊》,1934年)
1925年10月10日,民國政府在溥儀原來居住的宮禁成立了故宮博物院,即從乾清門往北至神武門一帶區(qū)域,開放御花園、后三宮、西六宮、養(yǎng)心殿、壽安宮、文淵閣、樂壽堂等處,增辟古物、圖書、文獻等陳列室任人參觀[47]。這樣一來,紫禁城內(nèi)就有了兩個博物館:南部是由東部的文華殿、西部的武英殿與中部的三大殿組成的古物陳列所,北部是由原先的皇宮區(qū)域構(gòu)成的故宮博物院(圖一)。自此,整個紫禁城基本全部開放。
古物陳列所的開放歷程體現(xiàn)了近代中國創(chuàng)辦博物館與保存國粹、啟蒙民智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博物館的倡導者與創(chuàng)辦者都寄希望于通過展示中國的歷史遺產(chǎn)來達到培育國民愛國精神的目的,這顯然比西方博物館提升“市民的心理與道德健康”[48]的目標更為實際,同時也體現(xiàn)了一定的民族主義色彩。因此,中國的第一所官辦博物館以古物陳列所命名也就順理成章了。然而,僅收藏古物也有悖“博物”的實質(zhì),魯迅在古物陳列所開放后即前去參觀,也認為不過是“殆如骨董店耳”[49]。更有人明確指出,古物陳列所中的物品“無一屬于國民之壯史,表尚武之精神者”,而外國博物館中的陳列品,“有關(guān)于工商實業(yè)者,亦有關(guān)于軍事范圍者,如愛國男兒之手跡,敵人炮彈之零星”[50],都未能收藏,這可能是因為,近代中國工商業(yè)落后與屢遭列強欺辱的現(xiàn)實使博物館的主辦者不得不從中國古代歷史遺產(chǎn)中尋找民族文化心理上的慰藉,并以此作為激發(fā)市民愛國精神的手段,這在客觀上削弱了公共博物館“博物”的性質(zhì)。
無論是古物陳列所還是故宮博物院,這兩個從空間上平分了紫禁城的現(xiàn)代公共機構(gòu)在開放后都收取高昂的門票費用,將廣大收入低下的平民擋在紫禁城門外,因而,紫禁城的開放“徒有開放之名,而無開放之實”[51]。如此一來,紫禁城在經(jīng)過了民國政府的努力之后,實際上只是向那些具有相當經(jīng)濟實力的上層人民與外籍人士開放,“實違共和原則”[52]。因此,當查爾斯·帕特里克·菲茨杰拉爾德(Charles Partrick FitzGerald)回憶其1924年進入紫禁城的情景時就感到了巨大的落差:“我從長安街步行到天安門,然后參觀了那些宏偉的宮殿。如果現(xiàn)在參觀故宮,你會淹沒在中外游客巨大的人流里。可是那一天我只付了微不足道的入場費(大約6個便士),便圓了游覽這座心儀已久、金碧輝煌的宮殿的美夢。我發(fā)現(xiàn)參觀者幾乎只有我自己。故宮里既沒有導游,也沒有外文寫的說明,告訴參觀者,你是在什么地方,或者看到的是什么。覲見皇帝的宮殿依然掛著小小的牌匾。那些牌匾始終是宮殿的裝飾。事實上,一切都沒有變,變化的是只是皇帝不在這些宮殿里臨朝理政了。故宮的這一部分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一座博物館。”[53]
因此,民國政府將紫禁城開辟為現(xiàn)代公共空間之后并未形成真正的公共領(lǐng)域,古物陳列所的創(chuàng)辦者對這一新型公共空間寄寓了特殊的政治目的,他們“熱切地通過提供公共空間促進新市民的形成,于是城市里出現(xiàn)了圖書館、博物館、展覽廳,教育人們并引導他們培養(yǎng)新的公共精神和國家意識”[54];同時,他們又通過經(jīng)濟手段將多數(shù)平民阻擋在紫禁城的門外,限制了其公共性的生長。結(jié)合民初北京政府開放紫禁城的實踐來看,民國政府在紫禁城內(nèi)開辦現(xiàn)代公共博物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開辟現(xiàn)代公共空間,而是借開啟民智、培育國民愛國精神之名來打破紫禁城的封閉狀況,從城市空間結(jié)構(gòu)上改變帝都北京的等級格局,以體現(xiàn)民國政權(quán)的優(yōu)越,這才是開放紫禁城的目的所在。
盡管如此,我們并不能就抹去創(chuàng)辦古物陳列所的歷史文化價值,在社會變革、觀念更新之際,古物陳列所的創(chuàng)立與運行,雖然承載了特定的國家意志與教化功能,但客觀上也改變了北京的城市空間結(jié)構(gòu),彰顯了一種新的社會秩序與國家觀念。古物陳列所開辟現(xiàn)代公共空間的努力及其構(gòu)建公共領(lǐng)域的局限,也折射出近代北京由帝制走向共和的艱難與曲折。城市空間的變遷表征了社會、文化的變化。
[1][45]〔英〕莊士敦著、陳時偉等譯:《紫禁城的黃昏》,求實出版社1989年,第123、240頁。
[2][36]段勇:《古物陳列所的興衰及其歷史地位述評》,《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3][47]傅連仲:《古物陳列所與故宮博物院》,《中國文化遺產(chǎn)》2005年第4期。
[4]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群眾出版社2007年,第32頁。
[5][37]吳十洲:《紫禁城的黎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124頁。
[6][7]張謇:《國家博物院圖書館規(guī)劃條議》,《張謇全集》(第四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80、281頁。
[8]陳志科:《蔡元培與中國博物館事業(yè)》,《中國博物館》1988年第4期。
[9]秦素銀:《蔡元培的博物館理論與實踐》,《中國博物館》2007年第4期。
[10][12]《教育部籌設(shè)歷史博物館簡況(1915年8月)》,《中國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5、275頁。
[11]《教育總長請撥國子監(jiān)籌設(shè)歷史博物館呈并大總統(tǒng)批》,《中國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4頁。
[13]魯迅:《談所謂“大內(nèi)檔案”》,《語絲》1928年1月第4卷第7期。
[14]《內(nèi)務(wù)部為籌設(shè)古物保存所致大總統(tǒng)呈(1912年10月1日)》,《中國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8頁。
[15]《先農(nóng)壇游覽十天》,《正宗愛國報》1912年12月27日。[16][49]《魯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3、137頁。
[17]《存古》,《正宗愛國報》1913年1月6日。
[18][20]《內(nèi)務(wù)部公布古物陳列所章程、保存古物協(xié)進會章程令(1913年12月24日)》,《中國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70、268-269頁。
[19]杭春曉:《繪畫資源:由“秘藏”走向“開放”——古物陳列所的成立與民國初期中國畫》,《文藝研究》2005年第12期。
[21][26]《保存古物》,《順天時報》1914年10月3日。
[22][23][24][28]北平古物陳列所編:《古物陳列所二十周年紀念專刊·緒言》,1934年,第1、4-5、3、4頁。
[25]《古物陳列所訂期開幕及其內(nèi)容》,《大自由報》1914年9月30日。
[27]原北平市政府秘書處編:《舊都文物略》,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05年,第31頁。
[29]《陳列所與社稷壇游覽記》,《申報》1914年10月16日。[30][40]顧頡剛:《古物陳列所書畫憶錄》,《寶權(quán)園文存》(卷五),中華書局2011年,第179、182頁。
[31][32]《周作人日記(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699、704頁。
[33]陳蘊茜:《空間維度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學術(shù)月刊》2009年第10期。
[34]宋兆霖:《中國宮廷博物館之權(quán)輿——古物陳列所》,臺灣“故宮博物院”2010年,第71頁。
[35][48]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 24, 18.
[38]《陳列售票》,《群強報》1914年9月12日。
[39]古物陳列所編:《古物陳列所游覽指南》,1932年。
[41]孟天培、甘博著,李景漢譯:《二十五年來北京之物價工資及生活程度》,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1926年,第56、87頁。
[42]陶孟和:《北平生活費之分析》,商務(wù)印書館2011年,第33-37頁。
[43]《陳列所之減價》,《順天時報》1915年5月23日。
[44]《修正內(nèi)政部北平古物陳列所規(guī)則(1929年9月)》,北平古物陳列所編《古物陳列所二十周年紀念專刊》,1934年,第108頁。
[46]《古物陳列所1914~1927年大事記》,故宮博物院藏《古物陳列所檔案·行政類》第39卷,轉(zhuǎn)引自段勇《古物陳列所的興衰及其歷史地位述評》,《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
[50]《最古之陳列所》,《群強報》1916年1月4日。
[51]《故宮參觀須改善限制》,《順天時報》1926年2月3日。[52]《故宮博物院索錢》,《順天時報》1926年2月10日。
[53]〔澳〕C.P.菲茨杰拉爾德著,郇忠、李堯譯:《為什么去中國——1923—1950年在中國的回憶》,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第34-35頁。
[54]〔美〕周錫瑞:《華北城市的近代化——對近年來國外研究的思考》,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津市城市科學研究會編《城市史研究》第21輯,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3頁。
(責任編輯:黃洋;校對:王霞)
The Founding of the Institute for Exhibiting Antiquities and the Opening of Beijing’s Public Space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WANG Q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Anhui, 246011)
Abstract:The founding of the Institute for Exhibiting Antiquities (Guwu Chenlie Suo) in the Forbidden City in the early time of the Republican Era reflected the social trend prevailing in China at the time that ad?vocated reviving China by education and culture. It also reflected the Beijing government’s endeavor to en?lighten the public by creating public spaces. The Institute was of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to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it deconstructed the previously closed space in the Forbidden City, created new type of urban space for the public, and provided the new site and channel of recreations for the citizen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of Beijing charged a high price for the entrance ticket, which restrained the publicity of the Institute.
Key words:Institute for Exhibiting Antiquities (Guwu Chenlie Suo); opening;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public space
中圖分類號:K876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5-12-07
作者簡介王謙(1982-),男,安慶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城市文化、城市史。
基金項目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院一般研究項目“近代京津城市空間變遷的比較研究(1860—1928)”(編號:ICS-2016-B-06);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國家文化中心建設(shè)的歷史現(xiàn)實與未來設(shè)計”(編號:12&ZD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