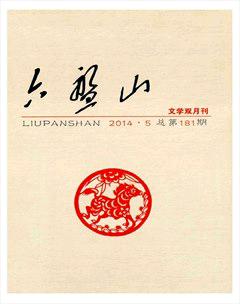懷念李成福老師
馬曉雁
2013年6月7日,農歷四月二十九,星期五。這一天的日記簡短不成章:將要在什么時候遇見什么人,冥冥中自有安排,不會早一步也不會晚一步。其后記錄的是李老師兩方閑章的內容:“北坡堂主人”“老莊三閑翁”。當時白發蒼蒼的柴老師坐在邊上的沙發里面帶微笑觀望的神情,敏像個孩子一樣歡快地跑進書房去拿東西的樣子,李老師細說那些印章玉石來歷時的自在自得,幾個老莊上來的親戚從灑滿陽光的臥室里張望過來的眼神……那些人,那些情景清晰地留存在記憶的底片上。
時光總是逃走如飛,一年不過一轉身。這期間,李老師病情加重,輾轉于銀川、北京、西安治療,后回到固原市中醫院時,幾位好友相約一同前去看望。李老師插著氧氣在兒子兒媳的攙扶下躬身坐在病床上。氣息短促,虛弱消瘦。即使在那樣的情況下,他依舊微笑著,示意我們坐下。同去的王老師跟李老師開玩笑:“快點好起來,跟你折牛拐子。”李老師含著笑點頭應和。麗君銜著淚逃出去哭泣。接過他的《北坡堂存稿》,翻開時正遇上他那張蕩秋千的照片,底端配以“老夫聊發少年狂”的文字。一時間,一個人的一輩子,一株生命的枯榮聚合起來震顫著我。
從病房出來,乘車北上出差。寫了短信想要安慰敏:“四霞,不哭!”想想又放棄了,怎么能不哭呢?那是一個人最后的時日,是他們父女在世共處的最后時光。
五月底,福銀高速兩岸的綠意已蔓延開來。但滿眼依舊是荒蕪與荒涼。從前從這里經過攝入眼簾的是千里赤地之上孤獨站立著描畫風的老樹,灰漠的天空下枯樹上的空巢,黃泥小屋上死寂的煙囪,寒風中叢生的白草……這一次,像是第一次,條條赤裸著肩胛骨的道路赫然入目。白光光的,也不十分曲折,在赤地溝壑間明滅。在這茫茫戈壁,在這草木不興寥無人煙的荒漠上,它們倒像是有生命的,是活在哪里的,裹挾著一種難以抗拒的力量。遠遠望過去,看得見它們的年輕力壯時,看得見它們的耄耋之年,看得見它們打滿褶皺的肌膚,看得見它們渾濁的雙眸,以及它們最后的風干、湮沒。是誰開踩了它們,它們將延伸向何方,它們將在哪里止步?在那樣的時刻,它們跳脫出來是要告訴我什么?
出差回來不幾日,傳來李老師不在了的消息。聽敏一聲“世上再無父親”,讓人心碎。也許因為他是好友的父親,我總自然而然從一個女兒的角度去看他;也許因為經歷了父親身陷車禍時的疼痛,所以能更深地理解敏的悲傷。回想去彭陽看桃花時他的樂觀開朗,回想他在仁山河要求糾正碑文中一個錯別字時的執著,回想他送給我的那方刻著“靜篤”二字的閑章……禁不住地淚流。
有位朋友曾經感慨,在這里生活,在這里工作,就不能鄙棄這里的貧弱,這里,將留下我們的崢嶸歲月。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李老師盡可能書寫著這個時代,《北坡堂存稿》記錄的是一代人,是一方水土。作為一名編輯,一疊疊書信訴說著他對作者付出的心血,給予讀者的熱忱。敏說李老師走后家人才發現他抽屜里放著幾冊圖畫本,紙張大小不一,有些畫面尚未完成,有些紙張打滿褶皺,但每一頁他都起了題目,寫了評語。那該是多么耐心多么細心的一位長者,那些畫本悄無聲息地表達著他對孫子孫女的厚愛與期冀。
后來幾次相聚,總會有些瞬間不經意觸碰到敏,讓她淚流滿面。那些時候,我和麗君也不知該說些什么,待敏擦干眼淚一起陷入沉默,一起望向窗外。
一個人就那樣遠行了么?人是生命原野上刮過的一陣西風么?
回想李老師這一代人,總會在某個地方給我們感動。他們上了年紀,開始離不開去疼片、安乃近以及傷濕膏,他們日漸衰老,但他們身上有種東西從未泯滅。終有一天,他們都將遠離我們而去。但他們一定留下了什么。他們是山,不為讓我們依靠,他們站立出一種高度,給我們參照。他們堅強勇毅,他們寬厚謙遜;他們兢兢業業,他們克勤克儉;他們珍愛人世,他們珍愛人……他們可能不是權貴,不是商賈,他們可能一生都在底層掙扎,他們可能一生困于貧窮,但他們總在承擔,總在創造。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我們焦灼、我們羸弱,我們在求新求變的路上一點點泯失著那些父輩們用一生去恪守的東西。那是我們的父輩用盡生命開踩的道路,作為他們的后人,不要讓它們風干、湮滅,這大約是我們對父輩最好的繼承,也是我們留給后人最寶貴的遺產。
敏說那天夜里她夢見了已逝的爺爺,是爺爺接走了她的父親。敏說那天父親飲下瓦罐里從老莊打來的泉水,安詳地離開了這個他奉獻過、深愛過的人世,沒有遺言、沒有遺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