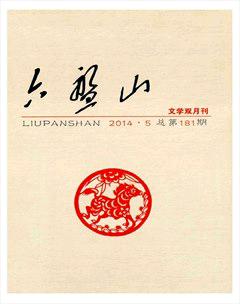杏仁如心
薛青峰
杏子熟了,讓我心醉。我像猴子一樣躥上門前的大杏樹,騎在樹杈上,舒服地享受一番。母親在下面邊撿我扔下來的杏核邊不停地提醒我,吃多了會鬧病的。然而,這個時候由不得母親。不吃飽我是不會下來的。感到肚子脹了我才往小籃子里摘。
籃子滿了,用繩子吊下來,母親接住。
半夜,我的肚子痛起來,害苦了母親。
進了城,再沒有這樣的盛宴了。母親會給我們買杏子吃。我們吃杏子的時候,母親會反復叮嚀不許亂扔杏核,要求我們將吃出的杏核投進一個鐵盒里,而我們總是大意,隨吃隨扔,母親就要邊嘮叨邊親自把杏核撿回來。我們出去玩,口袋里裝著杏子,回來時杏核沒有幾個,常遭到母親的批評。其實,小時候,吃杏子的時候不是很多,最多兩次,積累下來的杏核也就一大把。但到了秋天,母親像變戲法一樣,會變出一布袋杏核。一有空閑,母親就握起那把小榔頭,捏起杏核,小心翼翼地墊在一塊十公分見方的厚木板上,開始砸了。一顆、兩顆、三顆……母親手中頓時開放著白色的小花瓣。母親那么小心地砸,是要砸出完整的杏仁。完整的杏仁形狀如心。時而也有砸爛的杏仁瓣,母親就把這些分裂的杏仁放在一起。時間在母親手中流逝,杏仁終于砸完了。然后讓杏仁在滾燙的開水里翻個浪花,放在涼水里浸泡。母親說,這是脫苦解毒。經過浸泡一兩天的杏仁,吃起來微苦但毒已消。即使這樣,母親也不讓我們生吃杏仁。母親說,腌好的杏仁更好吃。這時,母親將杏仁分開裝起來,一個瓶子裝完整的,一個瓶子裝花瓣的,都不裝滿,留有一定的空間,最后把早已燒開又晾涼的花椒、大料、咸鹽水倒進瓶子里,母親把瓶蓋擰緊,腌泡的倒計時在我們的等待中開始了。少則半個月,多則要等到春節。往往是那一瓶花瓣杏仁讓我們提前吃掉了。那一瓶完整的杏仁母親絕對不會拿出來。等到春節,一盤完整的杏仁菜是年夜飯桌上醒目的潔白與碧綠。杏仁菜每年都會有新的名稱,母親把芹菜切成細絲,把黃瓜、胡蘿卜切成小丁,用鹽略微腌一會兒,與杏仁拌在一起,或是菠菜、青豆與杏仁相拌。我想象著給菜命名,就會脫口而出“雪映青豆、翡翠映心,春雪紅燈”。
家鄉的那棵杏樹的杏仁是甜的,在城里吃杏子,再沒有遇到甜杏仁了。雖然生活在城里,母親永遠不失農家婦女的本色。母親愛吃涼菜,且偏重酸。母親做的醋熘白菜是一道很受歡迎的下酒菜。母親不會做海參魷魚,況且那時也沒有條件吃這些。杏子上市的那一段時間,腳下隨時都會看到杏核。母親早晚遛彎回來,口袋里總是裝滿了杏核。一有空閑,她就開始砸杏核。母親作了長時間的準備,每年冬天,給我們兄妹四人一人一瓶腌好的杏仁。幾十年來沒有間斷過。母親去世以后,我在廚房里清理母親遺留下來的鍋碗瓢盆,看到一小袋杏核,還沒有砸。父親在杏子熟時,患病了。母親不停地跑醫院,沒有時間砸杏仁了,而母親給這一年的冬天準備了杏仁。
我又看到了那把小榔頭,還有那塊十公分見方的厚木板。厚木板已經不厚了,中間有一個杏仁大的小坑,形狀如心。
母親握起小榔頭,捏起杏核,小心翼翼地墊在厚木板上,開始砸了。頓時,母親手中開放著白色小花瓣,一顆、兩顆、三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