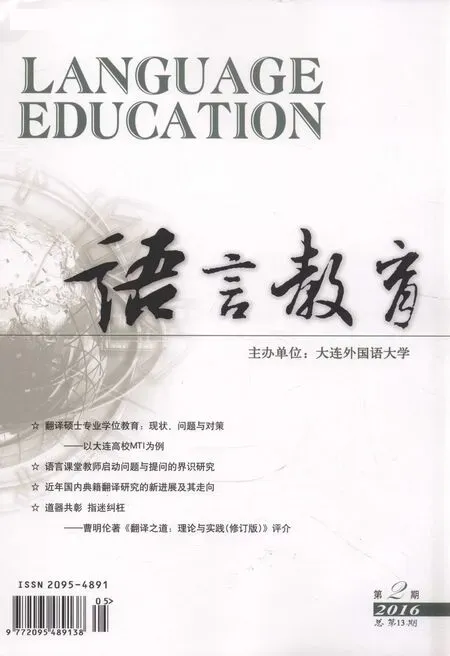突破時間“桎梏”:愛麗絲·門羅《好女人的愛情》敘事策略分析
丁 蔓 王 喬(大連理工大學(xué),遼寧大連)
?
突破時間“桎梏”:愛麗絲·門羅《好女人的愛情》敘事策略分析
丁 蔓 王 喬
(大連理工大學(xué),遼寧大連)
摘 要:愛麗絲·門羅在其眾多短篇中對敘事時間的嫻熟運(yùn)用,常常能夠突破傳統(tǒng)的線性敘事時間的桎梏,讓平淡無奇的故事在錯綜復(fù)雜的敘事時間中展示出神奇的魔力,也最大限度地調(diào)動了讀者的參與性。本文嘗試以愛麗絲·門羅的《好女人的愛情》為例,通過文本細(xì)讀的方式,探討作品中敘事時間的斷裂、跳躍、銜接與省略的特點(diǎn),故事在碎片化的敘事時間中逐步生成,融入了讀者的參與意識。門羅的敘事手法不僅激發(fā)了讀者的好奇心,而且引發(fā)了讀者強(qiáng)烈的參與意識和對現(xiàn)實(shí)的反思。
關(guān)鍵詞:敘事時間;桎梏;讀者;參與
1. 前言
時間是什么?“在日常生活里,經(jīng)驗告訴我們時間如同一條河流,綿延不斷地從‘過去’經(jīng)由‘現(xiàn)在’奔向‘未來’”(徐岱,2010: 281)。因此,人們運(yùn)用年、月、日、時、分、秒來衡量時間,認(rèn)為時間完全是連續(xù)的,是不斷延伸的,可以從數(shù)量上進(jìn)行測量,這其實(shí)是人為設(shè)置的一種機(jī)械化、一維的時間概念。人們普遍認(rèn)為,時間最大的特點(diǎn)在于其客觀流動性和不可重復(fù)性。因此,傳統(tǒng)小說一般也是遵照從過去經(jīng)由現(xiàn)在走向未來的時間順序完成一個封閉的小說空間塑造。然而,文學(xué)作品中的時間遠(yuǎn)比線性遞進(jìn)要復(fù)雜得多。
文學(xué)作品中的時間是經(jīng)過了作者的心靈孕育,不僅體現(xiàn)作者的主觀性,同時也是在文本與讀者的相互作用中生成的。也就是說,文學(xué)時間是在讀者參與文本閱讀中形成的,“不同讀者都以各自不同的閱讀方式,從自己獨(dú)特的時間經(jīng)驗出發(fā),投入文學(xué)閱讀和審美建構(gòu),使作品的文學(xué)時間以讀者個人方式生成”(馬大康,2008: 20)。文學(xué)時間融入了讀者的意識,讀者依據(jù)個人經(jīng)驗,對時間進(jìn)行重組,體驗不同的生存經(jīng)驗。讀者的參與和創(chuàng)造使得文學(xué)時間由傳統(tǒng)的線性流逝變得斷裂凌亂。在意識流小說、現(xiàn)代小說以及后現(xiàn)代小說中,時間也被各種各樣的方式分割、重組。在敘事文本中,時間隨著敘事者的不同而不斷發(fā)生變化,時間的統(tǒng)一性也被徹底打破。如愛麗絲·門羅在其短篇小說《好女人的愛情》中,完全打亂了時間的整體統(tǒng)一性,作品中時間倒錯現(xiàn)象的大量出現(xiàn)和貌似隨意的拼貼,讓小說的結(jié)構(gòu)呈現(xiàn)出凌亂松散的狀況。因此,文學(xué)時間的這種碎片化特點(diǎn)在敘事文本中體現(xiàn)得更加具體,敘事文本通過敘事時間的復(fù)雜多變?nèi)谌肓俗x者的參與意識,同時也回應(yīng)了讀者對現(xiàn)實(shí)的反思。
2. 敘事文本的時間
敘事文本的發(fā)展過程其實(shí)就是作家通過敘事來看待、探討和處理時間的過程。在敘事文本中,“時間成為一種特殊的修辭,暗中調(diào)節(jié)讀者與文本之間的關(guān)系,把讀者引領(lǐng)進(jìn)一個新奇迷人的世界”(馬大康,2008: 220)。而敘事文本又是一個具有雙線時間系列的轉(zhuǎn)換系統(tǒng),它包括故事時間和敘事時間。故事時間是故事發(fā)展的自然時間狀態(tài),是讀者在閱讀文本時根據(jù)故事內(nèi)容按照生活經(jīng)驗建構(gòu)起來的時間,這種時間是不能被更改的;而敘事時間則是敘事文本中具體表現(xiàn)出來的時間,這種時間經(jīng)過了作者的加工,是作者寫作意圖的表達(dá)。伊莉莎白·鮑溫在《小說家的技巧》中說“時間是小說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我認(rèn)為時間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凡是我所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說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對時間因素加以利用的”(1995: 602)。但以文字為表現(xiàn)形式的敘事文本本身不能展示出敘事時間維度,只有在讀者閱讀欣賞過程中,敘事時間才能不斷地生成、展開并且被讀者體驗。更確切地說,敘事時間是在讀者意識的參與中不斷形成的,讀者對敘事時間的不同建構(gòu)會得到不同風(fēng)格的敘事文本。
在傳統(tǒng)的敘事文本中,“敘事時間呈現(xiàn)出一維、線性特征,即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基本吻合”(陸麗霞,2012: 64),作家對敘事時間的處理在某種程度上是由過去走向未來,一般會遵循故事的起因—發(fā)展—高潮—原因—結(jié)局這一順序來敘述故事。這種敘事時間的安排,使得讀者只是被動地參與了敘事時間的建構(gòu),大體上按照事件發(fā)生的先后順序來閱讀文本。但在意識流小說中,敘事時間被分割成不同的時間碎片,在故事主人公意識的帶動下,讀者更傾向于接受心理時間觀念,在閱讀時對故事中人物心理時間的重構(gòu)過程即為敘事時間的生成。如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使用無意識回憶和自由聯(lián)想的方式來組織全篇,用心理時間取代線性敘事時間,把純粹的心理活動作為小說創(chuàng)作的全部內(nèi)容,讀者根據(jù)故事中人物心理的變化,重新組織小說,從而在小說中呈現(xiàn)出一種過去、現(xiàn)在、未來交錯存在的時間狀態(tài),打破了傳統(tǒng)小說對敘事時間的線性把握,給讀者留有參與空間。
在后現(xiàn)代主義敘事文本中,敘事時間本身便成為了主題,敘事文本中出現(xiàn)了關(guān)于敘事時間的游戲或是片段化的時間重組,亦或是過去、現(xiàn)在與將來時間的循環(huán),越來越融入了讀者的參與意識,錯綜復(fù)雜的敘事時間使得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融入了更多的主觀意識,極大地調(diào)動了讀者的參與性,徹底打破了傳統(tǒng)意義上時間的線性束縛,消泯了過去、現(xiàn)在與將來的時間界線,時間失去空間作為其坐標(biāo),給讀者留下想象空間。愛麗絲·門羅在其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也非常擅于處理敘事時間問題,通過非線性、循環(huán)性的“后現(xiàn)代”式的寫作手法,對敘事時間進(jìn)行重新安排,從而讓故事情節(jié)既有時間的斷裂,又有時間的突然銜接,在敘事時間的斷裂與銜接中,讀者將個人的生活經(jīng)驗與文本結(jié)合,激起了讀者對現(xiàn)實(shí)的思考。
愛麗絲·門羅的短篇小說《好女人的愛情》就是一部具有雙重敘事時間的敘事文本,該短篇看似具有傳統(tǒng)的時間序列,即從故事的起因到故事的結(jié)局,但門羅通過復(fù)雜的設(shè)計,打破時間的連貫性,讓讀者在不斷轉(zhuǎn)換的時間中能夠積極參與到小說的創(chuàng)造中,讀者不僅需要從傳統(tǒng)時間經(jīng)驗上理解小說,而且需要在故事主人公的記憶組合中重新理解小說。更重要的是,小說留有開放性的結(jié)尾,讀者擁有極大的空間對故事進(jìn)行梳理,根據(jù)個人的意識對小說的結(jié)尾進(jìn)行設(shè)置,讀者不再只是被動地進(jìn)行閱讀,而是有機(jī)會參與到文本的理解和創(chuàng)造中去。
3.《好女人的愛情》雙重敘事時間的交錯
愛麗絲·門羅作為短篇小說家,她的小說被認(rèn)為是“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哥特式的,涉及心理描寫的超小說”(Beran, 2000: 333)。因此,“她的每一部短篇都具有高度的濃縮感和延展性,能夠借助簡潔的敘述達(dá)到意蘊(yùn)深長的哲學(xué)感染力”(周怡,2014: 68)。換言之,門羅的短篇小說能夠用簡單的敘述達(dá)到一部長篇小說需要通過主人公從生到死想要明白的人生哲理,因此,她的短篇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長篇小說相媲美。門羅的短篇雖然“短”但并不“簡單”,需要讀者細(xì)細(xì)品讀才能體會到其中深刻的道理與內(nèi)涵。門羅的短篇之所以能夠突破篇幅的局限性而達(dá)到長篇小說具有的復(fù)雜深邃藝術(shù)體驗,是因為門羅創(chuàng)作過程中獨(dú)特的敘事藝術(shù)。門羅在敘述故事時,常常避免故事的平鋪直敘,而是將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交錯,她筆下的故事是一種拼接,是一種回旋往復(fù)的發(fā)現(xiàn),她對于敘事時間的安排更加獨(dú)特,常常通過敘事時間的復(fù)雜多變性來達(dá)到故事講述的最佳效果。
《好女人的愛情》是愛麗絲·門羅1998年的作品。在這部短篇小說中,門羅突破時間“桎梏”,打破線性敘事時間,對故事進(jìn)行重新組合,耐人尋味。這部小說通過敘事時間的斷裂、跳躍與銜接,使得故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環(huán)環(huán)相扣。通過對《好女人的愛情》整體敘事時間的分
析,可以得出以下敘事時間軸:

如果按照傳統(tǒng)小說對敘事時間的處理,小說正常的時間順序應(yīng)為:1951年孩子們發(fā)現(xiàn)魏倫斯先生的尸體—奎因夫人告訴伊內(nèi)德魏倫斯先生的死因—伊內(nèi)德照顧奎因夫人—伊內(nèi)德打算驗證奎因夫人的話語,但是后來又放棄這一打算—開放的結(jié)尾。然而,門羅在整體時間軸的基礎(chǔ)上,對敘事時間進(jìn)行了碎片化的處理,打破敘事時間的完整性,不遵照時間線性流逝的特點(diǎn),而是根據(jù)敘事要求,對敘事時間進(jìn)行重新拼接與組合,把伊內(nèi)德照顧奎因夫人并與奎因夫人的丈夫魯佩特之間的回憶和對未來的憧憬穿插在發(fā)現(xiàn)魏倫斯先生的尸體以及奎因夫人告訴伊內(nèi)德魏倫斯先生的死因之中。從整體上來看,小說的敘事時間是從現(xiàn)在某一時間點(diǎn)回到過去,又從過去某一時刻轉(zhuǎn)向現(xiàn)在的一種敘事移動;從局部上來看,小說的敘述時間融合了現(xiàn)在與未來的交錯,小說敘事時間的錯綜復(fù)雜性突破了傳統(tǒng)小說線性敘事時間的束縛。
當(dāng)然,在《好女人的愛情》中,門羅不僅突破線性敘事時間的束縛,同樣也加入了意識流小說遵照人物意識的流動特點(diǎn)來處理敘事時間,讀者跟著故事中人物意識的流動,不斷體會主人公思想情感的變化。故事中,伊內(nèi)德小的時候,在父親辦公室里看到的一幕一直影響著她對現(xiàn)在的判斷:“伊內(nèi)德四歲還是五歲的時候,有一次告訴媽媽,她去了父親的辦公室,看到他坐在辦公室后頭,腿上坐了個女人……她不知道乳房怎么說,不過知道它們應(yīng)當(dāng)是一對……‘像冰激凌蛋筒一樣。’伊內(nèi)德形容道……‘那你肯定是在做夢咯,’媽媽回答,‘有時候人會做一些愚蠢的夢……過了一年左右,她意識到這種解釋想必是正確的,冰激凌蛋筒不可能那樣倒扣在女士的胸脯上……扯謊”(愛麗絲·門羅,2013: 71-72)。在伊內(nèi)德意識的流動下,當(dāng)下的事件中夾雜著過去。因此,在奎因夫人告訴伊內(nèi)德關(guān)于魏倫斯先生的死因的時候,伊內(nèi)德回憶了過去,這些回憶可謂“最初的意識”對伊內(nèi)德當(dāng)下的判斷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她甚至想要相信奎因夫人同樣是在“扯謊”。這種意識的流動,使主人公對過去的回憶以及對未來的憧憬不斷穿插到人物當(dāng)前的意識中,體現(xiàn)了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三位一體的時間觀念。《好女人的愛情》敘事時間融合了線性敘事時間與意識流小說敘事時間,在人物意識的流動下,讀者對敘事時間進(jìn)行重新建構(gòu),充分體現(xiàn)了門羅對敘事時間的復(fù)雜處理。
這些碎片化的敘事看似支離破碎,沒有任何聯(lián)系,實(shí)際上卻在人的意識的帶動下,將故事整合在一起。通過人的意識,將過去發(fā)生的事、不遠(yuǎn)的將來以及眼前的現(xiàn)實(shí)交織在一起構(gòu)成了有厚度的當(dāng)下。門羅在小說片斷化的敘事中,更多地融入了故事主人公的意識與回憶。正如在意識流小說中,意識的流動相當(dāng)于時間的“綿延”,記憶中的事情是對生命的最初體驗,只是它以記憶的方式存在于人的意識中,但卻在反復(fù)地影響著人們當(dāng)下的生活,敘事時間中參與了意識,主人公能夠在當(dāng)下和記憶中對自身的處境建構(gòu)新的理解。同時,敘事時間中融入了故事人物的心理變化,根據(jù)人物心理的變化反映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復(fù)雜性與不確定性。并且在人物心理變化的帶動下,讀者更能體會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并結(jié)合個人經(jīng)驗對故事進(jìn)行判斷。
敘事時間在門羅的小說中是復(fù)雜多變的,《好女人的愛情》將傳統(tǒng)小說的線性敘事時間進(jìn)行了改造,并結(jié)合了意識流小說對敘事時間處理的技巧,突破了時間的“桎梏”,敘事不再是依照客觀現(xiàn)實(shí)的時間順序進(jìn)行敘述,而是更多地融入了人的意識,這種雙重敘事時間的融合,不僅將故事主人公的處境逐步展示給讀者,同時激發(fā)了讀者的好奇心以及強(qiáng)烈的參與意識。“敘事時間的倒錯以及碎片化的敘事讓讀者有機(jī)會參與到時間的重新建構(gòu)中,對小說故事進(jìn)行推斷”(Duncan, 2011: 93-94)。讀者在對小說敘事時間的重新梳理中,讓敘事時間帶上了感情色彩,成為一種主觀性的東西,能夠為讀者所把握,并且為敘事做鋪墊,時間的不同使得敘事效果也有著不同的變化。敘事時間在人的意識的參與下,更加復(fù)雜多變,在很大程度上調(diào)動了讀者的參與意識和對現(xiàn)實(shí)的反思。
4.《好女人的愛情》敘事時間交錯生成中讀者的參與意識
門羅在《好女人的愛情》中,交錯使用斷裂、跳躍與銜接的手法,使人物的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現(xiàn)實(shí)與回憶巧妙自然地結(jié)合在敘事時間中,將時間進(jìn)行切割和重新組合,讓敘事時間不斷在過去、現(xiàn)在與將來中回旋往復(fù),故事在讀者的參與中重新進(jìn)行拼接,形成一個完整的統(tǒng)一體。
小說中看似毫無關(guān)系的敘事片斷,在讀者的參與下彼此聯(lián)系:“魯佩特坐下來讀報,她問他是否想喝杯茶。他當(dāng)然回答說不用麻煩,她知道這個回答在鄉(xiāng)間交談中相當(dāng)于‘是的’,所以依然沏了茶……她第一次在這幢房子里看到他時,覺得他還是老樣子……她回想著坐在高年級教室里的情景”(愛麗絲·門羅,2013: 45-46)……這是伊內(nèi)德在照顧生病的奎因夫人時,與奎因夫人的丈夫,即她的高中同學(xué)魯佩特在一起的時候的一些心理活動,從中可以看出伊內(nèi)德對魯佩特先生產(chǎn)生了好感。這一心理活動似乎與全文敘事毫無關(guān)系,但是它卻為伊內(nèi)德后來在照顧奎因夫人時復(fù)雜的情感奠定了基礎(chǔ)。從看護(hù)人員角度出發(fā),伊內(nèi)德對待奎因夫人應(yīng)該是同情的,需要盡心照顧的;但從一個對奎因夫人丈夫有好感的女人的角度出發(fā),伊內(nèi)德對奎因夫人是憎惡的、厭倦的。伊內(nèi)德在日記中寫到“電扇關(guān)了又開,抱怨有噪音”(愛麗絲·門羅,2013: 64)。這雖然不是直接表露,卻表達(dá)了她的厭惡。因此,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將回憶與現(xiàn)實(shí)聯(lián)系起來,能夠成功地窺探到伊內(nèi)德對奎因夫人復(fù)雜的內(nèi)心感受,伊內(nèi)德性格的多面性、矛盾性與復(fù)雜性也恰恰是通過敘事時間的交錯慢慢呈現(xiàn)出來的。通過錯綜復(fù)雜的敘事時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也會融入自己對“好女人”的判斷,從而對現(xiàn)實(shí)進(jìn)行反思。像伊內(nèi)德這樣從事護(hù)理工作的女子,在開始還是讓人感到敬重的,畢竟這是一份任務(wù)繁重且艱苦的工作,但如果這其中融入了其它復(fù)雜的感情就不會讓人感到敬重,因此,讀者會不斷根據(jù)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尋求典范和答案。
此外,正是由于伊內(nèi)德對魯佩特產(chǎn)生了好感,她的生活也發(fā)生了細(xì)微的變化,她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是做惡夢:“當(dāng)然了,她也做過感覺很浪漫的夢,某個男人用胳膊摟著她,或者甚至緊緊擁抱她。要么是個陌生男人,也有可能是她認(rèn)識的男人—有時是一個想想都覺得可笑的男人。這些夢會讓她沉思,或者惆悵,不過也有點(diǎn)欣慰,它們表明這類情感對她而言也是可能的”(愛麗絲·門羅,2013: 49)……這其實(shí)只是伊內(nèi)德做的一個夢,原本一個普通的敘事碎片,在讀者對文本的參與與創(chuàng)造下,將伊內(nèi)德做夢這件瑣事與整個敘事事件聯(lián)系在一起,把未來與現(xiàn)在結(jié)合在一起。伊內(nèi)德對魯佩特的感情,不僅僅只是把他當(dāng)做自己的高中同學(xué)亦或是奎因太太的丈夫,她幻想與魯佩特先生的未來,因此在照顧奎因夫人的同時,對待奎因夫人的孩子也特別好,伊內(nèi)德在不斷地為自己與魯佩特的未來做準(zhǔn)備。
門羅雖然只是描寫了伊內(nèi)德的一個夢境,但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會不斷地去猜測、想象伊內(nèi)德與魯佩特的未來到底會是什么樣子的。讀者的參與與創(chuàng)造,將未來與當(dāng)下融合在一起,讀者在揣測故事中主人公的情感的同時,也會跟著門羅的筆觸反思現(xiàn)實(shí)生活,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人們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情感問題,到底應(yīng)該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去對待這個問題,需要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去體會。這種融入意識的“門羅式”敘事時間,讓讀者在表層的“生活流”結(jié)構(gòu)下挖掘深層的意義,給人留下一種“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思考,在“此言”與“彼意”的交錯中,讀者在嘗試?yán)斫忾T羅要展示的生活的同時必然要加入自己對生活的深刻體驗。“門羅在現(xiàn)實(shí)主義逼真的場景描寫基礎(chǔ)上,適當(dāng)?shù)卮┎濉⑦\(yùn)用了后現(xiàn)代主義的一些技巧,打斷線性敘事,創(chuàng)造性地重新組合情節(jié),呈現(xiàn)出‘碎片’式的審美哲學(xué)”(張磊,2014: 186)。時間結(jié)構(gòu)相當(dāng)于人的存在方式,是生命成長的跡線。門羅在敘事時間的處理上,讓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交錯出現(xiàn),使讀者也在不斷地穿梭于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之間,在現(xiàn)在的時間中與過去的自己進(jìn)行“對話”,反思人物的成長過程;把未來的時間融入到現(xiàn)在,根據(jù)故事主人公的情感變化,猜測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未來的可能性,對生活有著強(qiáng)烈的思考。
最后,門羅刻意回避了傳統(tǒng)小說封閉式的結(jié)尾,而選擇賦予故事開放的含混性。就在讀者想要知道伊內(nèi)德是否會驗證奎因夫人所說的關(guān)于魏倫斯先生的死因到底是真是假時,小說卻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船槳藏起來了。’魯佩特說。他鉆進(jìn)柳樹叢。她突然就看不到他了。她走近水邊,靴子微微陷進(jìn)泥中,阻擋她前進(jìn)。要是豎起耳朵,她還能聽到魯佩特在灌木叢里的動靜。不過,要是她全神貫注于船的起伏,一種微微的、隱隱的起伏,那么她會覺得周遭已是萬籟俱寂”(愛麗絲·門羅,2013: 75)。門羅省略了結(jié)尾,沒有給出固定的結(jié)局,這種留白不僅打破了傳統(tǒng)小說固定結(jié)尾的限制,同時還將結(jié)尾的設(shè)定權(quán)利留給了讀者:一方面,“陷進(jìn)泥中”之類的表述似乎暗示著“死亡”與“無望”,另一方面,魯佩特短暫的消失使得伊內(nèi)德的意識處于中心并對周圍的一切進(jìn)行控制與感知。這種門羅式的結(jié)尾創(chuàng)造出一種時間停滯的超驗感,同時也給出了多種可能性,讀者可能會認(rèn)為伊內(nèi)德在“無望”中驗證奎因夫人的話語,也可能會認(rèn)為伊內(nèi)德從此放棄驗證奎因夫人的話語,而選擇與魯佩特一起生活……結(jié)尾的留白,讓讀者有足夠的空間對小說進(jìn)行回顧與反思,讀者甚至可能為了發(fā)現(xiàn)一些沒有注意到的細(xì)節(jié)再重新看一遍小說,從而找到符合故事發(fā)展的結(jié)尾。門羅式的小說結(jié)尾不僅給讀者留下可以無限遐想的空間,同時也有力地推動了讀者要進(jìn)行重新整合信息和時間的行動,為讀者的理解和反思提供了可能性。
在整個小說中,充斥著各種謊言與真實(shí),對讀者的閱讀構(gòu)成了挑戰(zhàn)。讀者要想理解小說的內(nèi)容,在閱讀的時候就必須融入主觀的思考,這無疑激發(fā)了讀者的參與意識和反思。在整部短篇小說中,敘事時間的斷裂、跳躍與銜接看似偶然而隨意,但實(shí)際上卻有著嚴(yán)密的組織結(jié)構(gòu),是逐步生成的:“每一個行為都會產(chǎn)生連鎖反應(yīng),將敘事推向令人驚訝的結(jié)局,在回顧這個結(jié)局時,它似乎是必然發(fā)生的”(劉文,2014: 9)。但門羅小說敘事時間的安排既不同于意識流小說中敘事時間隨著主人公的心理變化而變化,也不同于傳統(tǒng)小說中敘事時間大多只是按照線性時間的發(fā)展而生成,門羅筆下的敘事時間是在讀者的參與中逐步生成的,門羅融合了意識流小說心理時間與傳統(tǒng)小說線性時間的特點(diǎn),將敘事時間打亂重組,讀者可以根據(jù)自己的閱讀經(jīng)驗,對敘事時間進(jìn)行重新把握,對現(xiàn)實(shí)進(jìn)行反思。
5. 結(jié)語
門羅在短篇小說《好女人的愛情》中,巧妙地將傳統(tǒng)線性敘事時間與意識流小說敘事時間相結(jié)合,將故事剪碎為幾個片斷,又重新進(jìn)行組合,徹底打亂了故事時間,突破了時間的“桎梏”,充分地體現(xiàn)了敘事時間的錯綜復(fù)雜性。在門羅的作品中,時間不是一維線性的,而是多維變化的,時間也不是機(jī)械的,而是富有生命的有機(jī)體,門羅將時間進(jìn)行重新組合,讓當(dāng)下的事件與過去的事件結(jié)合在一起,給予讀者想象的空間,讓讀者有機(jī)會參與文本創(chuàng)作,給人一種全新的思考。敘事時間也只有在讀者的參與下才更加富有意義,錯綜復(fù)雜的敘事時間也最大化地激起了讀者的好奇心,引發(fā)讀者的參與意識。此外,在每個敘事片斷中,門羅又使得故事情節(jié)在時間上斷裂、跳躍與銜接,令原本緊張的故事失去了緊張性,緩緩敘來,從而突出了小說的審美藝術(shù)。門羅這樣安排敘事時間主要是為了給讀者留有參與的空間,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斷融入主觀的思考,對現(xiàn)實(shí)進(jìn)行反思,而不只是被動地接受故事。《好女人的愛情》中,敘事時間的處理,突破了傳統(tǒng)時間的桎梏,重組了敘事時間,打碎了故事材料的硬度,激起了讀者的參與意識和對現(xiàn)實(shí)的反思,賦予小說全新的價值。
參考文獻(xiàn):
[1] Beran, C. 2000.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 Study of Alice. Munro’s Fiction[J]. Social Science Journal, (3): 329-345.
[2] Duncan, I. 2011. Alice Munro’s Narrative Art[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3] 愛麗絲·門羅.2013.殷杲譯.好女人的愛情[M].南京:譯林出版社.
[4] 劉文.2014.神秘、寓言與頓悟--愛麗絲·門羅小說研究[M].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
[5] 陸麗霞.2012.論《務(wù)虛筆記》的敘事時間策略[J].文藝?yán)碚?(09):64-69.
[6] 馬大康.2008.文學(xué)時間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
[7] 徐岱.2010.小說敘事學(xué)[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
[8] 張磊.2014.崛起的女性聲音——愛麗絲·門羅小說研究[M].北京:中國財富出版社.
[9] 周怡.2014.愛麗絲·門羅與短篇小說藝術(shù)[J].外國文學(xué),(05):62-73.
[10] 伊麗莎白·鮑溫.1995.小說家的技巧[A].呂同六編.20世紀(jì)世界小說理論經(jīng)典上卷[C].北京:華夏出版社.
Breaking the Shackle of Time: Analysis of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Alice Munro’s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Abstract:Alice Munro is good at dealing with narrative time in her short stories, which makes in her stories break the shackle of traditional linear time so as to show the magic of the plain stories in the mixed narrative time. With the help of the strategy of dealing time, readers could have opportunities to take part in the creation of short stories. This paper aims to take The Love of A Good Woman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fracture, jump, cohesion and ellipsis of time in this short stories with the method of close reading. Combined with readers’ participation, stories can be produced in the fragmentary time. Munro’s narrative strategies not only stimulate readers’ curiosity, but also arise readers’ strong sense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reflection of reality.
Key Words:narrative time; shackle; reader; participation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891(2016)02-0075-05
作者簡介:丁蔓,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學(xué)哲學(xué)、詮釋學(xué)。王喬,碩士生;研究方向:文學(xué)理論
通訊地址:116024 遼寧省大連市甘井子區(qū) 大連理工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