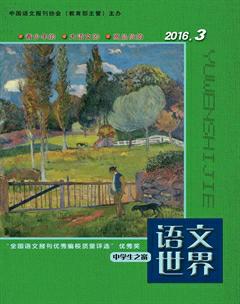春 望
洪忠佩
去游汀村的石板路是沿著溪邊的,連著古老的九間橋。朱熹當年站在九間橋的橋亭里,汀水溪畔綠蔭如蓋粉墻黛瓦的村莊是否隱約可見呢?婺源春天的景象生發得快,激蕩、酣暢,山野田地一天變一個模樣。之所以選擇一個春意盎然的日子從九間橋走進游汀,我是想與朱熹837年前去拜訪張敦頤的日子有個重合。然而,游汀村一路上夾雜著電線桿、蔬菜大棚的田地,自然要比朱熹去的時候少了一份純粹。朱熹少年得志,十九歲(紹興庚午年,即一一五〇年)考取進士后,便回到婺源故里省親祭祖。他此次去游汀,完全是一次私訪——答謝張敦頤代贖祖田。
張敦頤的家在游汀村,他是紹興戊午年(一一三八年)從九間橋離開村莊考中的進士,年齡比朱熹要長三十多歲。張敦頤在劍州(福建南平)做官,與朱熹的父親朱松關系友好,常有來往。朱松離開婺源去福建時,因為家境困難,不得不將祖田進行典當,以籌措搬家的費用。朱松去世后,張敦頤回到婺源,出資把朱松典當出去的祖田贖了回來,并寫信告訴了朱熹。“建炎庚戌文公生焉。同郡張侯敦頤教授于劍,邀與還徽。而吏部(指朱松)之來閩,質以先業百畝以為資,歸則無以為食也。張侯請為贖之,計十年之入,可以當其直,而后以田歸朱氏。”(元初虞集《朱氏家廟復田記》)當時,朱熹年少沒有成行。這次去游汀,朱熹是要面謝張敦頤,并將贖回的祖田交付族人,租田的收入用于祖墓祭掃和修繕。百畝祖田的贖金,對于剛剛考中進士的朱熹,應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吧。朱熹當時的心情是比較復雜的,甚至有些沉郁,因為,從張敦頤贖回祖田契約的那天起,到他上門答謝已是六年后了。
近三十米長的九間橋,始建于宋代,石拱、木橋亭,歷史上經過多次修繕,最近的一次維修已是二十多年前。九間橋下,汀水溪緩緩而淌。汀水溪的外圍,便是桐坑畈與連綿的山巒。溪不闊,但澄澈,面對一溪的清幽,我想游汀村名的由來,與這清溪是有關聯的。從字義上看,“汀”的意思就是水邊的平地。從唐代建村開始,游汀就離不開汀水的滋養,地面的平坦、闊大,有“四門”和“六村”(四門即方、胡、張、許四大姓,而六村則指新宅、正塢、洪村、塘下、北樓、焦園),讓這里曾經繁棲“千煙之村”。在游汀村,張敦頤與其兄長張敦實(紹興乙卯年即一一三五年進士)有“雙賢”之譽,他們留有許多舊事美談,卻沒有留下一宅一地。盡管,上世紀70年代在游汀張敦頤的墓地出土了青花瓷蓋罐、壽山石手鐲、硯臺等文物精品,仿佛游汀與張敦頤之間卻隔著一重荒蕪……山邊一樹樹燦爛如雪的野櫻桃花,點綴在蜿蜒起伏的綠色中,一畈畈流金涌動的油菜花,向著村莊的方向鋪展。我想,朱熹在溪水潺潺的游汀村貼近一片春色時,將聞到怎樣輕盈的芬芳?朱熹與張敦頤都是親山愛水的人,如果他們在一起不吟詩賦詞,似乎不合情理,遺憾的是直至今天,我都沒有讀到他們為游汀村寫下的詩賦辭章。而朱熹與張敦頤,都是婺源文脈的源流,他們把一生的認知、學識、思想,都寫進了自己的著作里。在婺源,古代著書最多當數朱熹(收入《四庫全書》四十部),每一部都是理學的浸潤與回聲,張敦頤(收入《四庫全書》三十九部)緊隨其后,他的史地雜記——《六朝事跡編類》,上溯吳越,下至唐宋,有著較高的存史價值。或許,對于游汀村與村人的記憶,宋朝的人和事都太遙遠了,都成了村莊隱匿的密碼。朱熹與張敦頤在游汀村的雅集,是被時光帶走了嗎?
“綠漲平湖水,朱欄跨小橋。舞雩千載事,歷歷在今朝。”朱熹的《詠歸橋》,應是他辭別張敦頤歸途的吟誦吧。在朱熹人生的旅程里,他只兩次回到家鄉婺源。朱熹與婺源的有關勝跡標志是朱氏一世祖墓、虹井、廉泉、文公山、文廟、書院,而他去游汀拜訪張敦頤,是表達一份藏在心中的情感。春天里,我曾幻想著穿越到他們生活的宋代,去感受張敦頤的氣度和朱熹的真誠,還有纏繞一起的故土情結。然而,隔著八百多年的時空,我在游汀的九間橋橋頭與他們一襲長衫的背影擦肩而過。
“故家歸來云樹長,向來辛苦夢家鄉。”“此夕情無限,故園何日歸?”僑寓他鄉的朱熹,內心永遠有一份情感溫潤著,那就是家園鄉土。婺源的河流與河流上的橋,都在寧靜地等待,等待一位游子魂歸故里。
- 語文世界(初中版)的其它文章
- 易寫錯字辨析(十一)
- 填字游戲
- 閱讀訓練
- 媒體用語中常見語病實例解析(一)
- 忠貞還是犧牲
- 原來要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