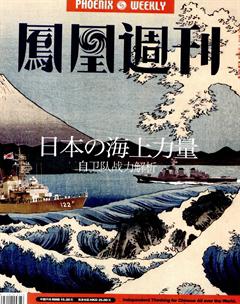新土改突圍:農地確權年底沖刺
席志剛


“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大上,涉及農村土地的征地制度改革首次寫進黨代會報。
早在2010年初,針對農村集體土地產權不明以及政府強制征地引發的種種問題,中共中央“一號文件”就提出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等確權登記頒證工作,要求用3年時間完成,為下一步土地流轉和征地改革提供法律基礎。
今年是中央要求完成農地確權的最后一年。年初國務院“一號文件”為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發證設定了“2012年12月前完成”的最后期限;3月初“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再次強調,認真搞好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制定出臺《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是2012年的主要任務之一。
然而,和當局預期相比,農地確權工作的實際進展并不樂觀。國土資源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9月底,全國集體土地所有權發證率僅為75%,有7省的土地確權登記發證率不足50%;即便是“先行先試”走在前列的四川省,也只有70%縣區完成集體土地確權登記。
年底沖刺
時間緊迫,農地確權現在到了必須全力以赴的沖刺階段,牽頭的國土資源部壓力陡增。
去年5月,國土資源部、財政部、農業部就農地確權聯合發文,要求到2012年底,全國范圍內的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證確認到位,做到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全覆蓋。
農村土地確權登記工作由此在全國悄然推開,然而進展甚為遲緩,不盡人意。今年7月中下旬,國土資源部聯合財政部、農業部成立督導組,相繼對內蒙古、江西、云南、陜西、甘肅、新疆等省(區、市)展開督導,督促地方政府加快為農村集體土地“確切頒證”;要求各地在確保操作規范的情況下,年底前務必完成農村集體土地確權登記發證任務。
為確保任務如期完成,國土資源部再次對地方施壓,重申去年5月三部門聯合規定的懲罰措施——凡是到2012年年底未按時完成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登記發證工作的,暫停農村集體土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及征地審批,農村土地整治項目不予立項。
土地儲備是地方財政收入的命根子,一旦停下來,地方財政立馬吃緊。對于地方政府而言,這項規定之嚴厲,前所未有。然而農地確權進展遲緩,確有不得已的原因,由于其所牽涉到的方方面面,以及確權過程中翻出來的大量歷史遺留問題,實非朝夕之間,能夠畢其功于—役。
當前農地確權涉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農用地承包經營權和農民宅基地使用權等四類產權。上世紀40年代末期中共建政之初,曾發起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實行“耕者有其田”;在其后興起的人民公社運動中,農村土地又轉為集體所有和集體經營;1980年代以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推行,人民公社體制瓦解,農村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產權制度更趨復雜。
60多年制度變遷所積累下的大量矛盾和遺留問題,都要在這次農地確權中——化解,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長周其仁坦言,年內完成全國農地的確權,“這個要求我看有一點理想化,做不到。”他以成都為例,2003年開始試驗農地確權,原來設想一兩年就可以結束,結果搞了好多年,遠遠超過預期,過程非常復雜。
成都經驗
周其仁長期跟蹤觀察成都在農地確權方面的試點和進展。他注意到,由于市場經濟下土地資源的價值越來越凸顯,巨大的經濟利益使得人們在確權過程中“寸土必爭”,引發大量土地權屬爭議。
在農地產權制度改革的探索中,成都走在了前面,2003年開始自發試驗,2009年獲國務院批準進行城鄉統籌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其近三年的試點經驗被稱為“成都模式”。在周其仁眼中,成都模式其實就是三句話:確權是基礎,流轉是核心,配套是關鍵。
成都剛開始土地確權的時候,問題千頭萬緒:村民外出打工,承包地由鄉鄰耕種多年,現在地算誰的?村集體成員生老病死、婚喪嫁娶帶來的土地增減問題糾紛不斷,如何處置?以前承包地兩年—小調、三年一大調,現在要確權了,還要“長久不變”,如何擺平?農村私搭亂建現象非常普遍,柴禾堆、牲口棚、豬圈相互占用,違章如何定性,確權如何劃界?各種意想不到的麻煩紛至沓來,—度讓工作人員瞠目結舌,束手無策。
對這些實際問題,各地因鄉土人情、鄉規村約不同,解決的方式也各異。成都模式的一條主要經驗是,由土地確權逼出了村莊治理結構的改革,產生了議事會制度——確權過程中的所有問題都提交村議事會,請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公道。
周其仁在成都雙流縣瓦窯村看到村民解決爭議的一個典型案例。娘胎里的孩子是否具有確權資格,村民各執一辭,爭議不下,村議事會也拿不出個方案。為此,他們專門請來婦產專家,從醫學角度進行解釋,最后確認,懷孕7個月以上的胎兒才能算一個生命。議事會據此拿出了一套富有人情味的方案:胎兒沒有資格參與承包經營權的確權,但孩子生出來就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下一步土地流轉有經濟收入效益的時候,可以給孩子分一份。
這個折中方案最后被各方認可接受,確權得以繼續推進。雙流農戶最后拿到手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標明了地塊的實測位置、邊界,配有坐標以及示意圖,權屬關系清晰明確,形成了一個可追溯的產權系統,他們自用的宅基地,獲得《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證》,《土地所有權證》則發給村集體經濟組織。
在確權的基礎上,成都提出要“還權賦能”,不但把農村集體土地的使用權經營權還給農民,而且要把由此派生出來的轉讓權也還給農民,賦予農民以更為全面和多樣的權能。“政府用其權威先幫老百姓確權。如果產權不明,土地流轉的收益最終恐怕落不到村民頭上。”在周其仁眼中,成都的可取之處在于把確權放在了流轉之前,這為未來的流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法律邊界
成都經驗是否要在全國推廣,曾一度被外界寄予厚望。不過,官方表態一向頗為謹慎。據知情人透露,決策層在給成都下放“先行先試”試點權的同時,對試點所應觸及的制度邊界仍感拿捏不準,要求改革試點做到“全面探索、局部試點、封閉運行、結果可控”。
周其仁認為,成都最引人注目的經驗就是確權,這也是當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第一要務。然而在國土資源部看來,成都經驗的可總結性仍顯不足。他們將成都經驗與福建的“三到位”、河南鄭東新區的“和諧拆遷”、重慶的“地票交易”制度,以及廣東的“三舊改造”等地方探索放到一起,認為其主要目標在于增加土地指標供給、繞開18億耕地紅線,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方面并沒有實質性的創新。
今年2月的全國國土資源工作會議上,國土資源部部長、國家土地總督察徐紹史提到,今年國土資源管理改革最重要的任務是,組織開展各類改革探索,并對各地試點經驗進行總結、提煉和規范。據他透露,在總結成都經驗的基礎上,國土資源部年內將新設一批土地制度改革試點,除了土地確權外,圍繞社會高度關注的征地拆遷問題、經營性集體建設用地模式進行試點。
北京唐家嶺試點主要探索集體建設用地建租賃房,由當地村民組成土地股份制合作社,取代以往由村委會代表的機制,作為完成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后的產權主體。國土資源部在下放給北京市“先行先試”試點權時,口頭要求北京“不要走得太快”。
周其仁表示,決策層希望通過“多地試點,總結經驗”,穩步推進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他們這種不宜“操之過急”的心態,可能是顧慮到在建立健全集體建設用地的收益分配機制以前,如果貿然推動土地流轉,會產生更大的經濟、法律和社會問題。
多地試點的另一著力點是尋求法律突破。徐紹史曾強調,探索創新總體上應該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內進行,需要突破現行法律的,應該履行申報程序。這意味著土地制度改革在探索中已經觸碰到現行法律的邊界。
迄今為止,在土地確權方面,中國還沒有一部完備的法律,有關土地權利的法律條款散見于《憲法》《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及各種土地法規和政策規定中。
很多法律條款需要重新加以討論。比如,是不是所有的城市土地都要歸國家所有?國家如何行使所有權?集體土地要不要有流轉權?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立法加以解釋固化。
目前,國務院法制辦正在制訂《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土地管理法》也在緊鑼密鼓修訂中,有望明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不過,周其仁并不贊成全面重修《土地管理法》和修改關于“城市土地屬于國家”的憲法準則。圍繞土地改革而來的利益格局的調整,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嚴謹應對,任何“急就章”式的變革都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利益主體的行為扭曲,陷入土地資源配置的嚴重失衡。他建議在已有的體制變化的基礎上,“吸收城市土地使用權市場化的歷史經驗,逐步、漸進地完成土地制度的根本變遷。”
事實上,中國農村土地承包制改革和城市土地出讓制改革,已經奠定了土地轉讓權的基礎。目前尚未解決的是上述兩個轉讓之間,即農用土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這一關鍵環節,癥結則在于現存體制仍然把政府強制征地視為農地轉用的唯一合法途徑。
征地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征地條例》,其條文目前已基本成型,但相關內容與現行《土地管理法》存在“與上位法沖突”的尷尬,不能單獨頒布,只能等《土地管理法》的修訂完成后配套實施,而《土地管理法》的修訂內容明年“兩會”時才提交討論。
“既然試點,就應該有些突破,有矛盾和抵觸才會觸及法律邊界。”周其仁建議,在《土地管理法》完成修訂之前,可以授權試點地區試行一些與現行土地法律不相一致的辦法,包括提高征地補償水平、開放城市一級土地市場,允許集體土地或農戶承包地進入土地市場,土地市場建設和管理等。
在試點地區“先行先試”提高征地補償水平時,周其仁認為對近年征地補償過低的農民,應該做出某種形式的補充補償,以緩解因補償相差懸殊而引發的不滿情緒,至于具體的補償方式,“既可以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賣地所得中拿出一定份額直接補償,也可以考慮以教育券或醫療券的形式向農戶發放。”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要對此前的征地進行全面補償。“太遠的事沒法追訴,只能當作發展過程中必須承擔的社會成本。”周其仁說,大量歷史遺留問題積攢的矛盾越來越多,越來越尖銳,需要政府理智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