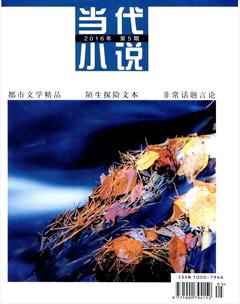在荒蕪與遺忘之間
劉穎穎
近年來,農村一直處在荒蕪與遺忘之間,由于快速城鎮化的沖擊,山清水秀也留不住一批批走出鄉村、走向世界、尋求發展的年輕人。農村不斷地被漠視、被遺棄,日漸沒落蕪雜。身在其中的農民,面臨著由此產生的種種問題卻無力解決,只能扼腕嘆息。對于這樣的現狀,盡管相當多的寫作者把目光轉向城市題材寫作,我們仍舊能夠看到一部分作家,不甘心逃跑或沉默,他們的觀察、思考和呈現,都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
周如鋼發表在《福建文學》2016年第2期的小說《盤根村的偶像》以一種由外到內的敘事視角,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昔日英勇抗日、而今蕪雜衰落的盤根村。小說敘事焦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鄉村衰落帶來的婦女情感缺失,面子工程上的英雄崇拜。這兩條主線并行不悖地穿梭于作品之中,揭示出盤根村的落后不僅僅表現在青壯年的流失、農村的窮困,還在于由此引發的婦女生理欲望無法滿足、英雄后代正大光明與村中婦女輪流發生關系,村中老人對此現狀難以容忍,卻又無力改變,以及領導對幫扶單位的敷衍了事等問題。首先是留守婦女的情感缺失問題。小說開篇用一種輕快明亮激昂的筆調講述豪氣干云的盤根傳奇,描寫七十多歲的連春外婆回旋抗日的英勇事跡,敘述陳大彪不懼生死,與鬼子在番薯洞同歸于盡的血性歷史;隨后通過番薯洞引出盤根村如今的衰落景象:僅有十一戶人家、滿眼盡是無人開墾的荒地,“番薯洞是曾經的傳奇,對于現在來說,那也是噱頭的一種吧”。到此周如鋼一直是用一種外人的眼光來描述盤根村,記者“我”是一個游客身份,隨著我與大嘴齙牙陳大寶、陳老伯、蘭花等人物的不斷接觸,對兩個女人吵架的不斷了解和深思,記者“我”才逐漸轉變為一個村民身份,深入盤根村內部,發現盤根村在英雄傳奇掩蓋下劣跡斑斑的真實面目。兩個女人粗俗的吵架聲中全部都是與男女生殖器官有關的字眼,一方面是由于農村婦女自身素質稍有欠缺,另一方面是婦女情感缺失的問題,性欲的渴求成了盤根村婦女生活的主要部分,因此她們能想到的,也是在她們心中最為看重的,就是如小狗小貓般那點男女性事。現在盤根村的婦女與連春外婆形成鮮明的對比,往日的巾幗英雄一去不復返,留下的只是落寞、潑辣、渴求肉體滿足的留守婦女。這與貞潔并沒有太大關系,正如村長所言“一年到頭男人不回家,或者幾年不回家,一年拿個萬把塊回來又有什么用”,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陳大寶彌補了盤根村九個年輕婦女生理上的需求,成為她們釋放內心情欲的工具。第二點是面子工程上的英雄崇拜問題,如果說昔日的連春外婆已不再,只留下丟人現眼的留守婦女,那么曾經豪情萬丈英勇抗戰的陳大彪也早已被人淡忘,只留下英雄后代陳大寶好吃懶惰、游戲婦女。領導將陳大寶視為英雄后代,多加照顧;村長苦心維護著盤根村在外界的傳奇英雄形象,這一切都是鏡花水月,仿佛有陳大寶在就有英雄陳大彪的存在,這是一種面子上的英雄主義、是錯誤的英雄崇拜。在村長終于擺脫英雄崇拜,痛下決心要驅逐陳大寶時,駐村干部出現了——“誰要弄陳大寶啊?”這是社會的現狀,英雄主義不再是一個正面的積極向上的旗幟,而成了一種噱頭,一種擺設,一種障礙。小說的結尾令我們反思,“領導說,咱市里這樣的村子多的是,放眼全國,更是多如牛毛”,明知多如牛毛卻不想著解決只想著敷衍,這就是現實。文中的“我”說:“盤根村真的要好好寫一寫了,再不能這樣去敷衍了。可是,我不能寫,我也不該寫,我也沒想好到底要怎么寫。我該怎么辦呢?”盤根村的偶像已無從談起,只剩下矮丑窮的英雄后代,年老體弱的老年人,情感缺失的婦女,而這一切都在報紙上敷衍了事的宣傳中被忽略了。
黃金明發表在《作品》2016年第2期的小說《人樹》以“我”的自述為主,老樟樹作為隱含的傾聽者,以蒼涼、無奈、超然的語調,講述了寡婦母親坎坷的一生、城市化進程沖擊下大孫村的悲涼,以及老樟樹終被砍伐的命運。母親吳彩霞有過姘頭、穿過破鞋、受過批斗,也熬到平反,她說:“一個寡婦在這個世界上生存太艱難了。你慢慢就會懂的。”每一個留守婦女都有一段難言之隱,人們只在乎女性完成了多少義務,卻從不過問她們缺少了多少權利。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成為主體,“很少有青壯年留守在村莊,連孩子也跟著父母外出讀書去了”,吳彩霞辭世那年(2005),“村中只剩下十幾位老人和幾個孩子”,“在之后不到十年時間里,那些孩子在成長并遠走高飛(或被父母接走),而年邁的土狗、蘭花等老人也相繼入土”,“從2015年起,村子里除了我,已經沒有活著的人了”,“鄉村山野無人侍弄,早已成了名副其實的荒村野地了”,村莊的大小路徑也早已面目全非。這一切都是現在農村的現狀,有的農村只剩下一個外殼,城鎮化建設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沖天的高樓大廈閑置著,外出打工的農民拼盡一輩子也買不上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可是,即使這樣也沒有人愿意留在農村,沒有人愿意花費幾年的精力去掙點可能有回報的錢,難道農村就象征著落后,城鎮就象征著進步么?農村和城鎮并不是對立的兩極,中國自古就是農業大國,崇尚小農經濟,農村中蘊含相當多的中國印記,當全部的農村衰敗不堪、無人問津,中國的特色又在哪里?農村的消失不一定帶來經濟的進步,但一定會導致中國許多的傳統習俗——祭拜的香火屋、掃墓等的日漸消失,傳承五千年的文化就在城鎮化的沖擊中以落后、繁瑣的罪名被改革了,傳統文化帶給人們的凝聚精神在改革中漸漸失去意義。活了三百年的香樟樹在“我”臨死前也被自稱大孫村的后人挖走賣錢了,“這棵樹是村莊的靈魂,砍了它村子就魂飛魄散了——”,“這可是保存了村子的記憶,你們日后還想回來,就一點記憶都沒有了——”,香樟樹的伐走,標志著整個村莊的徹底消失,當一個村莊的靈魂和記憶都被抹掉的時候,這個村莊就徹底成為一個棄村。每一段記憶都烙印著中國千百年來的發展軌跡,為了千篇一律的城鎮化建設而毀掉那份不可重來、獨一無二的記憶,無疑,在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卻得不償失。
本欄責任編輯: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