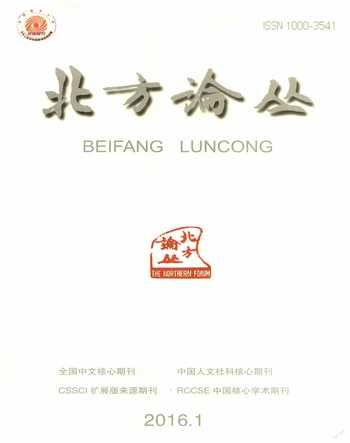創傷的言說:遲子建小說中創傷型人格探究
張良叢
[摘 要]創傷經驗的言說是遲子建小說塑造人物的一個重要主題,可以從中透視出其小說的審美價值。遲子建小說的創傷型人格分為個體創傷、集體創傷和文化創傷;與之相對應,也形成對創傷修復的三種方式。從個體創傷與審美修復、集體創傷與共同記憶塑造、文化創傷與文化反思等三個角度對遲子建小說的創傷型人格進行闡釋,全面呈現出遲子建小說創傷維度具有的深層意蘊。在創傷型人格的塑造中,遲子建對社會、文化等多層面的經驗感悟油然而發,也體現出遲子建小說以小見大的寫作特點。遲子建小說創傷型人物的塑造,秉持著“憂傷而不絕望”的創作宗旨,每個創傷人物最后都會獲得創傷的修復,從而讓人們在悲傷中看到生活的希望。
[關鍵詞]遲子建;創傷經驗;文化反思
[中圖分類號]I2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6)01-0050-05
Abstract: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s in Chi Zijians novel shapes the character of an important topic. From the individual trauma and aesthetic restoration, collective trauma and collective memory building, cultural trauma and Culture Reflection three respects,the text analyzes Chi Zijian trauma personality. thus showing a Chi Zijians aesthetic value and deep meaning. The traumatic characters in Chi Zijians novels, which is based on the “sad and not desperate” creation principle, each of the trauma characters would repair, so that people can see the hope of life in sorrow.
Key words: Chi Zijian;traumatic experience;cultural reflection
創傷不僅是一個病理學的概念,更是個文化概念。在《沉默的經驗》(Unclamed Experience,1996)中, 美國學者凱西·卡魯斯提出了“創傷”理論(trauma theory)。她認為,“創傷”是人們經歷了某一突發性或災難性事件在內心造成的陰影和傷害。心理創傷具有滯后性,而且會反復出現無法控制的幻覺。創傷理論把不同的創傷者群體作為整體來考察,將他們的創傷與社會政治期待、文化心理、社會結構等因素聯系在一起,從而揭示出受害的身體背后蘊含的各種社會力量和制約因素。在現實生活中,心理創傷往往以個體經驗表達,很難呈現公共空間的言說。文學作品恰恰為創傷經驗的言說打開了一扇窗。在遲子建的小說敘述中,我們發現有一類特殊的人物,經常浮現在讀者的面前,這就是有著創傷經歷的人物。遲子建從個體創傷,到集體創傷,再到文化創傷等多個層面描繪了形形色色的人物,通過小說講述各色人物的創傷故事,使小說具有特殊韻味。探析遲子建小說中的創傷型人物,可以更好地把握其小說的內在結構和深層內蘊。
一、個體創傷與審美修復
個體創傷主要是個人的生活歷程中經歷過某些事情,從而導致某種心理創傷。這種創傷總是與某種情感緊密聯系。“病人在僥幸逃脫死亡、突發事故或酷刑等恐怖經歷后會患上種種神經官能癥”[1](p186)。普通人也是這樣,在經歷這些恐怖經歷后也會形成一些特殊的心理經驗。創傷經驗首先來源于個體經歷,伴隨著過去的情感性記憶。在遲子建的小說中,我們發現大批有著個體創傷的人物形象,他們在其長期的生活經歷中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打擊,在內心深處壓抑大量的心理負能量,從而呈現出奇異的人格形態。心理創傷需要修復,如果沒有完成修復,會產生病態人格或神經官能癥。遲子建小說也對個體創傷的修復方式形成了自己的思考,顯示出特有的思想深度。
個體創傷的千姿百態,構成一幅人生百態圖。人生百態,各有各自的創傷,都深入到內心深處。個體創傷有的來源于個體的人生經歷,尤其是早期生活經歷,這種創傷直接貫穿其一生。《樹下》中的七斗就遭受了母親死亡、父親離開和死亡、姨媽冷酷、被姨夫強奸、兒子死亡。這一次次的心理創傷對她形成一種穿透,似乎世界上所有的悲傷都降落在她身上。這種悲慘境遇很容易磨掉生存的希望,七斗一次次徘徊在生死邊緣。她之所以能活下去,因為有一段馬蹄聲一直回響在頭腦中。《鬼魅丹青》中的羅郁,他的心理創傷來源于父親因強奸罪入獄,母親自殺,再加上周圍男同學的侮辱,女同學的躲避。他只能靠消除欲望來獲得心靈解放。《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蔣百嫂就是一個典型。她的丈夫蔣百礦難死亡,官員為了保住烏紗帽,瞞報了蔣百死亡,以錢彌補了蔣百嫂,自此蔣百只能躺在自家的冰柜里。對蔣百嫂而言,本來蔣百的死亡已經是可怕的創傷了,而日夜伴隨著蔣百尸首,痛苦無法對人言說,更加深了她的傷痛,使她深陷創傷中無法自拔。由此,蔣百嫂呈現出千奇百怪的行為。與不同的男人亂搞、喝酒買醉耍酒瘋、聽悲苦的“喪曲”等行為都是這種創傷無法表達的表征。這種深重的傷痛,只能以奇異的方式表現,才能得到修復。
遲子建筆下創傷的描述只是一個文學問題,而創傷的修復是遲子建小說最具有價值的部分,體現出作者對創傷的深刻反思。創傷的修復是研究遲子建小說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美學問題。創傷的修復有多種方式,如審美幻象的構造、創傷的敘述、信仰的建構,通過文學、藝術、宗教等形態達到對欲望對象的填充。對此,王杰先生指出:“對于個體來說,創傷的直接結果是個體欲望對象的空缺。欲望的投射對象由于真實的存在的缺失而轉向以替代性的象征物來充任,個體的內在欲望由于無法完全對象化而走向‘焦慮和 ‘浮躁,由此產生出對審美幻象的強烈需要。”[2](p95)創傷伴隨著痛苦的恐懼性情感體驗,這些往往壓抑在人的內心深處,會隨著語境的契合被喚醒,引發早期的創傷記憶,從而和現有的創傷語境構成一種綜合征。
創傷經驗建構起審美幻象,依靠幻象給創傷經驗的平復提供了重要前提。《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的蔣百嫂和陳紹純創傷的修復就是在審美幻象中完成的。蔣百嫂創傷的修復除了非理性的性欲釋放和借酒澆愁,聽民歌是最為重要的修復方式。“在烏塘,最愛聽他歌的就是蔣百嫂,蔣百失蹤后,蔣百嫂特別愛聽他的歌聲。她從不進店聽,而是像狗一樣蹲伏在畫店外,貼著門縫聽。她來聽歌,都是在晚上酒醉之后。有兩回他夜晚唱完了推門,想出去看看月亮,結果發現蔣百嫂依偎在水泥臺階前流淚”[3](p36)。陳紹純的歌聲觸動了蔣百嫂早期心靈深處的創傷,歌聲的悲涼正是其構造審美幻象的媒介,在審美幻象中,蔣百嫂獲得心理創傷的暫時解脫和修復。而陳紹純唱悲調為主的民歌也是因為一次死亡的經歷和“文革”被迫害,而唱民歌是他構造審美幻象支撐他活下去的動力。在這個意義上,蔣百嫂和陳紹純同是天涯淪落人,都是在民歌構造的審美幻象中獲得了解脫。同樣,《樹下》的七斗也是借助于內心構造的一段馬蹄聲來修復心理創傷的。實際上,七斗和白馬上的鄂倫春小伙子只見過幾次面,不是很熟悉。對七斗而言,白馬和鄂倫春小伙子并不是一個具體的事物,而是七斗在內心深處塑造出的一個意象,象征著七斗對自由的渴望。這其實是七斗內心的一個幻象。而這個幻象就一直伴隨著七斗,為她撐起生活的希望。
創傷的敘述把創傷變成一個表述的對象,也是非常有效的修復方式。創傷理論認為,創傷者故事的講述首先能保護自我免受過去幽靈的干擾。當然,它不僅僅是個人行為,也是一種集體行為。創傷經歷需要有聽眾、有人見證,通過非直接的、非常規的方式講述出來的經歷,才能分享共有的經驗。敘述者恰恰是在分享公共的創傷經驗,才把個體創傷融合到集體創傷中,個體經驗轉變為集體經驗,降低了個體創傷的濃度,才獲得了心靈的修復。《世界上的所有夜晚》小說中的敘述者“我”的解脫,似乎是在哀傷對比中獲得了解放,其實不然,她的創傷的修復是來自自我創傷被不斷地引起,從而不斷復述。再深入一步說,這里的“我”難道不正是小說作者個體情感經歷的文學敘述嗎?《晚安玫瑰》中的趙小娥,在精神病恢復之后,也是依靠敘述個人的故事,慢慢修復個人的創傷。在這種文學敘述中,創傷得到審美修復,就像一只湖藍色的蝴蝶輕飄飄地飛到遙遠的天邊。
除了審美幻象和敘述的方式,遲子建小說中還提到一種重要的創傷修復方式,這就是信仰。信仰最為集中的文化形態就是宗教。宗教之所以能夠成為人們修復自我的方式,很多時候在于她能夠提供一個想象空間。在這個空間中,有一個神靈在傾聽傾訴者的內心。神靈給傾訴者指出一條康莊大道,給生命的黑暗點上一盞明燈。《晚安玫瑰》中的吉蓮娜在被繼父出賣給日本人迷奸之后,毒死繼父。被侮辱和弒父使得吉蓮娜心靈遭到無限的創傷。如果沒有一種很好的修復方式,她無法獲得生存的理由。吉蓮娜找到了她們的民族宗教猶太教,在神的面前懺悔,洗脫了自身的罪惡。這種修復方式,在文學的表述中,也成為一個審美想象的構造,彼岸世界成為一個審美的象征物。
二、集體創傷與共同記憶的塑造
遲子建小說中還出現了很多普遍性創傷,我們可以稱之為集體創傷。集體性創傷多是自然災害、社會動蕩、社會變革等公共原因導致的,通過集體創傷故事的講述,就可以從一個側面對社會的控訴和反思,從而使一個個創傷故事帶有集體的共有意義。集體創傷的講述構成了某個家族、某個階層、某個民族、某個國家創傷表征。集體創傷的講述對于構造集體記憶、塑造族群的歷史、共享集體經驗、增強集體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指向了共同的結構。當然,集體創傷與個體創傷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講述集體創傷也是通過個體的故事來完成的。近年來,遲子建在小說中塑造了自然災害造成的創傷人物,也塑造了社會動蕩,以及社會變革給人們造成的創傷,敘述了一個個創傷故事,顯示出遲子建對社會、歷史、人生的深刻體驗和反思。
集體創傷的造成,自然災害往往是一個極為普遍的根源。瘟疫、地震、雪災、水災、旱災都會給人類帶來各種各樣的災難,造成普遍的集體創傷,從而構成一個個敘述,敘述著傷痛中人的故事。遲子建的小說也對這種集體創傷進行了講述。《白雪烏鴉》就是其中的典型。小說敘述的是1910年的哈爾濱大鼠疫,通過對鼠疫中的哈爾濱老道外的民眾日常生活的講述,塑造出自然災害中的民眾面對集體創傷的人生百態。王春申在妻子和兒子死亡后,選擇了參與到鼠疫死亡者的尸體搬運中,在為社會服務中獲得了心理創傷的修復。于晴秀則是在公公、丈夫和兒子死于救災中,默默地承受了創傷。伍連德臨危受命,從整體上拯救了哈爾濱的民眾,長子長明卻死于食物中毒。這些集體創傷事件的講述其實并不是單純的講述,背后也充滿著講述者本人的思考。“我要撥開那累累的白骨,探尋深處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將那縷死亡陰影籠罩下的生機,勾勒出來”[4](p259)。遲子建講述的這個集體創傷故事,本身并不是要呈現歷史,而是在尋找創傷背后的意義。這種意義就是中華民族面對災難的崇高品格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社會動蕩不安也會造成很多悲劇人格,遲子建的小說充分表現了這類人的創傷。《偽滿洲國》中的楊浩更是一個社會動蕩的犧牲品。在災難發生之前,他有一個幸福的大家庭,爸爸、媽媽、哥哥、弟弟圍繞在他的周圍。仲秋節,他們一家五口來到了平頂山煤礦和奶奶叔嬸團圓,全家人卻遭到無妄之災,只活下了10歲的他。他所遭受的創傷也是從天而降。因抗日游擊隊襲擊了日本鬼子的采礦所,平頂山的百姓就受到了日本人遷怒,全部被屠殺。楊浩卻非常幸運地在屠殺完畢和掩埋之間醒過來逃出來。逃出來后,楊浩遭受了嚴重的心理創傷,死去的親人時常出現在眼前。從常理來推斷,一個年僅10歲的兒童在這樣一個屠殺事件中存活下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在遲子建的筆下,楊浩卻存活了下來,而且被一個老漢救回了家。這種描述到底要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很明顯,楊浩的創傷描繪,遲子建是在控訴侵略者的暴行,而且是深深控訴,讓人感到的是揳入靈魂的傷痛。創傷理論認為,創傷的修復最為有效的手段是講述,通過講述自我的創傷經歷,創傷會慢慢得到修復。而在日本人的恐怖統治之下,作為幸存者的楊浩,卻無法向任何人傾訴自己的心靈創傷,只能把傷痛深深地埋在內心深處,慢慢地舔舐自己的傷口。悲憤無處說,幼小的心靈不斷地承受創傷的折磨,這種控訴不是更加令人記憶深刻,難以忘記嗎?楊浩的創傷正是近百年來多災多難民族創傷的表征和寓言,傷痕累累無處言說,只能自我慢慢地修復。
社會變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但是如果不是按照正常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變革,同樣會給人們帶來普遍性創傷。遲子建的小說立足于中華民族的發展的百年歷史,講述了不同時期的社會變革給民眾帶來的心理創傷。在她的小說里,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幅活生生的心理圖畫。《樹下》中的有精神疾病的船長就是社會變革的犧牲品。他本來是一個森林勘探工作者,卻因為在“文革”中犯了政治問題被隔離審查,坐了7年牢,在此期間他的孩子夭折,妻子懸梁自盡。出獄后,他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精神極為不正常。很明顯,船長是因社會運動遭受了嚴重的心理創傷,他修復受傷的心靈的唯一辦法就是返回過去,在回憶中獲得心理平靜。這個回憶的載體就是一條對他有恩的狗“雪地”的第九代玄孫,他給狗講故事,愛撫狗,對狗發脾氣,其實都是在自己制造的幻象中獲得心靈平衡。而當他在眾人陰謀和冷眼中被剝奪了這個幻象后,就在被送往精神病院的途中自殺了。遲子建塑造的船長形象傳達的到底是什么呢?在“文革”的社會變動中,船長不是一個單獨的形象,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過對典型的塑造,遲子建反思了那場社會運動給中國帶來的集體創傷。
文學呈現集體創傷就是提供給每個人一次回憶,是集體思想和情感經驗的再現。“每次回憶,無論它如何個人化,即使是有關尚未表達的思想和感情的回憶,都和其他許多人擁有的一整套概念相關共生:人物、地點、日期、詞匯、語言形式,即我們作為或曾作為成員的那些社會的全部物質和規范的生活”[5](p36)。遲子建對集體創傷的描述,并不是簡單呈現一個悲傷的故事,引起讀者唏噓感嘆。集體創傷是許多人共同承受的創傷經驗,其具有共同性。共同經歷隨著時間的流逝,會漸漸地沉淀到歷史中,變成一種潛在的社會無意識。只有借助于相同情景的浮現,社會無意識才能重新進入集體意識中。遲子建對集體創傷的文學浮現恰恰起到了這個作用,激活了人們共同的經驗,恢復了共同的記憶。
三、文化創傷與文化反思
文化是族群的生活構建起來的生存方式,每個族群都在長期的歷史中形成自己特定的文化。族群成員只能在其文化中獲得身份認同,構成一種文化標志。一旦超越該文化區域,作為個體的人就面臨如何重構文化身份的問題,有可能造成文化創傷。文化創傷主要指在文化轉換過程中,個人和群體身份的喪失,而造成的心理傷害。文化創傷能影響整個群體的存在狀況。當然,文化創傷不全是負面作用的,還具有積極意義。從文化創傷中,人們可以更好地反思文化狀況和歷史,從而構建新形態的文化。對于少數族群而言,文化創傷可以喚起集體記憶,從而增強群體的凝聚力,不失為一種討伐主流社會壓迫的邊緣反抗中心的策略。在文學表征當今社會文化轉型的今天,文化創傷在當代文學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遲子建的小說提供了一個典型的個案。遲子建描述了文化沖突中的文化創傷,人們可以對本民族文化傳統、少數族群文化進行反思,從而思考什么樣的文化才是最為合適的文化,才能提供詩性生存方式。
文化沖突會帶來個體命運的轉變,造成一種心理創傷。《白雪烏鴉》中的翟芳桂本來是一個普通農家大女兒,過著平靜的生活。一天晚上她去河邊洗頭,回家的路上,知道因信仰基督教父母和妹妹遭了無妄之災被活活燒死,她已經無家可歸了。自此一系列災難陸續降臨到她的頭上。通知她災難消息的張二郎卻趁著混亂強奸了她。為了生存,她跟隨了張二郎,張二郎卻因為教堂的鐘送了小命。隨后,她到哈爾濱投靠姑姑,在姑姑死亡之后就被賣到了哈爾濱的妓院,成了妓院頭牌香芝蘭。翟芳桂的創傷完全是義和團運動排外導致的,這是一種典型的文化創傷。義和團運動以“扶清滅洋”為口號,對洋人和華人基督徒進行了暴力運動。正是這個社會事件,直接導致一個與此沒有任何關系的普通人的命運出現了轉折,遭受了無盡的痛苦。遲子建描繪的是翟芳桂的創傷,其實更是從文化上反思義和團運動排外的盲目性,從日常生活的角度反思了一個文化事件。義和團運動是一種文化沖突,是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沖突,而翟芳桂不過是這個文化沖突的犧牲品。
傳統生活方式和現代生活方式的轉換也會給人帶來文化創傷,很多人成為選擇的文化的鐘情者。《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伊蓮娜是一個踏入現代社會的,而被現代化文化弄得遍體鱗傷的人物。伊蓮娜是鄂溫克女子,她也是藝術家。她的藝術啟蒙發生在鄂溫克居住地的河邊,是跟外祖母學習巖畫開始的。自此,她就和祖居地的山水叢林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她的靈魂扎根在鄂溫克文化中。當她作為鄂溫克第一個大學生踏出叢林,走向外面的世界時,生存之路就走向了另一個方向。自此,伊蓮娜就陷入了兩難中,她每年都背著畫架回來看外祖母,“伊蓮娜在山上呆煩了,會背著她的畫返回城市。然而要不了多久,她又回來了”[6](p250)。伊蓮娜掙扎在痛苦中無法自拔,最后她辭職了,重新回歸到山林中。但是,她仍然沒有完全回歸,在創作完兩幅皮毛畫后又進城了,因為她仍然沒有找到靈魂深處真正需要什么。可見,這時的伊蓮娜雖然回歸靈魂的呼喚占了上風,但是她并沒有完全回歸,直到她看到妮浩祈雨后,才徹底貫通了內心的靈魂,受傷的心靈才開始真正地得到修復凈化。她拿起了筆開始了兩年的祈雨畫創作,畫作完成后,伊蓮娜化作一頭潔白的馴鹿,真正地把生命融入到她寄托靈魂的山水中。伊蓮娜的人生就是尋找如何修復騷動的心靈的歷程,她不安的靈魂就是現代文化和鄂溫克的原始文化沖突產生的,是在現代文化還是在原始文化中尋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構成了一種心靈創傷。很明顯,這是一種文化創傷,是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的沖突造成的。遲子建最后把伊蓮娜的歸宿放在回歸原始神性文化中,心靈的創傷獲得真正的修復。無疑,這是一種詩性處理方式。
不但是少數族群進入現代化文化中會感覺到身份認同的困惑,造成文化創傷,同樣,跨入異域文化的人也會遭受心靈的創傷。在遲子建的小說中,我們看到了一些生活在中國的俄羅斯人的描述,在她們身上異域文化帶來的創傷明顯地體現出來。《北極村童話》中的“老蘇聯”是個被丈夫拋棄的可憐人,但是她的最令人可憐之處卻是孤獨。作為一個蘇聯人盡管認識漢字,會說漢語,但在北極村村民的眼中,她始終是一個“老蘇聯”,無法獲得文化身份的認同,因此,也無法融入北極村。只有一個文化身份還不是很明顯的7歲小女孩,才能克服大人給她灌輸的觀念,憑借好奇心偶爾進入到她的世界。而老蘇聯卻和小女孩只能形成感情交流,散發出慈愛的光輝。但她畢竟無法獲得更多的情感交流,最后只能在自己的屋子里孤獨地死去了。在《七十年代的四季歌》中,蘇聯老太太又出現了。這里的蘇聯老太太命運好多了,丈夫跑了卻留下了兩個兒子。但是,她還是被周圍人排斥,“外祖父就囑咐我,不準去老太太家里玩”。由此,在周圍人的冷落中,“蘇聯老太太基本不說話,像個啞巴”[7](p214)。她最快樂的時候就是看著小姑娘吃完蠶豆,跳舞后哈哈大笑,最后也是孤獨地死去了。我們看到,蘇聯老太太有著嚴重的心理創傷,它根源于文化語境的差異。外來人的文化身份往往在新文化語境中很難獲得,只能被排斥在該社會生活之外。正如麥格所言:“除了一套共同的文化特性,族群成員之間展現出一種社群意識,也就是一種親切的感覺或緊密聯系的意識。更簡潔地說,就是族群成員間存在著一個 ‘我們。”[8](p10)而后來進入該群體的人,卻是他者,是被這種社群意識排除在外的。她們無法獲得認同是必然的,也是無奈的。
由此可見,遲子建是一個典型實踐型知識分子,她“不僅是書齋式的、學究式的、批判性的,更主張走向操作和實踐,唯其如此,才能徹底改變知識分子身上存在著的濃厚的精英主義迷霧和烏托邦色彩”[9]。從創傷理論的角度透視,遲子建小說文本具有特殊的意味。她的小說從平凡的小人物故事出發,對個體、社會、族群、文化等方面對日常生活進行了多維度透視,從而加深了我們對于世界的理解和感悟。從平凡的人物中見出深刻的內蘊,體現出作家的深刻經驗式感悟,也體現出遲子建小說以小見大的寫作特點。當然,遲子建小說創傷人物的塑造,還是秉持著“憂傷而不絕望”的創作宗旨,每一個創傷人物最后都會獲得創傷的修復,從而留下了希望。或許正如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一書中說的那樣,小說存在的理由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護我們不至于墜入到對“存在的遺忘”。在創傷經歷中投射出的希望的力量,或許是遲子建小說更為吸引人的地方。
[參 考 文 獻]
[1][英]安東尼·斯托爾弗洛伊德與精神分析[M]尹莉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
[2]王杰審美幻象研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3]遲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0.
[4]遲子建白雪烏鴉[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5][美]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M]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7]遲子建黃雞白酒[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3.
[8][美]馬丁·N·麥格族群社會學:第6版[M]祖力亞提·司馬義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9]張玉勤歷史·社會·實踐:本尼特美學研究的理論維度[J]北方論叢,2010(3).
(作者系哈爾濱師范大學副教授,文學博士)
[責任編輯 吳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