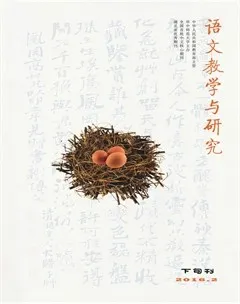豁然堂記
越中山之大者,若禹穴、香爐、蛾眉、秦望之屬,以十數,而小者至不可計。至于湖,則總之稱鑒湖[1],而支流之別出者,蓋不可勝計矣。郡城隍祠,在臥龍山之臂,其西有堂,當湖山環會處。語其似,大約繚青縈白,髻峙帶澄。而近俯雉堞[2],遠問村落。其間林莽田隰之布錯,人禽宮室之虧蔽,稻黍菱蒲蓮芡之產,耕漁犁楫之具,紛披于坻洼;煙云雪月之變,倏忽于昏旦。數十百里間,巨麗纖華,無不畢集人衿帶上。或至游舫冶尊[3],歌笑互答,若當時龜齡[4]所稱“蓮女”“漁郎”者,時亦點綴其中。
于是登斯堂,不問其人,即有外感中攻,抑郁無聊之事,每一流矚,煩慮頓消。而官斯土[5]者,每當宴集過客,亦往往寓庖[6]于此。獨規制無法,四蒙以辟,西面鑿牖,僅容兩軀。客主座必東,而既背湖山,起座一觀,還則隨失。是為坐斥曠明,而自取晦塞。予病其然,悉取西南牖之,直辟其東一面,令客座東而西向,倚幾以臨即湖山,終席不去。而后向之所云諸景,若舍塞而就曠,卻晦而即明。工既訖,擬其名,以為莫“豁然”宜。
既名矣,復思其義曰:“嗟乎,人之心一耳。當其為私所障時,僅僅知我有七尺軀,即同室之親,痛癢當前,而盲然若一無所見者,不猶向之湖山,雖近在目前,而蒙以辟者耶?及其所障既徹,即四海之疏,痛癢未必當吾前也,而燦然若無一而不嬰[7]于吾之見者,不猶今之湖山,雖遠在百里,而通以牖者耶?由此觀之,其豁與不豁,一間耳,而私一己、公萬物之幾系焉。此名斯堂者與登斯堂者,不可不交相勉者也,而直為一湖山也哉?”既以名于是義,將以共于人也,次而為之記。
【注釋】
[1]鑒湖:在浙江省紹興城西南,為浙江名湖之一。
[2]雉堞:城墻。
[3]治尊:飲酒。
[4]龜齡:宋代學者王十月,字龜齡,曾任紹興府判,作有《會稽風俗賦》,寫及鑒湖中蓮女、漁郎往來的風光。
[5]官斯土:在此地為官。
[6]寓庖:聘請廚師。
[7]嬰:纏繞,縈繞。
【閱讀指津】 記,是古代一種文體,一般指作者對現實生活中的某物或某事有所感受,然后記下來的一種文體。《豁然堂記》就是一篇和《岳陽樓記》一樣的將寫景狀物與議論抒情結合起來的“記”,而徐渭此文以行文綿密,敘述、寫景、說理三者交融一體見長。
整篇文章集中在“去晦塞即曠明”這一層意思上。臥龍山上的那一所堂,處在位置,可以遠眺群山眾水、田野叢林,漁舟蓮舫,令人心曠神怡,煩慮頓消,確實是佳勝之地。可是建造得極不合理:面向湖的一面,只開了一個僅能容兩個人身體的窗子,座位又是背對著湖山的。既不能讓所有的人同時看到窗外風光,觀景的人歸座時又不能再看到它,把人和景隔絕開來,那堂的美妙之處就無法充分顯示。改建后的堂完全避免了這些缺點:它在面向湖山的西南兩面全都開出窗子,把座位反過來向著窗外。這樣,堂內堂外連成了一片,人在堂內坐,如在畫中游。這就叫“去晦塞而即曠明”。改建后的堂稱為“豁然堂”,也就是常言所謂“豁然開朗”之意。
作者由此引申出一個頗為深刻的道理來:人心不也是如此嗎?當人心為一己之私所障時,就像豁然堂未經改建時那樣,外面明明有廣大世界、無限風光,卻什么也看不到;一旦拆除了這屏障,頓時眼界開朗,胸懷高遠。所以人心也需要“去晦塞而即曠明”。
本文所要論述的道理可以說是復雜而深刻的。但作者并沒有花多少筆墨就把它說清楚了,給讀者留下的印象十分鮮明。這是由于文章前半部分的敘述與寫景,是后半部分所說道理的極為貼切、生動的比喻,所以道理一點即明,無須多說。讀者閱讀前半部分時,已獲得新堂與舊堂孰優孰劣的鮮明印象,然后從中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人心之晦與曠明的道理,那完全是順勢而下,毫無牽強之處。再反過來說,有些文章的敘述與寫景,只是為最終要說的道理作鋪墊,道理一旦說明,其自身的意義也就消失了,本文卻并非如此。因為即使從單純的觀賞景物來說,也確實需要“去晦塞而即曠明”。正是因為前半部分作為審美經驗之談是充分成立的,用它來作為比喻才顯得有很強的說服力。
學習了前一篇文章內容,我們可以有這樣一點推測:本文可能是代筆。徐渭是紹興一帶的名士,卻一向窮困潦倒。他常代別人寫文章。本文似乎是以一個官員的口氣寫的,與作者身份不合。而且,以徐渭的社會地位和財力,也不大可能去改建紹興城內官員經常在此宴集的名勝。“豁然亭”的亭名則可能是徐渭代擬的。
在考察本文時,讀者需注意一些詞的用法:“若禹穴、香爐、蛾眉、秦望之屬”的“屬”,結合《桃花源記》中的“良田美池桑竹之屬”我們就不難理解這個字的意思了。“寓庖”的“寓”意為“聘請”,這個意思不多見,讀者可以作為實詞含義的積累記住它。還有“辟其東一面”的“辟”為通假字,意為“避開”,這種音形相近的通假用法很常見,也不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