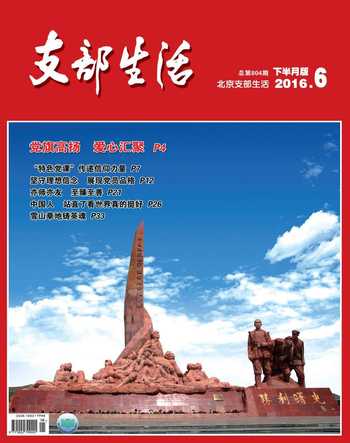紅軍故事代代傳
王硯文 譚夢



從松潘到若爾蓋,戰火紛飛的歲月早已逝去,紅軍長征的故事卻在這片遍灑戰士鮮血的土地上代代相傳。報道組此次專程走訪了數位紅軍及其后代,聽他們講述那些從未忘卻、也無法忘卻的悲壯故事。
最大的心愿是一件軍大衣
從松潘縣城驅車向南70公里,在縣域最南端的鎮坪鄉新民村,記者見到了全縣唯一一位健在的老紅軍、105歲高齡的羌族老人尹全學。
因為年事已高,老人耳背嚴重,一只眼睛幾乎看不見了,說起話來也含糊顫抖,口音濃重,但提起長征,他仍然難掩激動。
那是1935年,紅軍翻過樺子嶺到達鎮坪、鎮江關一帶。6月,24歲的尹全學在隔壁的茂縣太平鄉楊柳溝正式加入羌民游擊隊,當上了紅軍。不久,他參加了攻打松潘縣城的戰役。“跟胡宗南的部隊打。”老人摸著左肩膀,提高了音量,“敵人一槍打在這里,現在還痛。”這一槍,打碎了尹全學的左肩胛骨,把眼睛也擦傷了,埋下了長達80年的病根。
松潘戰役后,尹全學又隨紅軍離開家鄉,前往毛爾蓋地區籌糧,過黑水,踏上了荒無人煙的茫茫草地。由于途中缺水少食,加上負傷嚴重得不到醫治,1936年1月,尹全學掉了隊,最終流落在異鄉。直到解放后,他才回到鎮坪老家。
顫抖著雙手,老人找出兩個小紅本——《流落紅軍證明書》和為退伍軍人發放的《定期定量補助證》,也從側面佐證了這段經歷。
回憶起過草地的經歷,尹全學最難忘的記憶是“餓,沒得吃” 。
“過草地苦哦,沒得吃。” 老人喘著氣,重復了好幾遍,“打仗死了好多人,餓也餓死了好多人。沒有食物,也沒有水可以喝。草葉底下有積水,可那是黑水臭水,不干凈,喝了就生病,又沒有醫生和藥,還是要死人”。
更可怕的是沼澤。紅軍過草地時正值夏天,山上的冰雪消融,流進草地,一不小心,戰士們踏進茂盛水草掩蓋下的沼澤,轉眼就被淹到膝蓋,然后被滅頂吞沒。尹全學說,后來大家把泥土加草和成“土墩墩”,扔在沼澤上面踩著過去。這種辦法對付淺的沼澤尚且管用,碰到深的泥潭,就只能聽天由命。
困苦終成往事。如今,這位百歲老紅軍和自己的養女、女婿以及孫子、曾孫住在一起,四代同堂其樂融融。養老有保險,看病有新農合,每月國家還補助他400元,逢年過節,鎮上、村里的干部都會來探望慰問。
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尹全學頻頻豎起大拇指表達了內心的滿足。采訪臨近尾聲,記者問老人家有什么心愿,老人沉默了一陣,然后用濃重的川音努力表達:
一是“想去北京看看毛主席”,二是“想要一件軍大衣”。
“爸爸一直記著他是個軍人。”尹全學的養女尹全秀在一旁補充。從1935年的毛頭小伙,到81年后的歲至期頤,尹全學從未忘卻自己的戰士身份。
回京后,報道組即刻聯系有關方面,為老人寄送了舊式和新式的軍大衣各一件,以償所愿……
臨終前念念不忘的一個詞
順著若爾蓋縣求吉鄉巴西河旁的省道一路向東,不知盤過幾道山梁,在大山深處的藏鄉甲吉村,記者終于尋訪到今年70歲的退休教師徐長友,聽他講述父母的傳奇經歷——兩位老人在上世紀90年代先后過世,生前曾是若爾蓋縣唯一一對幸存的流落紅軍夫婦。
徐長友的父親徐國富,四川廣源人。1934年,年僅15歲的徐國富參軍,在紅四方面軍三十八軍八十八師二旅三團二營五連當勤務兵,曾隨部隊三過草地。“父親跟我說,過草地時沒糧食,他挖草根、扒樹皮、煮皮帶和皮鞋,什么都吃過。捉魚生吃算是好的,最差時,還吃過從牲畜沒有消化完的糞便中挑出來的青稞粒。”徐長友感嘆,“苦不堪言啊。”
打班佑,攻甲吉,參加包座戰役……1936年,歷經戰斗的徐國富在第三次過草地時,因傷口化膿發炎,不幸掉隊被俘,在敵營里充當伙夫。趁一次上山背洋芋的機會,他易裝逃了出來,跟著好心的木匠師傅四處打零工,這才遇到了徐長友的母親。
徐母向金蘭,四川宣漢人,曾加入紅四方面軍宣傳隊和衛生隊。隨部隊過草地到茂縣后,因為長期吃野菜導致身體不適,向金蘭和30多名傷病員一同掉了隊,被當地武裝俘虜,溺入河中。“聽我母親說,他們被剝光衣服,推到河里,然后被抓住頭發,按到水里又拉上來,再按下去,來回十幾次。戰友們大多被溺死了,我母親僥幸逃上了岸。”
1943年,兩位流落紅軍組建了家庭,并遷居甲吉村。婚后,他們孕育了9個孩子,但生活艱辛,孩子陸續夭折,如今只有身為老大的徐長友還在世。
這段傳奇經歷,徐長友并不時常聽父母說起,然而,烽火歲月顯然在二人身上刻下了難以抹去的烙印。解放后生活漸漸穩定下來,但二老直到去世始終過著簡樸的日子:每頓只吃加些咸菜的米飯或者糌粑,多年穿著打滿補丁的衣服。“我母親說,一開始她是因為家里窮才參加紅軍的,后來真正感覺到紅軍是幫助窮人的隊伍,所以一輩子都以曾是一名紅軍戰士為榮。”徐長友記得,母親去世前已經昏迷,但口中始終念叨著一個詞——“紅軍”。“那是她幾十年沒有說過漢語的情況下,至死都沒有忘記的一個詞。”
這些事,被徐長友密密麻麻地記在了一個紅皮本里。翻開厚厚的本子,歷史躍然紙上。“我怕自己年紀大了,好多事記不得了,以后沒辦法跟子孫們講——父母的故事,紅軍的故事,我們不能忘!”
“紅色土司”犧牲50年家人方知
“你們采訪過尹全學了?我曾祖父犧牲的消息,就是他1985年回松潘才帶回來的。”37歲的松潘縣青云鄉中心小學教師安成勇坐在藏式長凳上,邊說邊陷入沉思。他的曾祖父,正是1935年尹全學加入的羌民游擊隊的大隊長,羌族史上第一位“紅色土司”安登榜。
雖然沒有親眼見過曾祖父,安成勇卻從長輩那里知道了許多他的故事。“我們安家本來是鎮坪呷竹寺世襲的土司家庭,曾祖父出生在1895年,他接任土司職位后,管轄著6關32寨及白羊11團,在當地的威望很高。因為屢次抵抗國民黨對羌民的攤派和壓榨,曾祖父受到當局迫害,1935年春天,他帶著十幾個親隨逃亡,在路過武安時,和紅四方面軍第四軍十二師的先頭部隊相遇了。”
這支先頭部隊是為策應中央紅軍渡江北上向川北少數民族地區推進而來,打出了“羌、回、番窮苦群眾,與漢族工農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民狗黨!”的標語,宣傳民族平等團結政策,使安登榜大為震動。“他還特意留心觀察了一陣,發現這個隊伍真的是跟欺壓百姓的惡勢力對著干,立刻就帶著親隨加入了紅軍。”
作為羌族首領,又精通漢、羌、藏三門語言,安登榜在隊伍里擔任了通司(翻譯)、向導和前衛宣傳工作。他無數次突破敵軍封鎖線,深入敵后偵查情況,勸降番民士兵。北川走馬嶺一役中,在得知敵方先頭部隊是羌族士兵,頭領王光宗是自己的老部屬后,安登榜連夜寫信給王光宗,勸其“認清形勢,不要再受騙上當,為國民黨政府賣命,充當走狗”。他還以自己的感受,在信中情真意切地啟發王光宗:“(紅軍)政策很好,是為受壓迫、受苦難的各族民眾謀福利的軍隊,紅軍好得很!”王光宗接到信件后倍感悔恨,很快配合紅軍拿下了土門天險。
“除了宣傳紅軍政策,曾祖父還提供了很多后勤支持。比如動員族人為紅軍洗補衣服、打草鞋、做綁腿帶等等,最主要的就是籌糧。”安成勇說,安登榜參軍后最后一次回鄉,就是到地處茶園坪的安家糧倉,拉了大批糧食、牛羊和馬匹給部隊做補給。
1935年7月,安登榜奉命隨軍北上。途徑毛爾蓋的一天晚上,他帶著七八個戰士又去籌糧。可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來。第二天天亮,大家在索花寨后山的一處山坳里找到了他們的遺體。“曾祖父和戰友的身上到處是彈孔和刀傷,敵人伏擊射殺了他們,還把點著的干柴丟進山坳企圖毀尸滅跡。因為戰事緊張,當時只能將遺體就地掩埋。”安成勇頓了頓,說,“因為當年跟出去的族人一直沒有回來的,家里也就一直不知道曾祖父犧牲的消息。后來知道了,也考慮過要不要把曾祖父的尸骨遷回來,但我爺爺說,就讓他安息在那里吧,那是他戰斗過的地方。”
安成勇說,曾祖父北上前,曾告訴自己的妻子,“等我落腳安頓好了,就來接你和孩子”。“曾祖母一直記著這句話,盼他回來,幾十年不肯改嫁,一個人硬是把四個孩子都拉扯大了。”安成勇放輕聲音,“直到尹全學帶回消息之前,她都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經死了50年了。”
如今,安登榜的革命烈士證書被復印成四份裝裱起來,掛在他每個孩子家中的正堂上。“我們一直在搜索整理有關曾祖父的資料,不僅僅是留給自己的孩子,還想讓更多人知道他的故事。”說到這,安成勇停頓了一下,“有一首寫曾祖父的歌,可惜我還不會唱,我想著自己趕緊先學會了,才好教更多的人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