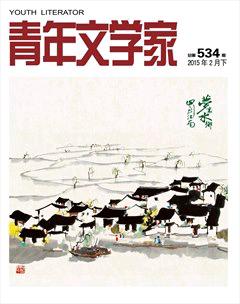茨威格短篇小說中東方女性形象解讀
摘 要:茨威格以塑造女性形象著稱,但不難發現在他的作品中大多數女性都是典型的歐洲白人女子,在其短篇小說中也有對東方女性形象的塑造,筆調卻完全不一樣,她們成為茨威格塑造歐洲白人女子的反面對照,成為“他者”,而這正是茨威格的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以及對東方的偏見所造成的文化誤讀,這種帶有個人主觀主義的寫作方式勢必為東方女性形象的客觀展現帶來困擾。
關鍵詞:東方女性形象;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文化誤讀;異國人;異國環境
作者簡介:曾丹(1991-),女,漢族,在讀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世界少數族裔文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06-0-02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作品大多充滿人道主義情懷,尤其是對女性充滿同情和憐憫。如《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中的陌生女人,《一個女人一生中的24小時》中的C太太,《雷潑萊拉》中的女仆克萊岑莎,中篇小說《家庭女教師》中的女教師,以及《恐懼》中的依萊娜太太。她們都是生活在男權社會中的女性,用女權主義者波伏娃的觀點來看,女性是附屬于男性的第二性,是處于從屬的次要地位的他者形象,因此,在茨威格的筆下,這些女性都在不同的故事情節中遭受不同的傷害與打擊,但是茨威格的筆調是清晰明朗的,他所塑造的歐洲女人無疑又是高貴的,自由的,個性鮮明,敢愛敢恨。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歐洲女人儼然成了“愛、美、慧”的象征。而反觀茨威格短篇小說中一些對東方女性形象的描寫,呈現給讀者的卻是完全相反的兩種形象,東方女性的溫婉大方、勤勞善良都被遮蔽了,取而代之的是被茨威格主觀塑造出來的惡俗、低下、卑微的仆人和妓女形象,在歐洲白人女性高貴端正的形象之下,茨威格筆下的東方女性儼然成了美的反襯,而這種偏見書寫勢必為東方女性的客觀呈現帶來困擾,同時也讓真正的東方女性形象被遮蔽。
一、茨威格對東方女性形象的主觀解讀
茨威格曾游歷過亞洲,主要在印度、尼泊爾地區,對亞洲社會的一些現狀有所目睹,印度社會的貧窮,治安的混亂,國家的動蕩,這一切讓茨威格以篇蓋全地認為整個亞洲社會都是如此,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女性也被他以一個歐洲白人高貴血統的姿態貶低于筆下。在小說《火燒火燎的秘密》中關于印度有這樣兩段描寫:“他只在書本里讀到過這些事情,獵虎啦,棕色人種啦,印度人啦,札格那特啦,那可怕的輪子,把上千萬的人都埋葬在它的福輪之下,他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真會有這樣的人,同樣他也不相信會有這種童話里的國度。”[1]p115,“他看見他的朋友高踞在配有紫色鞍褥的大象背上,左右兩邊是棕色皮膚的人,頭上纏著珍貴的頭巾,然后突然從叢林間跳出一只猛虎,露出森林白牙,用前爪襲擊大象的鼻子”[1]p115。從這兩段話我們讀到的只有印度社會的野蠻與原始,似乎現代文明從來沒有涉足過這片土地,好像在茨威格所處的時代它都還生活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一般,而在這兩段描寫中茨威格都提到了人種,都寫到了棕色皮膚,字里行間都透露出一個歐洲白種人的優越感與高姿態。
懷著這種主觀偏見,茨威格的小說中出現了東方女性形象,這些女子都被塑造成仆人、妓女等,她們低劣、下賤、愛慕虛榮,因此在他塑造的一眾歐洲貴婦中這些東方女人更加顯得黯淡無光。在《熱帶癲狂癥患者》(又名《馬來狂人》)中,有這樣幾段描寫:“雨季剛過,已經一年有幾個星期,雨水拍打著屋頂,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歐洲人來過,整日價坐在屋里和我的黃皮膚女仆們做伴,和我的上等威士忌,我當時情緒好低落,日夜思念歐洲,我要在哪本小說里讀到陽光普照的大街和白皮膚的女人,我的手指就激動得抖個不住”[1]p169。在這段描寫中作者又特意寫到了皮膚,黃皮膚的亞洲人被設置成了低等仆人,而我這個歐洲白人喝的是上等威士忌,這一上一下間很明顯地看出茨威格的主觀傾向,他甚至夸張的寫到在書上看到白皮膚女人都會激動地發抖,可見這一黃一白間茨威格嚴重的種族歧視觀念,以及對東方女性形象的丑化。
同樣在《熱帶癲癇癥患者》中還有這樣兩段描寫:“如果歐洲人離開大城市,來到一個該死的罪惡的小鎮(印度小鎮),不知怎的,就會判若兩人,遲早都會受到損害,有的酗酒,有的抽鴉片,有的打人,變成野獸——每個人都會沾染上一種毛病,他們向往著歐洲,夢想著有朝一日又能在一條大街上漫步,在一間豁亮的石頭房里和白種人坐在一起。”,“本地姑娘,這些嘰嘰喳喳纖小秀氣的鳥兒,只要有個白人,有個“洋老爺”要她們,她們就畢恭畢敬地渾身哆嗦,低三下四地委身相從,她們對你總是張開懷抱,總是準備咯咯地輕聲嬌笑著來伺候你”[1]p177。這兩段描寫更為直白的將東方女性形象丑態展現,和作者筆下有著鮮明個性、感情充沛果敢的歐洲白人女性不同,東方女性被塑造成了輕佻、風騷的浪女形象,這就更為明顯地看到茨威格對東方女性形象的主觀誤讀與曲解。
二、茨威格主觀創作的原因分析
種族主義起源于19世紀末,非洲黑奴的悲慘遭遇就是種族主義造成的最直接后果,隨著歐洲資本向全世界范圍的擴張,這種觀念逐漸深入以高貴血統自居的歐洲人意識里,尤其是以德國納粹政權為代表,希特勒上臺之后,開展了一系列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活動,茨威格也被納粹逐出故居,流亡英國、巴西。正是這種從小生長的環境、潛意識的萌發以及后來希特勒的種族滅絕幾方面的因素讓茨威格意識里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雖然他是一個學者但也最終沒有擺脫種族歧視的觀念,所以從這一點來看,他對東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就可以解釋了。正如薩義德在作品《東方學》中描述的那樣:“‘東方就是專門為西方文化虛設的、幻覺中的東方,它不是真實的東方,東方人就是按照這種虛設和幻覺被塑造出來的,東方的男性常被表現為非常軟弱,甚至有點女性化,但同時又是對白人女性構成威脅的危險人物,東方女性則被表現得心甘情愿處于被統治、被壓迫的地位……在這種觀念中東方被表現為破碎的、零亂而沒有中心、落后的、異樣的、淫亂的和馴服的,并且總是存在著暴亂的傾向。”[2],從薩義德的觀點出發就更能解釋茨威格對東方女性的偏見寫作,他始終沒有擺脫西方中心話語霸權的束縛,仍然是站在主流立場的霸權寫作。
另外,茨威格對東方女性的主觀偏見也離不開殖民主義的影響。了解歷史的人都知道,英國是最早發生產業革命的國家,曾經是“世界工廠”,資本的擴張讓它成為最大的宗主國,擁有的殖民地最多。而茨威格本人曾經是一名奧地利人,后來奧地利并入德國后他加入了英國籍成為了一名英國公民,當他到達亞洲國家,腳下的土地成了自己國家的殖民地,殖民與被殖民的經歷,造成的必然結果就是文化的霸權與奴役,正如后殖民著作《逆寫帝國》中所寫到的:“當今世界上超過四分之三的人口及其生活是由殖民經歷所塑造的,這種經歷對于政治和經濟領域的重要性顯而易見,但對于當代人的認知建構所產生的普遍影響卻不容易被察覺,文學常常是這種新型認知的重要表現形式”。[3]因此,茨威格對東方女性的偏見塑造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文學形式的殖民手段。
比較文學研究中經常會提到這樣一個理論,那就是“文化過濾”,“它是指文學交流中接受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傳統對交流信息的選擇,改造、移植、滲透的作用,也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發生影響時,由于接收方的創造性接受而形成的對影響的反作用。”[4]p98這一概念也可以用來解釋茨威格這一偏見創作,文化過濾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其中有一方面就是關于接受者的文化構成,任何接受者都生長于特定的時空里,接受者受其社會、歷史、文化語境和民族心理因素的制約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心理與欣賞習慣,這種獨特的文化構成必然會影響接受者對外來文學與文化的接受。東方文化、東方女性對于茨威格來說就是外來文化,于是當他面對這些外來東西,必然本能的以自己的文化構成去度量外來文化,一切不符合自身價值體系的文化當然就會遭遇本能抵觸,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思想的根深蒂固也讓茨威格在接受東方文化時不斷過濾,最終得出了自己的主觀結論。
三、茨威格偏見塑造造成的后果探析
茨威格在世界文學史上一直以堅持人道主義立場自居,但是就在其眾多的文學作品中為數不多的關于東方女性的描寫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其人道主義狹隘的一面。在韋勒克與沃倫的著作《文學理論》一書中,著重把“文學與社會”單獨列了一節來闡釋,其中就講到,“文學的產生通常與某些特殊的社會實踐有密切的聯系……文學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或效用,它不單純是個人的事情……一個作家不可避免地要表現他的生活經驗和他對生活的總的觀念。”[5]這里韋勒克和沃倫就明確提出了文學的社會功效和作家的作用,因此茨威格的創作在某種程度上并不僅僅是代表一個人,他的創作所建構出的社會形態勢必會影響到接受者。
在比較文學形象學中就明確表示形象學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形象研究,它是對一部作品、一種文學中異國形象的研究。“這種形象是異國的形象,是出自一個民族(社會、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個作家特殊感受創作出的形象,在這里,形象是作家及作為對他者的異國和異民族的想象物”[4]p121。這里強調了作家創作對異國人與異國環境建構的決定性影響,作家不同的經歷和看問題的角度會直接影響到異國他者形象的效果。茨威格在作品中塑造的東方女性形象帶有明顯的主觀偏見,把東方女性的柔美、善良、勤勞、智慧都隱藏了,呈現給西方讀者的都是丑陋、惡俗的一面,讀者在沒有親身走進東方文化,了解東方女性的情況下就會誤以為茨威格筆下的仆人、妓女就是東方女性的典型,這就勢必會因為作者所建構的思想文化給接受者造成文化誤讀,而這一文化誤讀的背后造成的更是一連串的種族歧視與偏見觀念的惡性循環。
四、結語
雖然茨威格作品中對東方女性形象的描寫并不多,但他的立場是鮮明的,這一主觀偏見帶有明顯的種族歧視、殖民主義以及文化誤讀的成分在里面,對東方女性的不實描寫勢必造成歐洲社會對東方女性乃至東方文化的偏見。雖然在東方各國較早的歷史時期,女性地位的確不高,男尊女卑的思想泛濫,但是不能忽視的是,在歐洲女權運動興起之后,伍爾芙提出需要一間屬于自己的屋子,女人需要精神自治之時,在波伏娃討論歷史各個時期女性處境、地位和權利演變,并讓女性意識開始覺醒之時,西方社會女權思想的崛起也讓東方女性有了權利自覺意識,她們同樣知道自尊、自愛、自強、自信的道理,因此,茨威格的偏見寫作勢必會因為偏離事實和真相而不被人們認可。其實當今文壇已有很多學者開始嘗試著拋開民族身份進行創作,如印度裔作家奈保爾、斯里蘭卡裔加拿大作家邁克爾·翁達杰等,他們都是有著移民經歷與混雜身份的作家,和茨威格在經歷上有著很大的相似之處,但是他們的寫作都是站在無國界立場上進行的世界小說的創作,作品的內容多是表現的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混雜,而不是死守自己的所謂的民族身份,他們的寫作都是一種“超民族主義”的無國界書寫,而這也正是世界文化融合所必需的。正如安德森對“民族”這一概念進行的界定一樣,民族只是一個“想象的社群”,不是永久不變的,它是文化撞擊與融合的產物。狹隘民族主義尚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更何況是極端落后的種族主義,試想茨威格在創作的時候能夠意識到這一點,以平等的眼光來看待不同文化的存在,也許他的作品將會更值得閱讀。
參考文獻:
[1]斯蒂芬·茨威格.斯蒂芬·茨威格中短篇小說選[M]. 張玉書.譯,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3年6月.
[2][美]薩義德.東方學[M]. 王宇根.譯,上海:三聯書店 2007年7月版.
[3][澳]比爾·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倫·蒂芬. 逆寫帝國:后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M]. 任一鳴,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4]曹順慶.比較文學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3月版.
[5][美]勒內·韋勒克 ,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M].劉象愚,邢培明,陳圣生,李哲明.譯,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5年8月第一版.